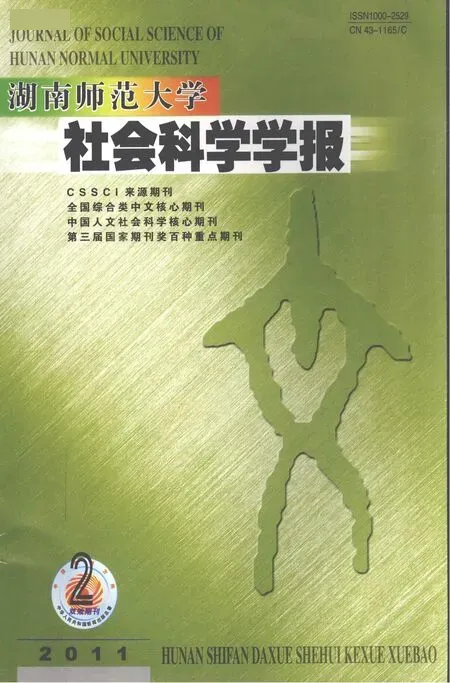清末以降黄宗羲研究批判
黄勇军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清末以降黄宗羲研究批判
黄勇军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清末以降,对黄宗羲的研究出现了各种误读现象。清末民初,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学者们将他的思想直接与西方民主、自由等思想相嫁接;五四时期,学者们在中西对立的框架下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他进行了新的阶级定性;文革时期,他被当成法家的代表人物予以肯定;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港台、海外学者开始在多元化的框架下建立起共同的研究平台。
清末以降、黄宗羲研究、误读
一、清末的黄宗羲研究
明清鼎革之后,晚明以来,汉人士大夫们为改造自身文明与制度而进行的持久、深入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受到了清廷长期的打压与忽视。满洲人的这一做法导致了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从帝国内部而言,这一持续270年之久的异族统治,严重抑制了以汉族为主的中国文化与政治体制的进一步良性发展;二是从帝国外部而言,这一历史状况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应对西方挑战的成败与速度。在此格局下,黄宗羲基于明代弊政而展开的对中国政治传统的整体性批判与改造,无疑被全盘接受明代政治体制的清代统治者所排斥,从而沉寂了二百三十余年之久。直到强势的西方文化带给清末士大夫们一套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理念时,黄宗羲这种对传统的整体性批判才在西方的整体性挑战中被迅速地推上历史前台,成为“中国的卢梭”[1](P52)。
尽管在彻底质疑中国政治传统之前,晚清士大夫也曾试图在传统内部,通过利用黄宗羲等人的“经世致用”之学,以期解决所面临的困境,但这种努力由于无法阻止西方的入侵以及国内的农民起义而陷入了更深的内忧外患之中。他们的失败无疑有多种原因,但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如魏源与龚自珍等人在政治理念与政治作为上都远不及晚明士大夫这一事实,也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华帝国内部无法产生《明夷待访录》这样的政治理论与格局,所谓“《待访录》以后,整个清代,在政治理论方面,几乎就没有可看之作”[2](P1)。
如果说龚自珍、魏源等人还是在帝国体制内寻求解决方案,那么此后的“洋务派”则主要放眼于帝国之外的资源了。曾国藩无疑是这一时代的代表人物,他的作为使如下方案成为可能:对外学习技术,对内整合资源。这一“内”“外”分野的模式在后来被张之洞、郑观应等人的“中体西用”学说推至顶点。但是以“‘体用’模式作为工业化运动的一件思想外衣而被广泛使用这一事实表明,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为将工业化作为一种价值来接受作内部的准备”[3](P62)。在这一模式下,黄宗羲作为“体”的批判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并不是说黄宗羲在这一时期没有任何影响,而是说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致力于将西方的冲击限制在“器”的层面,而不曾对“体”提出质疑。
总体而言,清末士人对待自身所面临的困境时,缺乏明末士人那种整体上的颠覆感与幻灭感,从而也缺少如黄宗羲等人那种对政治体制进行整体性变革的冲动。这一切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首的“维新变法”,在彻底质疑传统体制本身从而试图寻求变革的可能性的同时,将黄宗羲推向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现代学界对这一时期的黄宗羲研究持有如下观点:清末学者、行动者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对黄宗羲作出了一种功利性的“误读”。这种误读不仅针对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传统资源”,同时也针对这一时期来自西方与日本的“外部资源”,并且是在一种“有意为之”的状态下完成的。[4](P47)他们希望通过对中西文化的这种双重误读,以期达到“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现实目的。这种误读使黄宗羲在清末的时代背景中实现了所谓的“文化增值”[5](P328-353)。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等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对他表示了敬意。即使是他的反对者如李滋然,同样将他的思想与“反君主制”和“民权”联系到了一起。[6](P338-349)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对于上述评价,基本上持批判态度。诚然,他的批判在学理层面是完全成立的:将西方思想“不加思索地、主观主义地假托于黄宗羲的思想”无论如何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但如果以“黄宗羲之后没有出现第二、第三个黄宗羲,而在卢梭之后则出现了千百个卢梭”为论点来强调这一批判的话[7](P254),却没有太大的道理。事实上,黄宗羲的思想在晚明士人阶层中拥有足够多的“知音”,而且他的许多观点基本上是那个时代的共识。可以肯定,当时的中国确实存在着“千百个”黄宗羲,只是以蛮族身份出现的满族人的统治,改变了整个中华帝国寻求突破与创新的历史进程。
二、“五四”模式下的黄宗羲研究
1911年鼎革之后,虽然孙中山的让位给后人留下了无穷遐想的余地,但中国轻而易举地落入了武人之手,这一结局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发展与前程。作为“曾经是一个神圣的制度,象征着中国价值体系和社会—政治秩序的独立”的君主制崩溃后,所带来的是“长久而深远的沮丧和不安”[8](P370)。
在这个混乱的后革命年代里,新文化运动无疑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在“五四”的语境里,晚清以来开始流行的“新”与“旧”、“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尽管张灏认为现代学者在研究中过于重视五四而忽略了清末思想的重要性,但是,在本文看来,五四之所以占据了中国人关注的中心,就在于自此之后,整个中国思想界对于“自我”(中)与“他我”(西)的认同进行了激烈而彻底地转移。正如福柯的理论所揭示的:此时的中国在西方这一“正常人”的关照下,已然成为了无可救药的“疯人院”[9]。
五四风潮所及,黄宗羲迅速退出了公众的视野,从而被当作一种思想、一种文本、一种历史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五四之后的黄宗羲研究,主要在如下两个层面上得到了推进:
一方面,学者们以传统学问为根基,以西方学问为参照,对黄宗羲的思想进行深入探悉。坚持这一路径的学者在评价黄宗羲时,往往持有相似的观点:他们都极其赞赏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但又都认为这种政治思想过于简单而无法实践,如梁启超一直认为黄宗羲的思想“含有民主主义”,但同时强调“很幼稚”;[1](P53)钱穆也认为黄宗羲在“发明民主精义”,但认为是一种“空想”[10](P33)。
学者们在评价中所出现的上述共性,主要是由于他们所持有的参照体系仍然是自己所面对的强势“西方”,而不是黄宗羲所处的明清鼎革之际的“中国”。也就是说,不论他们是在赞扬还是在批评黄宗羲,他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黄宗羲思想在黄宗羲本人的时代处境与历史际遇中是否可能,而是关心黄宗羲的思想在20世纪的中国是否可能。与清末士人为了政治的需要而推崇黄宗羲相比,五四时期的学者们已经在学理上将黄宗羲的研究极大地向前推进了,但是,他们的研究与清末士人一样都带有以传统吸收、抵抗西方文化的目的论色彩。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不间断地传入中国,许多有西方教育背景或掌握了西方研究方法的学者们开始完全以西学为参照,展开对黄宗羲的研究。这类研究具备如下两个特征:(1)以西方学科划分的模式,将黄宗羲的思想划分为哲学、政治、历史等不同的研究层面;(2)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西方思潮为范式展开研究。
此时的黄宗羲研究在深度、广度以及新鲜度上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问题也极为明显,如胡适与冯友兰在成功建立近年来饱受质疑的“中国哲学”这一学科后,黄宗羲的思想尤其是其形而上学的层面就开始被剥离于其整体框架之外受到了格外的关注。同样,萧公权极具创造性的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为黄宗羲思想中的“政治思想”找到了归宿,而萧氏认为黄宗羲思想属于“民本”而不是“民主”的判断[11](P560)由于尽反前人之论而开启了至今不决的“民本与民主”之争,问题是,这种将黄宗羲放在几千年的政治思想史之中的做法,往往导致观念性的剥离而不是历史性的存在。而侯外庐与谭丕模同样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黄宗羲究竟是进步的“启蒙思想家”[12](P144-203)还是落后的“开明地主阶级”?[13](P170-180)同样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三、建国后到改革初期的黄宗羲研究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与蒋介石政府的退守台湾,加上仍然属于殖民地的香港与澳门的存在,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变得更加多样化、复杂化。这一政治上的重大变迁很快就在学术界体现出来——不同体制、不同地域、不同意识形态下的中国人开始了完全不同的黄宗羲研究之旅。
从大陆而言,建国后到“文革”前无疑是一个时段,虽然政治风潮屡有变化,但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被最终僵化与教条化,此时的黄宗羲研究主要沿着侯外庐、谭丕模等人的路径继续向前发展。“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启蒙思潮”等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一时期的观点往往在总体上认可而在具体上进行两分,如侯外庐、杨廷福认为黄宗羲带有“幻想”的基础上坚持认为他是“启蒙思想家”,嵇文甫则在强调他的积极性的基础上坚持他是“民本思想”。[14]
换言之,这一时期的黄宗羲研究是在民国时期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尽管民国时期学者们在立场、方法论、价值观念等层面上的多元竞争态势此时已然一统于马克思主义,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内部,争论与差异依然存在。这种“一统”下的多样性特征在“文革”中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在“全民动员”的近乎疯狂的群众运动中,黄宗羲基于“士”这一儒生精英群体立场所展开的对传统的理性反思被暂时遗忘,学界对他的研究自1966年之后停滞了9年之久。最终,在新的“批林批孔”的形式下,学者们终于得出了新的结论与定性: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与李贽、张居正一道,作为“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成为了“儒法斗争”的主力军。[15]
从1978年开始,反思“文革”、批判“四人帮”的声音成为主旋律,学者们从历史中寻找“文革”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这种将“文革”与“封建主义”联系起来的做法,引发了人们对传统的声讨。黄宗羲也因其反传统的姿态被人们再次用于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与“封建君主制度”的时代主题上。此时的黄宗羲研究出现了极大地倒退:一方面,从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与“封建君主制度”这样的现实目的而言,此时的学者们在力度、强度、有效程度等方面都远不及清末的士人们,更不用说这一目标本身所存在的“误读”问题了:难道“封建专制主义”与“封建君主制度”不是在1911年就结束了吗?另一方面,从对黄宗羲思想的认识方面,这一时期更是对民国、建国初期所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与方法论的倒退,此时的文章大部分都在介绍而不是研究。
四、当前的争论及其问题
80年代中期以后,黄宗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由于文革十年中“清洗画布”的努力与骤然的改革开放,新的、旧的,中的、西的,传统的、现代的……这些五四时期中国学界所讨论、面对的问题又回来了,不同的是,我们还将面对诸如后现代、女性主义、东方主义等等不曾面对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中,对黄宗羲的研究再一次出现了多元化与多样性的趋向。
1.“民主”与“民本”之争
清末以来基于现实政治需要所形成的对黄宗羲思想的定性,在改革初期得到了再次强化:民主、启蒙、反君主专制。围绕这一定性,支持者与反对者展开了至今未决的“民主与民本”之争。这一争论主要从两大路径得以展开:
一方面,支持者基本上在继承清末以来的传统,但并没有找出更有力的证据,也没能进行更有力的论述。如刘岐梅的博士论文《走出中世纪——黄宗羲早期启蒙思想研究》一文,就是这一路径难以继续向前发展的代表性努力。尽管作者对“民主”与“民本”双方的争论点非常清楚,但在论文中并没有对这一争论进行有效地回应,而是简单地强调“早期启蒙思想”这一概念,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回避。如果我们假定其立论没有问题,那么,基于这一立论从而对“早期启蒙思想”所进行的全方面的考察无疑是必要的,然而,在这一概念本身已经遭到极大质疑的情况下,却没能成功回应这一问题,就使得她的整个努力最终成为了前人的一个注脚而不是新的发展。
另一方面,反对者却在近年来凯歌高进,将这一思路推至极至,从根本上否定了黄宗羲的现代意义。张师伟博士的《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一书无疑是这一路径的代表。他从哲学层面的所谓“追求至善”、“成就圣人”、“天人合一”、“道德专制”,以及政治学层面的所谓“天降王权”、“教化万民”、“维护君权”等角度对黄宗羲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在与西方政治哲学之间所进行的简单的全方位的比较基础上,得出了如下结论:“黄宗羲的哲学、政治思想还完全是传统时代的产物,它不仅不是王权体系的掘墓人,反而继续攀附在王权体系的大树上,变本加厉地点缀和武装着王权”[16](P17)。
2.“新民本”概念的提出及其问题
基于“民主”与“民本”相持不下的现状,以及“新儒家”的流行,有学者提出了“新民本”的概念,作为对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之际思想特征的新定性。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冯天瑜与谢贵安二人在《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一书中对这一概念所进行的详尽论述与界定。但是正如其批评者所言:“本书在论证的过程中无不显露启蒙说的迹象,但作者又认为‘启蒙说’有缺陷,把这种民本思想界定在君主专制和近代民主之间,有折中的嫌疑。”[17]此外,潘起造重申:“黄宗羲的政治思想突破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具有民主思想的诉求了。”[18]这进一步说明新民本的概念并没有超出“民主”、“启蒙”的范畴。
可见,“新民本”这一概念并不是对以往误读的修正,而只是在创造一个新概念的基础上解决“民主”与“民本”问题的主观臆测。
3.“现代新儒家”的问题
五四以来,现代新儒家已经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其中,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一书,可以视作对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儒家政治资源进行创新的典范之作。但是,他所解决的与其说是“政治”问题,不如说是“哲学”问题。以一种思辨的方式将政治区分为“政道”、“治道”,并进而通过与西方的比较得出中国“有治道而无政道”,最后企盼“道德(良知)的自我坎陷”来解决这一“内圣”与“外王”隔绝的问题,这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中的重构而并不一定是历史中的真实。这一哲学路径落实到黄宗羲的研究中,在成中英这里演化成为“批判的理学”、“批判的心学”、“批判的融合理学与心学”、“批判的史学”。[19](P298-332)而在刘述先这里则是对黄宗羲心学的再定位。
此外,余英时提出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基调的转换”问题,与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坐标转移”问题一起,成为了中国“前近代”研究的新范式。尽管有学者认为二人有“目的论”的倾向,但他们的研究已经使学者开始关注黄宗羲与儒学转向的问题。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无论是黄宗羲的支持者还是批判者,都有着同样的思维模式与逻辑推理:(一)西方是理想的参照物,(二)中国应该像西方一样,(三)中国传统中符合西方的就是好的,不符合的就是坏的,(四)结论:黄宗羲作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也应当接受西方的检验以确定其好坏。二者之间的差别主要来源于对黄宗羲(包括中国传统)的不同观感:在支持者看来,中国传统毕竟还有好的方面,至少像黄宗羲这样的反传统者,仍需要我们继承发扬。在反对者看来,中国的传统彻头彻尾都是坏的,即使像黄宗羲这样的反传统者也只是在更高的层面上维护传统,因而需要彻底抛弃。
因此,要想避免误读,就需要我们重回黄宗羲的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从而在他的历史情境中考量其方案的可行性,并在他的思维世界中重构其思想体系,而不是相反。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Audrey Wells.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un Yat-sen:Development and Impact[M].New York:Palgrave,2001.
[5]朱义禄.黄宗羲与中国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6]吴 光.黄宗羲论[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7] [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华书局,2005.
[8][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9][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7.
[10] 钱 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2]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 谭丕模.中国文学思想史合璧[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4] 嵇文甫.黄梨洲思想的分析[J].新建设,1959,(12):18.
[15] 肖任武.评明清之际三大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J].文史哲,1975,(1):49-56.
[16]张师伟.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7]孙卫华.“新民本”:传统目标与近代民主的中间地带——读《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J].江汉论坛,2005,(8):142-143.
[18] 潘起造.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启蒙意义及局限[J].浙江学刊,2006,(5):83-89.
[19]成中英.合内外之道——儒家哲学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Abstract:From Late Qing Dynasty,scholars believed that‘western’and‘modern’were the right standards when they did their research of Huang zong-xi’s thoughts,and thus induced lots of misunderstand.In late Qing and early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as the result of the political purpose,they regarded his political thoughts had equal value as the western ideas.In‘May 4th Movement’,they compared his thought with Western under the models of‘East vs.West’.In the early period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arxism scholars re-classified his social position.During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he was highly valued as a Legalist.From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the research about him became more and more diverse,and scholars have begun to build a common research frame.
Keywords:Huang Zong-xi;from late Qing Dynasty;misinterpretation
(责任编校:文 心)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f Huang Zong-xi Since Late Qing Dynasty
HUANG Yong-ju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nan 410081,China)
K249
A
1000-2529(2011)02-0125-04
2010-11-20
教育部2010年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传统中国女性政治的合法性研究”(10YJC810034)
黄勇军(1979-),男,湖南隆回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