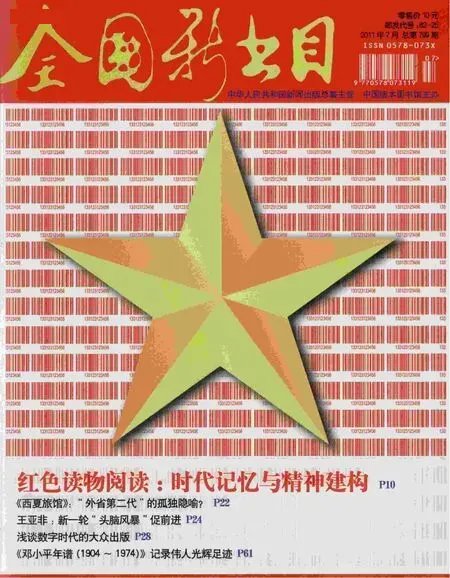《西夏旅馆》:“外省第二代”的孤独隐喻?
⊙对话嘉宾/骆以军 梁文道 张悦然
骆以军,1967年生于台北,台湾中生代代表作家。著有小说集《红字团》、《遣悲怀》、《月球姓氏》、《第三个舞者》等。《西夏旅馆》是骆以军耗时4年,在三度遭受忧郁症侵袭的情况下写就的杰作。2010年获得华文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项“红楼梦奖”,组委会认为这部小说“以十一世纪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作为历史托喻,以一座颓废怪诞的旅馆作为空间符号,写出一部关于创伤与救赎、离散与追寻的传奇故事。”
6月上旬,这部长达40万言的小说简体中文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台湾“外省第二代”骆以军重回大陆,先后与文化人梁文道、80后作家张悦然展开了三场对话,主题分别为:“六个抬棺人——经验匮乏世代的小说幻术”、“经验匮乏与穷而后工”和“铸风成形、编沙为绳”。骆以军以自己和父辈的故事作为讲述重点,非常精彩地阐释了《西夏旅馆》的创作意图和主旨。以下内容以这三次对话为底本,本刊重新进行了编辑整理。
“五年级生”骆以军
生于50年代(民国40年代)的张大春,朱天文、天心姐妹是台湾文坛“四年级”,60年代的骆以军自然是“五年级生”。他自己觉得“四年级”混得特好,“五年级”混得特差,很调皮,很虚无,很无赖。但在很多人眼里,他是最好的台湾五年级生。
梁文道:在做电视节目的时候,我为了要吸引电视观众对骆以军的注意,所以特别强调骆以军小说的特点就是很黄、很暴力。我介绍骆以军主要写的就是乱伦、杂交、大屠杀、奸杀,等等。但是我想这么讲,三个同年生的,骆以军、香港作家董启章,还有另外一位我心仪已久,恨今未识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黄锦树,在我心目中,他们是这三个地方中生代里面最出色的作家。
张悦然:我跟骆以军的友情主要是建立在一个相同的爱好上,那就是我们都是同样的迷信,相信各种算命系统,从塔罗、占星、紫薇斗数、八字、古卦各种乱七八糟所有的全部都相信。
骆以军的星盘跟他的《西夏旅馆》有个一致的地方,就是他的审美倾向。他喜欢那种破的、烂的、喜欢那种倒霉的、短命的,然后那种动物性的、野蛮的、蒙昧的、未开化的。就像他在《西夏旅馆》里面写过的,他说那个文字是长着毛的文字,这种审美倾向常常在他讲故事当中带出来。他当然希望他的命好,每次总是问我,我的运气怎么样?我后面有没有更好?同时他又觉得自己是那个最倒霉的人,扫把星的角色,到哪里,哪里一片人倒霉的人。骆以军常常想象自己有这样一种破坏力:他上过的学校都关门,他出过书的出版社也都关门。这种想象,我觉得是他的一种美学倾向。
除了隐喻,还有其他
《西夏旅馆》所讲述的故事很难用简单的几句去总结,线索庞杂,结构疏离,是一个巨大的“歧路花园”。小说一方面是讲古国“西夏”最后的逃亡历史,另一方面又是发生在现代“旅馆”这个局促空间中的想象。作家黄锦树曾经写了一篇论文来探讨这部小说,认为“西夏”和“旅馆”拼贴在一起有深层的隐喻,是在暗示台湾“外省第二代”的命运、历史和身份认同。作为“外省第二代”的骆以军,后代会彻底成为本省人,外省人这样一个族群迟早会消融,而这样一种命运就像中国历史上曾经创建西夏的党项人。骆以军不否认这种说法,但他和梁文道都认为除了隐喻,小说本身更复杂,有外省人及第二代的影子,还有本省族群的内心焦虑,以及其他若干等待读者去发现的东西。

《西夏旅馆(上、下)》骆以军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6定价:78.00元
骆以军:我父亲是很典型当时国民党打输了跑到台湾去的。这一整批外省的迁移者,他们其实很像这些西夏被灭绝掉以后的人,其实他们是跑到别人的土地上,别人的梦是完整的,他是听不懂别人的。
像李元昊(西夏开国皇帝)一样,蒋介石会骗他们说,有一天我们可以统一中国,我们可以反攻大陆,就像我写西夏人,是活在李元昊一个人的梦境里,我们父亲这一辈是这样的,他们始终没有在台湾真正的生活,我觉得我父亲后来到他快80岁过世,其实他几乎后半辈子是活在他人的梦境,就是很奇怪、很困惑,他听不懂旁人的语言,他始终是这样。
我父亲晚年在中风以前,就有阿兹海默症,我那时候不懂。他特别糊涂,困在一个东西里,永远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永远他跟我们回忆,他20岁逃离南京之前,所有他童年发生的非常细节、非常细的往事。他不断的在讲,像一个坏掉的录音机。夸张到什么地步?我爸每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跟我讲两个小时,重复的讲那些老人的往事。我常常会不耐烦,有一天我跟我太太带小孩从台北回去。那个年代有一种答录机,里面装一个很小的录音带,一面录满是一小时,两面录满是两小时,我发觉那个灯在亮,我发觉是我爸爸打电话给我,对着那个答录机讲满两个小时。他像一个爬虫类,活在一个不知道怎样孤独的世界里。
梁文道:这是骆以军讲话的方式,总是在讲故事,好像很难懂,其实要看你听进去多少,因为这些都是他小说里在说的东西。
说《西夏旅馆》之前要先说一下民国,是今年非常热门的话题。我在台湾成长,对我们这些外省二、三代的人来讲,所谓的民国是个虚幻不可及的东西,很多朋友误以为在台湾能够找到民国。但是,在我们的经验里,民国是什么?民国是个影像而已。20多年前第一次来北京,按照书中看到的北京来寻索那个所谓的北平,我到琉璃厂以为就像当年鲁迅他们那样的在旧书摊翻书,翻累了就到信远斋喝冰镇酸梅汤,那个酸梅汤应该是放在一个大瓮里面,舀出来一碗里面浮着一层冰渣,入口即化,传说是这样的。传说早餐应该吃豆汁配焦圈,我去找,结果当时的北京人问我说的是不是酸奶。
我们那个民国早就不见了,它是一个我们父辈告诉我们的记忆、传说,这个消失掉了。大家于是就想骆以军是不是要用这个来暗喻,用西夏,一个最后曾经强盛,但是终于消失在历史中,到了今天大家能读西夏文的人并不多。西夏的遗迹被破坏得很厉害,用这个状态来讲所谓的“外省第二代”在台湾?

骆以军和张悦然在时尚廊书店以“铸风成形、编沙为绳”为题展开对话。
但是我个人以为他的小说之所以有价值,并不在于他要比前辈写出一种不同的这种外省二代的经验,而是要把这个经验上升到某一种审美上的、历史哲学上的一个构想的层次。所以,我曾经开玩笑跟他说,看完《西夏旅馆》,我说原来西夏旅馆,大家都以为西夏是为了要来写这个民国,其实不是,恰恰相反,我觉得他是要用这个消失掉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来写西夏,是反过来,其实西夏才是重点。是要用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外省二代”在台湾的离散经验,来写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西夏,当这么写起来之后,这个西夏就不是真正的西夏,西夏是一种人类历史中不断出现的状态,那个状态是什么?就是所有曾经在旷野建立起来古怪的王朝忽然又被黄沙掩埋,终于消失无影无踪这样一种状态,历史中消失掉的、离散掉的、被伤害的,这种种的记忆经验,西夏旅馆是关于这种经验的一种沉思跟探索。
孤独的现代主义书写
骆以军师承以后现代主义风格闻名的张大春,处女作《红字团》深受其影响,被认为带着张大春的腔调写成。所以在后来的创作中,骆以军刻意与张大春文风相疏离,渗透进诗意成分在小说中,转而形成自己夹带戏谑与自嘲的蒙太奇叙事风格,然而孤独是他写作永远的母题。
骆以军:我们这一代文学刚启蒙的时刻,基本直接进门的就是读西方经典现代主义作品,像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还有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这些拉美的作家,这一批小说其实最核心的关注是在一个单一的个人的绝对的孤独,和在这种绝对孤独下的绝望。所以我们初期的小说写的都是很像,都是这样一个孤独的人,他在一个密室里,他在一个空房子里,或者困在一个公寓里,大家都是这样。
这和个人经验有关。我这一代创作者,特别是这种外省第二代的背景,从小成长的客厅不存在亲属的树枝状的脉络。我父亲20多岁自己跑到台湾去,到快40岁娶了我妈妈,前半生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孤儿,我妈妈是一个养女。从小到大在老房子里,我见到的亲戚只有我爸爸、我妈妈,还有我哥哥、我姐姐,还有家里的一些狗,我没有见过其他亲戚。一直到我结婚以后,我太太是台湾澎湖人,家族非常庞大,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亲属。我所以我没有办法写出像张爱玲,或者是《红楼梦》那样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理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二十几岁,快速的进入到孤独的现代主义式的书写。
《西夏旅馆》里面有一段叫《洗梦人》,那句话太棒了,它说“神,不愿意再到你的梦里来,是因为你的梦太脏了。”我觉得这特别棒,洗梦对我这个“外省第二代“,很像聚斯金德写《香水》里的格雷诺耶,我是没有故事的,我是一个没有身世的,就像那个家伙是一个没有气味的人,可是他可以透过他对于各种香水的专业技术,萃取的方式,最后可以伪造出一个让所有人疯掉的香水。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变成说故事的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