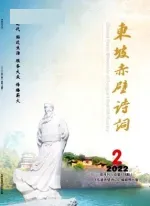试论诗人的忧患意识
丁国成
试论诗人的忧患意识
丁国成
一
忧患意识,古已有之,是我国诗歌文化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文化,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客观世界在人们的头脑中的一种主观反映。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尽劫波,饱经忧患。灾荒、战乱、剥削、压迫、强盗、土匪……致使劳苦大众、平民百姓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备受艰辛,饱尝苦难。先进的人们自然而生忧患情结,并且见诸文字。《尚书·君牙》:“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水。”《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战国策·楚策》引用古语:“居安思危,危则虑安。”《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孔子《论语·卫灵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告子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忧患意识,堪称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可谓百代传承,历久不衰。
诗歌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学宝库的璀璨明珠。历代诗人,作为先知先觉的社会精英,大都富有忧患意识。从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民歌,忧患意识如同红线,一以贯之,成为我国诗歌的宝贵灵魂。《诗经》开创了爱国主义诗歌的先声,也开启了诗人忧患意识的先河;而忧患意识与爱国主义又密不可分,互为因果,各成表里。如《诗经·邶风·柏舟》:“心之忧矣,如痱浣衣。”“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诗经·王风·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忧虑朝政,愠怒小人,爱在邦国,前所鲜见。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刻骨铭心:“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心 絓(挂)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九章·哀郢》)为“皇舆”担忧,替“生民”叹息,心心念念,系于家邦。其后,忧患之作,爱国之作,不绝如缕,屡见不鲜。如三国时的曹植有《杂诗六首》:“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唐代的忧患诗作更多,如: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李白的“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白居易的“心有千载忧,身无一日闲”(《秋山》),“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刘长卿的“惟有家兼国,终身共所忧”(《湖南使还留辞辛大夫》);张为的“向北望星提剑立,一生长为国家忧”(《渔阳将军》)等。宋代陆游有爱国名篇忧民佳作:“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病起书怀》),“残虏游魂苗渴雨,杜门忧国复忧民”(《春晚即事》);楼钥有诗:“一生忧国心,千古敢言气”(《送刘德修少卿潼川漕》)。明代袁宏道为诗,批评创作的不良倾向:“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清代刘岩有诗《赠人》,肯定“古人大业成,皆自忧患始”……
到了近代、现代,由于统治阶级昏匮无能、黑暗腐朽,加以列强欺凌、入侵瓜分,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重重灾难,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痛苦深渊。救亡图存,共赴国难,成了中国先进分子的唯一出路,自然也成了爱国诗人的创作目标。恰如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的《章程》所呼唤:“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
诗人丘逢甲有首《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面对良辰美景、绚丽春光,诗人无心去赏;为遣忧愁,强行看山,谁知反倒进一步加深忧愁,悲泪欲滴:因为不仅兵连祸结,灾难深重的“往事”让人“惊心”,而且连祖国的大好河山——台湾,都于去年(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割让国土)割给日本,沦入敌手,更使人心痛。举国同悲,诗人能不哀痛!至今读来,犹能令人悲愤难忍。女诗人秋瑾有诗道:“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杞人忧》)“好将十万头颅血,一洗腥膻祖国尘。”(《赠蒋鹿珊先生言志且为他日成鸿爪也》)魏源也有诗:“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这些诗作,都是忧患酿就,爱恨激成。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忧患随之愈重。似乎可以说近现代诗人的忧患意识达到又一巅峰,诗作的爱国精神臻于新的极致,爱国主义与忧患意识成了这个时期中国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的主旋律,应了那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清·赵翼《题元遗山集》)的老话头。
总而言之,深沉而又强烈的忧患意识,纵贯历代诗人诗作,形成了一道异常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极其宝贵的诗歌传统。优秀诗人那种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救国救民、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与担当意识,经千年而不泯,历万劫而不磨,至今犹在诗歌史上熠熠闪光,耀耀生辉,引人共鸣,启人深思,让人感奋不已。
二
忧患意识是我们文学(包括诗词)创作的永恒的主题。著名诗人公刘生前说过:“忧患意识、悲悯心态和历史沧桑感,正是我诗国之宝,是足赤的金饭碗,是流贯于中国古诗、新诗血管中的血液,堪称命脉之所系。”(《忧患、悲悯及历史沧桑感——论新诗不可丢了自家的金饭碗》,见丁国成主编《中华诗词·十年评论选》)又说:“许多歪门邪道的‘理论’,全指向了‘淡化’,教年青人去游戏人生,远离社会。忧患意识这个文化国宝,反而遭受嘲笑和调侃。”(致桂汉标的信,见2000年5月总第128期《五月诗笺》文《从五月诗社诗歌创作看中国新诗走向》)诗人发自肺腑的金玉良言,我们不该忘记,因为他说得在情在理。
从社会学上看。诗歌自古以来就被誉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魏·曹丕《典论论文》),虽然未必准确,但也不无道理。如今,诗歌连同文化,已被纳入国家的综合国力之中,成为重要的软实力,亟待予以加强。“国计民生”一向都是相提并论的,因为“民生”决定“国计”,“国计”关乎“民生”。亦即古人所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业》)而要“本固”,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作为诗歌精神和人文精神核心的忧患意识,自然显得更加重要和珍贵。
从哲学上看。自然世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矛盾;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矛盾还可以互相转化。忧患与安乐同样是对矛盾,相融相谐,互动互变。乐里存忧,安中有患,如果不加警觉,缺乏应变能力,乐可成忧,安能遗患。也就是古人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正与邪,善与恶,盛与衰,存与亡,进与退,成与败,生与死……莫不如此。它们共处于统一体中,既有矛盾性,又有同一性,还可彼此转化。然而,矛盾只有揭露出来,方能得以解决。如果长期掩盖、隐蔽,矛盾非但不能解决,反而越积越大,终致酿成巨祸,世人遭殃。诗人满怀忧患意识,富有哲人眼光,能够洞见未来,发现隐忧,透过现象看出本质,于无声处听到惊雷,那就不仅会在变动不居的复杂世界中,自身不被矛盾所困扰,而且可以主动自觉地向世人发出警醒呼唤,为社会进步、人类发展做出独特贡献。
从心理学和诗美学上看。诗中的忧患意识是诗美的培养基,是心理的平衡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中,引用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诗句,指出:“‘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资料。”诗的本质,重在抒情。愤怒与忧患虽属两种不同的情感类型,却都出于同一失衡心理,互为因果,彼此相生。而情感心理失衡,必然寻求发泄,即唐代韩愈所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陈兆仑认为:“盖乐主散,一发而无余;忧主留,辗转而不尽。意味之深浅别矣。”钱钟书说得更为明白:“欢乐‘发而无余’,要挽留它也留不住;忧愁‘转而不尽’,要消除它也除不掉。用歌德的比喻来说,快乐是圆球形,愁苦是多角物体形。圆球一滚而过,多角体‘辗转即停’。”(《谈艺录》)忧患愁苦,凝如结,重如石,的确“转而不尽”,需要着力排遣,摆脱苦闷,以求心理平衡。而遣闷的最佳方式,就是吟诗作赋。清代李渔深有体会:“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谮作两间最乐之人。”(《闲情偶寄》)当代诗词巨匠聂绀弩也有如此体验。
而且,无论是因愤怒而忧患,还是因忧患而愤怒,发而为诗,均易成为佳作,创造诗美,打动读者。古人常说,“欢愉之辞难工,而愁苦之言易好也。”(韩愈《荆潭唱和诗序》,见《韩昌黎全集》)“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清·纳兰性德)英国诗人雪莱也认为:“悲愁中的快感比那从快乐本身所获得的快感更其甜蜜。”(《论辩》、《西方文论选》下卷)因为愁苦之言、忧患之作既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作者的创作激情,又能极其强烈地引发读者的心理共鸣。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说得好:“痛苦与忧愁叩打我们的大门,比幸福与快乐发出更大的声响;它们的沉重脚印也更不容易抹去。”(《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一般说来,诗作产生共鸣的强弱多少,表明其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的大小高低。同是杜甫描写花鸟的成功之作,“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家》)不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更为慑人心魄,入人骨髓,便是由于前者属于“欢愉之辞”,后者则是“愁苦之言”其社会效果和美学价值,比较而言,尽管皆能给人审美愉悦,但后者显然更大更高,是一种恒久而又沉重的悲壮美。也许正因如此,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才说:“几乎不能想象,任何一种美会没有‘不幸’在其中的。”
1949年12月,当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表达他对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所写诗词的赞叹时,诗人毛泽东深有体会地说过:“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了。”(朱向前《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这大概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现象:愤怒多出诗人,忧患易生佳作。
三
遗憾的是,当前诗界却有些人对于忧患意识从理论到创作随意否定,妄加轻蔑。
一种理论,可称为“无益论”:“正如歌里所唱的,‘不要把地球扛在自己肩上’,这句话对极了。每天,全世界都有犯罪、饥饿、不孝、不公正、堕落、罪恶在发生。如果我们选择关注所有这一切,那么这只会把我们拖入更彻底的绝望之中。爱惜自己吧!别这样折磨自己。”(《你为何如此疯狂》,2002.9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见《书摘》)由于价值观念不同,人生信仰有别,对待忧患意识的态度、结论也就截然相反。苏联作家、世界文豪高尔基认为:“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因此他要求诗人“不要把自己集中在自己身上,而要把全世界集中在自己身上。”(《给基·谢·阿胡米英》)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就是要忧国不忧身、忧民不忧己、忧道不忧贫,心甘情愿地“把地球扛在自己肩上”,为国家、为民族、为世界、为人类忧劳不止,死而后己,因为他懂得人要活得有价值,就必须创造价值,只为自己苟活毫无意义,社会并不需要他,人类也不缺少他。
另种理论,可称为“过时论”:“忧患意识已不应也不能再成为提倡的审美意识……忧患虽然是封建社会优秀的传统意识,但其本质是为维护旧秩序服务的,忧患说到底,除了伤害自己的身体,不能触动腐朽事物的一根毫毛……忧患毕竟是属于过去。”(王林书《让诗心永远年轻》,见粤北文学丛书第一辑《追寻永远的美丽》)此论不能自圆其说。“优秀的传统意识”与“维护旧秩序”自相矛盾,不能并存。恰恰相反,忧患意识的出发点就是要改变“旧秩序”,以求完善。忧患意识是个历史的概念,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前进也在不断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乃至不同的国家民族,有着完全不同的涵义。但是,其本质则是一致,即爱国爱民的爱国主义和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也就是以人为本的博爱精神。从古到今,由中至外,忧患意识都是利于国家、益于民族、裨于人类的崇高的思想道德。不管社会怎样发展,世界如何变化,国家是否兴亡,只要人类存在,这种博爱精神就永远需要,而绝对不会过时。它将恒久地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类和谐。
唐代吕温有诗道:“四月带花移芍药,不知忧国是何人。”(《贞元十四年旱甚见权门移芍药花》)千年之叹,又见如今文坛。我们的一些诗人、作家,不知忧国为何物,却热衷于玩诗码字,陶醉于自娱自乐,沉浸于自叹自怜,迷恋于自怨自艾,脱离现实,躲避崇高,缺乏担当意识,丧失人文关怀。他们无视业已泛滥成灾的欢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面对官场腐败、社会丑恶、道德沦丧和世风堕落而哑言失声。这样的诗人、作家,怎么可能写出震聋发聩的优秀作品来呢?从水管里流出来的,自然只能是水——被人宽容地称为“小文人诗歌”。写的是小天地、小感觉、小情趣、小哀怨、小感悟、小哲理。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求之以有益无害,已属过甚期望,遑论其裨于家国人类!不少诗人,毫无忧患意识,领略逸豫享乐,似乎一切都已完美无缺,耽于游山玩水、吟风弄月。真的“似鹤如云一个身,不忧家国不忧贫。”(唐·杜光府《偶题》)青年诗人康卓然予以批评:“岂知今日文章事,花月春风总不休。”(《怀杜甫》,见2004.12《中华诗词》)对于这种创作倾向,古人早就痛下针砭:“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白居易《采诗官》)
等而下之者,沉湎于“下半身写作”,泡制淫诗脏诗,毫无节制地制造文字垃圾;或以“持不同政见者”自居,杜撰异端诗词,肆无忌惮地污染精神环境。这是道德品位大幅滑坡、价值观念严重倾斜、思想意识极其混乱的突出表现。令人奇怪而不解的是,这类丑陋东西居然堂而皇之地获得国家大奖——例如“非毛化”(不是一般批评毛泽东的错误)的诗词家攫取了全国性的“华夏诗词奖”;有写“下半身”新体诗的《只有大海苍茫如幕》(作者于坚)竟被中国作家协会授予“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后者引起世界华文诗人的强烈不满,遭到诗坛内外读者的严厉批评,直至有人告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至立那里,中国作协才给陈至立写了“报告”,承认评奖“尚有缺欠”,承认“于坚的这几首诗作的确格调不高,文字粗疏”(见2009.4.25《华夏诗报》报道)。但这只是“内部”上报中央领导的检查报告,既未公开承认评错,更未纠正错评、收回“获奖证书”。尽管诗坛批评一直未断,中国作协却至今沉默不语。非特此也,且于2009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 /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选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诗歌卷》,由中国作协所属作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内收于坚近照、小传及获奖诗集中的18首诗作,为书特制宣传“腰带”,上面一边大书:“国家最高级别文学大奖 /最权威选本/中国作家协会唯一授权/代表2004-2006年度中国文学最高成就”;另一边大书:“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首度面世/中国当代文学新经典/值得阅读和珍藏 /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哪里存有认错之意?分明掩盖错评之非!!咒骂鲁迅“乌烟瘴气鸟导师”、大写淫诗的于坚因而仍被国内一些报刊竞相追捧。这就是中国文坛诗界铁铸一般的现实!
当然,从整体看,无论新诗,还是旧体,成绩都是主要的,有目共睹,不容否定。但是,存在的严重问题也不容忽视,亟待认真加以解决,方能促进中国诗歌走向真正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