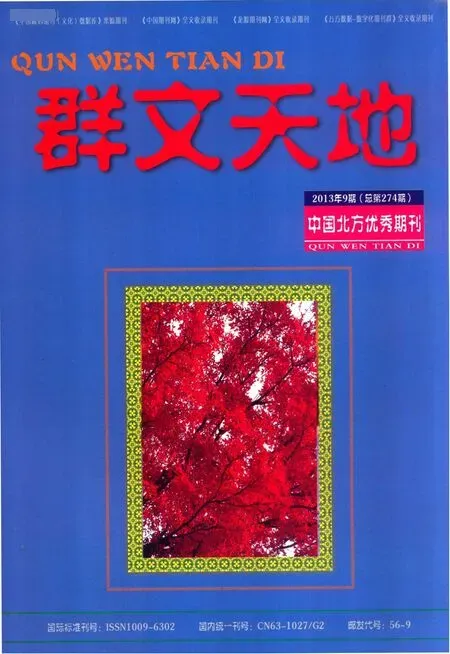谈审美态度的培育与生态人格的养成
■苏中
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谈到审美态度时,曾以古松为喻,指出人对古松可以有三种态度:这是什么样的松树,有多少年份了——是为科学的态度;古松有什么用处——这是功利的态度;不在乎其是什么树也不管有何用,只是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它,发现了古松是一种美的形式,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这是审美态度,在这里,古松成了表现人情趣的意象或形象。朱良志教授在其《真水无香》一书中也提到了一种所谓“生命的态度”,他将之称为“第四种态度”:“在这里,审美主体和对象都没有了,古松在这里根本就不是审美对象,是一个与我生命相关的宇宙,我来看古松,在山林中,在清泉旁,在月光下,在薄雾里,古松一时间活了起来,成了一个瞬间形成的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我的发现使古松和我、世界成了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①朱良志先生以此为中国美学迥异于西方美学的独特气质。细究之,我们可以发现,此“生命的态度”,其实就是审美的态度,特别是指审美心理中的“移情现象”。
我们知道,审美欣赏实质上是一个移情的过程,欣赏主体把自己的情感、意志、思想等主体因素转移到客体对象身上,使对象成为自我的化身,而主体则在情感的自由解放中获得心理的快适体验。简单说,所谓移情作用,“就是人在观察外界事物时,设身处在事物的境地,把原来没有生命的东西看成有生命的东西,仿佛它也有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同时,人自己也受到对事物的这种错觉的影响,多少和事物发生同情和共鸣。”②这种现象是很原始、普遍的。意大利思想家维科将移情现象看作形象思维的基本要求,认为“人心的最崇高的劳力是赋予感觉和情欲于本无感觉的事物”,语言、宗教、神话和诗的起源都要用这个原则来解释。可以说,人们对此是早有注意和认识的,如在我国古代文艺心理思想中有所谓“兴”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注意到所谓移情即为一种隐喻,英国经验派美学家休谟、博克把移情看作同情和摹仿,康德在分析崇高时将移情现象称为“偷换”(Subreption)。在西方美学史上,德国美学家立普斯(Theodor Lipps,1851-1914)的“移情说”第一次从理论上总结了人类审美活动中主体与客体实现同一、互相沉入的现象:主体完全沉没在对象中,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客体则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显得情趣盎然,灵意弥漫。这非常类似于中国美学中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的体验,恰如庄子“相忘于江湖”之鱼、“濠上之乐”、“不知我为蝴蝶,还是蝴蝶为我”的认识。代表中国古代审美心理思想最高成就的“情景交融”说,其核心也在“移情作用”。
应该说“移情”是审美态度的核心,唯“移情”,故而审美活动具有超越逻辑、超越道德、超越功利的性质,就是在物与我的实际利害之间插入了一段“心理距离”,使我们能够摆脱世俗的、功利的偏见,换一种眼光或角度去观照世界。瑞士心理学家、美学家和语言学家布洛在其《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一文中指出:“距离是通过把客体及其吸引力与人的本身分离而取得的,也是通过使客体摆脱了人本身的实际需要与目的而取得的。”正如我们所理解的庄子的“精神超越”,因在庄子看来,功利之心、是非之心、欲望之心不能把握到“道”,只有离形去智、解粘去缚的“虚静之心”才能捕捉到“道”的朗然显现。毕达哥拉斯云:“人只有处在旁观者的地位,才能获得审美愉悦。”康德也说:“人只有处在冷静观察者的地位,才可以作审美判断。”
因为在审美体验中,如一味移情则使审美主体与对象的界限完全消除了,艺术世界被还原为世俗世界,结果就造成美感的消失或变成熟视无睹、习焉不察之麻木或变成主体的自伤身世、自怨自艾。而距离能带来“超然”的效果,如同我们追忆似水年华、久远之童年记忆,遥想缥缈之未来,总会因为模糊朦胧的距离而增添别样的美感。审美态度要求于我们的,即是这种“若即若离”的、既为“分享者”同时又是“旁观者”的立场。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有一段话说得透彻:“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又,“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柔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③审美或曰“移情”,实在此“出入”之间耳。我们可以继续说,入乎其内,故有悲悯和同情;出乎其外,故有觉醒和超迈;入乎其内,故能移情观照;出乎其外,故能超然审视;入乎其内,故有人间情怀,出乎其外,故有天地精神。入与出因而矛盾统一,移情卷入和远距反观因而对立统一,这体现在审美中,就成为内蕴了天人之道的审美张力空间,独特而深远的审美意味,就内蕴于其中了。④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有言:“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可谓深得之。
如果我们站在皮亚杰认知发生主义的立场,可以发现,艺术活动非仅为“复现”或“摹仿”自然,亦非单纯是人的情感意志之“表现”,而是主客双方的互动、“沉入”,是一种意义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来看王阳明一段著名的对话,对我们理解审美中的移情作用也许是有意义的,在《传习录下》中有如下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种“生命的态度”是须建筑在“生态人格”基础上的。王茜在其《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人格的培育》一文中描述了生态人格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诗性智慧和栖居意识。⑤可以说是审美态度的最好注解。
敬畏生命首先意味着对生命神圣性的一种类似信仰的体认。可以说,敬畏之心源于人对自身有限性和宇宙无限性的认识。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早已去除了自然曾有的神秘光环,有着丰富生命内涵的自然在现代科学中变成了面目苍白的公式和数字。由于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人愈来愈变得自私自大,自恃己能,把自然看作可以凭借人类理性和技术就能够征服的对象,心灵骄纵,无惧无畏。敬畏生命意味着用一种不同于科学思维的体验能力最大限度地接近自然,但这并非要人们放弃对自然世界的科学认识,而意在让人们意识到科学认知的有限性。人是浩瀚苍茫的生命存在中的一个微渺个体,如果用对象性认知方式去理解自然,就决定了它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对象的一部分,因此以有限去把握自身所处的无限就永远有其局限性。科学是理解生命的一个必要步骤,但唯有通过与生命个体息息相通的真诚体验,人才能在一个更高境界中靠拢生命的奥秘。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时刻怀抱对自然生命的无限敬意时,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才会充满希望。敬畏生命中还包含着一种道德内涵,既把生命理解为一种自然现象,又把生命当作一种道德现象,在这种超越人际关系的道德指引下从事个体实践活动。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通过科学研究探索自然规律,又要善于在此基础上领会自然中一切生命现象所蕴涵的灵性,把自然的生命规律当作个体道德实践的前提基础,使行动尽量符合自然世界所启示的生存法则,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共在互动的道德观。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先驱史怀泽就将敬畏生命当作一种最基本和最深刻的道德要求,认为人要善于体会一切生命之间的休戚与共,并尽自己所能保护和帮助其他生命。
生态人格还是一种富有诗性智慧的人格,在具有诗性智慧的人看来,世界原本就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体,情感体验和理性思维一样是人与世界发生关联的方式。他善于运用自己的感受力和直觉,不对理性认知世界和情感体验世界做出真假对错好坏的简单判断。诗性智慧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存在的真实面目:自然是随时凝聚着人类的目光和心灵的自然,而不是价值中立的客观事物;人是通过自然来确认自我生命的人,而不是仅拥有一些主观情绪的主体。人在流水中体会到的柔情与水分子结构、在花中感受到的微笑与花的植物学属性同样真实。诗性智慧并不排斥对自然世界的科学认知,不应被斥责为儿童式的天真或者艺术家式的幻想,但这种智慧却让人心中弥漫了对于自然和生命的柔情。在“大地伦理学之父”利奥波特的《沙乡年鉴》中,科学观察与统计方法和对土地深沉的热爱并存。雷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用细致的观察、优美动人的笔触带给读者震撼,唤起人们对生态危机的警觉,被誉为生态文学的里程碑。这些生态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更为深沉、更为精神化的接近自然的方式,那就是调动起情感、直觉、体验等人为之人的全部生命力,更加敏感地向世界敞开,使原本枯燥苍白的科学实验成为用全部柔情与一个瑰丽多彩的生命世界展开的交谈。培育这种人格,就要“学会欣赏宁静和孤独,并且学会去聆听……在理解的时候更加善于接受、有信任感和整体意识,并且建立在一种非攫取性的科学技术的视野中。”“忠诚于并且信任我们的直觉;勇敢地采取直接行动;怀着愉快的自信与感觉的和谐共同舞蹈,这种感觉的和谐是通过与我们身体的节奏、流水的节奏、天气和季节的变化、地球上所有生命过程的自发而富有游戏精神的对话而被发现的”(生态学家比尔·戴维尔),怀抱一种审美的精神生存。这种诗性智慧,其实在中国文化中有更为深刻的表述,它广泛存在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各种形式中,成为中国文化的自觉追求。
相应地,生态人格也包含着“栖居”意识。“栖居”意识不同于“环境”思维,环境思维把人当作世界的中心,自然则是环绕在人类世界周围的、被人支配利用的对象,在环境思维作用下产生的很多环保科技、制度规定都只能暂时缓和生态危机,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对自然的破坏。我国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以人类为中心,哲学总说不通。哲学虽不是求科学或历史学的真理的学问,然而总不能违背别的学问所发现的真理。就自然史说,人类是近多少万年才出现的动物,人类的聪明也许空前,但是从自然史的观点说,它绝不至于绝后。天地也是老在变化的,在多少年前地球是人类不能生存的地方,在多少年后它也许会回到一种景况使人类不能继续生存。人类中心观在天文在地理在地质学总是说不通的,在这许多方面说不通的思想在哲学上也是站不住脚”。⑥在西方,德国哲学家荷林德尔最早提出了“人诗意地栖居”这一命题,在他看来,“栖居”有两重含义:栖息和筑造。栖息意味着人和一切生命一样自然地生存在地球家园中,接受天空、大地和季节的馈赠,尽量让人类个体的生命节奏与自然的生命节奏协调一致,像美国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所说:“去感受那些在本地表现的特别明显的周期性的普遍现象——季节、生命的巨大的再生能力、生命支撑、时间与空间的协调一致”。而不以征服者的姿态把人从自然中连根拔起。建筑房屋、修建桥梁、耕种田地,一切为生存而进行的实践活动都可以被称为筑造,筑造本质在于对生命的爱护和保养,在于对生命家园的修葺与维护,在于对栖息的守护与积极筹划。栖息是筑造的目的与前提,筑造是人之为人的栖息得以展开的方式。具有栖居意识的人拥有对生命的平和之心,他的使命就是让自身和一切自然生命都处于自由自在的本然状态中。他理解并尊重作为生命母体的大地,因此能够安于在大地上劳作,作为大地的守护者而存在,并通过劳作理解一切非人类存在与人类的关联,尊重它们独立的生命价值;他懂得维系昼夜交替、四时轮转的天空蕴涵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命运力量,因此能够安然于这种生命的节律,不使黑夜成为白昼,也不使白昼变得忙乱不安;然而,栖居之人并不像动植物一样只有被动的顺从,生命的灵性同时使他心中有所疑惑、有所期待、有所敬畏,因此他在栖居中会为对自然的神圣性留出位置,然后从容地安排自己最终会走向死亡的生命。在这里,栖居意味着人在一个完整生命境界里的生存,这个生命境界不能被简单地划分成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而是由群星闪耀的天空、沉实厚重的大地、自然神圣的光芒和人共同构成,人身处其中,在对这种完整性的体验中展开生命。
审美活动中的“生命态度”的确立,实上述“生态人格”之精髓,自无须赘言。昔孔子与诸弟子论议,深许曾点之志,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朱熹注云:“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欲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⑦可知儒家思想之情怀固在现实社会人际之和谐秩序,然其终极关怀亦见出对人的自我实现的安排,按照冯友兰的说法,其最高境界即是“天地境界”——植根于人类心灵结构最深层的“志性”⑧的朗然自觉与明白——一种审美的精神生存。
通过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通过这种审美态度之确立,我们能看到人与世界重建和谐的希望。因为古希腊先哲们早就见出:城邦的终极目的与人的终极目的是一样的。作为现实政治安排的“政体”,与体现在每个人身上的“政意”关系甚大。用言说的“逻格斯”建立的城邦,在地上是找不到的,但能看见这种“天上的原型”的人,却能凭借他的所见,将这种城邦建在自己的身上。
注释:
①朱良志.真水无香[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②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③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④朱兵、马正平.失败的小说:审美张力空间的匮乏[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6).
⑤王茜.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人格的培育[J].中国教育报,2004年10月18日.
⑥金岳霖.知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⑦朱熹.论语集注[M].齐鲁书社.2006.
⑧胡家祥.审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