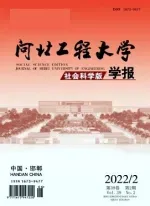论清初文禁对杜诗学的直接影响
王新芳,孙 微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
论清初文禁对杜诗学的直接影响
王新芳,孙 微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
清初日益严酷的文禁对文化摧残严重,对杜诗学亦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对学者人身迫害及其著作的禁毁,另一方面文化禁令使得清初形成的文人广泛交流的学术氛围得到压制,日渐残酷文字狱摧残了士人的文化品格,让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面前噤若寒蝉,对杜诗的阐释也随之由明末的自由活跃而一归于古板正统。
清初;文禁;杜诗学
清代是杜诗学史上的集大成时代,清初杜诗学形成了杜诗学史上的第二次高潮。然而随着满清统治者日益严酷的集权高压统治的加强,多次大兴文字狱,对文化摧残严重,同时也对杜诗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简要论析。
一、对学者的人身摧残及其著作的禁毁
在清初日益残酷的政治环境中,许多杜诗研究者遭到人身摧残。在“哭庙”案中殒身的金圣叹,是清初较早死于统治者屠刀下的杜诗学者,其临刑时杜诗尚未批解完成,留下了“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如何”那样的遗憾。金圣叹死后,由族兄金昌整理问世的《杜诗解》在清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因政治原因一直被禁,当时的学者即已很难访求,如吴县王大错在《才子杜诗解叙》中曾称其“二十年来百觅不得”[1],此书直至民国初年方与《钱注杜诗》等得以大量翻刻问世,其流布方广。
此外,曾与撰明史的著名学者潘柽章,康熙二年六月,因庄廷鑨《明史》案起,与吴炎一起被斩首于杭州弼教坊。其所著书,亦因之而被禁废。他遇难后,友人戴笠作《潘力田传》,记其著书有《杜诗博议》。钮锈《觚賸》卷一“力田遗时”条载:“潘柽章著作甚富,悉于被系时遗亡。间有留之故人家者,因其罹法甚酷,辄废匿之。如《杜诗博议》一书,引据考证,纠讹辟舛,可谓少陵功臣。朱长孺笺诗,多所采取,竟讳而不著其姓氏矣。”[2]此书仅因为朱鹤龄《杜诗辑注》的征引而得以部分被保存,仇兆鳌赞其“发挥独畅”[3]。而此后该书竟被嫁名于明王道俊、宋杜田等,被搞的扑朔迷离,直至当代学者蔡锦芳撰文指出,《杜诗博议》一书的真正作者应该是潘柽章[4],这样一部沉埋了三百馀年的杜诗学文献才得以重新纳入学界的视野。
在南京图书馆所藏方贞观《批杜诗辑注》中,方氏有这样的卓见:“子美诗势力绝人,读之久自有裨益处。然当领其大意,不必深求,愈深求,愈入窟穴。非子美不可学,恐学者自缠魔障耳!”“吾愿天下之读杜者,勿攻其实,勿遗其虚,勿惑于‘诗史’之说,勿惑于‘一饭不忘君’之言。含咀其精华,吐弃其渣滓,庶几斯道正宗,不终断绝也。”而在戴名世《南山集》案中方贞观被谴戍塞外。另外还有方孝标其因所著《滇黔纪闻》为戴名世《南山集》所采,坐戮尸之祸,罪连家族,方氏之文也全部被禁。陈式与方孝标为同乡,其所著《问斋杜意》前因有方孝标序,使得此书的流布也受到很大影响。在戴名世《南山集》案中,除方孝标、方贞观受到牵连外,还有汪灏亦受到处分。据全祖望《江浙两大狱记》记载,汪灏因为戴名世所著《孑遗录》作序被累镌秩,以纂书有功得免死。康熙五十一年四月,皇帝对大学士等人说:“案内拟绞之汪灏,在内廷纂修已久,已经革职,著从宽免死,但令家口入旗。”汪灏曾著《知本堂读杜》二十四卷,因作者罹文祸之故,此书在道光重刻时被删去原序,易名为《树人堂读杜》。
至乾隆朝的文字狱愈演愈烈,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有关杜诗的禁书有钱谦益《钱注杜诗》和两种朱鹤龄《杜诗辑注》[5]。钱谦益被乾隆帝目为“反复小人”,列其名于《贰臣传》乙编,欲使其天壤间不留一字,对其作品严加禁毁,甚至有钱氏做序的所有诗文集也因之被禁,真可谓殃及池鱼。《钱注杜诗》作为有清杜诗学的开山之作,自然首当其冲。从乾隆四十年开始《钱注杜诗》即遭禁毁,所以此后诸家引用钱注时往往闪烁其辞,或称“旧本”或称“旧注”。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所收录的仇兆鳌《杜诗详注》即将仇氏所引钱谦益字句尽数删去。直至清季文网既驰,宣统二年(1910)国学扶轮社及寄青霞馆据何焯批点排印本、宣统二年袁康集评之上海时中书局石印本的出现,此书始见天日,得以大行于天下。另四库馆臣将明傅振商所著白文本《杜诗分类》列入存目,而经清张缙彦辑定的傅氏《杜诗分类集注》虽仍为白文本,题下皆加注,周采泉先生认为《集注》本远胜于傅振商的原书[6](P139)。四库馆臣将版本较胜的张氏《集注》本摒弃不录,乃是因为乾隆亦将张缙彦打入《贰臣传》中,因此避讳,四库馆臣只能弃善而存劣。另外,许多由明入清的学者,因为诗文中带有民族意识而被禁,牵带着其学术著作的被禁止和消亡。如曾批杜诗的吕留良,因曾静案的牵连,死后竟被戮尸。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刘世教《分类杜工部诗全集》中,吕留良在对《北征》批云:“取杜诗以忠义,自是宋人一病。词家谁不可忠义?要看手段,即《离骚》亦然,且如丈夫经天纬地事业,岂止忠义云乎哉!”极易让人联想起他的“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那样的严华夷之辨的议论。假如这种思想象其所评时文那样得以广泛流传,对清统治者自是极端不利,此书理所当然地遭严禁。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还著录了石卓槐《批杜工部集》一部以及《读杜心解》一部[7],系乾隆四十四年(1779)湖北巡抚姚成烈奏缴。石卓槐,字廷三,黄梅人,监生。石氏以《芥园诗钞》有“悖逆”语,被凌迟处死。其所谓“悖逆”语,即“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这样的诗句。石卓槐本文名不彰,所批点杜诗竟以其人被祸,列入禁书,虽与杜学本无甚关涉,亦可见乾隆朝文禁之烈。
与钱注相垺的朱鹤龄《杜诗辑注》亦因为前有钱谦益所作《草堂诗笺元本序》而遭禁。《清代禁书总述》中就载有河南巡抚富勒浑奏缴,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二十九日准奏的朱氏辑《杜工部诗集》。朱氏本欲借钱氏之名,以达与钱注各擅胜场之功,讵料适得其反。本应于清朝乃至整个杜诗学史上处于高峰地位的两编巨册,就这样变得湮没不彰。此后朱鹤龄《杜诗辑注》一直处于被“抽毁”书目之列。如果说《钱注杜诗》虽然遭禁仍能暗中流布的话,那么《杜诗辑注》除被诸家所引用外,仅乾隆间有过一次翻刻(金陵三多斋刻本),此后一直无再刻本。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杜诗辑注》本是康熙九年金陵叶永茹万卷楼刻本,其中凡是杜诗中涉及到“胡”、“杂种”、“夷”、“虏”等字样,均被涂改成墨丁,全书多达百余处。其实这一时期同样遭到挖改命运的杜诗学文献还有很多,如康熙十一年岱渊堂刻吴见思《杜诗论文》,书中凡涉及“胡羯”、“胡虏”、“戎”、“夷”、“狄”、“犬戎”等字时均缺,缺字多达160余处。吴氏在该书《凡例》中虽隐晦地说:“开元至今,传之千载,岂无讹字阙文,若为傅会,便多穿凿矣。故意见未明处,谨为阙疑,以俟君子。”[8]但我们从此类阙文中仍可明显看出文字狱的风声鹤唳。康熙二十一年镌版之陈式《问斋杜意》亦避讳“胡”、“匈奴”等字,亦遇之皆阙。可见当时同遭此厄的图书当不在少数,而且这还是处在文网未密的顺、康朝的情形。到乾隆朝《四库全书》的编纂,其“寓毁于征”的策略更是使得大批杜集版本或湮没不彰,或损失殆尽,兹不赘述。
二、对学术思想自由的压制
明末清初由于文网未张,文人之间的交流显得自由活跃,那些学者的治杜,不再是一个人面壁的“野狐禅”,而是众多学者相互研讨、争论,形成了广泛深入的学术研讨氛围。如杨凤苞《书南山草堂集》云:“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其最盛者,东越则甬上,三吴则松陵。”“甬上僻处海边,多其乡之遗老,间参一二寓公;松陵为东南舟车之都会,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盛于越中。而惊隐诗社,又为吴社之冠……今考入社名流……顾炎武、朱长孺……”[9](卷一)其活跃可见一斑。可以看到,这些党社活动的成员当中包括许多杜诗学者,他们在结社活动中得以广泛交流思想,印证心得,无疑对促进清初杜诗学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统治的日趋严密,清世祖于顺治九年(1652)正式颁布禁止党社的敕令:“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10](卷下)顺治十七年(1660)春,礼科给事中杨雍建上《严禁社盟疏》曰:“纠集盟誓者所在多省,江南之苏杭,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建议“严禁结社订盟”[11]。顺治帝批准,并重申顺治九年的禁令。遭到这样的打击,清初的党社活动因而一蹶不振。
清初顾炎武等人的结社固然有反清复明的政治目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清政府的统治日益稳固,反清力量渐次衰歇之后,这些文士的结社唱和便更多地带有了学术交流的性质。严厉的文化禁令使得清初形成的文人广泛交流的学术氛围得到压制。另外,日渐残酷文字狱还摧残了士人的文化品格,让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面前噤若寒蝉,对杜诗的阐释也由明末的自由活跃而一归于古板、迂腐。如康熙三十二年,仇兆鳌《杜诗详注》进呈御览,其在《杜诗详注序》及《附进书表》中关于弘扬杜甫忠君思想的大肆表白中,哪里还可见到初清学者的批判精神的影子!流风所及,对杜诗的阐释与笺注又逐渐形成了一种声音,就是推崇杜诗的“温柔敦厚”与“一饭不忘君”,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开始为正统古板的大一统时代所掩盖、取代,其杜诗学在音韵训诂方面取得的考证成绩,又是以通达简明的释杜精神的丧失为代价的,这都给后世的杜诗学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启迪。
[1]金圣叹.才子杜诗解[M].上海:震华书局石印本,1919.
[2]钮锈.觚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蔡锦芳.《杜诗博议》质疑[J].杜甫研究学刊.1989(2).
[5]王彬.清代禁书总述[M].北京:中国书店,1999.
[6]周采泉.杜集书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吴见思.杜诗论文[M].清康熙十一年(1672)常州岱渊堂刻本.
[9]杨凤苞.秋室集[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佚名.松下杂钞[M].涵芬楼秘笈第三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11]杨雍建.杨黄门奏疏[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On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literary inquisition on Du Fu poetics at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WANG Xin - fang,SUN Wei
(Literature College,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China)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devastated seriously the culture at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so it had the enormous negative influence on Du Fu poetics.On the one hand,it caused scholars’personal persecution and work destroying.On the other hand,it suppressed the academic exchanges formed at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The cultural prohibition rule devastated the gentleman person’s cultural moral character day after day,and made them keep silent in front of the high -pressured politics,so the tendency of Du Fu poem’s explanation changed from freedom and active to the traditional orthodox.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literary inquisition;Du Fu poetics
K203
A
1673-9477(2011)03-0061-02
2011-06-12
河北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项目编号:SZ2011935)
王新芳(1973-),女,山东临沂人,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责任编辑:王云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