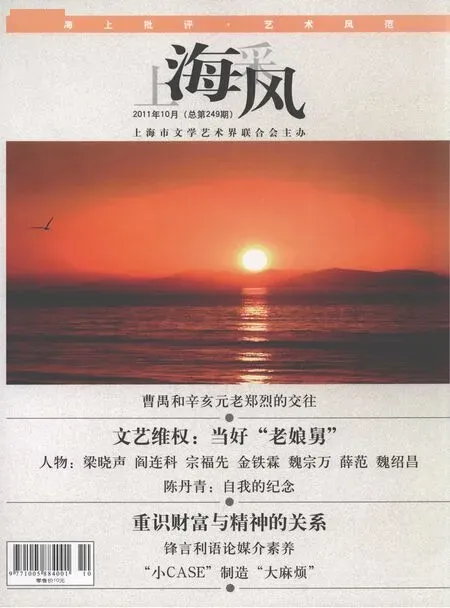薛范:与歌同行,与爱相伴
文/刘 屏

薛范先生的家在上海中山南一路的一条里弄里。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乘地铁8号线到西藏南路的3号口出来就是,很方便。因为我对上海的交通不太熟悉,决定还是打车前往,好在轰轰烈烈的世博会刚刚结束,路面上已不拥堵,从我们住的昌平路到他家走了大约40分钟,下午3点准时到达。出租车司机热情地告诉我们:从中山南路再往前走一点儿就是世博会在浦西的场馆了。
薛范先生住的楼房不高,也不豪华,从外观看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建设的简易楼房,在上海这个繁华大都市里,这类楼房应该属于平民区。按响门铃,薛范先生亲自摇着轮椅为我们开门,然后又麻利地掉转车子带我们通过狭窄洁净堆满物品的短走廊,拐进一间门厅不大的房间,走进房间,迎面扑入眼帘的是四处堆满的报纸期刊、书籍和光盘,一台打开的电脑和音响被包围在书山报海中,门边的书柜里外摆满了他的作品集和荣获的各种证书、奖状、奖杯等,四壁除了时钟,没有任何装点,可见主人生活的简洁。
我们隔着报刊垛和一张堆满了资料的圆桌对话。眼前的薛范先生面色清癯,热情的脸上带着少许的疲惫。我听说,他每晚都要工作到凌晨,上午睡觉,下午才起来开始新一天的工作,所以这次与他见面的时间定在了下午3点。薛范告诉我,他今天早上8点才睡觉,在翻译朝鲜电影《一个护士的故事》中的主题歌《护士之歌》。因为影像的解码软件不匹配,弄了一夜,不过总算是弄好了。说着,他打开电脑,为我们播放一夜辛劳完成的杰作。荧屏上出现熟悉的电影画面,房间里响起熟悉的乐曲,我竟然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啊!原来这是我当兵时就会唱的朝鲜歌曲呀,熟悉的歌曲、熟悉的影像一下子把我带回到那个青春如火的年代,也把我和薛范先生的情感融合到一起。这种美妙的感觉,跟我同去的年轻人小慕,是怎么也不会理解和感悟到的。看到我这样的激动和沉醉,薛范先生又给我们放了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原唱者演唱的音乐影视,那熟悉的音乐,歌唱家声情并茂的演唱都深深地打动着我,此刻,我发觉薛范先生也沉浸在悠扬的音乐中。
曲罢,我们都没有说话,久久沉浸在那弯明月和歌声带来的氛围中。稍倾,薛范问我是否知道《列宁山》这首歌曲?我说知道,但不熟悉。他看着我点点头,似乎有点遗憾。的确,作为一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我唱得最多听得最多的苏俄歌曲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小路》《山楂树》《灯光》《红莓花儿开》《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等。
闪回:我与薛范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去年夏天,我去哈尔滨参加高莽先生“中俄文化名人肖像画展”的开幕式,在充满俄罗斯风情的伏尔加庄园的欢迎晚宴上,高莽先生告诉我,坐在旁边轮椅上的人是薛范,著名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翻译者。我耳边仿佛立刻响起那悠扬动人的熟悉旋律,无限敬意从心中肃然升起。晚宴上,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先生声情并茂地演唱了《伏尔加船夫曲》,博得大家的热烈掌声。薛范先生是作为画展的特邀嘉宾专程从上海赶来的。他和高莽先生都是中俄文化艺术交流的功臣和使者,一个借助流动的绘画——音乐,一个借助凝固的音乐——绘画。开幕式结束后,我有机会在哈尔滨市图书馆听了薛范先生题为“我与俄罗斯——中俄文化交流一席谈”的讲座。会场爆满,各个年龄段的听众都有。主讲人没有过多地谈自己的创作历程和成就,而是把讲座变成了一场苏俄音乐歌曲的欣赏会。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是第一次听这位俄罗斯歌曲翻译大家的讲演,太精彩了。中间插播了他精心挑选的苏俄歌曲,不时伴有简洁明了的讲解,让人感觉到苏俄歌曲的厚重和文化积淀,也让我第一次对俄罗斯歌曲有了全新的认识,从他搭起的彩虹桥上走过,走进俄罗斯歌曲的万花园。”那天,薛范先生还介绍了一首新的俄罗斯歌曲,是描写卫国战争时期战斗生活的,全新的曲调,全新的角度,加上他全新的理解,让台上台下都沉醉在歌声中。
第二次见到薛范先生是两个月之后,他来北京参加基辅餐厅为他举行的一次新书发布会,其间,他专门来了一趟中国现代文学馆,带来了他翻译俄罗斯歌曲的手稿和出版的多部歌曲集,赠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看得出,文学馆也是他多年向往的艺术殿堂,我陪他参观了展览,他在那个三米多高、有着五千多个现当代作家亲笔签名的景德镇青花大瓷瓶上找到了自己的签名,我给他在门厅的大壁画前留了影,拿出本子请他题句话,他想了一下,写下:“文学是人类的良知 薛范 二0一0年八月廿日”。短短一个多小时,薛范先生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愿,我们相约在上海见面。
今天已是第三次与薛范先生见面。来前,我认真地做了功课,看了许多有关他的文章,并拉了一份详细的采访提纲。首先谈到的话题自然是他翻译的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曲自从问世以来的半个世纪,一直盛传不衰,成为拥有世界声誉的一首经典作品。薛范先生说它是“世界音乐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是俄苏歌曲的骄傲”。1957年,薛范在中国翻译发表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达到了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
闪回:《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苏联著名作曲家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与著名诗人马都索夫斯基合作,为1956年举行的全国运动会摄制的纪录片《在运动大会的日子》所写的四首插曲之一。当时并未被电影厂的音乐权威看好,但第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这首抒情歌曲却在参赛中引起了轰动,夺得了金奖! 大会闭幕,各国青年唱着“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告别莫斯科,回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这首歌曲也在世界上不胫而走。这一年7月,薛范从《苏维埃文化报》上刊登的联欢节获奖歌曲名单上看到这首歌曲。他手头正好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原谱,一试唱,就被深深打动了。深邃的意境、优美的旋律,把他带到了遥远神秘的莫斯科郊外,带到了那个有着厚重文化艺术积淀的国家。薛范决定立即着手翻译,尽快把它介绍给大家。可是真正干起来并没有那么顺手,整整工作了两个夜晚,笔下译出的歌词也没达到令自己满意的意境和感觉。
晚上,薛范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小剧场”听歌剧,换换脑子。歌剧散场了,薛范摇着手摇车顺着淮海西路匆匆往回走,天刚下过一场小雨,路边的法国梧桐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水珠,湿漉漉的路面洒满金色的碎片,突然,一阵悦耳的钢琴声从弥漫着清新湿润空气的夜空中飘然而至,薛范一下就听出是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他不由得把车轻轻地停在了路边,倾心聆听起来。多么熟悉的旋律啊,宁静中交融着柔美、伤感、冲动和渴望,让他想起了少年时代的甜酸苦辣。不知为什么,他固执地认为弹奏者一定是位美丽的妙龄少女。夜深了,悠扬舒缓的琴音,甜蜜的意蕴,像一只神秘的手牵着他的思绪在遐想和幻想中遨游。薛范被陶醉了,他闭上眼睛,仿佛走进弹琴少女和大师肖邦的心中,聆听他们的倾诉。不知过了多久,琴声飘走了,夜又恢复了宁静。薛范到家已是凌晨一点,他丝毫没有睡意,心情还沉浸在那纯净的心灵之声中,坐在桌前,平复下心态,凝望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未完成稿,他忽然来了灵感,内心的情感像喷涌的甘泉,顺着笔端汩汩流出,一个多小时,就把满意的歌词译了出来。
不久,北京的《歌曲》和上海的《广播歌选》同时发表了薛范译配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很快,这首苏联歌曲在全国流传开来。此时离世界青年联欢节闭幕还不到两个月。

据后来的调查,薛范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这首苏联歌曲译成俄文以外文字的人,是中国第一个传唱它的人。还有人统计过,在世界上,用汉语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人远比用俄语唱的人多。这首歌曲早已成为一首中国人自己的歌曲。它已不是一首单纯的爱情歌曲,而是融入了人们对祖国、家乡、亲人、朋友的挚爱和深情,以及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希望,成为代代传世的经典歌曲。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给薛范带来意想不到的荣誉,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94年冬天,中央乐团在北京首演“伏尔加之声”俄苏歌曲音乐会。薛范受邀参加,当他在晚会结束前以歌曲翻译家的身份坐着轮椅登上舞台时,整个音乐厅齐声唱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激动人心的场面让他永生不忘。后来,这成了约定俗成的模式:无论他到哪里参加音乐会、联谊会、大型活动或上荧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是他的背景音乐。每次他和乐友们见面时,台上台下总是同声高唱这首歌曲向他致意。
再讲一段有趣的插曲:1997年,俄红旗歌舞团第三次访华,4月23日在上海演出,薛范向主办方提议:演出谢幕时,他要上台向演员献花致敬,主办方一口答应。歌舞团团长索莫夫上校听到当即说:“怎么能让他来给我们献花?是他在传播和推广我们的歌曲,使俄苏歌曲在中国获得第二次生命。应该是我们向他献花才对。”于是,演出结束谢幕时,薛范被邀上台,歌舞团的指挥家、独唱家、合唱队长、乐队长和舞蹈队长分别在全场观众热烈的鼓掌声中,向薛范献花。
他没有刻意去炒作自己,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成了他最响亮的名片。他给素无交往的刊物寄稿,很快收到编辑的复信,说熟悉他的名字,因为念大学时就唱过他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他第一次去北京拜访《歌曲》编辑部时,一位老编辑大声向同事们说:“喏,这就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译者”,于是大家都围过来,热情地和他握手。
他在机场大厅候机,听见排队的旅客中,有人悄悄地对身边的同伴说:“喏,就是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欢迎会上,一位教授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说道:“您的歌曲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
几个热心的听众把他抬上了北京的八达岭长城,让他也当了一回真正的“好汉”。
在云南的广场音乐会上,主持人热情地致词:“您的每一首歌就是一朵鲜花,您使我们拥有一座春天的花园。”
上海师范大学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从没进过大学校园的他,成了大学教授。“站”在高等学府的殿堂上,用五线谱架起一座座心灵之桥、友谊之桥。
类似的插曲和例子太多了。每当这时,薛范都会感到愉快和欣慰,但从来没有得意和飘然过。因为他清醒地知道:他的名字与这首风靡全球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联结在一起;是因为他数十年的工作有幸通过一首歌曲——获得社会的承认。他说:人们“爱屋及乌”,把本属于原作者的荣誉给了他,这是对他独特工作方式莫大鼓励和最高奖赏。
薛范对我说:翻译家只不过是“二传手”,当然要做一个优秀的“二传手”并不容易。要说他是音乐家,那他就是一个平民音乐家。
他诙谐地说,网上有一首歌这样唱的:你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一个传说。也可以这样来唱我:你不要迷恋薛范,薛范只是一个传说。
我们把话题转到了他的人生选择和毕生从事的音乐事业上。薛范说:他从学生时代就喜欢古典文学、中外戏剧、电影,以及诗词歌赋;他还喜欢历史,特别是南宋的历史,那个时代产生了许多让他钦佩仰止的人物,像岳飞、文天祥、屈原、辛弃疾等等。薛范又说,他崇拜闻一多、徐志摩、曹禺、梅兰芳、斯坦尼斯基的戏剧理论体系,崇拜诗与音乐。他曾经很想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文学评论家,甚至一个无线电工程师,但唯独没有想到后来会走上音乐之路,成为一个歌曲翻译家。命运是一把双刃剑,顺境逆境都可以助你成功,也可以让你失败。
闪回:解放初期,薛范正读高二,当时中苏建交,他有机会大量接触苏联的小说、电影和歌曲。作品中沸腾的生活和燃烧的激情,每每撞击着他年轻的心灵,产生着强烈的共鸣。他也同样怀揣着理想,憧憬着未来。薛范喜欢音乐,生活中离不开收音机,非常喜欢无线电。高三要填报高考志愿了,他想读理工,今后做工程师。班主任对他说,你的身体不适宜读理工,还是去学文科学俄语吧。现在是中苏关系最好时期,但会俄文的人才比较少。你文学功底好,今后会有发展的。薛范想想,觉得老师的话有道理,就报考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俄语专科学校。1952年,18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但当他兴冲冲地摇着手摇车到学校报到时,校方才发现这个考试成绩优秀的新生竟然下肢严重瘫痪,断然拒绝他入学就读。
巨大的打击对年轻的薛范是前所未有的,他除了身体残疾外,其他的一切都不比健康人差,为什么命运如此不公?内心的悲怆,沉重的郁闷,是就此消沉,任由命运的摆布,还是振作起来,初衷不改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也是所有亲人朋友,老师同学最为他担心的时期。薛范真心感激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正是这首他平时最喜欢的《命运》交响曲,拯救并改变了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他。命运在敲门,贝多芬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不能使我完全屈服”。贝多芬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那荡气回肠的音乐,给了薛范信心和鼓励。这首创作于十九世纪初的《命运》,是贝多芬在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创作的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那段时间他不知听了多少遍,每次都会热泪盈眶、热血沸腾。他的心在音乐洗涤中平静下来,眼前仿佛又有了光明和方向。每日,他在家跟着广播自学俄语,也常摇着轮椅到电台去向别人讨教,电台编辑们都熟悉了这个执着的“函授学员”,热情地带着他到电台的各个工作间去参观。
有志者事竟成。1953年薛范试着翻译了苏联歌曲穆拉杰里的《和平战士之歌》,他投给了上海的《广播歌选》,没有想到竟然发表了,并由电台教唱了。这是他翻译发表的第一首苏联歌曲,这一个极大的鼓舞,让他从此一发难收。他把靠自己劳动挣到的第一笔稿费12元统统买了翻译词典。此时20岁的他,还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跟着感觉走的音乐爱好者。
薛范去电台,有时会碰上广播乐团的乐队排练,他便静静地坐在一边看,思绪会出神入化地跟着乐声飘荡。乐队负责人见状对他说:“你不是学俄语吗?给我们翻几首苏联歌曲吧?”人家一邀请他就答应了,过不了多久,他真的为上海广播乐团译配了混声合唱曲杜纳耶夫斯基的《春天进行曲》。之后的几年里,他的译笔生花,在翻译歌曲万花园中不断耕耘、播种、收获,相继译配出版了《苏联歌曲集》等多部大部头作品,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成才之路。
薛范在创作上是勤奋的。当时上海有个中苏友谊馆,常放映苏联电影,举办苏联音乐唱片欣赏会,薛范是那里的常客。每有新的苏联电影上映,他都第一时间把影片插曲译介过来,介绍给歌曲爱好者们。像《忠诚的考验》《伊凡从军记》《忠实的朋友》《青年时代》《心儿在歌唱》等等都是这样走入大家视野的。
说到薛范勤奋执着,还有这样一个让人感动的小故事。
五十年代他翻译苏联歌曲成名后,又开始扩大视野翻译其他国家的歌曲,可是找乐谱成了一大难题,他就到处借录音带,去电影院记录歌曲。为了翻译埃及电影《阿尔及利亚姑娘》中的一首插曲,他在朋友家的阁楼上,几乎把朋友的老式钟声牌录音机听爆了。当时薛范买不起录音机,更没有袖珍录音机,只能靠买票去电影院摸黑记谱,遇到比较复杂的歌曲,甚至要买几次票去看去记。不多的稿费几乎都搁在了电影院里。
薛范说他喜欢戏剧,尤其喜欢话剧,他非常想去看,但很少去剧场看,原因是咱们的剧场大多没有残疾人专用通道,要去看会给很多人添麻烦。他说这话时语气轻松平静,但我听时却感到震撼,在各种场合薛范先生都不希望别人把他当做残疾人对待,但在现实世界和生活面前,他又不得不去面对。
闪回:薛范从小就有着语言的天赋,他喜欢音乐,但自认为直到高中时代才“开窍”。逐渐走向成熟的他痴迷上了唱歌,在音乐中寻找精神寄托。每逢课间,总有一些同学围着他开心地唱歌:解放区歌曲、陕北民歌、苏联歌曲……凡是能找到的,他们都一遍一遍唱,让心情乘着歌声的翅膀飞翔,真是快乐无比。在歌声中,薛范忘记了世间的一切忧愁和烦恼。
但当同学们七嘴八舌地争说最近在外边听到的音乐会时,他沉默了,只能用想象去分享别人的喜悦,同学们从他羡慕的眼神中看出了一切,于是商量着背他去露天广场听“星海之夜音乐会”。这是一次让薛范永世难忘的音乐会,一场让他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的音乐会。他第一次在现场体验到音乐的力量,第一次见到如此气势恢弘的场面:五六百人的合唱队沿舞台向两侧伸展,像张开的双臂拥抱着观众,台口是上百人的交响乐队,让人眼花缭乱。晚会的重头戏是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他至今还清晰记得,当那嘹亮高亢浑厚的男生朗诵“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当夜空下的舞台上喊出黄河船夫的第一声号子,他整个心灵就随着“黄河的波涛”起伏升华,一步一步地奔向艺术的巅峰。整个晚上,薛范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他感激同学们所做的一切,把《黄河》永远珍藏心中,但他此后没有再让同学们背自己去听音乐会。
薛范说:请注视我,别注视我的轮椅。他不想在他的事业和成功中注入世人对他的怜悯,他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无时无刻不向自己的残疾挑战和抗争。
我们交谈的话题自然也少不了“十年浩劫”,我说:那个毁灭文化毁灭艺术的年代您是怎么度过的?
薛范说:那段时间是他和家人最惨的岁月。文革开始后,作为高级职员的父母工资被扣了一半,薛范也没有了稿费收入。为了生活,父母几乎变卖了家里所有的东西,他寄信连张4分钱的邮票都买不起。
薛范没有单位,文革前是靠稿费生活的自由职业者,没有单位抓他去批斗,街道上批判了他一下,就无人过问了。多少个夜晚,薛范熄了灯躺在小阁楼里仰望星空,窗外的月光洒在脸上、身上、床上,一任思绪张开梦幻般的翅膀,寻觅那个远去的夏夜、雨后的梧桐、迷人的夜曲、弹琴的少女、笔下的激情…… 想象中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真是太迷人了。在那个喧嚣荒谬的时代里,这是他内心深处一块无可侵犯的净土,无论什么样的尘嚣都无法玷污占据的圣洁之地。不能翻译苏联歌曲了,他就悄悄地翻译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的插曲。他怕脑子生锈,就一章一章地背诵毛泽东选集,有时也会望着天花板发呆。
最让薛范肝胆欲碎的是“破四旧”时,红卫兵抄走并损毁了他十几年来搜集积累的中外图书、期刊、乐谱、唱片、图册等音乐资料,还有花了大量心血一字一字摘录的笔记卡片、诗词抄本及未完成的译著文稿等。那里边还有他和苏联作曲家协会、苏军红旗歌舞团以及著名作曲家诺维柯夫、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赫连尼柯夫等人往来的书信,他们寄赠的不少乐谱和歌集。这些大多是尚未正式出版的新作品的手抄乐谱和影印谱,都是他的精神财富啊!浩劫过后,发还抄家物资,所有珍贵的东西几乎都荡然无存了,只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作曲家索洛维约夫·谢多伊送他的一本扉页上有作曲家亲笔题签的个人作品选集,奇迹般地回到他的手上,成为中苏文化交流的见证和那场灾难的见证。
在万马齐喑的漫漫长夜里,苏俄歌曲成了“苏修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深受大家喜爱的抒情歌曲也成了黄色禁歌。但也有令他欣慰的事,无数的知识青年,在远离父母亲人家乡故土的广阔天地里,偷偷学会并相互传唱着苏俄歌曲,正是这些充满了感伤、温暖和爱情、希望的歌曲,给予他们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关爱和寄托。
1994年,薛范在北京电视台《梦里情怀》栏目做嘉宾时,一位当年的知青告诉他:那时候《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农村是不敢唱的,因为农民虽然不懂外国歌,但是知道“莫斯科”的,于是他们就改唱“北京郊外的晚上”。
文革中,薛范有一次在街上听见两个少年边走边轻声唱着歌,竟然有好多人驻足看着他们,虽然声音不高,曲调不准,但他一下就听出是他译配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要知道这可是在禁歌的年代啊!他听过多少中外著名歌唱家演唱这首歌,但唯有这一次让他最为动容如此难忘。
文革过后,万物复苏,但真正从事翻译歌曲的人却太少了,外国歌曲翻译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层,翻译者有的老去,有的转行,有的出国,有的荒疏了外语,队伍凋零。薛范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人生的攀登。他怀念五十年代外国歌曲翻译的黄金时期,渴望又一个歌曲翻译的黄金时期的到来。他翻译了世界各国的一些传统民歌,也采用看电影记谱的方式译配了一些公映的外国电影的插曲,还出版了《外国电影歌曲选》和《新编外国名歌120首》等集子。他文革后发表的第一首翻译歌曲的5元钱稿费,依然是用来买了最需要的俄汉词典。

1985年,冰封了25年的中苏关系解冻了。一阵春风吹进歌曲翻译的百花园,特别是那些耳熟能详的苏俄歌曲,更牵起了无数人的怀旧情结。进入九十年代,外国歌曲翻译领域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时期。数十年风风雨雨后,仍在这个艺术领域里不懈耕耘的薛范,也就当之无愧地进入了大家的视线。如果说五十年代是他事业的腾飞时期,那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就是他事业成熟收获的金色时代。歌迷、听众、读者、社会给了他太多的荣誉、爱戴、敬重、关注。这种与歌相伴的厚爱让他感激不尽,同时也有些惶恐。
1994年8月和11月,上海、北京相继举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台俄苏歌曲音乐会。北京,中央乐团合唱团以“伏尔加之声”为题的俄苏歌曲专场音乐会,现场气氛前所未有的热烈,观众们忘了平时的矜持,合着节拍鼓掌,观众、演员的激情热情交相辉映,融为一体。演出谢幕时,薛范出场和观众见面,台上台下同声放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许多观众情不自禁流下了热泪。“伏尔加之声”原定演出3场,结果短短的两个多月里,演了23场。作为保留节目,到1998年底,“伏尔加之声”共演了50场,场场沸腾。那些年里,薛范的个人翻译作品音乐会和俄苏歌曲专场音乐会在全国许多大城市此起彼伏地举办。各地歌迷们自发组织歌友会,欢迎会、联谊会更似雨后春笋,每每让他感动至极,也更加自知。
薛范2岁生病残疾,但是他从来没有靠着别人来生活,他说:凭什么要人来养活我,但是靠翻译歌词是很难自己养活自己的,别说是残疾人,就是个健全的人也很难。
闪回:薛范1934年9月出生于上海,这是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父母在工厂做高级职员,生活无忧。若不是两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以及烧退后悄然降临的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后遗症,他的人生或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残酷的命运把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锁”在了房间的小床和轮椅上。
回首童年往事,薛范的记忆里没有“独立行走”这四个字,有的只是抱着背着搀着扶着,再大些是拐杖、轮椅,在窄小的活动生存空间里,他只能让自己的眼睛、耳朵、声音和想象力跟着其他快乐无忧的孩子们奔跑。尽管父母对这个不幸的孩子给予了更多的关爱呵护,仍无法平复他内心的自卑和孤寂。他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在别的孩子无忧无虑的年龄,他已开始思索自己如何才能自立,不被父母永远养着。
从小学开始,他的学习成绩就一直很好。他知道别的孩子学习不好,还可以靠体力吃饭,而他如果学习不好,就只能永远成为父母亲友的“累赘”。那么多年里,都是家里人背着他去上学。为了克服残疾带来的不便,他强迫自己养成了上学不喝水的习惯,这样就可以尽量不上或者少上厕所,少麻烦别人了,他在艰辛的努力中上完了小学、中学和高中。
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出门乘车乘飞机,开会参加活动,他都尽量少喝水。
薛范曾多次感慨:“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自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自立,对于一个肢体健全的人来说,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何况是对一个下肢严重残疾的人,这需要树立何等的决心,付出何等的努力才能实现啊。
薛范说:现在大家都说社会上许多年轻人是“啃老族”,其实我这几十年一直都是“啃老族”,直到前几年母亲去世,我才没有了依靠。
说到母亲,薛范有些动容。这几十年来,他大多时间是依靠父母的退休工资生活,不管环境如何,母亲始终支持他的事业。母亲是他心中的支柱,他是母亲心中的希望。他们始终相依为命。晚年,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对许多事情都已经淡忘疏远,但她走后儿子怎么生活却始终牵挂在心。她让儿子去买个摔打不碎的塑料碗,实在无路时,摇着轮椅,带着碗还可以乞讨为生。这话让古稀之年的儿子伤心落泪了。母亲的牵挂深深地折磨着他,老人这一生为他付出的太多太多,而他回报的又太少太少。他一生最大遗憾,就是靠母亲养活,而不能养活母亲。母亲走了,去世时,他在北京。听到电话里的噩耗,他没有大悲大恸,为他操劳了一生的最亲的人终于解脱了。对于生死,薛范早已淡定。他希望能为社会和大家留下更多的好歌,在离去时不拖累他人。
五十多年的歌曲译配是一条艰难的创作道路,我问他怎么能够给大家留下那么多经典之作,这其中有什么技巧和奥妙,他笑笑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把话题转到歌词翻译要关注“潜台词”。他说:《红灯记》里李玉和对女儿李铁梅说,不要把表叔的事告诉别人,铁梅说:“我知道”,虽然只有三个字,却包含了太多的潜台词,翻译歌词就要有这种感觉。
他说:技巧可以学会,而艺术感觉是没法传授的,那是一个人的修养、天份和才华的综合体现。
毋庸置疑,他翻译的每一首歌都是他内心世界的充分展现,都倾注了他满腔的情感和心血。
薛范说,他在翻译歌曲时会有所选择,选择那些比较有品位的,又可以流传的。之所以那些古典的东西可以流传于世,是因为他们经受了时间的筛选和大浪淘沙!
数十年来,薛范一直在从事外国歌曲的翻译工作,他除了俄苏歌曲,还翻译了一百多个国家的大量歌曲,总共2000多首。其中俄罗斯歌曲就有800多首,影响最大最出名的也是俄罗斯的歌曲。他是音乐天才,语言奇才,懂俄、英、意、西、法、日等多种语言,而且都是自学的。
闪回:我查阅资料发现他的音乐理念和观念是传统中蕴育着现代,看看下面我列出的他译配的歌曲,你一定也会跟我有同感的:
美国电影《魂断蓝桥》主题歌《忆往日》,日本电影《人证》主题歌《草帽歌》,印度电影《流浪者》主题歌《丽达之歌》,美国电影《音乐之声》中的诸多插曲,《友谊地久天长》等经典的外国歌曲。
他介绍到中国的具有代表性的外国现代歌曲还有:汉城奥运会主题歌《手拉手》,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歌《意大利之夏》,美国流行歌曲《说你说我》,摇滚歌曲《天下一家》等。
还有孩子们熟悉的动画片《变形金刚》的主题歌,《花仙子》《机器猫》中的音乐歌曲等。以及年轻人喜爱的音乐剧《猫》中的《回忆》(《memory》),惠特尼·休斯顿主演的电影《保镖》中的《我会永远爱你》,《人鬼情未了》《月亮河》等。
薛范在外国歌曲翻译,特别是俄苏歌曲翻译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功,为世人瞩目。成为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翻译家和作家。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特别是中俄文化交流的使者。
闪回:
1997年11月10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亲自向薛范授予“友谊勋章”,荣誉证书上这样写着:“鉴于语言文学家薛范对俄中友谊和俄中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功绩”。和薛范同时接受这一殊荣的还有著名的俄文学翻译家、画家高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著名作曲家吴祖强。叶利钦在授勋仪式的简短讲话中,高度评价了他们为中俄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他们为中俄两国传统友谊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1999年10月6日,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罗高寿大使和俄中友协联合召开的庆祝中俄建交五十周年、中俄友协成立五十周年的招待会上。薛范又分别获得了两国政府颁发的“中俄友谊纪念奖章”和“俄中友谊纪念奖章”及荣誉证书。
2007年6月,薛范访问俄罗斯期间,俄罗斯联邦政府授予他“尼·奥斯特罗夫斯基金质奖章”。
2003年,那是薛范从事外国歌曲翻译50周年。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五十年的艰辛坎坷,五十年的耕耘收获都让他无怨无悔,也让他心绪难平。
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命运给了他无数的辛酸苦辣,但社会和歌迷也给了他更多的雨露阳光、厚爱和认可。国内许多重要的乐团合唱团都在酝酿着为他举办专场音乐会。武汉出版社的朋友廖国放先生鼓动他何不编一本50年译配作品精选集?薛范怦然心动了。他决定从自己翻译的2000多首歌曲中,遴选出150首,结果反复筛选,到194首就再也减不下去了。朋友看了稿本说正好,再删任何一首都可惜。精选集编罢,薛范写了一篇长长的感人的后记,他要把这部反映他一生劳绩,凝聚了他一生精力和心血的世界经典名歌精选本,献给爱乐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通过这些不时拨动着我们心弦的作品”,更深地了解他所从事的工作。风雨长途,冷暖自知,人生中那一长串深深浅浅的足迹里,留下更多的是温暖与支持。他对所有给予过他帮助的人都是心存感激的。他写道:“我不能不提起曾搀扶着我、提携着我、推送着我,关心、帮助、鼓励并支持着我的许许多多热心的人们。”后记中他列了一份长长的感谢名单,各个时期,各行各业的都有,但仍然无法把帮助过他的人全都写上。他深深地知道,与歌同行与爱同行的是一支洪流般的队伍,正是他们的厚爱和帮助,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努力实现人生价值的信念。
在后记的最后,薛范写道:“我想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已故的母亲……没有她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母亲是薛范最崇拜最尊敬的人,她不但给了薛范生命,而且是他一生的守护神和精神支柱。他真诚地希望厚爱着他的朋友们也记住这位平凡女性的名字——黄景。
我问他:薛范老师,你在歌曲翻译领域不懈跋涉了近70年,翻译了这么多的外国歌曲,什么是你创作的动力?
他想都没有想就说:我的创作没有什么动力,真的没有,许多记者都这么问过我。
后来他想想又说:要是非要说动力,那就是我太喜欢音乐了,音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早已融入我的生活和生命,我不能想象每天如果没有音乐,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再有,音乐给了我安慰、信心、温暖和力量。每天和音乐对话,我觉得非常充实,幸福。
我们推心置腹地交谈了近两个小时。
薛范知道文学馆可以收藏他的歌本著作,非常高兴,他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一大摞他的歌曲集。我让他一本本地在扉页签上了名字。他又拿出一本厚厚的精装歌曲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薛范50年翻译歌曲精选》,签上名字送我。
告别薛范,走出他那音乐的“天堂”,我耳边久久回响着的依然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悠扬旋律,还有他的一段话:我还有余力去和“命运”搏斗吗?但我还是愿意以贝多芬的精神去走完我生命的最后里程,我常常默念着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波兰的密茨凯维支的《航海者》,它仿佛座右铭,从我年青时代起一直伴随我到今天:
……不,我愿同风暴比一比力量,
把最后的瞬息交付战斗;
我不愿挣扎着踏上沉寂的海岸,
悲哀地计数着身上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