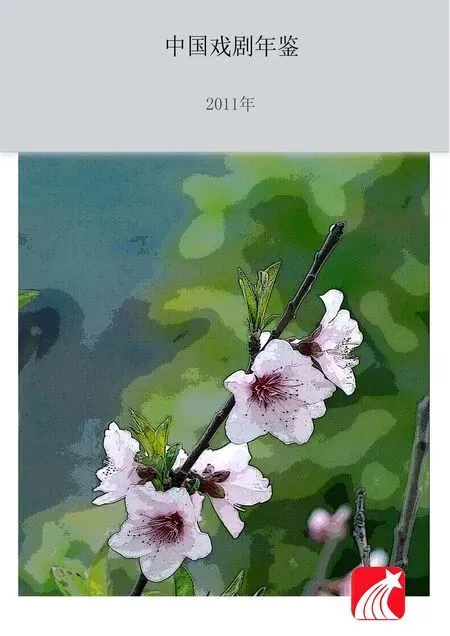那一刻我坐在曹老面前写在曹禺大师百年
刘锦云
那一刻我坐在曹老面前写在曹禺大师百年
刘锦云
1992年9月28日,我上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兼党委书记的第三天。下午,雨后,于是之老师带我去北京医院拜望曹禺院长。医院的高干病房区静悄悄的,我们绕着地上的一片又一片的水洼儿走。水洼儿映着蓝天落霞。我心里有几分紧张。1982年我来剧院任编剧的时候,第一副院长刁光覃主持院务,曹禺院长已不来院理事,因而见老人家的机会不多。此后10年里我写了6个戏。今天接替第一副院长于是之来主持剧院工作。
终于坐在了曹老的面前。
老人在用似审视又似不经意的目光打量着我,笑了,接着叮咛:“人艺的事不大好办哟,到时候你可不要哭哦!”老人家是嘱咐也是告诫我,遇到难事不要哭。人生难逃难事。是啊,曹老年长我近30岁,我在老人面前,分明是个“孩童”,虽然已年过半百。
那一刻,我浮想联翩。
眼前这位像普通老大爷一样的老人,就是伟大的剧作家、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并以其作品标志中国话剧成熟的北京人艺之父曹禺吗?那部在中国戏剧史和世界戏剧史上必将彪炳千秋的《雷雨》,就是出自眼前这个小个儿老头儿之手吗?真的,多少年来,冥冥之中,我总觉得那万钧雷霆、万斛天水的《雷雨》,确乎来自天上!只是戏剧之神差使一个名叫万家宝的23岁的娃娃(用现在的话叫文学青年),把这一鬼斧神工(人工不可思议)的精品(注意:这才是精品)带到了人间。人间这才有了《雷雨》。
记得上中学时,在人大附中大餐厅的舞台上看过某外地剧团演出的《雷雨》,至今脑海里还呈现鲁贵家后窗打开时,鬼火般显现的蘩漪阴鸷的面孔和那丝丝雨线;又在人民大学的露天剧场看某剧团演出的《家》,仍记得扮演觉慧的演员比那鸣凤高出了一头。在北大中文系的课堂上,听与曹老同是清华出身的王瑶先生讲曹禺剧作,王先生对老校友的敬重推崇,溢于言表。(彼时,二位还都是四十多岁的年轻人啊!这会儿,忽有风光不在之感)是听王瑶先生讲课的影响么,也许不是,反正是获得了这样一个印象,而且这印象保留至今,那就是,恕大不敬作如是想:当年以降的小说家,似可缺少某一位,缺少了,小说大厦顶多塌落一角;设若少了《雷雨》作者,中国的话剧大厦便整个倾覆无疑。纯遐想,或瞎想也。
因经济拮据和交通不便之故,一直在西郊读书的我,直到1960年夏天才随北大话剧团第一次来首都剧场看北京人艺的戏(学校花钱)。剧目是《同志,你走错了路!》(配合当时“反修”的,北大话剧团要学演此剧),座位是5排15号副座。每向剧院同事谈此事,他们便笑问:那时,你想到20年后来人艺吗?那哪敢想啊!既没想到大学毕业多年后会在曹老麾下领命,更没想到老爷子在看完《狗儿爷涅槃》于排练厅连排之后,紧拉着我的手说:“感谢你为剧院写了一个好戏,看戏时感到时光在哗哗地流啊!‘涅槃’,戏的名字好……”后因《狗》剧参演某次艺术节受阻,曹老闻言甚是激动,双手做着捧物的动作,大声疾呼:“这是一块玉呀!”
又哪敢想呢——此刻,作为学生和助手,坐在曹老的面前,为曹老执鞭策马……
那一天,我忘记是怎样辞别曹老的了。只记得老人家在护工小白(这个小白伺候了曹老8年,算得“功臣”,原是陕西农民,曹老去世后,剧院给他安排了工作)的陪伴下,把是之老师和我送到了电梯入口处。以后每次即使是我一人去看曹老,临走时,他都是这样送到电梯入口处,拦也拦不住。先是自行送,后是被人搀扶行走送,最后是坐轮椅送。劝他免劳累,不行,一定坚持送。
在以后的几年里,还是常去看望曹老。有时是去汇报工作。我怕老人费神,总是扼要汇报。可是不行,不能亲临一线的院长,总要多听听情况,要我多说说细节。每到这时,我便深深感到,老人家太爱这个剧院了!北京人艺是他42岁时亲手创建的。他视她为亲人,视她为神圣,为她爱所系、神所安,为她毫无保留地献出了全部心魂。他用他崇高的理想引领了她,他用他伟大的剧作哺育了她——他是当之无愧的北京人艺之父!
有时是节日看望,春节时送过几次微薄的生活补贴。说到此处,有点儿令人心酸。曹老去世后,我们把他的书房照原样搬到首都剧场前侧厅陈列。万方看后说:“把我们的家搬这里来了!”那家的家具太陈旧了,不是一般的陈旧。然而眼前的一切,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身外之物”,什么叫真正的“富有”。高耸云端的大山不需要披挂,也无从披挂。若有,也自是历久弥新、生命永垂的天上人间的瑰丽风光!
还有,我多次奉陪市领导去医院看望曹老。有时,我还要提前去“铺垫”,告诉老人家明天将要来的是哪位。第二天老人家就能把姓名和头衔加在一起热情地接待。还有一次,为了让领导更多地了解大师,我们把一本田本相先生写的《曹禺传》给领导送去了。
自知对曹禺大师的了解很肤浅,亦表面,曹老爱女万方回忆父亲的文章,我非常爱读,每读都有很大触动。万方写到曹老当年“改造思想”的痛苦,那苦状如一片一片“切”自己的灵感;写到进入新时期后老人家是多么想写,却又写不出新作品的苦闷,悔恨“耽误”了那么多大好时光;也写到老人家晚年深深的寂寞和自己对自己的“怀疑”。黄昏时节,大师眼望窗外暮色,似发问似自语:“托尔斯泰晚年在想些什么……”无人回答,他也不需要回答。《雷雨》在首都剧场再度演出,大师问女儿万方:“人们还真的爱看这个戏吗?”
万方的一篇文章,“释”了我长达二十多年的一个“疑”,也加深了我对曹老的“理解”,甚至(不恭地说)引起我对老人家的“怜悯”。1982年6月12日是北京人艺建院30周年的日子,剧院安排了一系列庆祝活动。这期间曹禺院长在上海,未能回京出席院庆大会,委托刁光覃副院长在大会上宣读了祝词。对曹禺院长未能回京参加院庆活动的原因,我一直有些不解,近读万方的一篇文章才知道,在那段时间里曹老正处在构思一个戏的胶着中!原来是这样。作为一个同样写戏的后生小子,不禁做这样的猜测:彼时他实在不忍打断自己的文思,深怕打断了,纵逝了,再也寻不回来!这可能是他写戏生涯的最后一搏!若是这样,他该是面临多大的心理矛盾,忍受着多么巨大的熬煎!这是他亲手创建的剧院30岁生日呀!叫人心碎的是,这个戏最终还是没有写出来!23岁就写出《雷雨》的神童、大师呀!天下的写戏人愿为你一哭——而且是放声嚎啕!
1996年12月13日凌晨4时余,电话打来,告我:曹老仙逝。
我赶到医院。曹老还安卧在原来的病房内。适遇一直住在隔壁病房的赵朴初先生自曹老房中出来,想是来与老友最后告别。我守在曹老身旁。屋中再无旁人。我伏下身来,凝视曹老宛如安睡的面容,觉得亲切又异样。我禁不住用右手轻轻地抚摸老人尚未冷却的前额,直至头顶那稀疏的灰白的头发……
作为写戏人,和曹禺同时代,我们是幸运的。后辈会羡慕我们。就像我们羡慕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同时代的执笔人一样。
曹禺百年。
不朽《雷雨》77年。
此时,定会有大量文字开列累累硕果。各种获奖剧目及项目算下来亦会数以千计。这无疑是必要的,应该的,乐观的文字鼓舞士气。
面对大师审视、希冀的目光,我们焉能报喜不报忧,何况状况甚堪忧。而且我又记起早年刚刚步人社会时,一位长者对我说过的话:年轻人,记住,成绩即使不去说它,永远也跑不了;问题要时时想着。
不是吗,时下一个“奖”字,把偌大剧坛搅得天翻地覆。评奖是领导方略,应该;然而戏剧毕竟不是为“奖”而生。
尊敬的曹老,您的皇皇大著好像没得过啥奖吧?哦,得过,还是剧院的晚生小子们给您发的呢,1993年您获得了您的北京人艺给您颁发的《王昭君》演出“百场奖”,奖金1万元。
还有,时下某些做戏之人,往往是为了(政绩的)“绩”,或为了(利益的)“利”,恰恰丢了(艺术的)“艺”!
对此,我醍醐灌顶般想起您在1985年写下的评价奥尼尔的那段经典之语:“奥尼尔一生反对商业性(对这个“商业性”不妨理解得宽泛些——引者注)戏剧。他严肃地致力于戏剧的探索与创造……有人说他是悲观的,有人说他有神秘色彩。我以为他确实是一个正视人生的勇士,一个正直、有理想的大艺术家。”
曹老,在您面前,我是“童言无忌”的。不再用我的饶舌打扰您在天堂的宁静。只是想禀告您,为剧院,为话剧,我不曾哭,却也容不得笑,来路正长,吾辈将行行重行行……
请允许我再一次重复剧评家童道明先生的话:向曹禺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