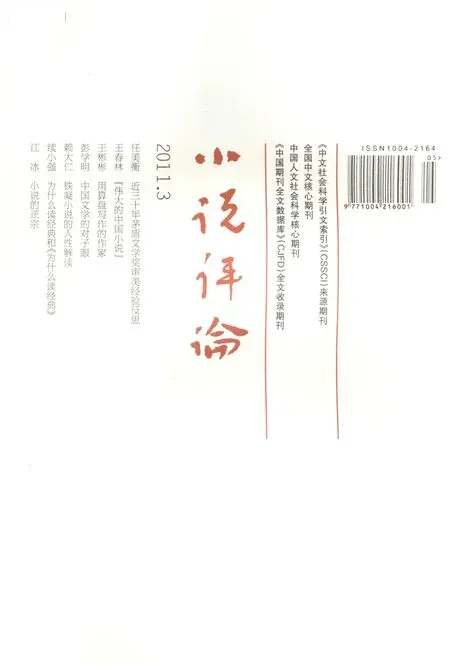《古炉》的视角和超越
韩蕊
《古炉》的视角和超越
韩蕊
贾平凹新作《古炉》的问世,使已经淡出读者视野多年的文革题材小说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相较于以前伤痕及反思文学的控诉与揭露,《古炉》寓言式的写作更多地透露出作家本人对于文革、人生及人性的理性思考。文本以一个倍受歧视儿童的纯白内心去关注整个古炉村所发生的文革,近乎童话般的世界让读者第一次从人性角度对当年文革的发生重新审视。像古炉这样一个偏远山村为什么同样也会遭受文革的灾难?原本和平共处的邻里乡亲转眼间怎么反目成仇甚至要你死我活?是什么使人们变得如此冷漠残忍?文革似的运动以后还会发生吗?……这一系列问号不仅摄取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也构成了《古炉》写作上独有的哲理化特色,显示出作家独到的人文关怀。正是在这种哲理性视角关照下,小说通过对底层人生的叙写及立体杂糅人物的塑造,形成对文革一种别样的日常哲理叙事,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文革小说的题材,对此类小说创作的整体推进亦厥功至伟,确值一议。
文革是文学创作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1980年代最初书写文革题材的“伤痕文学”揭露文革给人们带来的伤害,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干部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悲剧性遭遇。其代表作如卢新华《伤痕》,“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并“呼吁疗治创伤”①,随后,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铺花的歧路》、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系列作品涉及题材虽丰,但大都以朴实甚至有失单薄直白的形式,晾晒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创伤,释放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强烈情感,具体表现为对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与批判意识,伤感、失落、苦闷和迷惘的情绪弥漫于作品之中。
相较于“伤痕文学”浓重的感伤情绪,其后的“反思文学”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1990年代以后,文学处于无名时代,文革题材小说的创作虽不绝如缕,但基本延续反思文学的方法,如余华《活着》重点在于揭示老百姓在灾难面前的承受与隐忍,《马桥词典》《玫瑰门》《血色黄昏》等都是将文革作为展开故事或描摹人物的时代背景出现,对于文革本身的思考则因为作家的回避态度而基本消散了。
《古炉》的问世,又使文革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相较于以往文革小说不同的是,作者第一次从人性的深处追索挖掘文革的起因,在情节叙事背后,一条理性思考且带有某种预言性的线索隐约可见,常会使读者对照联想当下的现实。文本中,文革已经不仅仅是当事人的某种回忆叙事,而是渗透着作家以当下观念对这段沉重历史的理性思考,我们将这一与众不同的视点称之为“哲理化”。再次回望那一段蹉跎岁月,再次看到人们惨痛的付出,文本的哲理化视角更带给我们深深的思索,我们应珍视书中发生的往事,因为这不仅仅是作家一个人的记忆,更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整体记忆。
一、追问人性本源,直击底层人生
开篇的古炉村还是一派宁静气象。人们遵照既有秩序生活、劳动、休息,虽然每个人心中的幸福指数并不太高,彼此间也存在一些矛盾冲突,但没有外来干涉的话,基本上很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平静生活下去。然而该发生的都按照它既定的方式发生了,从霸槽抢军帽开始,古炉村与文革发生了联系,下来的成立榔头队、贴大字报、打砸抢、成立红大刀队、两派武斗、枪毙武斗指挥者都“水到渠成”地相继发生。“如果一件事的因已经开始,它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一个果,被特定的文化或文明局限及牵制的整个过程,这可以称之为命运。”②事情的出现一定有它内在外在的原因,古炉村怎么就有了文革的命运?
古语云:不患贫,患不均。特别是这种不均是通过不正当手段造成的,表面的平静中就会潜伏危机,日积月累的高压到了临界点总会爆发。古炉村里早就存在不公正现象,因为地偏人贫,村民们年年是要等上级发救济粮的,而在大部分人家吃酸菜麸皮喝稀糊汤时,支书朱大柜家在晒点心、吃荷包蛋,特别是在被造反派打倒并关押后,老婆每天要送一罐鸡肉。在位时,支书以权谋私的事情时有发生,为自己拉关系将公有财产送给上级,导致出窑的瓷货数与卖出的数目严重不符;为给儿子结婚,自己用仅仅300元买下队里的公房等等。这些以往不为或少为人知的现象一旦公之于众,可以想见的村民的义愤填膺,霸槽也正是利用群众的这种极端的情绪达到了推翻支书自己取而代之的目的。
贫富不均还只是不公正的一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便是人不能通过正当途径展现其才华,获得其应有的肯定,“不平则鸣”,他的力量就会通过其他渠道以非正常方式表达。霸槽可谓是古炉村最不安定的因素,他不满于现状,既不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私自在大路上补轮胎又不按规定给队里交钱,在阅读之初我们就明显感觉到霸槽总是跃跃欲试地想改变什么,一旦机会到来,他一定是风头浪尖上的人物。果然,从强抢黄生生军帽开始,历经组织榔头队、打砸村里四旧、抢占神庙古窑,结识马部长,他逐渐地达到了自己人生的巅峰时期。问题是当反抗者获得想要的一切,特别是对被反抗者取而代之以后会怎样呢?
“人人爱当官,当官都一样,”中国的官本位思想早已积淀为集体无意识,掌权之后新一轮的恶性循环从头开始,反抗者会成为新的不公正者或曰压迫者。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正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可以和《古炉》形成映证。昔日家里被称为“穷坑”的平头农民旷开田,在娶了暖暖后日子富了,又在妻子的支持下当选了村主任,特别是实景演出中“楚王赀”的扮演使他在心理上完全将自己等同于“楚王”,直至最后成为楚王庄的土皇上。开田不再是过去那个朴实的农民,完全是一个自私贪婪暴虐的压迫者。人性的变化可谓惊心,只是因为全书的主人公是暖暖,开田虽然刻画最成功却是作为陪衬人物出现,这个充满张力的形象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与开田相比,霸槽更具主动性与进攻性,一旦掌权,就利用人们彼此间自私相斗的心理,发起了第一次的打砸抢。当年与杏开的婚事一直不被杏开父亲老队长满盆同意,就是因为他的“不务正业”,霸槽对此事是怀恨在心的,今非昔比后有了一定地位,不仅仅是完成过去的心愿,个人私欲的极度膨胀使他也变得和从前不一样了,抛弃爱他的还怀着他的孩子的杏开,另攀高枝与城里来的女造反部长相好。而狗尿苔之所以在一开始喜欢和霸槽在一起,一是因为自己喜欢杏开而他和杏开相好,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霸槽不因为他的怯弱欺负他,但后来霸槽也变了,甚至要利用狗尿苔让他做自己的“特务”,丝毫没有想到一旦被对方发现会给孩子带来的危险。
自动盖章环节结束以后进入自动下料,机构上抬至中间上方位置,然后继续移动至右侧上方位置,机构下放放纸后回到上料初始位置。子程序如图6。
人性中的自私与贪欲是这场运动兴起并迅速扩大的另一个重压原因。霸槽振臂一呼,为什么能迅速组建起榔头队?看一下其组成人员,秃子金、水皮大部分是平日被轻视的、受压抑的不得志之人,物以类聚,他们大都是想借此机会改变自己的处境与地位;而对立派红大刀队的天布、磨子、灶火等都是村里以前的干部,他们维护老村委会,最终目的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霸槽开始的造反似乎在替民说话,但实际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左右着古炉村的一切。其他跟着跑的人则多是出于自保的缘故——作为群居的社会人,村民觉得自己总得有个归属,不孤立才有安全感。狗尿苔之所以委屈而自卑,就是因为哪一派都不接纳他,孤独是对一个人尤其是孩子的最大惩罚。
对比伤痕与反思文学多将文革悲剧归咎于上层政治或社会时代等外来因素,《古炉》在探究文革起因时,直指人心,因为在事物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人性中的功利、自私与贪婪造成了村民们的争强斗胜,而未能完全摆脱的动物嗜暴性又使这场争斗愈演愈烈,人们打着革命的旗号做的是维护自己利益的事情。当彼此的私利发生冲突时,更激起加倍的贪欲,仇恨与报复最终演化为肉体的搏斗:“古炉村的人们在文革中有他们的小仇小恨,有他们的小利小益,有他们的小幻小想,各人在水里扑腾,却会使水波动,而波动大了,浪头就起,如同过浮桥,谁也并不故意要摆,可人人都在惊慌地走,桥就摆起来,摆得厉害了肯定要翻覆。这浮桥便好似古炉村了。”③《古炉》村的运动,外来的政治因素只是导火索而已,悲剧的酿成完全来自村民们日积月累的人祸,来自劣根的人性,而这些或卑劣或残忍的性格特征,文本则通过对各色人物的准确刻画得以真切体现。
二、小人物大命运,杂糅中呈动态立体
《古炉》虽然处外孕育着哲理化的思索,但作者毕竟不是思想家,他的所有思考必须以文学的方式来传达,其意切情深是通过人物的丰富性表现出来的,这沿袭了作者一以贯之的小说风格。
《古炉》人物形象承继作家《秦腔》、《高兴》等作品的底层写作特点,在真实性上还原生活本真,避免伤痕及反思文学中由道德完备意志坚定的老干部、处心积虑品德败坏的得志小人、心地善良同情弱者的人民群众组成的“铁三角”式的程式化写作,人物来自生活原型,作家在塑造丰满立体艺术形象的同时,揭示出人性的复杂与多变。
古炉村文革的始作俑者霸槽的性格张扬彪悍,在造反之初他还有正义的一面,揭发支书的贪污、给村里得了瘟病的猪打针等等,而最后的砸窑、武斗就已经走上穷凶极恶的歧途了。上文重点从官本位思想对其行为的前后变化作了分析,实际上,从人性的角度同样可以切入:反抗者在自身弱小时往往是谨慎的,容易彰显其人性中高尚的一面;当获得想要的一切,特别是对被反抗者取而代之以后,人物的性格发生了变化,或曰卑劣性一面得以充分的扩张。人的欲望没有穷尽,当狗尿苔强调杏开是队长的女儿时,他说“要的就是队长的女儿。”可见他的爱情是掺杂功利的,当更有来头的马部长出现时,他立刻弃旧从新了。
天布开始似乎很像正面角色,但和秃子金老婆半香的相好就显得苟且,在与秃子金的冲突中又很是以强欺弱,直接导致了后者加入榔头队的反抗行为。所以无论是榔头队还是红大刀队,从霸槽到天布,从秃子金到灶火,很难以道德标准来衡量谁是好人坏人,就是在传统文革小说中往往被塑造为正面形象的被打倒的老干部支书朱大柜,平日在村民眼中德高望重,在任时也有贪污和行贿行为,在给天布和秃子金断私通案时,又官官相护地偏袒天布。
每个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但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后天的努力达到平等甚或超越原来的次序是至关重要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也早已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发展的需求,如果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被定位的低贱人生,这个人物无疑是悲剧的,也是不合理的。在《古炉》“后记”中,作家表达在写作的时候,常有一种幻觉:“狗尿苔会不会就是我呢?我喜欢着这个人物,他实在是太丑陋、太精怪、太委屈,他前无来处,后无落脚,如星外之客”④,狗尿苔既是作家的创作,带着很多他自己主观意念的痕迹,又是那样地真实和贴近生活,而恰恰是狗尿苔的存在,让读者感受到小说的一缕暖意,看到古炉村的一线希望,也许霸槽儿子在狗尿苔的带动与影响下,会涤荡人性中恶的部分,以善良来统一本心。
与狗尿苔一样有着善良美德的,古炉村就还剩善人、蚕婆、杏开了,他们却都是村里的弱者。作为古炉村道德象征的善人,总是用自己的思想为别人排忧解难,多少人的病被他“说”好了,最终自己烧死在屋中。善不在了,还有多少人在继续得病却无治呢?蚕婆战战兢兢而又是坚强地活着,也是帮助一切她所能帮助的人,从不落井下石,就是这样的一个具有地母象征的人物,最后却全然地聋了,完全地沉浸在自己剪纸的艺术世界里,或许是她实在不愿再听见这人世间一切的争斗与烦扰。蚕婆是狗尿苔唯一的保护神,也是古炉村善良的最后守护者,在一切都卷入文革而混乱迷失的时候,毕竟还有未失本心的真正人在。
三、哲理来源生活,深刻寓于日常
任何小说作品可以也必须写出作家的思考,而且思考的独特性是衡量一部作品的重要标准,但关键的是这种思考是必须不露痕迹地融于人物与情节之中。对此《古炉》作者有自己的看法,
以我狭隘的认识吧,长篇小说就是写生活,写生活的经验,如果写出让读者读时不觉得它是小说了,而相信真有那么一个村子,有一群人在那个村子里过着封闭的庸俗的柴米油盐和悲欢离合的日子,发生着就是那个村子发生的故事,等他们有这种认同了,甚至还觉得这样的村子和村子里的人太朴素和简单,太平常了,这样也称之为小说,那他们自己也可以写了,这就是我最满意的成功。⑤
后记中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作家的经验之谈,只有先相信了书中的生活,才会认可由这生活而来思考与结论。考察贾平凹的创作轨迹,再看他的《四十大话》、《五十大话》,我们会真切地触摸到作家日益的洞明澄澈与慈悲宽厚,但这种大觉大悟也是要通过人物和情节来传达的。作家首先必须是会讲故事的,而贾氏小说历来是以人物和细节著称的,《秦腔》和《高兴》已经显示出作家书写日常生活炉火纯青、返璞归真的艺术技巧。
从生活琐事中去发现和书写哲理是《古炉》创作的显著特征。最容易的其实是最难的,与《秦腔》一样,《古炉》看起来也是鸡零狗碎的日子,只是有了“文革”的主题,有了武斗出了人命才显得血腥而揪心。村民们的吃喝拉撒、家长里短、下田劳动及后来的政治活动均是表现内容,而正是在这些平常的生活图景中,注入了作家的理性思考。譬如丢钥匙事件就写得极为有趣,虽然带有夸张性,但却合情合理。如果说狗尿苔最早偷水皮家钥匙是为报复后者的冤枉自己,所有人家都去用邻居的钥匙开自家的门并且一借不还而导致全村丢钥匙,这就是人本性中损人利己的表现了。另如文本结尾处安排了一个奇怪的情节,狗尿苔和牛铃打赌吃屎,情节看似荒诞,但因为有了疯子老顺摆炒面屎的伏笔,就显得顺理成章,狗尿苔与牛铃的吃屎也就寓意深刻,可谓是对全书的总结:榔头队与红大刀队的争斗谁也没得到任何好处,两败俱伤正像这两个孩子做的孩子事,成人不仅仅是年龄的划分,心智的成熟才是衡量的标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成人呢?
哲理生活化的另一个独到表现是善人的说病,他从自身经历出发的悟道,朴素中透露出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光辉。他是医治人们心病的心理学专家,更成为了古炉村道德的代表,走街串户的善人联系起几乎所有的村民,他们生活中的婆媳关系、邻里相处、生男育女、清心减欲等等无不是他最关心的,几乎磨破嘴皮的耐心劝说是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善人的出现既符合古炉村地处偏远医疗落后的现实,更是小说中理想人格的一种象征,而他的最终自焚则是善的毁灭,古炉村真的陷入了灭顶之灾。作家的思想正是这样借助于人物之口得以巧妙而自然地传达,这也是贾氏写作的一贯风格。
《古炉》能够将哲理融于生活,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自己就是这段生活的亲历者。海明威认为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不愉快的童年,⑥这里的童年应扩大为早年生活。不愉快的甚至是不正常的少年经历使作家较同龄人早熟,养成了性格中内省的倾向,这种倾向使他们能够从自身的经历中提取更多的东西,进而拥有一份独到的人生经验,加之各人的聪灵早慧,这有限的阅历便转化为深度的人性体验,并以此为依托,形成其稳定的人生观和审视人生的独特视角。贾平凹正是如此,少年时期的他极少说话,但内心世界却丰富多彩,而恰恰是这种向内心的回归,发展了他细腻的观察力和敏锐的感受力。拿《我是农民》和《古炉》对照着看,就会明白小说写得风声水起而又自然天成的原因,明白其中很多的人物和事件都是源出有自,并且这些人与事给当时处于少年期的作家留下的印象是铭心刻骨和不可磨灭的,这里沉淀的不仅仅是历史,更有个体人对于具体历史时段的那份独特的情感。这一切构成贾平凹式的笔式文法,无人能够仿效,而正是有了这些日常生活的萦绕与渗透,作家的那些哲理性的写作才不是条条框框,才与老百姓的日子显得水乳交融,也才成就了《古炉》的深刻与日常。
韩蕊 陕西师范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注释
①冯牧:对文学创作的一个回顾和展望——兼谈革命作家的庄严职责,《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上卷)》,李庚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第154页。
②③④⑤贾平凹:《古炉·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604页,第606页。
⑥乔治·曾林浦敦:海明威访问记,海明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11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