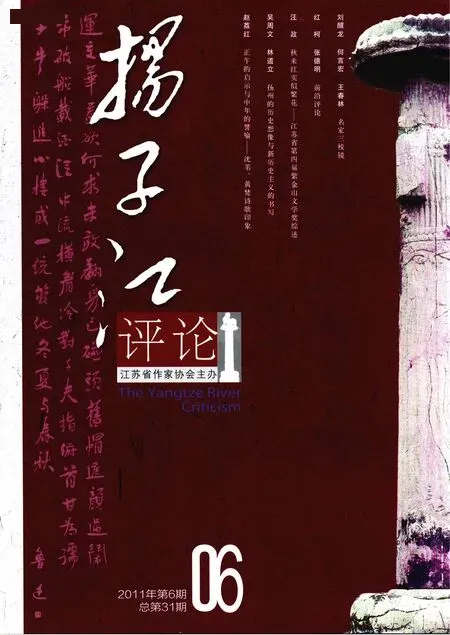论新世纪小说“西藏叙事”的几个问题
雷 鸣
“西藏”①远离中原大地与中心都市地带,地理上属于边远之地,但文学上却成为了“要塞中心”。在当代文学的不同时段,“西藏题材”热总是一波接续一波,从未表现出衰萎之趋。可以说,西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想象和诗性建构空间,宛若磁石与铁,持久地吸引着汉、藏族作家或其他民族作家的想象和思考,不断地激起他们书写的欲望。就以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为例,西藏叙事是集约式的“井喷”,如马丽华的《如意高地》,范稳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阿来的《空山》、《格萨尔王》,宁肯的《天·藏》,杨志军的《藏獒》三部曲、《伏藏》、《敲响人头鼓》,何马的《藏地密码》,安妮宝贝的《莲花》,严歌苓的小说《爱犬颗勒》,曾哲的《美丽日斑》,乔萨的《雪域情殇》,党益民的《一路格桑花》,七堇年的长篇小说《大地之灯》……综观这些文本,尽管有些小说已臻很高的艺术水准,但它们的西藏叙事呈现出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奇观化依赖:日常生活谱系的遮蔽
西藏有着茕茕孑立的地理位置,雪域高原的旖旎风光,神秘蛮荒的宗教民俗,相对于中原与沿海地区而言,其灼人的魅力直接表现为她所流溢出来独有的“异域情调”(Exoticsim)。法国诗人谢阁兰认为,异域情调不是一般的旅行者或庸俗的观察家们看到的万花筒式的景象,而是一个强大的个体在面对客体时感受到的距离,和体验到的新鲜生动的冲击。它是在观察主体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不可磨灭的文化差异的同时,还能体验这种差异。②正是因为异域情调体现的是对文化差异的关注,具有神秘色彩的西藏便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场”,吸引了许多人在描述西藏时,往往依托各自不同的源出文化,去恣肆铺陈其中的差异因素,从而向描述的接受者提供有效的异域暗示。正是基于此,很多作家“西藏书写”的挖掘取向与读者的阅读期待,差不多都框定在一个双方默契的定势和共识之中了——对西藏进行奇观化展示,专注于炫耀“异域风情”。于是飞扬飘动的经幡,虔诚地匍匐前行的朝圣者,哈达、酥油茶、糌粑团、转经轮、唐卡、天葬、藏獒,似乎是西藏的全部。历史的民俗典故,奇特的自然风光,永远是被津津乐道和描述的景观。西藏俨然成了没有人间烟火气,唯有宗教天籁氤氲的神秘圣地。这种西藏书写的奇观化,当年的先锋作家马原、扎西达娃等是先驱。正如学者陈晓明所说的那样:马原“一直是运用了大量的上等的填充物填补他的‘叙述圈套’,诸如天葬、狩猎、偷情、乱伦、麻风、神秘和虚无等等”③。确然,马原借助叙述圈套的迷宫,将西藏的诸多表征符号与奇闻异事,嫁接在一起,将西藏的奇观化发挥得淋漓尽致。
新世纪小说的西藏书写,依然接过了“奇观化”西藏这根接力棒。虽然大多数小说不再设置叙述圈套,但却是穿新鞋走老路,神秘、魔幻仍然是这些作品的最大卖点,对西藏的书写还是以“奇观化”作为小说成功的命门。他们要么以史诗情结,记叙西藏历史风云人物的异类传奇;要么以宗教情绪,把西藏独特地域文化的神秘,演绎到极致。文本中唯独没有当下西藏的日常生活状态,没有真实的充满血肉和肌理的西藏城市和乡土,没有普通藏族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很少去挖掘新世纪的西藏人在社会转型期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变迁,很少去呈现西藏当代社会前行与嬗变的蛩蛩足音。总而言之,它们所呈现的西藏匮缺时代的面容和表情,一如既往地披着神秘、玄奥的外衣,腾云驾雾,高居仙境,而非一个实实在在、切切可触的真实西藏。
就以好评如潮的范稳的作品为例,《水乳大地》被誉为“中国的《百年孤独》”④,这部小说以飞腾的想象力、神奇诡异的文字,写出了滇藏交界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重构了一种本土文化的绚丽与神奇。但是我们发现,作者那样一种无法完全融入于表现对象之中的文化猎奇目光的存在还是相当明显的。作品主要的篇幅和重要关节还是描绘了藏地“奇观化”的生活,其中有着太多的超出日常生活之外的魔幻和空灵的场景,比如死而复生的凯瑟琳,骑着羊皮鼓飞行的敦根桑布喇嘛,滚动的有知觉的头颅,手接响雷的人,颜色变幻的盐田等。这里,我不能不说,写作者在体现一定精神厚度的同时,也在倚靠自己作为文化学者掌握史籍的稀罕与神秘而炫奇斗艳,倚靠宗教生活的怪异场景而取悦读者。在将西藏“魔幻化”、“奇观化”的同时,也遮蔽了西藏一百多年历史变迁中的日常生活本来面目。他的另一部小说《悲悯大地》描写的生活则更显单向度,只是专注对藏族生活一个维度,亦即宗教生活的描述,正如该书封面所写的一样,“这部作品主要讲述的是一个藏人(阿拉西)的成佛史。”小说塑造了一个义无反顾的朝圣求佛的佛界英雄形象。阿拉西只有出家做喇嘛,以磕长头的方式去拉萨朝圣,求得“佛、法、僧”这“佛三宝”,才能斩断家族仇恨纷争的种子和轮回,所以小说重点就讲述了在漫长的转经朝佛路上,阿拉西历经艰辛和灾难,终成正果的故事。文本写了阿拉西大量不同凡人的奇异故事,如刚生出时的哭喊声像寺庙里那些喇嘛们的念经声,能听懂动物的语言等等,同时作品还不时穿插斗法斗术的宗教奇观。小说依然未能摆脱迎合“他者”的好奇心与窥视癖之窠臼。在“藏地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大地雅歌》中,作者希望“写信仰对一场凄美爱情的拯救,以及信仰对人生命运的改变,还想讴歌爱情的守望与坚韧”。然而作为一部描写藏地文化的作品,《大地雅歌》通篇都没能向我们呈示出那种源于藏地本身的鲜活淋漓的异质感和绵密感,依旧凭借对藏地独有修辞习惯的挪用,人为构造出一个符号化的藏地情境来置放故事的发生。作者叙述的扎西嘉措(史蒂文)、央金玛(玛丽亚)与格桑多吉(奥古斯丁)三人间看似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其背后并无明显的藏地文化背景或独特信仰予以支撑,如果我们把故事发生的场景做一个调换,这场缠绵悱恻、风花雪月的爱情剧似乎在世界各地皆可上演。
还有杨志军的《藏獒》三部曲,我以为,其实就是一部藏地“灵兽”的传奇,作者将动物的雄性、神性高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笔下的藏獒,可以说是“欲状其智而近妖”。与藏獒勾连的西藏文化的神秘性悉数展露,而在这块土地上人的生活,仅仅作为“藏獒大侠”行走江湖的舞台布景。尽管有很多论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寓言,即便如此,这种文化寓言,也是通过奇观化的景观完成的,因为“藏獒”在许多人眼里,已然成为了西藏神秘光环的一道弧光和套语符号。《藏獒》三部曲之后的《伏藏》将西藏奇观化,似乎又“更上一层楼”,伏藏、掘藏、仓央嘉措情歌、七度母之门、隐身人血咒殿堂、光透文字……所有你能想到或未想到的西藏神秘符号,都能在他这本书中看到。再加上悬念重峦叠嶂的非常《达·芬奇密码》的故事套路——伏藏与掘藏、逃亡与追杀、历史与现实的回溯与呼应,宗教历史中的黑暗与血腥、仓央嘉措伏藏内容的悬而未知……悬念层层推进,奇观化效果也愈益叠加。何马的《藏地密码》,120万字的超长篇幅,依托的仍然是具有神秘感的西藏文化与西藏的地理。其神秘配方,无不外乎人们认知西藏的习惯性三味药:藏传佛教的历史与传说;藏獒的知识与传说;青藏地理及探险。小说的标题冠有“密码”二字,密码本身就是难解的、神秘的,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除了搭《达·芬奇密码》的“顺风车”营销策略外,还清晰地传达出了增强西藏文化的神秘之感的意图。可以说,何马“奇观化”西藏也是司马昭之心。
有人会说,藏地本身富含着诸多的神秘文化,这本身就是“奇观”,就是西藏的本来面目,如果不表现这些神秘奇观,与写其他地方的题材又有何异?我要回答的是,如果总是以某种单一形态和单一语义的夸张化具象,去传达或建构西藏的一种基本的、原始的、第一和最终的形象,是一种对文化和精神的惊人“省略”,是片面而肤浅的。海德格尔说得好:“自由空闲的好奇操劳于看,却不是为了领会所见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为了进入一种向着所见之事的存在,而仅止为了看。它贪新骛奇,仅止为了从一新奇重新跳到另一新奇上去。这种看之操心不是为了把捉,不是为了有所知地在真相中存在,而只是为了放纵自己于世界。所以好奇的特征恰恰是不逗留于切近的事物。所以,好奇也不寻求闲暇以便有所逗留考察,而是通过不断翻新的东西、通过照面者的变异寻求着不安和激动。”⑤由此,我觉得,一些西藏书写的小说,以一种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的方式,去浓墨重彩渲染西藏神秘的一个侧面,而侵吞和遮蔽西藏的其他维度,实际上就是以海德格尔的“闲言”方式制造事端,进而吸引大众的猎奇心理。
一切文化的深层支撑无不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人类精神的原生态,具有本原意义,正如卢卡奇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对存在的追问必须从日常生活出发,如果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最简单的事实当中去寻找对社会存在进行本体论考察的第一出发点,那就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考察。”⑥因此,要想获得对西藏全整而切实的认识,我们必须经过对西藏日常生活的描绘和分析,从日常生活这条长河中推导出西藏文化的特殊范畴和结构,唯其如此,我们对西藏的认知,才能是一个真实的西藏,一个生活的西藏。尼玛潘多的《紫青稞》则给我们以耳目一新的正面启迪,这部25万字的作品就摒弃了“奇观化”西藏的时髦写法,作者以地处喜马拉雅山脉附近的偏僻村庄——普村为切入点,展示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外部世界的巨大变革给普村带来的冲击,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普村年轻人,怀着或好奇、或向往、或怀疑的心情,以各种方式走出世代居住的大山,来到山外闯世界。曲宗阿妈的几个女儿性格各异,但在走出大山闯世界的热潮中,她们有的自觉、有的被迫来到山外的世界,她们秉承了普村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以普村人的韧性,在“陌生”的城市找寻自己的位置。小说触摸着当下西藏乡村生活的真实与质感:用青稞换录像、糌粑清茶、春耕仪式、借来衣服过节、邻里忽远忽近的人情关系、茶馆里生活场景、藏族年轻人那份投入生活改变命运的期盼……照相式记录,老老实实地描绘出了当下西藏农村的日常状态,直接地、毫不借助神秘光环,还原了一个与时代发生紧密冲撞的真实的西藏。作者也展示了很多西藏的地域文化和风俗,但非抽象处理,而是被放回到了生活的原生态,按生活自身的逻辑运动,让生活本身叙述、解释这些地域文化风俗在当下西藏乡土社会留存的印记。总之,用作者的话说:“在很多媒介中,西藏已经符号化了,或是神秘的,或是艰险的。我想做的就是剥去西藏的神秘与玄奥的外衣,以普通藏族人的真实生活展现跨越民族界限的、人类共通的真实情感。”⑦由斯而言,笔者不得不说,只可惜这样切入生活、贴近藏族百姓,充满时代气息和人文关怀的“西藏书写”的作品太少了,过多的是主观渲染和盲目轻浮的抒情,要么追求猎奇和神秘,要么卡通化式地表现民俗民情。
二、诗意化洁癖:理性批判精神的缺失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持续变革,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其相伴而生的价值观念的现实推动,中国进入消费社会或准消费社会。国人的生活质量不断跃升,但都市激烈的职场竞争及生活物化的快节奏带来的如精神空虚、价值颠覆、人类生存意义虚无等诸多弊端亦随之产生。可以说,在中国大地上,尤其是在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躲避崇高、英雄隐退、道德沦丧等共同构成了一个精神贬值的文化景观。而与之不同的是,西藏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相比于内地风行的那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它所呈现出来的精神景观则要纯净、明朗许多,加之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许多主动放弃可能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离开故乡父母、儿女亲人来到西藏工作的内地人,他们扎根边疆、建设西藏的甘于清贫、耐于寂寞的无私奉献精神,在这个理想失落、崇高隐退的时代情境下,显出了难能可贵的崇高精神“飞地”效应。事实上,这种一直延续至今的“老西藏精神”也感动了几代人。
麦克卢汉在《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一书中,曾深刻地论述美国西部片中的边疆生活,为何令美国人着迷:“机械化常规把我们搞得污秽满身,经济和家庭的复杂变革把我们搞得稀里糊涂,这个幻想中的西部给我们提供了骑士的冲劲,提供了生机勃勃、没有顾忌的个人主义。昔日的敌人是狡诈的封建贵族;新兴的敌人是聪明而独立的机器。对于被宏大的工业搞得晕头转向的人而言,幻想中的西部恢复了人性的尺度。”⑧从麦氏的论述中,可以明白一点,美国的西部边疆,为当时处于工业社会的美国人提供了一种深深的怀旧情绪,一种精神补偿意义上的心理治疗。与此类似,如同当时处于工业社会的美国人对西部边疆的向往一样,此时的西藏,恰如上述与内地不同的特点,正好为在汉族都市中的人群提供了一种“恢复人性的尺度”的心理治疗,成为一个心灵舒缓净化的有效通道。于是,处于内地都市地带的人们,在初涉西藏或粗走西藏时,随着感情的浸润其中而产生震惊体验,不由地借助西藏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把西藏看做一个可以慰藉心灵创伤的圣地,是比喧嚣纷乱物欲高蹈相对宁静的纯洁之地,正如作家蓝讯所说的一样:“在内地,理想逐渐被人抛弃;西藏却成了理想主义者的漫游之地。我想到了一条被搅浑了水的河,鱼们都游到河边,游向有野草和清水的地方,张大嘴巴呼吸着没有被搅浑的河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西藏被人们誉为中国的最后一片净土。”⑨
正是基于心灵救赎的需要,许多作家笔下的西藏写作,从不去建构一种认知西藏的典型标本和权威体系,而总是把西藏想象成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一种没有任何丑陋、污秽与负面的完美空间,一个净化、纯化、非人间化的诗意栖居地,对西藏是一种单纯的理想热爱,有关西藏的传说甚至恶劣的气候、苦难的人生都是那么具有魅惑力和吸引力。宁肯的《天·藏》虽然内容丰盈,但对宁肯的叙述来说,西藏也只是一种诗、哲学、宗教的象征力量,是脱离了一切世俗世界轨道的终极之地,每个人在这里的存在,更多地呈现为非世俗、非时间的一面。小说中的王摩诘,为了追寻生活的意义,作为志愿者来到西藏,成为了拉萨附近一所中学的教员。在西藏,他存在的方式,就是思考,静思成为每天的生活内容。他认为西藏就是一个让人静思的地方,别人问他“……每天都干什么?”,他回答:“没事,就是待着。”另一个人物马丁格,来自法国,一次假期的喜马拉雅山之行,改变了他的价值取向,使他转向了东方的佛教,他更是一个安详、平静、雕塑般的沉思者,时常与父亲进行着宗教与哲学的对话。很显然,这部小说所要表现的西藏并非一个实体的西藏,而只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一种宗教、哲学的终极形式,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西藏给人的感觉,更多时候像音乐一样,是抽象的,诉诸感觉的,非叙事的。两者概括起来可称为‘存在与音乐’。这对我是两个关键性的东西,它们涉及我对西藏总体概括。”⑩但我不得不指出,把西藏叙述为一种只是形而上的存在,西藏反而显得很贫瘠、苍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西藏,亦失去了形而上思索的现实支撑,而成为了一种哲学理论话语的推演。安妮宝贝的《莲花》中的西藏墨脱,在作者笔下被建构成了指引人从黑暗走向光亮的心灵圣地,在这里,人与自然诗意栖居,人们精神相契相融,充满着彼岸性的光辉。作品中写了三个人物,一个是事业如日中天,但内心却不断挣扎的男子善生;一个身患精神疾病的女子庆昭;还有一个命途多舛的女子苏内河。为了摆脱内心的创伤,去寻找生命的本相,三人殊途同归地踏上了墨脱之旅,远离都市的喧嚣,在葱山绿水茂林蓝天下,他们获得新的生命感悟。马丽华的《如意高地》则把笔伸向西藏历史深处,挖掘延衍出一段冰清玉洁的爱情绝唱,作品叙述了清末民初由川进藏的军队统领陈渠珍一生与一位西藏女性的爱情故事。在陈渠珍进藏之后不久,新娶了藏族妻子西原。此后,无论陈渠珍面临难关和遭遇危难,她都会及时现身排忧解难。一直忙于政务和军务的陈渠珍没有认真体察到这种以“战友”方式表现出来的挚情与深爱,而当他走出战乱的藏区,远离危难,西原突然得了绝症之后,他才醒悟过来,痛惜起来,但一切为时已晚。他只能万分愧疚地感叹“我欠了你一生的幸福”,并时时陷入“不知魂归何处”的无尽思念。惟有藏地才能产生这样弥足珍贵的爱情童话,当中心地带的我们把爱情附丽于对宝马香车、豪宅别墅、金钱财富的追逐时,这个至纯至真至情的西原,宛若在欲望功利的滚滚热浪中荡来一阵怡人的清风。在作者看来,雪域高原才是盛产真正爱情的地方。党益民的《一路格桑花》中的西藏,具有着“涅槃”或再生的意味。小说中的都市白领郭红怀疑丈夫有外遇,愤然离婚去了西藏,年轻女记者安宁怀着忐忑要把自己嫁给远在天边的男友……到西藏后,女人们看到了驻藏官兵,这些人的人生如格桑花般绚丽而寂寞——这是一个冰雪般澄澈的世界、一个丝毫没有受到污染的绿色群体,女人们震撼了。
不难看出,这些文本着迷于诗意化、浪漫化“西藏”,表达的重点在于西藏的“超凡脱俗”,在于作家自己曾经从游历西藏中得到的助益于人生的感悟、收获,更多的只是切割传统的西藏文明中能为内地或中心城市输出精神资源的一个侧面,而非为藏民族的未来、西藏的生存、发展、建设等宏大问题去思索。正是由于作家对西藏的诗意化洁癖,他们没有审慎地剖析西藏在时代变革中新旧文化的碰撞,特别是旧文化精神的重重帘幕;没有透析世代生于西藏长于西藏的子民们因受制思想和文化的局限而面对世界的新变化时的艰难蜕变和求索;没有描绘西藏文明中具有传统影响力的封闭意识、小农思想和心态,对于现代文明的种种节制和消解;没有思考与追问西藏在存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因子的同时,如何急迫地选择新文化精神。总而言之,这种把西藏诗意化洁癖的写作路向,缺乏对西藏精神文化的缺陷和负价值的审视,没有从不同文化的精神扭击中张扬“新生”而抨击“方死”,而想法单纯地把西藏文化的一切都作为一种诗意之美,加以浓烈渲染。也正是基于作品中这种理性批判精神的缺席,他们笔下的西藏也仍然是一个非真实、扭曲的西藏。这正如马丽华所说:“诗化和美意构筑的感性世界,也使它的真实性多少被打了折扣——在中国,异文化进入者的边疆作品不约而同的困难所在。”⑪还有西藏作家色波在《遥远的记忆——答姚新勇博士》一文中写道:“将藏区诗意化,正是内地人写作的一种偏见,好像藏区就没有切切实实的日常生活一样。”⑫这句话恰切地道破了内地汉族作家书写西藏的特点和缺失,亦即一种过度美化和简单处理的惯用套路。
如何摆脱对西藏的诗意浪漫“误读”,打破人们对西藏的固定印象和想象方式,让我们真正进入那个远离汉文化中心的边疆生活的细部。阿来所说的这番话,或许对我们有所启示:“藏族并不是另类人生。欢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获得与失落,所有这些需要,从他们让感情承载的重荷来看,生活在此处与别处,生活在此时与彼时并无太大区别……因为故事里面的角色与我们大家有同样的名字:人。”⑬事实上,阿来也是这样进行创作实践的,他的六卷本长篇《空山》以绵密的细节与乡村琐碎的日常生活叙事,展现了自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川藏边地一个藏民居住的地方机村的命运变迁。作者没有对藏文化作单向度的诗化处理,而是呈示出藏地丰富多维的表情。小说中的机村人不是其他西藏书写所展现的那般“超凡脱俗”,他们既容纳着仇恨、嫉妒和残暴;也栖息着怜爱、宽容和善良,比如他们对私生子格拉的蔑视,在对桑丹和格拉肆意施暴,把他们母子赶走之后,他们的羞愧和悔恨又涌上心头。小说既展露了现代性对藏文化的破坏和伤人的一面,如砍伐森林的电锯,炸毁神湖的炸药,又真切地描绘了“新社会”伴随着大量的“新事物”如水电站、脱粒机、马车、喇叭,给机村人带来惊奇、兴奋与惶惑。在现代性的冲击下,藏族文化中遵循的看重义理、讲究诚实的精神疏远了人们的生活,旧有信仰和传统伦理遭到了摒弃,作者对此流露出悲切地哀挽;同时又对机村人暴露出来的无知、人性蒙昧表示出了强烈的讥讽和义愤。如此走出那种惯常的诗意“共名”的方式,不以陈腐的浪漫来稀释当代藏地生活的真切性,而以多焦的视点与多重的变奏,理性而全面地审视生活西藏、文化西藏,我以为,这应该成为小说“西藏书写”的未来与方向。
三、原生态崇拜:“东方主义”话语的复制
在许多西方人眼中,西藏几百年的黑暗的、残酷的农奴制度,都被有意识地遗忘或抹煞掉,西藏以其高原险远、原始风情、宗教信仰的迷惑、神秘的雪域文化……而被看做是一块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是一片人间的至乐之地。对后现代的西方人来说,他们似乎总是期盼着看到一个“原生态”的西藏,一个所谓“时间停滞的香格里拉”,一个静态的理想社会,正如穆伦在《美国占领藏传佛教》一书所论:仍然幻想从自然和人文方面保持西藏的纯洁性,实际上是要满足其身心的需求:信仰、探险、旅游、休闲、健身,以缓解竞争压力,慰藉空虚的心灵。⑭
为何后现代的西方人要如此钟情“原生态”的西藏?可以借用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观点为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萨义德指出:“在西方文化中,“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⑮当然,东方并非仅仅出自想象,“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⑯。这就是说,西方视角中的西藏形象和西藏话语,是西方所建构的关于非西方的“文化他者”的话语,这种西藏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是西方文化对西藏的皈化利用与自助性地建构。我们知道,20世纪中叶以来,进入“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的西方开始反思现代性,当意识到正是价值理性的衰落和工业主义的过度扩张导致种种灾难时,一些西方人将目光投向了东方文明和宗教,尤其是注重精神,带有原生态的前现代色彩的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他们出于“自助”的心灵需要,制造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香格里拉神话”、“最后一块净土”,以此寄托着他们的梦想和怀旧之情,于是神秘的中国西藏,又成为了西方怀旧的故乡,或者后现代的乌托邦。
在东方主义视野的规约下,西方人总是大量描述和评价1959年以前的所谓“原生态”西藏,纵情想象西藏未受任何现代文明的污染。在看待西藏文化时,只要求保持其多样性,不愿看到西藏文化的发展和适应现代化。由此,他们过分沉溺于陈旧的幻想,而忽视西藏普通民众的发展;热衷于藏文化保持恒久原生态的神圣意义,却淡漠文化承载者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状况;纠缠于孤立、虚构的历史,却置几十年来西藏改革与发展的成就而不顾。
遗憾的是,我们有些作家也东施效颦,承袭了这种西方中心观的东方主义逻辑,并将之置换为一种“内部东方主义”的思维路向,亦即习惯性地从主体性文明出发,把民族国家内部从属性文明,书写成一种原生态“牧歌”,以此作为对过去怀念的对象,从而反思主体性现代文明。于是作家们通常预设一种“现代与传统的冲突”的陈词滥调般的主题,对西藏原始的民俗风习、人情世态与落后的封闭意识、传统的思想惰力,不加辨析地颂赞讴歌;对西藏自然的本真状态抱持偏执式迷恋,以所谓小布尔乔亚分子的格调,沉溺于“欣赏”和“艳羡”西藏的原始风景;对西藏的新生活流露出不可抑制的惶悚与疑惑,有意无意地漏掉西藏现实中发展变化的另一面。比如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就流露出期翼拉萨继续现状或回归更古老的过去的强烈心绪:“从前的拉萨像一场久远的梦,……叶瓣恍若雨滴飘落到我的双肩,滑落到潮湿的泥土里。树林里天籁摇曳,一阵清脆悠长的铜铃声由远而至,一对洁白的小羊儿从林子深处走来,满地浅黄淡绿的落叶在羊儿轻巧的步履下翻涌着,争先绽放,仿佛一朵朵灵光闪耀的圣莲……”“以雪山和草原为背景,自由的情侣本该骑在马背上奔驰,在沉静的家园里私语,在古老的床板上热烈的地相爱,拥有祖辈们曾经的好时光……”然而现在,“所谓的老城区危房改建工程令一些人发了一笔横财,但改建后的老城区面貌全非,人们的居住空间变得拥挤、嘈杂和更加混乱。……没有了甘洌的水井、白色的桑炉,也没有了友善的老邻居……”“牧人们从雪地迢迢而至,但拉萨——他们的家变了,甚至穿过一条马路,也要冒生命的危险。家园没有了安全感,只有无情的车辆、高楼和紧闭的门……”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作者对当代拉萨的忧思,但在面对急遽前行的时代巨轮时,如果排拒任何新变,只是一味如条件反射地认同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张力与裂缝,不去寻找它们之间的平衡与弥合点,则将这个问题简单化了。郭阿利的《走进草原的两种方式》中的北京人李辉生长在北京城,向往自然生态,来藏北草原就是寻找梦中的香巴拉。文本中借李辉之口,不时流露出对科学技术进入草原的失望情绪:“看着眼前一排排钢筋水泥结构的小楼,再看那趾高气扬的所长心里就不舒服,凭感觉爹就知道,这里除了比北京小以外,其它一定和北京区别不大,爹不希望刚走出现代化的北京城就又进了现代化的草原。”草原上为牛羊采取人工受精的新生产方式,这样每年都会按规定的数量生产出优质的牛羊,既提高了牛羊肉的产量,也调节了草场的生态平衡。可是作者借小说中的人物作如此议论:“抹杀了人的本性还不够,现在连牛羊也不放过了,多么残忍的现代科学技术呀。”还有杨金花的《天堂高度》、摩卡的《情断西藏》、七堇年的《大地之灯》等文本也是极力渲染西藏原生态风景的美好,似乎只有一片蛮荒的、未经开化的西藏,才是真正产生纯美爱情,或升华精神格调的天堂,才是美好、丰富、纯洁、神圣、充满着浪漫气息和脱俗气质的“香格里拉”。质言之,这些小说痴迷原生态的西藏,反映出他们对西藏的共同理解或者期待:西藏本应该就是“永远的香巴拉”,不属于也不应该属于这个正在现代化的世界,西藏的任何现代性新变,都只能被看做是一种异己力量,并成为破坏藏文化纯洁的象征,任何传统的衰微,都隐喻着藏文化的危机。这样自以为是的想象方式,完全抹杀了现代化发展对西藏的积极意义。
其实,对于现代化有些腻味的所谓城市“中产阶级”或“白领”来说,要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地球上的任何族群都有权利分享人类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现代化带来的成果,这是“天赋人权”。当我们一方面在中心地带受益于现代化所提供的一切时,另一方面却为了满足我们自己所谓怀旧梦境的想象,而要求西藏是永远静止的、原生态的,这是极不人道的,是一种普世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缺失。西藏的现代性追求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或者说其现代性即当下性和现实性,正如作家书云所说:“对西藏普通的百姓而言,他们需要对过去灿烂历史文化的记忆,但更需要在变化中追求现代化的美好未来。他们渴望享受现代化的生活,不希望被当作古老的文物加以收藏和展示,更不希望把他们当作虚拟中的‘香格里拉’或‘香巴拉’让人观摩,被人误解、误会”。⑰诚哉斯言,真切的西藏完全不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而是进步与问题并存,在巨大变化中延续着古老的传统。
总之,我以为,虽然在这个特定时期和一些特定群体中,西藏已经成为了某种前锋或受到强烈的关注,但是西藏是无言的,言说的只是我们自己。因此,对于西藏叙事的主体来说,我们在以各自的方式感受西藏的时候,要寻找到真正抵达人类心灵的精神和感动,真正产生开发、建设、保护、发展西藏的紧迫性和忧患意识。由之,藏族作家央珍的创作谈可作为我们的镜鉴:“我……力求阐明西藏的形象既不是有些人单一视为的‘净土’和‘香巴拉’,更不是单一的‘落后’和‘野蛮’之地;西藏人的形象既不是‘天天灿烂微笑’的人们,更不是电影《农奴》中的强巴们。它的形象的确是独特的,这种独特就在于文明与野蛮、信仰与亵渎、皈依与反叛、生灵与自然的交织相容;它的美与丑准确地说不在那块土地,而是在生存于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灵里。”⑱
【注释】
①本文所说的“西藏”,并非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不是单指解放后建立的西藏自治区,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西藏”,它标示着一种历史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藏民作为生活的主体民族,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等方面迥异于内地中原。
②张隆溪:《异域情调之美》,李博婷译,《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
③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④孟繁华:《红尘不能淹没的文学——2006上半年的长篇小说》,《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9期。
⑤[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00页。
⑥[匈]卢卡奇、[德]本泽勒:《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张西本、李秋零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⑦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0/2010-03-16/83583.html。
⑧[加]马歇尔·麦克卢汉:《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⑨蓝讯:《西藏片羽》,史小溪编《中国西部散文·下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71页。
⑩宁肯:《为什么不同》,《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1期。
⑪马丽华:《西行阿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⑫色波:《遥远的记忆——答姚新勇博士》,《西藏文学》2006年第1期。
⑬阿来:《落不定的尘埃》,《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1997 年第 2 期。
⑭转引自杜永彬《西方对西藏的误读及其原因》,《当代世界》2009年第4期。
⑮⑯[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6-8页。
⑰卜昌伟:《旅英华人作家书云用〈西藏一年〉记录藏民寻常生活》,《京华时报》2009年7月24日。
⑱央珍:《走进西藏》,《文艺报》1996 年 2 月 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