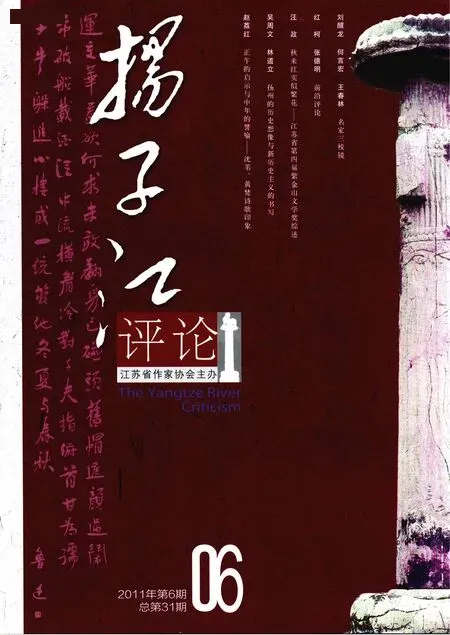“我”与“我们”——当代诗歌中的个体形象和群体形象试析
颜炼军
如何处理私人领域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契合与裂痕,是当代汉语诗歌写作面临的共同问题。其实,最晚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还不是汉语诗歌抒情的核心。中国社会中个体与集体之间隔阂的真正形成,是八九十年代才大面积出现的情景。文变染乎世情,诗歌也得对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对立进行抒情性化解。可以说,当代诗歌在这方面的解决办法,展示了这时期诗歌最困难、也是最有成效的部分。因此诗人臧棣说:“九十年代是诗歌主题有两个: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①通过阅读当代汉语诗歌,我们可以更好地明白,诗歌社会学意义上的自我,无论如何都必须以某种显而易见或隐秘的集体性作为背景。
在现代汉语文学中,鲁迅著名的《影的告别》这样的作品中也表达了这个主题。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结构,也致使汉语新诗发明出不同的自我形象,它们与所依靠的不同“集体性”背景之间,也曾经寻找化解隔膜的方式,但因为诗歌之外的集体性力量(比如民族危机)的强力介入,诗歌便可以兴高采烈或者颓废哀伤地书写它们的时代的核心命题,将它们化约到对某种个体性的发现上,这种抒情模式,甚至可以不顾及诗歌本体论意义上的疑虑。大概只有九十年代以来的汉语新诗,因为其生成的特殊语境,才对“我”与“我们”之间的分裂特征进行了充满本体性质疑的、成规模的书写,并展示了新的个体形象。
二
诗人清平九十年代初期的作品《鱼》,虽不太被研究界提及,却比较典型地显示了当代诗歌中自我意识的微妙转变:
在水上
一条鱼度过老年时光
它脱下心爱的衣裳和
皮,肉,骨头
挂在水草上
一条鱼把随身携带的事物分给大家
变成一条更小的鱼
属于它自己。②
在此前的汉语新诗中,似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关于自我的明确寓言:诗人希望通过剥离所有附加于自我身上的时间、色彩等与“大家”有关的事物,以达成一种对于自我的纯粹梦想——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的诗歌中,自我形象天然地与宏大的事物,比如革命、祖国、解放、光明、明天、远方、梦想等“相信未来”的愿景相关,并形成了许多与它们相关的自我的隐喻。即诗歌的抒情主体能在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中获得一种自我完善的典范,在灌满革命乐观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大众与个体之间,找到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力量,甚至到了海子这样的诗人笔下,依然激发着一个巨大的、高音量的自我形象。敬文东曾精确归纳道,八十年代的诗歌大多“嗓门奇大”、“似乎人人真理在握”地“对着人间众生说话”。③在这一切随着历史的变幻而烟消云散之后,如何重新修复破损的抒情主体?凭什么再来描写事物和“大家”?
九十年代的汉语新诗一边还原和剥离出“更小的自己”,同时也针对新的社会和历史语境,抒写新的诗意化的自我;以新的姿态出发,走进别人或“大家”。比如,诗人朱朱1992年的一首诗中就展示了一种对于人群的特殊的“看”:
雨中的男人,有一圈细密的茸毛,
他们行走时像褐色的树,那么稀疏。
整条街道像粗大的萨克斯管伸过。
——《小镇萨克斯》④
这某种意义上仍是从“更小的自己”发出的“看”。按照诗人自己的说法,这是“一个为经验所限的观察者”⑤进行的观察。在这种“看”的风景里,看者与被看者之间虽是近距离的,却是目光与背影或侧影之间的关系,即作为被看者的灵魂的泄露的脸,没有正面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虚化成为人与风景(树)之间的关系,成为灵魂的萨克斯在默默演奏的一种象征,而非“我”与“我们”之间的正面相遇。这里暗示了这个时期诗歌抒情主体与抒情对象之间关系的一种特征:即便是近处的人群,近处的事物,只有通过“萨克斯”,才能被纳入到诗人的“看”之中。正如诗人阿吾九十年代初期写道,“这里没有意义,只有言语/这里没有个人,只有人群”⑥,“意义”或者占有它的“个人”都随着宏大事物在诗歌中的寂灭和解体而消失了,只剩下“言语”和“人群”,像风景一样参与诗人独自的“演奏”。可以说,经过了八九十年代之交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段,诗歌之“看”已经退回到“有限”的观察里:个人与群体之间已经丧失了此前的阶级同情、革命友谊、人民情感或集体情绪等汉语新诗中一直展示的内容。在九十年代的诗歌抒情里,这一切都变形为人与“风景”的关系,而不再是面孔与面孔之间的关系,诗人不再愿意随意地“走入”他人,或者说开始调整观察人们的词语姿态,对于“人群”常怀警惕之心,甚至自己就是人群中盲目的一员。因此,诗人王小妮说,诗人作为看者之所以不能“走进”他人,是因为其背后的“神的盲目”。她在九十年代初期的作品中,展示出作为看者的“神”的不确定,因此神即使面对着“多好的人群”,也成了善恶不分的盲人:“神/你的光这样游移不定/你这可怜的/站在中天的盲人/你看见的善也是恶/恶也是善”⑦。在现代新诗史上,曾有许多力量让诗歌中的“我”可以与“人群”融合,它们某种意义上就是“攫住了民众和胆大的城市”⑧的现代“神力”。而在一切“神力”都烟消云散之后,“我无法判断他们的孤独是否和我的相似”⑨:
她在……
她,就在她们中间
还有他,他们
她回头时,也在所有逝者中间
——周瓒《1995年,梦想,或自我观察》⑩
在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丧失了抒情上的共通性基础后,诗歌如何表达“神的盲目”留下的空白?在这样的处境下,诗人说,“诗只满足小众,首先满足写诗的人自己,它就足够了,不能要求它不胜任的。”⑪也就是说,“看”是为了勾勒出自我的风景,或者说,是自我从人群中分离出来的过程,是落落寡欢的、有些冷漠地在室内不经意地向外看,而不是兴高采烈或满怀希望地进入“大家”。即使诗人对劳动者进行观察,也倾向于将劳动简化为诗艺的象征,而非马克思意义上异化的劳动,比如多多写道:“闪电是个织布的人,毫不理会/午后一阵高过一阵的劈柴声”⑫,西川写道:“喧闹世界的隐蔽的法则通过我的女邻居传入我的耳朵,冷酷地打击我的温情。所以当尘土弄脏了我的白手套,我不起诉,不抱怨,而是像牛一样费力地想象它们怎样洁白地戴在灵魂的手上。”⑬即使诗人“看”到的,是街头拾垃圾的女人,她想表现的也是一种迷醉地献身于“自己”的冲动:
在一排深绿色的垃圾箱跟前
驼背的老妇人正谦恭地
俯身于她喜悦的发现
她忙碌的前臂隐蔽在铁盖背后
而她的蛇皮口袋,胃口大开
她那双被灰色毛裤紧箍的瘦腿
又直又长,像用旧了的船桨
从背后看去,她肩骨高耸
固执地贴近她的工作,从那里
捕捞、赞叹、欢乐……
她的身体分裂出细小的动作
正散发着我能看到的幸福,她的幸福
——周瓒《1995年,梦想,或自我观察》⑭
在这里,拾垃圾的老妇人被诗人看到的,也是背影:“驼背”、“背后”等形象,都表明了一种看的尴尬,如果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那么,看者与被看者的灵魂没有相遇,因为“她”的头和脸,都隐藏在垃圾桶中。也就是说,诗人虽然尽可能细致地描绘下层女劳动者艰辛工作的情景,但她想写的,显然是“另一个我”,把“她的幸福”变形为“我能看到的幸福”。像波德莱尔写过的拾垃圾者一样,这里的“她”也是现代诗人的自我幻像。即使如张曙光说的那样,除了美好的事物,诗歌还“应该成为一只垃圾箱/包容下我们时代的全部生命”⑮,但在现代都市里,诗歌描绘的是“有限观察”视野中的“垃圾”部分,而并非要让个体融进“大家”之中,因此,拾垃圾者的形象,事实上是诗人劳作的形象。汉语新诗对待劳动者的态度,在周瓒这里显示了一些有趣的新特征,知识分子与底层劳动者之间,不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也不是广场上为某个崇高的信念呼喊奋战的战友,而是一种有限的看与被看的关系。他们常常背对着那些享有正常都市生活秩序公众和人群,把脑袋和眼睛都藏在了不易察觉的阴暗或肮脏之处;即使面对茫茫人海中的无数盲目的眼睛,黑暗也无处不在:“黑暗的中午/我们走过王府井大街/突然,一条蜥蜴闪电一样/在人群中穿过。”⑯1997年炎热的夏天,诗人西渡面对北京城里奔忙而密集的建筑工人,也写下这样的诗句:“戴安全帽的城建工人/像奔忙的蚂蚁,费劲地/拖曳着春天巨大的尸体。”⑰在某种意义上,都市里的诗人面对的现实,正是“春天巨大的尸体”,他们的写作,是一种在炎热的现实里的“拖曳”。诗人描写室内的劳动,也具有类似的方式,张枣1995年写《厨师》一诗是这样描绘厨师的劳动的:
未来是一阵冷颤从体内搜刮
而过,翻倒的醋瓶渗透筋骨。
厨师推门,看见黄昏像一个小女孩,
正用舌尖四处摸找着灯的开关。
室内有着一个孔雀一样的具体,
天花板上几个气球,还活着一种活:
厨师忍住突然。他把豆腐一分为二,
又切成小寸片,放进鼓掌的油锅,
煎成金黄的双面;
再换成另一个锅,
煎香些许姜末肉泥和红颜的豆瓣,
汇入豆腐;再添点黄酒味精清水,
令其被吸入内部而成为软的奥秘;
现在,撒些青白葱丁即可盛盘啦。
厨师因某个梦而发明了这个现实,
户外大雪纷飞,在找着一个名字。
从他痛牙的深处,天空正慢慢地
把那小花裙抽走。
从近视镜片,往事如精液向外溢出。
厨师极端地把
头颅伸到窗外,菜谱冻成了一座桥,
通向死不相认的田野。他听呀听呀:
果真,有人在做这道菜,并把
这香喷喷的诱饵摆进暗夜的后院。
有两声“不”字奔走在时代的虚构中,
像两个舌头的小野兽,冒着热气
在冰封的河面,扭打成一团……⑱
在这首诗里,尽管张枣对于厨艺进行了精确描述,但厨师的劳动已经成为一种元诗暗喻。观看豆腐制作的过程,不由得让我们想起阅读阿喀琉斯之盾的制作过程。“有两声‘不’字奔走在时代的虚构中”,显示了持有这种劳动观的诗人的坦然和傲慢。类似的作品,还有欧阳江河的《毕加索画牛》。以艺术家甜蜜而傲慢的劳动,来应对和抛弃工业消费社会中劳动的枯燥,是现代艺术家应付现实的一种办法。在臧棣看来,这种纯粹的劳作可以不顾及倾听者,他称之为“哑剧”:
现在谁是倾听者?在哪里倾听?
对我来说已并不重要。或许
我只是对自己诉说:一种失传的技艺
一种人和他的自我之间的语言交易⑲
因为,对于诗人来说,倾听者和倾听的语境也是混乱和不确定的。“人和自我之间的语言交易”,就意味着诗人通过语言来确认个体不确定的本质特征,它既是自我的危机所在,又是敞开的存在。也就是说,在这个神灵“盲目”的时代,诗歌作为神性的现代遗传,它只能以语言技艺来确认和命名个体,从“盲目”中将之沉析出来。对诗人来说,发明新的自我,澄清不同自我之间的关系,正是诗歌追思和解决存在之难的手段。因为,个体的角色永远依赖于群体性的背景,上述内倾的姿态,也意味着由此可能打开的新的诗意世界。诗人翟永明在《潜水艇的悲伤》中也展示了一种内倾的、与自我进行语言交易的姿态,但她试图在书写者与社会实践之间搭建一种象征结构:
当我开始写 我看见
可爱的鱼 包围了造船厂
国有企业的烂账 以及
邻国经济的萧瑟 还有
小姐们趋时的妆容
这些不稳定的收据 包围了
我的浅水塘⑳
在这节诗中,震慑我们的,是一切非诗意的事物的秩序“包围”了“我”的“浅水塘”,正如臧棣诗中的写者被倾听的缺在所包围一样,这首诗中的写者的姿态与写者的处境之间,也激烈地相互否定,又借否定向对方转化。诗人面对和进入自我之外的人和事物,是灵魂的冒险,也是将它们凝定于自我“风景”中的过程。在这种转化构成的象征中,诗人所处的具体时代之难,被转换为诗意的困难。所以,整首诗一方面在展示歌命名具体事物的困难,同时,又说出了诗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我必须造水,为每一件事物的悲伤/制造它不可多得的完美”㉑,这也是一种“语言的交易”。
三
九十年代以来,纵然那些有意回到“大家”之中的诗作,也得借助左翼文学和革命话语资源,以克服象征之难。因为只有把“看”植入历史的参照系中,“看”才意味着一种走进“大家”的空念头:怀旧感和“新人不如故”的无奈。比如,诗人柏桦这样写棉花工厂:“哈哈大笑的棉花来了/哈哈大笑的一日三餐来了/哈哈大笑的工人阶级来了//一日复一日,明日何其多。”㉒萧开愚九十年代初的重要诗作《雨中——纪念克鲁泡特金》,也写诗人在雨中观看到的“风景”。诗人面对不远处在雨中干苦力的码头工人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这时,我希望能够用巴枯宁的手/加入他们去搬运湿漉漉的煤炭”。在此,诗人不只是怀念“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曾经的情感和理想的合作模式,而且还摆出了这样的问题:丧失了这种理想的情结支撑之后,二者之间的相互漠视、对立和误解,如何在诗歌中得到调和?如诗人姜涛分析此诗时指出的,这首诗似乎回到了茅盾《子夜》的传统中,“显示了‘我’与‘我们’、‘我’与历史实践之间不可消除的距离,显示了诗歌可能的社会位置”。㉓萧开愚另一首广受赞誉的诗作《北站》,也生动地展示了知识分子的这种调和在大时代滚滚旋涡里的枉然:个体在历史和国家现代化推进所造成的集体生活变迁面前之渺小。可以说,即使古希腊人面对时间体悟到的“一切皆流”,孔子感慨的“逝者如斯夫”,都只表达了人类被水激发的时间幻象,它们都不足以描绘我们每个人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具体而微的消逝。在《北站》中,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和城市改造带来的历史和时间的恍惚感、消逝感,被萧开愚浓缩于对一个已经化为乌有的火车站的反复忆叹中。通过对记忆场景的反复呈现,诗人将社会历史的变幻和芸芸众生之被驱役,以及这一切的更迭和消失,都内化为“我”内心翻涌的世界。火车、废弃的铁道、曾经的拥挤的客流,似乎都成为个人身体中复活的内容,同时,也是“我”内心丢失的部分。在这个所有事物都遭受着大规模拆迁的时代里,“我”与已经消失在时间中的“一群人”是同一的,具有同样渺小的质地和命运,“我”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又是所有消失的卑微的记录和见证者。“我们”和没有方向的群氓一样,内心依靠的生活世界都在被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拆迁:
我感到我是一群人。
走在废弃的铁道上,踢着铁轨的卷锈,
哦,身体里拥挤不堪,
好像有人上车,有人下车,
一辆火车迎面开来,
另一辆从我的身体里呼啸而出。㉔
大众心理学研究认为,个体是智慧清醒的,但这些个体一旦聚集在一起,群体就诞生了。群体的形成,就可能导致智慧、同情和道德活力的丧失。爱因斯坦曾感慨:“这个事实给人带来多少苦难!它是所有战争和每一种压迫的根源,使得世界充满痛苦、叹息和怨恨。”㉕上举的诗句中,也表达了一种对于群体的幻觉,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人的共有幻觉:一方面,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另一方面,世界变化和更新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每一个个体自我更新的速度,因此群体的特征也在发生着令个体捉摸不定的变化。二者的混杂,给个体带来被淹没的感觉,似乎个体与群体之间在感觉上是模糊的:每一个个体都淹没于正在流动的各种人群之中,但各种人群又因为种种社会变化而转瞬即逝。那些已经消失的群体,正以新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组成一个更为无边的群盲社会,它成为我们每一个体具体的存在背景。因此,诗人在另外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我如何从我救出一个我?/我厌弃了我,就像厌弃了/那些曾经着迷的事实”㉖。受各种外在的凌乱而强大的力量的支使,个体不断被裹挟进各种群体中,同时也不断从各种群体中走出,这种“厌”和“弃”,是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里频繁发生的个体性事件。诗人宋琳1997年写的《漂泊状态的隐喻》中,也从另一个角度写出了这种现代都市人的幻觉:“强烈感觉到分裂的自我/仿佛十二座桥上都站着你”㉗。诗人周瓒也表达了类似的感觉:“在人群中,就像掉在了/自己编织的罗网里”㉘。现代都市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群体,其中个体单一的精神面孔让诗人感到,似乎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分裂出去的一部分,他们身上都牵挂着同样的丧失感。诗人李亚伟以对排山倒海的语言气势,对“我”的这种处境进行了细致的描绘:
我是生的零件、死的装饰、命的封面
我是床上的无业游民,性世界的盲流
混迹于水中的一头鱼,反过来握住了水
……
我是一个叛变的字,出卖了文章中的同伙
我是一个好样的字,打击了写作
我是人的俘虏,要么死在人中,要么逃掉
我是一朵好样的花,袭击了大个儿植物
我是一只好汉鸟,勇敢地射击了古老的天空
我是一条不紧不慢的路,去捅远方的老底
我是疾驰的流星,去粉碎你远方的瞳孔
伙计,我是一颗心,彻底粉碎了爱,也粉碎了恨
也收了自己的命!
伙计,我是大地的凸部,被飘来飘去的空气视为笑柄
又被自己捏在手中,并且交了差
伙计,人民是被开除的神仙!
我是人民的零头!㉙
我是谁?自我的确认,自我公共角色的选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自我的模糊和分裂,成为一个严酷的事实,各种自我的并置,相互之间的否定和嘲笑,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危机最为生动的体现。诗人将这组诗命名为《野马与尘埃》,似乎寓意着个体的渺小,以及个体之间的无差异给我们带来的慌张和虚无。这是当代中国都市生活的生动体现,拥挤、繁忙,每一个体都似乎处在城市社会这一巨大的群体中,丧失了自我,诗人对这种丧失的担忧和嘲讽,正是建立在“我”与“我们”之间的既分裂又紧密的关系基础上。因此,诗人张枣曾说:“我完全感觉到我生活在一个我追赶我自己的时代,一个神经质的、表情同一的、众物疲惫的时代。”㉚王家新在《变暗的镜子》中写道:“为什么你要避开他们眼中的辛酸?为什么你总是羞于在你的诗歌中诉说人类的徒劳?”㉛而诗歌对这些处境的描述,又该向谁诉说呢?诗人西渡90年代后期写的《在硬卧车厢里》一诗,被许多研究者视为90年代诗歌的代表作之一。诗里写的,也是诗人在巨大的人群流动中的聆听与观察。诗歌中以特殊的观察视点,描绘了一对在硬卧车厢里的陌生男女,以最短的时间建立起暧昧关系的过程:
在开往南昌的硬卧车厢里
他用大哥大操纵着北京的生意
他运筹帷幄的男人气概发动起邻座
一位异性图书推销员的谈兴。
——他之所以没有乘上飞机
或者在软卧车厢内伸躺他得体的四肢
再一次表明:在我们的国家
金钱还远远不是万能的。
“你原先的单位一定状况不佳
是它成全了你,至于我,就坏在
有一份相当令人陶醉的工作,想想
十年前我就拿到这个数。”她竖起
一根小葱般的手指,“心满意足
是成不了气候的。但你必须相信
如果我早年下海,干得绝不会比你逊色!
你能够相信这一点,是不是?”
“你怀疑?你是故意气我的
你这人!”他在不失风度地道歉之后
开始叙述他漫长的奋斗史,他的失意
他的挫折,他后来的成功,他现今的抱负
他对未来的判断。她为他的失意
唉声叹气,她的眼眶中仿佛镶进了
一粒钻石,为他的成功而惊喜
几乎像一对恋人,他撕开一袋方便面
“让我来”,她在方便面里冲上开水,
“看你那样,就知道离不开女人的照顾。”
——如果把“女人”后面的补充省略也许
更符合实际情况。谈话渐渐滑入
不适于第三者旁听的氛围。我退进过道
回避陈腐的羞耻心。在火车进入南方
的稻田之后,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城市
他们提前下了车,合乎情理的说法是
图书推销员生了病,因此男人的手
恰到好处地扶住她的腰,以防她跌倒㉜
许多论者都称赞过这首诗的叙事和戏剧化的特征,以及它对90年代南方商品社会引发的人性和道德变化的精确描述。比如罗振亚说,在此诗中,“日常情境画面的再现和含蓄微讽的批评立场的结合,显示了诗人介入复杂微妙生活能力之强。”㉝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事实上,这首诗里有许多反叙事性的元素,也就是说,诗人在处理他描绘的画面和故事时,其实处处在警惕写作的散文化。无论在时间感上、修辞和句法上,还是在情节的剪辑上,都摆明了对叙事的忤逆。九十年代诗歌中备受关注的“叙事性”的成功,恰恰是建立于对叙事的警惕之心上。许多作品的失败,也正在于缺少这种警惕之心,让诗歌丧失抒情的品质,携带“口腔痢疾症”而“招摇撞骗”㉞。我在此想讨论的,是这首诗中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关系。在诗中,“我”是一个旁听者,而且在诗句中只出现了一次。诗中记录的所有对话和情景,作为当代中国人,只要乘坐过火车都非常熟悉。因此,诗中的“我”某种意义上可以置换为我们任何人,诗人某种意义上在处理一种普遍性的经验。也就是说,诗人的角色在这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不标榜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诗人的“浅水塘”或者寻找“倾听者”的焦虑,不将他者“背影”化或宣称把“他们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幸福”,而是一边“回避陈腐的羞耻心”,一边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们”的全部。诗中的“我”,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他们”的故事的一部分,是“他们”的故事或八卦的倾听者和传播者。可以说,这是一种新的抒情化的自我形象,他对在路上的芸芸众生的描绘方式,呈现出一种新的写者的姿态:在商品和消费为主流的社会中,自我经验与他者经验相遇的新的可能性。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社会个体间的隔膜的加剧,一些诗人更加考虑写者的姿态与写者的处境之间的关系。诗人王小妮2005年写的诗作《那个人,他退到黑影里去了》,展开了一幅抒情者眼中的卑微的劳动者的剪影。这首诗对于“另外的人”,尤其是工业化中的底层劳动者,显然有一种不同于翟永明和周瓒的游移:
灯捏在手心里。
他退到煤粉熏暗了的巷子最深处
还退到黑色的灯芯绒中
退进九层套盒最紧闭的那一只
月亮藏住阴森的背面。
他一退再退
雪地戴上卖炭翁的帽子
那个人完全被黑暗吃透了。
而他举着的手电筒迟缓了那么半步
光芒依旧在。
在水和水纹中间
在树木正工作的绿色机芯里
在人们暗自心虚的平面
幽幽一过。
所有的,都亮了那么一下
游离了恍惚了幻象了
这种最短的分离,我一生只遇见过三次。
这首诗呈现了诗人是如何观察一个面目脏得不清晰的劳动者的。在当代中国诗歌里,这是一种非常有意味的对立。我们可以在诗中感觉到某种久违的阶级同情、人道主义,但更为有趣的,是诗歌呈现出一种“美”与“真”的博弈和游移。亚里士多德曾经将文学作品里描写的主人公分为两大类:“高摹仿”和“低摹仿”。前者包括神话人物、英雄人物、人间首领,后者包括小人物、喜剧人物、滑稽人物,由此分出不同的文学作品类型。㉟也许现代文学在这一点上出乎亚理士多德的意料,从波德莱尔面对巴黎街头的芸芸众生开始,现代文学必须面对那些它们完全不能进入其灵魂的主人公。在王小妮的诗歌中,我们依然能读出这种困境:一方面,这个被黑暗吃透的“他”是匿名的,“他”身上凝聚的黑的一切,以及微弱的闪亮,与经典现代主义文学中被异化的个体形象有相似之处,比如,早年的王小妮会写:“黑暗从高处叫你。/黑暗从低出叫你。//你是一截/石阶上犹豫的小黑暗”,这是现代主义文学中典型的陷入黑暗的形象。同时,也有一些变化:早年的那个被黑暗呼唤的“你”,某种意义上是“我”的对象化称谓,或者是一个他者的影子;而在这首写于21世纪初的作品里,“黑暗”和“他”都有了新的内涵:诗人沉浸在黑暗感之中的同时,也尽力地把“他”塑造为真正意义上的“另外一个人”,正如在西渡上面的诗里,诗人捕捉到的戏剧化情景,反过来可以理解为自我内心的戏剧。这就陷入了悖论:一方面,当代都市社会阶层的差别,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方式,使一个人理解另一个人遇到了新的困难,对诗人来说,这是理解面临的“黑暗”,进入另外一个人的灵魂,就意味着进入黑暗;同时,诗人特别尽力地体谅和理解他者或底层黑暗的部分。诗中“雪地戴上卖炭翁的帽子”、“暗自心虚的平面”这样的句子,生动地表明了“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纷争”(耿占春语)。因此悖论浮现了:“所有的都亮了一下”,照明的却是隔膜。这首诗微妙地暗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直面普罗大众时内心的尴尬和冲突,以及诗人将它们转化为写作困境的方式。被“照亮”的“我”和“我们”,都常常不得不退避回到自身。因为,在都市生活所划定的想象空间内,我们更习惯面对的事物、人群或他者,其多样性,都是由各色隐蔽的消费和政治意识形态所包装起来的。无论“美”与“真”,还是阶级、苦难和贫乏,都有可能戴着意识形态的面具:“有一刻,我一门心思寻找美,/却看到丑陋就是美,直到发现政治/已成为色彩艳丽的面具,把一个人/变成了所有的人”㊱。因为这种遍地存在的纠结,诗歌的命名就得不时回到对于“我”与“我们”,“我”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反思上,回到抒情化的个体与世界之间如何实现充满突破性地化约的纠结中:
我们抓住它们,就像我的软弱
是它们造成。而
它们什么也没有做
我暗中垂下头,向它们致歉。
——池凌云《别的事物》(2009)㊲
然而,这种当代汉语诗歌中处处可见的纠结,虽是美学意识形态和现实逼迫的标志,同时,也是汉语诗歌内在的潜力所在。因为,正是在纠结中,诗歌不时对词语与世界的关系进行反省,不依附于即有的事物间关系和意识形态,发明出事物之间新的联姻——它们就是诗歌用以防御外在的暴力的内在力量。它们促成私人领域与公共生活之间,“我”与“我们”之间的诗意转化,促成无数的“镜子”立在诗歌与现实之间。其中的每一面,都可以发明一对“亲爱的”,预示着一种可能被放大的未来。
【注释】
①臧棣:《人怎样通过诗歌说话》,《风吹草动》,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②清平:《一类人》,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③敬文东:《道旁的智慧——敬文东诗学论集》,台北秀威出版社2010年版,第35-36页。
④朱朱:《枯草上的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⑤朱朱:《枯草上的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
⑥阿吾:《足以安慰曾经的沧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01页。
⑦王小妮:《等巴士的人》(1993年),《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⑧[德]荷尔德林:《人民的声音》,见《追忆》,林克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
⑨臧棣:《哑剧的轶事》,见《燕园纪事》,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⑩周瓒:《松开》,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⑪王小妮:《半个我在疼痛》,华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
⑫多多:《小麦的光芒》(1996),见《多多诗选》,花城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0页。
⑬西川:《鹰的话语》(1997-1998),《深浅·西川诗文录》,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⑭周瓒:《松开》,作家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4 页。
⑮张曙光:《垃圾箱》,《小丑的花格外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⑯西渡:《轮回》,《雪景中的柏拉图》,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⑰西渡:《为白颐路上的建设者而写的一支赞歌》,见《草之家》,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⑱张枣:《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
⑲臧棣:《哑剧的轶事》,见《燕园纪事》,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49页。
⑳翟永明:《女人》,作家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6-127 页。
㉑翟永明:《女人》,作家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8 页。
㉒柏桦:《山水手记》,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148页。
㉓姜涛:《巴枯宁的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㉔肖开愚:《北站》,《肖开愚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7 页。
㉕[法]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㉖萧开愚:《获救之诗》,见蒋浩主编《新诗》(民刊)2002年8月第2辑,第34页。㉗宋琳:《门厅》,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1 页。
㉘周瓒:《松开》,作家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6 页。
㉙ 李 亚 伟 :《野 马 和 尘 埃·自 我》(http://sjycn.2008red.com/sjycn/article_269_6312_1.shtml)。
㉚颜炼军:《“甜”——与诗人张枣一席谈》,《名作欣赏》2010年第4期。
㉛西渡、郭骅编:《先锋诗歌档案》,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㉜西渡:见《草之家》,新世界出版社 2002 年,第 14 页。
㉝罗振亚:《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叙事诗学”》,《文学评论》2003 年第 3 期。
㉞敬文东:《道旁的智慧——敬文东诗学论集》,台北秀威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㉟[加拿大]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45-48页。
㊱蒋浩:《与 798无关》(2006),《新诗》(民刊)2006 年9 月第 10 辑,第38页。
㊲池凌云:《池凌云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