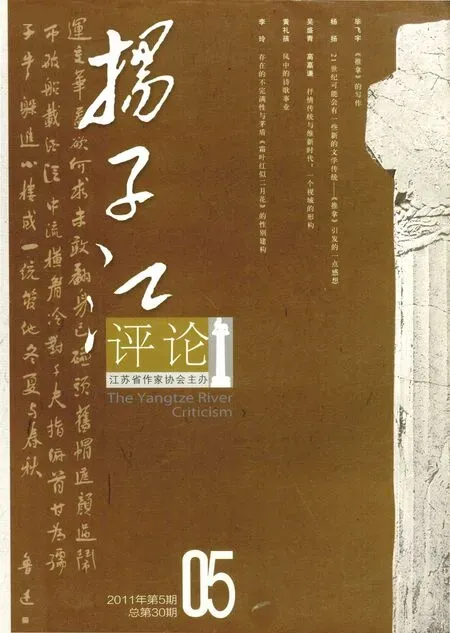21世纪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文学传统——《推拿》引发的一点感想
杨 扬
有评论家私下表示,茅盾文学奖颁给毕飞宇是不是误读的结果?照例,茅盾文学奖偏重于宏观的历史题材的作品,而毕飞宇的《推拿》全无宏大的叙述,人物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事件是上不了台面的小事件,叙事也是小叙事。所以,五部获奖小说中,《推拿》排名末尾,似乎一不小心就要从茅奖的队伍中滑落下去。的确,从评委的角度,我们可以想象这类不幸事件发生的诸多可能。如果还是以往茅奖的评委班底,或许第八届茅奖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结果,而那时,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欣赏毕飞宇的才华,为《推拿》献上鲜花和掌声?事实上,对作家而言,要坚持一种属于自己的写作理念,是很不容易的。对照中国当代作家的言行表现,最常见的现象是作家写作时是一种方式,而对自己的写作发表意见时,又是另一种方式。譬如,阿城的《棋王》、《孩子王》,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知青生活很原生态的把握,写出了“知青”在无聊又无奈的现实面前的一些生活状态。阿城的小说一扫同时期“知青小说”的严肃面目,让读者的眼光从“伤痕文学”的空间中解放出来,转向更宽松、辽阔的文学天地。但轮到阿城出场,对文学创作发表意见时,我们听到的却是一派文化高调,作者唯恐读者忽略了他的创作宏旨,于是下棋和男女饮食都赋予了沉重的文化意味,好像如此一来,小说才有价值。对照毕飞宇的《推拿》,尽管作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声称有多大的宏旨潜藏其中,但一些批评解释,却是只想往高调里拔,生怕毕飞宇没有鸿鹄之志,生怕读者像读普通小说那样寻求阅读快乐,而忘了挖掘《推拿》的微言大义。于是,一些评论将《推拿》与人道主义问题捆绑在一起,说《推拿》思考的是人的问题,表现的是人的尊严问题,好像只有这样《推拿》才有了一种文学的严肃性。这些解说确有善意,但很难说准确。毕竟,在小说与人道主义问题上,最强势的应该是巴金、王蒙、高晓声、张贤亮、张洁、谌容、戴厚英等一批作家的写作,而不是毕飞宇。毕飞宇的创作长处不在于关注人道主义或写人的尊严问题,依我之见,《推拿》的价值在其他地方,尤其对新世纪小说创作而言,它面对的是新世纪当代小说的问题,针对这样的现状,《推拿》显示出一种积极的时代意义。
一
与一些写作者喜欢标榜自己的写作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或对当代社会生活思考的写作不同,毕飞宇的《推拿》很少见到这样的影响痕迹。从小说一开始,读者便会被作者那种捕捉生活细节的锐利眼光所折服。有评论者说《推拿》是细节造就的作品,就细节在《推拿》中所起的作用而言,此话一点都不假,离开了那些精彩的细节的支撑,《推拿》将会逊色不少。但问题在于细节在不少当代作家作品中被淡化,甚至在一些作家眼中只有思想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才是写作的追求目标时,毕飞宇着意于细节的小说艺术,是有新的探索价值的。
读《推拿》,我不知不觉想到了著名作家汪曾祺在《晚翠文谈新编》中,批评1980年代一些小说家创作的意见,他说,一些作家把小说当做发表个人意见的地方,大段大段地议论,完全忽略了小说的叙事艺术。汪曾祺的意见在那个时期可能属于少数派,不然那种开口便见喉咙响的小说何以盛行至今?那种喜欢发议论的小说写作的方式,说到底,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一种积习,它与中国传统小说所追求的讲故事方式是有区别的。小说在中国文学中,有自己的传统,与“文”的载道传统,与“诗”的言志传统相比,小说出于“稗官”的“残丛小语”传统①。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中国小说传统的梳理,清楚地揭示了“小说”具有“街谈巷说”、“细碎其言”的特点。这样的小说传统,除具有供统治者以观民风的资政功用外,从小说自身的需求看,主要是娱乐。鲁迅先生在《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一文中,指出小说源于杂戏、市人之口述和庆祝及斋会时用之。这种娱乐为主的小说传统,与诗教为主的文史传统,在道统上是有区别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功能差异,小说一直是文学正统之外的末流,徘徊于文学的边缘地带。但这种边缘地带的小说创作成就了小说文体自己的文学气象,它的叙事娱乐功能胜于教化功能,而且,不像诗歌抒情言志那么郑重其事,也不像文以载道要担负那么多的社会功能,小说文体的卑微,甚至显示出有点不登大雅之堂的琐碎特色,让这一文体始终保留着较多的世俗生活的面相和民间的乐趣。但这种小说文体的传统特色,到近代发生了变异,变异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具有政治抱负的现代知识分子加入到小说作者的行列之中,在倡导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他们借鉴西方的经验,将小说作为一种开启民智的思想工具,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到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理想追求,小说在现代启蒙者的思想视野中,超越诗歌、散文,一跃而成为现代文学中最受社会关注的文体。这种新文学的功能大转换,使得中国原有的小说传统也发生了转变。小说以娱乐为主的传统价值认同,让位于借小说来表达民意的社会批判功能。所以,鲁迅先生曾说:“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本不是古国的一般人们所能轻易了解的,尤其是在这特别的中国。”②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小说方式的被改造同步进行的,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的逐渐强化,所谓文学介入社会生活,所谓作家作品的道德良知,以及知识分子的写作等等说法,其实都可以归入文学意识形态范畴来认识。总而言之,是现代政治在文学结构关系中的强势介入,打破了原来以娱乐为主的小说欣赏习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包括知识分子道德理想的文学诉求,合理合法地走进了现代文学。在传统小说创作中,写作者的身份是才子和文人,写作完全是个人的事,反思传统,批判现实,不是说没有,但很个别,而且点评家们对此常常会以浅、显、露、直等概念加以否定。到了现代,因为道德立场和批判意识在意识形态视野中的特殊地位,小说创作中作者跳到前台,扮演道德传道者的身份角色,已经让读者不再感到陌生。这种立场在先、姿态在先的现代文学景观,从梁启超的“新小说”开始,经过五四白话文,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一直进入到1949年之后的当代中国文学阶段。从文学艺术层面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思想立场和批判现实的价值认同上,新文学与当代文学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差别只在于具体内容上当代文学赋予了小说创作、文学评论以更加明确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斗争的内涵。“新时期”以来,这种新文学传统并没有弱化,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日常世俗生活场景在小说艺术中逐渐增多的同时,招致左右两种思想营垒的共同不满。这些批评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越来越缺乏思想了,他们的潜台词是小说应该是一种关注社会、批判现实的大说,而不应该专注于鸡毛蒜皮的日常琐事。
小说是不是一定都要承担社会批判任务,担当社会民意的代表,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汪曾祺是一个接受过现代小说影响而又带有反现代小说美学面目的重要作家,他不喜欢法郎士在小说中大段大段议论的做法,而喜欢伍尔夫简洁流动的意识流手法。汪曾祺的小说《受戒》等,时至今日很多人还喜欢,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遵守了传统小说的家法,浅处见才,细致入微。但大多数评论者对汪曾祺小说的阐释至今还停留在人性的解释层面,很少有人从中国小说传统方面加以系统阐释。我以为汪曾祺晚年小说创作的最大意义,是摆脱了新文学批判传统的约束,回归到传统小说的娱乐、趣味世界。汪曾祺晚年有两篇文章,专门谈中国小说传统,一篇是《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还有一篇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收入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这两篇文章加之汪曾祺自己的小说实践,清楚地表明“新时期”以来,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在重新复燃,并且构成了一种文学探索。汪曾祺自己的创作谈,很多都是借助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术语。如他认为小说要自然本真,当行本色。他没有用当时文艺理论中流行的“典型”和“真实”概念,显示了价值取向上汪曾祺更倾向于中国俗文学的精神传统,而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所以,他的小说写得像话本、传奇,接近市井闲谈的飘逸风格,说的都是好玩的事情,意趣和谈资是小说立意中最重要的部分。假如忽略了汪曾祺的这种努力,一味地在人性问题上强调汪曾祺小说的价值,那与汪曾祺创作的本意是有一定距离的。再说同时期对人性问题的文学探索,比汪曾祺写得更加深入、更加执着的,大有人在,像谌容的《人到中年》、戴厚英的《人啊,人!》等,对人性的呼唤,几乎是到了呼之欲出的境地,汪曾祺的小说与她们相比,人性的强度和尖锐性显然要弱多了,所以,我认为人性的表现不是汪曾祺小说的强项。汪曾祺的小说另有一功,优势在别处。当很多当代中国作家眼睛向外,以西方的现代小说为参照,从社会、历史等宏观方面探讨小说艺术时,汪曾祺却是从中国俗文学的“小”说传统里小心翼翼地探寻中国小说发展的可能性,尝试着将当代中国小说创作与这个“小”说传统对接起来。这种探索,让一些注重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写作者有一种虚无感,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当代小说的探索方向应该是朝着西方现代化的路子走,好像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没落的东西,需要现代西方文化来改造。但汪曾祺的小说不但没有朝着西化的路子走,反而退向中国传统世界,这种复古后退的审美取向,产生的审美效果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腐朽不堪,反倒是活色生香、熠熠生辉。这让一些在西化道路上急步奔走的知识分子写作有些尴尬。的确,中国传统小说的小道并不比现代化的阳关道逊色,尤其从小说艺术上来考虑,汪曾祺的小说不仅没有失去小说的思想灵魂,而且在小说艺术上远比那些将立场、价值、反思、批判挂在嘴边的写作更具思想魅力。汪曾祺在小说中不大谈论批判现实问题、道德良知问题、思想启蒙问题,他笔下呈现的是花花草草、吃吃喝喝、平民百姓,整个小说的探索似乎是朝着反现代的美学方向发展。他没有选择他熟悉的知识分子做小说的人物,而是选择小尼姑、小和尚,就像《受戒》中出现的人物,都是一些时代身份感比较弱的人物,但这样的人物经过汪曾祺的艺术处理,有一种玉树临风、独树一帜的风姿和意趣。
毕飞宇的《推拿》与汪曾祺的创作有一种呼应,尤其是在对待现实问题上,作者的批判色彩要弱于小说的叙事艺术。《推拿》凸显的是故事,是人物和细节,而不是人道主义、尊严、底层等社会问题。这是毕飞宇创作与很多同时代作家创作的一个不同。其实这样的写作风格也不是始于《推拿》,早在《地球上的王家庄》和《平原》等作品中,毕飞宇就已经呈现出他自己的写作面目,他是一个愿意让小说写作大放光彩的作家,而不是问题意识鲜明的作家。在《地球上的王家庄》里,我们领略到一个可爱的放鸭少年在“文革”时期放眼世界的浪漫故事。作品对“文革”生活保持着一种嘲弄的姿态,但小说的着意点不在批判现实上,而在展示江南水乡生活方面。整部作品饱满、健康,充满阳光和喜悦,不同于我们所见识过的各种描写“文革”的小说。《平原》虽然写“文革”,而且写得比较沉闷,但依然属于汪曾祺所说的本真一类的创作,没有“知青小说”中那种夸大和自恋的成分。至于《推拿》,延续了这种风俗画的小说写法,但驾驭技巧比前两部小说更娴熟,尤其是开头一大段描写推拿的场景,简直是以一种出神入化的戏剧笔法,以精彩纷呈的歌唱姿态,徐徐展开推拿的细节。这是一种盯住细节不放,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小说处理方式。当交代完推拿的技法和种种行规之后,紧接着就是人物出场。这是由盲人推拿师王大夫牵出的一系列人物故事,主要有王大夫的恋人小孔、徒弟小马和推拿店老板沙复明。紧随这些人物的,是一些出彩的细节描写。让很多读者感到惊讶的,不仅是毕飞宇对于推拿行业的熟悉,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普通读者有点隔膜或看不上眼的推拿题材里,竟藏有那么多有声有色、引人入胜的故事,这真让人大开眼界。普通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能不会过多去思考毕飞宇用了哪些特殊技巧将普普通通的推拿演化出那么多出神入化的故事,但读完小说,回过头去想想,其实也没有多少神秘的东西,毕飞宇在《推拿》中寻求的是最平实的叙事方法,抓住那些自己感触最深的生活细节,不折不扣地写,而且要写得像那么回事。这就是汪曾祺一直强调的小说的平实本真的作风。
二
小说的平实本真不是味道寡淡,而是作者心中有底,能够牢牢抓住对象,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这种平实的风格,与慢叙事有关。汪曾祺曾说过,小说家写东西,语言要舒缓,不要像喊口号、吵架一样。读《推拿》,让人觉得一点都不喧闹,作家在慢慢地叙述,读者在耐心地等待,一切都有章法,不会随心所欲。你不会因为阅读《推拿》而激情燃烧,或情绪失控,但一曲终了,放下小说,你会由衷地赞叹这部小说。这是文学阅读最常见的状态。它不需要借助题材和道德姿态来虚张声势,一个优秀的作家有充分的自信,靠语言文字的力量来吸引读者。这种由作品文字所触发的更为丰富的阅读感受和思想联想,我以为是属于小说思想范畴的最有力的东西,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思想深度。小说的思想不同于政治思想,不需要首先端正立场。它表现为作者对自己所表现的生活和人物的一定看法,是有趣味的发现和有滋味的叙述,单单是感觉到问题存在,对小说家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生活中敏感的人很多,有思想的人也不少,甚至是作家当中,有思想家气质的人也不乏存在,但艺术的敏感是属于美学范畴的东西,它是思想,但不是抽象的思想,它是在小说形式控制之下的思想情感的有序表现,它不是宣泄,不是情感失控,而是审美净化和情感升华,用汪曾祺的话说,就是做到“浅处显才”(见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这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思想类型的方式。《推拿》没有什么高深玄妙的思想,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人物和很平常的琐事,但毕飞宇表现得舒缓有致,体现出文学叙事的朴素和美感,很有气度。很多读者都会说,这部小说让人温暖,的确,这与毕飞宇能够有效地调动文学语言、烘托气氛有关,但这种文学语言的调节,不全都是靠技巧。我以为与作者对生活的熟悉和个人生活经验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不妨对照毕飞宇描写农村生活的一组中篇小说来领会毕飞宇小说语言上的探索。《玉米》、《玉秧》和《玉秀》是毕飞宇中篇小说的代表,在这三部作品中,当描写到一些触及人物命运转变的关键细节时,毕飞宇笔下那种尖锐和批判性的情感话语,常常会忍不住爆发出来,一股不平之气会在急切的语言表达中不可遏制地倾泻而出,我们会为玉米、玉秧和玉秀这些命运坎坷的农村姑娘感到不平,并由衷地对社会现实提出批评。但在《推拿》中,这种紧张、尖锐、局促的文学语言开始被一种从容不迫、更为舒缓的情感语言所替代。在整部作品中,你看不到一个坏人;在小说叙述中,也没有听到叙述者用一些比较尖刻的词语讲述故事。即便是厄运当头,叙事者也是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不紧不慢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当然,《推拿》不是一部粉饰太平的小说,但也不是一部问题小说,它更像是一幅时代的风俗画卷。在《玉米》等系列作品中,作者的眼光是外向的、批判社会的。而在《推拿》中,作者的聚焦点是小人物,一群盲人,写他们当下生活状况,但目光是向内的,或者说,叙述者主要是从一个盲人视角看待周围的人和事,这与一个身体健全的平常人的想法有些不一样,关注点也不一样。有些人和事,是超乎盲人视野、感觉之外的,他不会去主动关心它们。毕飞宇在《推拿》中非常有耐心地一点一滴地告诉读者,那些盲人推拿师关心的都是些什么问题,因为这些视角的独特,常常有一些出人意料的细节和情景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如,小说对沙复明刻苦学习一段的描写,让我们明白这个小老板真是不容易,为了学本领,差点把命都搭上了。因为盲人分不清白天黑夜,一用功也不分白天黑夜,这样身体就受不了,等到自己感到身体不行时,那已经是疾病缠身了。这里有很多经验性的陈述,像小孔和小马暗恋时的状态,作者用“情欲是一条四通八达的路”来形容,而对于盲人沙复明心目中的暗恋对象——盲人姑娘都红的美的理解,也是别具新意。作者着意点不在歌颂盲人,而在于讲故事的艺术。毕飞宇像揭秘高手那样,凝神静气,不慌不忙,一边紧盯对象,一边将对象身上最具表现力的秘密一层一层地揭给人看。所以,细节的捕捉和描写的准确是毕飞宇在《推拿》中始终不敢掉以轻心的地方,作品的用心之处也在这里。当一个极具表现力的细节被作者捕捉到并转化成小说情景时,我想毕飞宇一定是暗自得意,他为自己能够寻找到这样一些不为人注意的艺术突破口而暗暗高兴。这种喜悦犹如收藏者不经意间发现一件珍贵的藏品,他无法对着周围大喊大叫,欢呼自己的发现,而只是耐心地等待懂行者的出现,以便分享这种发现的喜悦。由此我想到对毕飞宇《推拿》的一些肯定性的评论中,有一些解释是大而化之、笼统含糊的。评论者强调毕飞宇是在用小说的方式探讨人类尊严问题,体现了人性的温暖。这种论述的基点其实是社会学或是新闻观察方面的,与小说艺术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毕飞宇如果要张扬盲人的尊严,他应该像新闻记者那样记录一些盲人自强自立的故事,那岂不是更加励志,更加彰显盲人的尊严和人性的抗争力度么?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毕飞宇的《推拿》了,说到底,作家在《推拿》中所表现的是一种生活中的感触,是由感触而引发的讲故事的冲动,尊严问题、人性问题当然包含在其中,但这些都是在最广泛的抽象意义上的说法,对小说艺术而言,不是首当其冲的目标。对毕飞宇而言,他是用最基本的小说家法,从人物、细节、情景着手,讲述盲人的故事。他要考验自己有没有本事,将人物写活,将故事讲得引人入胜。这些在传统小说中最基本的看家功夫,对于今天的很多作家而言,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
三
在第八届茅奖获奖的五部作品中,《推拿》是最好读、最没有阅读障碍的一部作品。所谓好读,是作品没有很费解的用语和思想,明白如话,一字一句都看得懂。所谓没有阅读障碍,是作品流畅、饱满,故事情节飞流直下,细节栩栩如生,差不多所有读者都可以一口气读下来,很少有停顿。这样的小说写法,不新不奇,不怪不异,说到底,与汉语写作最稳定的小说构造法相距很近,彼此之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稔和旧谊,读者阅读这样的小说,犹如他乡逢故人,不断被那种熟悉、温暖和家常的经验所召唤,读者和作者之间往来交流的信息,不是天下奇观、天方夜谭,而是彼此之间对熟悉事物的认同和共同记忆。谁没有见识过盲人,但盲人的认知世界是怎样的呢?谁不知道盲人与一般正常人有一些不一样,但这个不一样到底表现在哪些细节上?轮到小说家来表述这些问题时,情况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毕竟写盲人故事不是就事论事,实话实说,而是需要精心构思。而且,在现代传媒发达的今天,影像技术对于细节的呈现手段远胜于小说。伊朗导演阿巴斯的《天堂的颜色》不就是描写一个盲童的生活?他可以通过声光画面多重手段来表现盲童的表情,将一个细节表现推到极致。那么,轮到毕飞宇来描写盲人故事,他有什么高招,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吸引读者的注意?小说家的招术不外乎用语言来传递自己的经验,毕飞宇的本领就是将自己的生活经验艺术地呈现出来。这话可能跟没说一样,哪一位作家写小说能够脱离语言,脱离自己的经验呢?但我以为对毕飞宇而言,艺术地呈现自己的经验是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吸引毕飞宇一辈作家的小说方式基本上是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这样一类作家作品。而对现实关系的理解上,又大都是持新文学的批判现实的态度。所以,现代派技巧加批判现实态度,基本上可以涵盖很多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但在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中,毕飞宇是同辈作家中最早以一种成熟的面貌提供给新世纪的读者以新的小说样本。所谓成熟,是指他最早摆脱了那种不接地气的洋腔洋调的小说写法,代之以本色的中国世俗生活画面。毕飞宇的创作,很长时间也是沉浸在先锋小说的梦幻之中,这种小说的最大特色,是文学实验,寻求新、奇、异、断裂和刺激。但《玉米》系列摆脱了这种先锋小说的审美轨迹,回过头去,与中国的乡土经验接轨,与中国俗文学的叙事传统遥遥呼应。从那时起,毕飞宇的创作好像脱胎换骨一样,变得很质朴,很常态,尤其是《推拿》,延续了一种舒缓稳定的叙事作风,它将小说创作推向了不同于知识分子写作、不同于先锋派写作的方向,朝着更加中国化的方向行进。如果说以往毕飞宇的小说创作追求的是才华的光芒四射,欲以新奇比高低,那么,在《推拿》中,那种咄咄逼人的创作才情变得极其内敛,就像是一位瓷艺高手在仿制传统器皿,他不需要张扬自己的超人才艺,而只需仿照前人的作品,在人人都知道的常规程序上与前辈高人做一拼比。的确,这样的小说写作不是在比才气,而是在考验写作者的功力。《推拿》写得很随意,故事推进也很缓慢,但细节描写出其不意,有一种石破天惊的功力,有写作经验的作者和长期阅读经验的读者都会体会到其中的分量,很多人会不约而同地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想象:假如换一个作者,这样的题材能不能写得得心应手、引人入胜呢?熟悉生活是毕飞宇《推拿》成功的一条经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毕飞宇承认当年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教书的经验以及平时推拿康复治疗经验,对他的《推拿》有帮助。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毕飞宇较早地启悟到自己在小说写作方面的发展前景问题。一个作家写到一定程度,一定会静下心来考虑自己事业的发展前途。摆在毕飞宇面前的几种选择,一是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相连接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二是1980年代兴起的先锋小说的文学实验的路数;三是包括汪曾祺在内的一些接近于中国俗文学传统的小说探索路子。毕飞宇究竟要走哪条路?批判现实的路子,在当代作家创作中不乏其人,像阎连科、张炜、韩少功等一批作家都应承着这一传统。第二条路径中,苏童、余华以及相似年龄的一大批小说家,都在形式技巧上咬紧牙关,持续不断地实验再实验。但老实说,上述两种小说不太像中国小说,或者准确地说,语言和思维习惯不太接近一般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如果从世俗生活的角度来关照中国小说创作,还是汪曾祺的俗文学路子更接近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当然不是说其他两种类型没有触及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我是指精神意蕴上,汪曾祺的小说方式更接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以,摆在一个文学的共时态中探讨中国小说的出路问题,细心的毕飞宇或许会有一点感触,再这么胡乱地写下去,或许就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写作年华。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有一些感悟,毕飞宇悬崖勒马,掉转方向,将写作的探索转向中国的乡土生活。这应该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写作探索。至少从《推拿》的写作中,我们感受到毕飞宇的写作视野比先锋小说时期更为朴实,褪去了很多浮躁轻佻的成分,也没有了那种在刀锋上舞蹈的紧张感。至于批判现实的态度,这对毕飞宇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他可以置之而不顾。接下来,就像卸下包袱的行者,毕飞宇有了更快捷的速度去迎接新的目标。就表现现实题材时所具有的那份从容和淡定,我们可以说毕飞宇的写作超越了很多当代中国作家对现实的认知,在《推拿》中,毕飞宇告别了革命,告别了正义,告别了封闭在知识分子写作狭小管见之中的所谓对现实的忧思,他尝试着在更广阔的天地之间,领会人生的悲悯和欢欣,《推拿》中的盲人生活不是意识形态牢笼中的好人坏人的生死搏斗,而是与生俱来的生命极限的约束与超越约束的可能。人不再与天斗、与周围环境斗,而是与自我想象的多种可能性作斗争。心气太高,磨难很多;平平常常,安之若素,生活会平静一些。生活就像水流一般,筑起的坝越高,水流就越湍急,而一览无遗,顺其自然,反倒是风光无限。不过水涨水落,来来去去,该来时,躲也躲不了,该去时,拦也拦不住。《推拿》中的盲人们好像有点宿命。毕飞宇对这些盲人生活有一种洞观,他似乎早就将他们的生死结局看穿,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劳费心思,盲人的处境也就是这个样子了,难道还想有什么天翻地覆的大逆转?怀着一份怜悯,他再来捕捉这些小人物的欢乐和悲苦,笔底下常常会有一种更加朴素的同情和理解。当然,《推拿》也还只是一种开始,毕飞宇能走多远,那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2011年10月于沪上
【注释】
①参见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辅仁学志》6卷1、2期,1937年6月。
②鲁迅:《关于〈小说世界〉》,《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