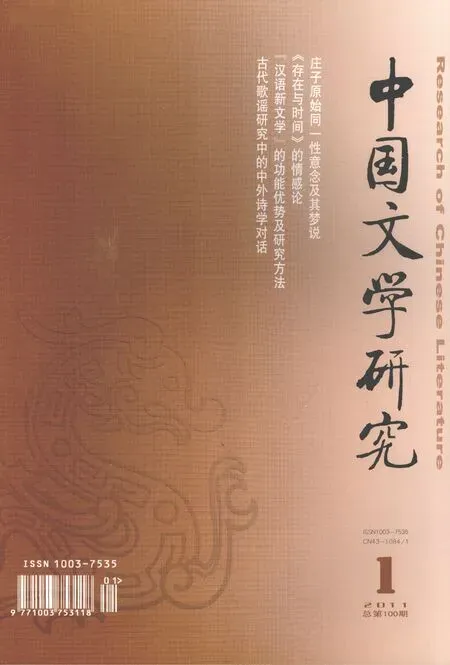语言共同体的建构与方言、土语的规训
——共和国初期的语言规范化与现代作家的语言观念
刘进才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河南 开封 475001)
汉语规范化与现代作家语言观念的转变
中国自秦以来,由于用超方言的方块汉字作为全国通用的书写形式,汉语书面语很快实现了统一,但汉语口语的统一却是一个长期艰难的历程。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民族统一语的建构密切相关。尽管民国以来的国语倡导与渐次推广曾风行一时,事实上由于国民政府政令不一,加之三十年代以后中国步步沦亡的危机现实,民族救亡占据了历史主导,虽然中国这一多民族的国家早已在血与火的抗战洗礼中建立起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但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之形成,更需要从民族统一语中获取观念支持。抗战中出于救亡宣传的需要,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对方言土语的重视,某种程度延宕了国语统一的历史进程。
共和国的建立为构建民族统一语奠定了坚实基础。时任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明确提出:“解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历史上空前的统一,全国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人们就越来越感觉到实用一种共同语言的迫切需要。因此,在我国汉族人民中努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1〕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的政府面临着国家统一、复兴经济的艰巨任务,汉语方言的严重分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不同方言区域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也进一步影响汉语共同语的成熟和发展,加之当时中国仍有80%以上的文盲人口,中国政府在文字改革方面采取了积极稳妥的汉字简化的方针政策,把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作为语言规划的共同任务积极施行。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拉开了汉语规范化的序幕。但规范化的标准语在当初并未达成共识,语言学界产生了各执一词的争论。这一争论不但关涉汉民族标准语的语音,也牵涉到汉语的标准语汇问题。当然,这种被后来学者称之为“千家争鸣”的标准语争论,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最终通过政策和法规得以确立:“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2〕会议强调了新的规范和标准的重要性:
推广普通话和实现汉语的规范化决不只是为着文字改革。无论为了加强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为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为了充分地发挥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交际作用,以至为了有效地发展民族间和国际间的联系、团结工作,都必须使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明确,并且推广到全民族的范围。〔3〕
规范如此重要,遵循规范也就无可争议。于是,对作家提出了严格要求:
语言的规范必须寄托在有形的东西上。这首先是一切作品,特别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因为语言的规范主要是通过作品传播开来的。作家们和翻译工作者们重视或不重视语言的规范,影响所及是难以估计的,我们不能不对他们提出特别严格的要求。〔4〕
任何语言规范一旦落实在具体的创作中,尺度很难把握。就文学创作所用的语汇而言,到底哪些属于标准语——普通话的词汇,那些属于标准语应尽力驱逐的地方方言词汇,界限并不那么清楚。况且,其间还牵涉到作家与工农兵相结合学习群众语言的问题,延安时期成为一时之风走向民间、运用方言创作的潮流与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冲突。
事实上,这一冲突早在建国之初的1950年就已经被语言学家敏锐地觉察到了。邢公畹情绪激昂的批评直指40年代末的方言文学创作:“‘方言文学’这个口号不是引导着我们向前看,而是引导我们向后看的东西;不是引导着我们走向统一,而是引导着我们走向分裂的东西。”〔5〕当然,邢公畹并未完全抹杀方言文学曾经肩负的历史使命及其合理性,他认为在过去的解放战争时期,支援战争的主要是农民,革命的阵地也在农村,因此文艺活动主要是反映农民的活动,而文艺作品所使用的表现中介主要也是地方色彩极为浓厚的语言(方言),方言文学只是当时斗争的策略之一。作为延安《讲话》后积极与工农兵相结合并努力学习农民语言的代表作家,周立波也参与了这场关于方言文学的争论,他从文学创作本身应有的艺术性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
我以为我们在创作中应该继续采用各地的方言,继续使用地方性的土话。要是不采用在人民的口头上天天反复使用的生动活泼的、适宜于表现实际生活的地方性的土话,我们的创作就不会精彩,而统一的民族语也将不过是空谈,或是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根筋。〔6〕
周立波不但把方言土语视作增加地方色彩、丰富语言表达、提高艺术魅力的手段,而且认为方言是建立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同时,他还借助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学习人民语言的有关理论资源维护方言土语的正当性:“毛主席指示我们说:人民的语言是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方言土语正是各地人民天天使用的活的语言,从学校出身的,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对于这种活的语言都不大熟悉……学生腔往往语汇贫乏,枯燥无味。”〔7〕周立波坚守方言的文学创作立场,在1952年谈《暴风骤雨》的创作经验时仍在继续:“写农民的对话,就得用农民的口语,要不写不像……”〔8〕。这种口语至上的语言观念与创作实践和随后不久逐渐展开的汉语规范化运动的确有龃龉之处。
“语言规范化”所要“规范”的“语言”主要是以书面形式存在和传播的文学语言,出于构建汉民族共同语的需要,语言学界重新界定了书面语言和日常口语的关系,五四时期提出的言文一致被重新表述:“我们必须首先对于书面语言和日常口语之间的关系求得正确的认识,否则就会产生各种偏差。或者过分强调它们的共同性,要求书面语言同日常口语完全一致,形成一种口语至上主义”,“如果这样,就会限制文学语言的发展,降低它的质量;同时,在目前的情况下,也很容易助长滥用方言俚语的趋势。”〔9〕
五四以后,新文学作品方言土语的运用一直是众说纷纭的难题,新文学革命初期出于更新并精密本民族语言的需要,欧化句式、外来术语的引入是许多有意强调而积极积推行的,歌谣运动对方言的整理是立意要在民间语言中采撷为建立统一国语可资利用的优秀资源。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既是对欧化语言的纠偏,也进一步把眼光投向民间,方言土语的运用得到大多数知识者的重视与认可。抗日战争的烽火促使文艺工作者从繁华的都市走向回响着方言土语的乡村,由于民族救亡、抗日宣传的区域性动员所需,方言土语再度进入知识者的视野,伴随着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以及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日渐展开,尤其是《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工作者的下乡改造运动,剔除知识分子腔、自觉向群众语言学习成为一时之风尚,文学作品能否运用农民的语言几乎是考量一个作家愿意还是反对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试金石。
共和国的建立要求与统一的民族国家建构相一致的民族共同语,现代民族共同语的语言规划必然对区域方言进行适度的规训和限制。作家、文艺工作者因而多了一层身份——“语言规范的宣传家”、“推广普通话的示范者”〔10〕。夏衍把汉语规范化提升到政治高度,提醒文艺工作者应该担当的重大责任:
语言混乱现象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是对于人民利益的损害,因此我们必须把语言的统一、汉语规范化当作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文艺工作者要通过语言来进行工作,而他们的语言又经常要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起示范作用,因此,在大力推广普通话和实现汉语规范化工作中,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是特别重大的。〔11〕
在这样强大的时代氛围中,作家不能不及时调整自己的语言观念和创作实践,即使怀着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真诚也必须有节制地运用方言土语。
非常反讽的是,曾经以方言创作获得巨大好评的周立波此时却成为批评的对象,这种批评恰恰针对其文学作品中方言土语的大量运用。文学作品运用方言土语借以提高传神功能的创作观念受到质疑和批判:“有的作家(像周立波同志这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在贯彻毛主席的关于语言问题的指示时,似乎只偏重于从方言的角度去了解,尤其偏重于从农村方言土语的角度去了解,去表现”,“在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行的今天,在方言土语只有日渐缩小使用范围的形势下,在这个时候还强调在文艺作品里尽量使用方言土语的话,非但对毛主席关于语言问题的指示的理解具有片面性,而且也不符合国家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总的要求。”〔12〕强调规范与重视艺术,孰轻孰重,语言学家和文艺工作者发生了不同的看法。作家往往从艺术传达的典型性和传神性出发,强调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必须与人物的地域身份相符,以传达出地方特有的情调韵味。面对汉语规范对作家方言创作的干预,有人仍坚守文学语言的审美立场,反对把小说作为“推行普通话的课本”〔13〕。
然而,在语言规范的强势浪潮中,这种声音显得极其微弱。作家逐渐认识到转变语言观念、调整创作实践的必要性。即使像周立波以方言运用为主要特色的作家,开始自觉提炼和加工方言土语。在1958年的《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一文中,他谈到:“我以为文学语言,特别是小说里的人物的对话,应该尽可能地口语化,但也要提炼、润色,要多少有一些藻饰。”〔14〕这提炼润色的工作呈露出向汉语规范的主动靠拢,与《暴风骤雨》中强调农民语言应原汁原味的语言观念判然有别。
老舍的反应显然比周立波迅捷,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汉语规范化的座谈会上,老舍以自身的话剧创作实践向人们表明向语言规范化自觉认同的语言立场:
我在《龙须沟》里本来用的北京土话比较多,演员们又给加上了一些,因此有许多人不能全部了解,演出就受限制,翻译也增多了困难,这给我的教育很大。我近来收敛多了。作家们用自己所熟悉的方言、土语,认为这样语言才生动有力。其实美不美倒不都在那些方言、土语,简明而有力就美……语言的统一是个政治任务,个人须克服自由主义,克服一些困难,要求自己在往统一的路上走的过程中有些帮助,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5〕
如果对照老舍写于30年代力倡话剧演出运用方言土语的有关文章,不难看出其语言观念转变之大——简明有力的语言观念代替了此前所坚守的方言土语所具有的自然真实的语言观念:
新剧的言语自然应该利用国语,但是为提倡新剧,就是全用方言,也无所不可。……在各地方演剧——除非是为国语运动——满可以用方言,以免去那不自然的背诵官话;——不自然便损坏真实。〔16〕
的确,当政治任务的重要性远远大于艺术真实的创作理念,恪守语言规范、为政治服务成为老舍的责任担当和神圣使命:
对于推行普通话,我也热烈拥护。以一个作家来说,我应该尽到我所能尽的力量去负起应尽的责任。我以后写东西必定尽量用普通话,不乱用土语方言,以我的作品配合这个重大的政治任务。〔17〕
作为“人民艺术家”,老舍非常清楚艺术工作者在方言向普通话之间转换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对于那些非北方方言区的作家/艺术家来说更是如此,他感同身受地指出:
一个生在某地的作家或演员,极其自然地愿意用本地话或一部分本地话去写作或表演,因为容易写的顺口,演的顺口。用普通话去写作或表演须费更多的事,费了事还不见得写得或说得够味儿。可是,这也是作家与演员更该努力苦学的地方。我知道,割舍摇笔即来的方言而代之以普通话是不无困难的。可是,我也体会到躲避着局限性很大的方言而代之以多数人能懂的普通话,的确是一种崇高的努力……〔18〕
老舍在这里所讲的“方言的局限性”,只不过是重提40年代方言文学运动中那些质疑方言文学的老话题,更何况,即使创作中引入一些方言土语也并不能一概称之为“方言文学”。如果仅仅从完成政治任务或担当责任的角度推广普通话并不能根本解决建立民族共同语的难题,必须借助新的语言理论资源,重新整合文学语言和民族共同语、方言土语和普通话的关系。
汉民族共同语语建构的理论资源
事实上,引进、借鉴新的语言理论资源的工作,语言学界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已悄然进行。
1950年7月11日《人民日报》整版发表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这篇近两万字的长文以问答形式回应了苏联语言学界围绕《真理报》展开的许多语言学问题。该文对民族共同语和方言的关系做了简洁权威的表述:“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最高形式,而把低级形式的方言、习惯语服从于自己。”斯大林把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作了等级区分,“低级形式的方言必须服从高级形式的共同语”这一观点在中国语言学界得到高度认同和发挥。斯大林对马克思语言学的独特阐释影响中国语言学界甚巨,以致语言学界讨论汉民族标准语问题“也必须以斯大林的学说为根据”。〔19〕那么,民族共同语是如何形成的呢?斯大林在这篇长文中指出:
在两种语言融合的时候通常都是有其中某一种成为胜利者,保存自己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继续按其内部发展的规律发展着,另一种语言就逐渐失去自己的质,而逐渐衰亡。
可见两种语言融合并不产生什么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其中的一种保存起来,保存它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使它能按其内部发展规律继续发展着。
斯大林认为民族共同语(即胜利的语言)的形成不是多种语言相互融合的结果,而是以一种语言为主体,从其他失败的语言中取得一些词而使自己的词汇丰富起来,俄国语言的形成就在于从其它语言中取得了许多词汇而充实起来,保存了自己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继续按照自己内部发展规律而发展。不同的语言学派对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有不同的理论观念,马克思曾经对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有过较为全面的论述:“在任何一种发达的现代语言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言语之所以提高为民族语言,部分是由于现成材料所构成的语言的历史发展,如拉丁语和日耳曼语;部分是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混合,如英语;部分是由于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20〕马克思谈到民族共同语形成的三种情况,马尔的语言融合论即是其中之一,马尔认为共同语的形成是在不同方言的共同发展相互渗透的多元竞争中融合而成,这一观点曾经在3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产生过深刻影响,方言拉丁化的积极推行者受马尔语言观念的启发即认为发展不同区域的方言,在交互融会中以形成统一的民族语言。马尔的语言融合论强调语言在融合过程中会从旧质到新质的突然过渡而产生第三种新型的语言。事实上,就前苏联而言,俄罗斯民族共同语是在库尔斯克——奥勒尔方言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并非像马尔所主张的在多种语言的融合中形成。斯大林的这一长文严厉批判马尔的语言学理论:“我们的语言学摆脱马尔的错误愈快,就能愈快地摆脱它现在所处的危机。我认为取消语言学中军事统治制度,抛弃马尔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语言学中去,这才会是苏联语言学健全发展的道路。”批判马尔的语言融合论,就意味着从另一方面肯定了以某一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方言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合法性。这一观念自然深刻影响中国语言学界,王力遵循着斯大林的思路对语言融合论做了清理和批判:“方言融合论其实是和语言融合论同一性质的东西。而大家知道,对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的语言来说,两种语言融合产生第三种语言的语言融合论是斯大林所不同意的。”〔21〕对于中国语言学界来讲,批判马尔的语言融合论意味着以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作为标准语的合理性。
1952年12月,《斯大林论语言学的著作与苏联文艺学问题》在中国翻译出版,对斯大林有关理论的阐释迅即成为中国语言文学艺术界又一可资利用的有效资源,该书对文学语言的重要性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论述:
文学语言乃是巩固和加强各个社会主义民族的团结和全民性的重要手段。为文学语言的全民性而斗争,为它的准确、易解、明晰、灵活、精密、丰富以及在语言发展的最优秀的、全民的民族传统基础上不断进行革新而斗争,同时也就是为社会主义民族的进一步巩固与胜利而斗争。〔22〕
苏联社会各界对于文学语言功能的强调,对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语言学界具有强大的示范作用和感召力量,汉语规范化正是凸显了汉民族共同语在巩固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中的重大作用。语言学家罗常培、吕叔湘认为“科学的发展,文学的繁荣,文化、教育设施的有效利用,政治、社会生活的顺利进行,无一不同语言的使用有关。争取民族语言的高度发展是民族意识增长、民族文化高涨的自然而直接的表现。”〔23〕王力强调汉民族共同语是汉民族的基本标志之一,“中国是一多民族的国家,在建国的共同事业上,也应该有一种民族间共同使用的语言”。〔24〕
晚清以降的中国现代语言规划,尽管北方方言作为权威方言的地位早已呈现,但以北京音作为标准音经历经诸多波折和争论。在1955年10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张奚若对普通话作了权威表述:“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25〕随后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既是对文字改革会议的呼应和支持,也是对汉民族共同语深入的学理探讨。尽管当时关于民族共同语仍有不同声音,两个会议的先后召开使各种声音逐渐统一到普通话这一由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所决定的汉语标准语上来。
语言在民族情感认同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6〕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建构统一的语言乃是巩固这一想象的有效途径。既然汉民族语言共同体的标准已经形成,文学创作对方言土语的限制和规训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1〕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6-7.
〔2〕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年2月6日)〔Z〕.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组编.语言政策学习资料(内部资料)〔Z〕.
〔3〕〔4〕〔10〕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N〕.人民日报,1955-12-26.
〔5〕邢公畹.谈“方言文学”〔J〕.文艺学习2(1),1950-08-01.
〔6〕〔7〕周立波.谈方言问题〔N〕.文艺报,3(10),1951-03-10.
〔8〕周立波.“暴风骤雨”创作经过〔N〕.中国青年报,1952-04-18.
〔9〕罗常培、吕叔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A〕.胡裕树编.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上)〔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92.
〔11〕夏衍.文艺工作和汉语规范化〔N〕.人民日报,1955-12-14.
〔12〕周定一.论文艺作品中的方言土语〔J〕.中国语文,1959(5).
〔13〕方明、杨昭敏.山乡的巨变,人的巨变〔A〕.评“山乡巨变”〔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35.
〔14〕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J〕.人民文学,1958(7).
〔15〕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召开汉语规范化问题座谈会〔J〕.中国语文,1955(7).
〔16〕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47.
〔17〕老舍.拥护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N〕.北京日报,1955-10-25.
〔18〕老舍.土话与普通话〔J〕.中国语文,1959(9).
〔19〕〔21〕王力.论汉族标准语〔A〕.中国语文杂志社编.汉族的共同语和标准音〔C〕.北京:中华书局,1956:1,4.
〔2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00.
〔22〕〔苏〕B.维诺格拉陀夫等著.斯大林论语言学的著作与苏联文艺学问题〔M〕.张孟恢等译.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1952:194-195.
〔23〕罗常培、吕叔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A〕.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C〕.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5.
〔24〕王力.论汉语规范化〔N〕.人民日报,1955-10-12.
〔25〕张奚若.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A〕.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C〕.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277.
〔26〕民族问题著作选〔C〕.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发行,1985: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