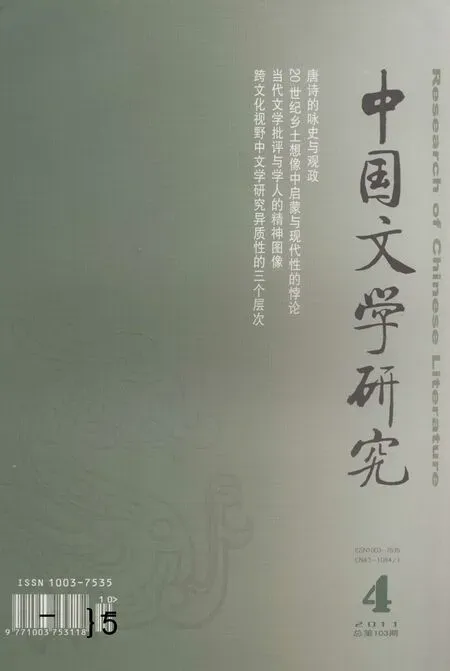被“遗忘”的“文学巨子”——王钟麒研究述评
邓百意
(海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王钟麒(1880~1913),字毓仁,一字郁仁,又字旡生、无生,号天僇、天僇生、僇民等,安徽歙县人。因生于扬州,故又自称扬州人。作为近代报界,特别是小说界非常活跃的一个人物,王钟麒引起当代学人的普遍关注,是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郭绍虞、罗根泽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文论选》,其中收录了54位近代学人的90篇文论,涵盖了文学史论、散文论、诗论、戏剧论、小说论等种类,尤以小说类论文收录最富。王钟麒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剧场之教育》3篇文论入选。以单个人收录文论篇目总数高低进行排名,王钟麒当排第6位,在梁启超(5篇)、金天翮(5篇)、王国维(4篇)、刘师培(4篇)、严复(4篇)几人之后。若单以小说文论言之,王钟麒以2篇小说论荣登总数榜的第3位,仅逊于梁启超(3篇)和吴沃尧(3篇)。此后,凡编选近代文论选本或者编写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王钟麒均成为一个重点关注的人物〔1〕。在近代小说理论研究界,王钟麒更成为一个绕不开的巨大存在,不少小说理论批评史为之开辟专节讨论〔2〕。随着研究视域的拓展和理论研讨的进一步深入,部分学者开始着手王钟麒个案研究,特别将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小说、戏剧理论及实践创作研究上。以颜廷亮的《王旡生的小说理论》,张恺的《“南社”的文艺理论家王钟麒》,颜廷亮、赵淑妍的《南社作家王钟麒的小说戏剧理论和创作》,左鹏军的《王旡生<血泪痕传奇>新考》,左鹏军的《王钟麒戏曲创作考论》、吴家荣的《一曲弘扬爱国豪情的颂歌:<孤臣碧血记>评》等论文的出现为代表,标志着学界对王钟麒的研究开始向纵深推进。张恺、颜廷亮、赵淑妍、左鹏军等学人在郭绍虞、黄霖、韩同文、陈平原、夏晓虹、王运熙诸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新材料,使得王钟麒作为近代文坛多面手的形象逐渐凸显。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始重新审视王钟麒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如颜廷亮、赵淑妍认为,“在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戏剧家中,有一些既在理论探讨上颇有成就,又在实际创作上很有建树的人物。其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南社作家王钟麒。”〔3〕甚之者,张恺认为王钟麒“在小说理论上却有显著的成就,成为我国近代文坛上一位努力学习借鉴中外优秀文学遗产并善于运用的小说理论家。在当时,他可与鲁迅、苏曼殊、马君武等齐名。”〔4〕以上学者给予王钟麒新的定位,其精准与否在此姑且不论,仅从他们新发掘的相关材料看(颜廷亮、左鹏军等人掌握的材料仍然是非常不全面的),就已经足以说明一点,王钟麒确实是中国近代文坛难得一见的多面手人物,必须对他投注足够的注意力。但是,论者仍认为,尽管一部分学人已经着手做了一些工作,至目前为止,作为辛亥革命时期沪上文坛被誉为“文学巨子”(此号出于高旭)的革命主将,王钟麒是受到学界众多关注的同时,又被严重略视的代表性人物。这个结论看似十分矛盾,然而是可以成立的。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虽然王钟麒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部分学人开始着手做一些拓展研究视域、加深理论探讨的工作,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王钟麒在近代文坛所具有的实际成就和针对他所展开的相关研究仍处在严重不对等的状态。
王钟麒的实践创作和理论文字是如此的丰富庞杂,论者目前已经查实的就包括小说创作(36篇)、小说译作(6篇)、小说专论(3篇)、戏剧创作(11篇)、戏剧专论(3篇)、其它文学论及学术论(16篇)、时论(293篇)、史地类著述(12篇)、诗话(4种)、词话(3种)、诗(38首)、词(13首)、骈散文(37篇)、不宜于归入以上诸类的其它类(82篇),用“著述宏富,卷佚浩繁”来形容丝毫不为过。与之相对应的王钟麒研究,却显得十分局促,仅有5篇论文以王钟麒的少部分小说、戏剧创作和理论文字为研究对象,专著类研究至今未见。各种相关研究(包括单篇论文和各类近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小说理论批评史)或将之归入资产阶级革命派,或以之为改良派的代表,在群体性研究中忽略甚至湮没了王钟麒个人的特色。所以,无论是材料开掘的广度,还是理论研究的深度,都远未臻于完善,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第二,已有的研究中,论述面比较狭窄,多将注意力放在王钟麒的小说、戏剧理论研究上,于其丰富的创作实践罕少提及。
经过论者近年仔细地发掘整理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王钟麒已经公开发表的各类文章总量当在450种以上(连载发表的作品均按1种计算),即便只限于小说、戏剧两个领域,王钟麒的创作总量也是十分惊人的:包括了小说创作36种、小说译作6种、戏剧创作11种。这些作品,直到1996年,才有人将《孤臣碧血记》一种提出来专门研究。至1997年,梁淑安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设立“王钟麒”条目,其中提及王钟麒的7种小说、3种剧本。2001年,颜廷亮、赵淑妍在《南社作家王钟麒的小说戏剧理论和创作》一文中,提及王钟麒小说16种(其中有两种尚存疑),剧本5种(其中不少篇目颜、赵二人并未亲见,仅有存目)。与论者现在找到的42种小说、11种戏剧总量相比,仍然有25种小说,6种戏剧未能进入人们的视野。至于文学理论类文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只有《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剧场之教育》、《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4篇文字为人们知悉,《中国四千年文学变迁大势论》、《欧洲文学革新论》、《论戏曲改良与群治之关系》、《悲剧自序》等非常有价值的文论则罕为人知。其中一些篇目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讨价值,甚至有可能推翻目前的某些成论。此外,王钟麒尤为丰富的各类诗、词、文、诗话、词话、史论、时论类文章一直散落在各近代各报章杂志中,总量300余种,无人查问,研究阙如。而这些文字,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王钟麒,颇有价值。
第三,从目前可见的各类研究成果看,以讹传讹、张冠李戴的现象比较常见,严重混淆了人们的研究视域。
相对于更早时期的人物个案研究,生活于清末民初的王钟麒距离我们现在的时代还不算十分久远,按理说一些基本信息不至有大的错讹。遗憾的是,目前可以找见的各类相关材料中,错讹之处是如此之多,使得我们目前亟待要做的研究,不得不从最基础的审定王钟麒的名、字、号、籍贯、生卒年开始。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比王钟麒(旡生)的出生年份晚10年,江苏吴县还有一个王钟麒(伯祥),他们的生存时代相差不远,都在20世纪初活跃于文界,都有文史类著述,这造成不少学人(包括柳亚子、郑逸梅等在内的一批人)论及王钟麒(旡生)时,把吴县的王钟麒(伯祥)也牵扯进来,指鹿为马,张冠李戴,严重扰乱了王钟麒(旡生)研究的视域。现在看来,只有搞清楚了这些最基本的情况,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综上可见,在近代文学领域,王钟麒其实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既有研究的主攻方向(小说戏剧创作与批评),同时还在诗、词、文、赋、文学史论、学术史论等各个领域都有不凡建树,是个难得一见的“多面手”;他既为研究界所熟知,同时人们对其认识与研究可谓“窥一斑而未见全豹”,尚局限于非常狭隘的范畴。
作为这样一个有着重大研究价值的“文学巨子”,如果对他的认识还停留在“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浅层次上,用3~5篇小说戏剧理论来涵盖他在近代文坛上的的全部成就,是很不公平的,也是非常短视的。在近代文学、文化学研究走向深入开拓的当代,柳亚子、于右任、刘师培、包天笑、贡少芹等历史文化名人的重新发掘整理工作都取得了大的进展,作为当时互为师友、成就不遑多让的王钟麒,仅以“著述宏富,什九散佚”作为交代,显得甚不合宜。
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未来的王钟麒研究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在大量挖掘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着手于基本信息的全面清理工作。
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各种资料的发掘、对比、甄别和整理,厘定王钟麒的籍贯、名、字、号、生卒年、生平经历等情况,全面梳集整理王钟麒的创作。
其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重点关注。其一是王钟麒报人活动的梳理。以1903年和刘师培一起赴上海谋求发展为界,王钟麒的生平可以分成扬州时期和上海时期。23岁以前,王钟麒长居扬州。此期他广泛阅读经史子集,积累了丰厚的学养,同时也开始接触近代新式书报,对时局颇为关注,初步形成了排满革命思想。23岁以后,王钟麒的主要活动区域转向上海。从最初的在《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江苏》、《国粹学报》上零星撰文,发展到担任《申报》、《南方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国民白话日报》、《安徽白话报》等报刊的专任主笔,再到与章士钊合办《独立周报》,“王无生”逐渐成为沪上报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就是在参与办报的同时,王钟麒加入了国学保存会和南社,与同盟会有着密切联系,亲自参加了江浙诸省联军为攻占南京而组织的系列军事活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还一度充任过总统府的秘书。这些经历,对于王钟麒的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其二是王钟麒的交游问题。王钟麒的交游同样可以分成扬州时期和上海时期两个阶段。居留扬州时期,王钟麒广交师友,与方地山方泽山兄弟、黄叶翁、宣古愚、周美权等并称“扬州五虎将”。此期交往最亲密者,有周美权、周学渊、方泽山兄弟、闵葆之、陈大镫、陈霞章、陈若木、陈心来、程善之、刘师培等人。至上海之后,王钟麒的交游更为广泛,所交之人多为寓沪进步人士,章士钊、林獬、陈去病、谢无量、马君武、陈独秀、高旭、柳亚子等,都和王钟麒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与“元老记者”于右任和“隐士儒宗”马一浮的密切交往,更是影响到了王钟麒的整个职业生涯和思想状况,与其特定文学价值观念的形成休戚相关。
第二,全面深入地展开王钟麒文学创作及理论研究工作。
在解决了材料问题的基础上,将王钟麒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总结结合起来,重点从当时的文艺思潮及实践创作的全面分析入手,重新给予王钟麒恰切的定位。仅以小说理论及创作研究言之,从1906年9月在《申报》上发表《论戏曲改良与群治之关系》开始,王钟麒相继在《申报》、《神州日报》、《月月小说》等报刊上发表小说理论文章。目今可见王钟麒有21种文论,其中8种为专论,13种为散论。小说理论方面,王钟麒非常注重小说纵向的“史”的流程的清理,第一次明确标举“小说史”的概念。在小说理论的作品、作者、读者3个层级,王钟麒都进行过相关的理论探讨。王钟麒的小说创作研究是王钟麒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直至1996年,还有人认为王钟麒只创作了一部《孤臣碧血记》。其实,从1907年开始,以《申报》、《神州日报》、《月月小说》、《安徽白话报》为中心,王钟麒全面展开了他的小说创作活动。经过全面梳理,论者一共查实了王钟麒的42部小说作品,其中36部为自撰小说,6部为译作。通过对这42部作品的全面研究,我们可以获悉王钟麒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以及小说题材、篇幅、语体、叙事等各方面的问题。小说、诗文等领域的理论与创作,亦可作如是观。
最后,想在此文中谈一谈学界曾讨论过的王钟麒的归派问题。
学术界发起王钟麒究竟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曰维新派)的探讨,是比较晚近的事情。阿英在20世纪30年代所著《晚清小说史》中提及众多小说理论家,其时并没有将梁启超、黄摩西、王钟麒等划归革命派或者改良派,因为在阿英写作这本小说史时,恐怕还没有改良派、革命派的提法。当然,也有研究者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不是没有将王钟麒划入哪个派别,根据“其内容,仍不外《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阐明”,“其观点也是从《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出发”,阿英是不言自明将他划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5〕1960年初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小说史》秉承了阿英的思路,没用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提法,而是笼统地说“其共同目的都是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服务的”〔6〕。1979年初版的南开大学中文系编著《中国小说史简编》也持相同态度。第一次将近代小说理论家按照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区分,并将王钟麒系于某派之下的,应该是舒芜编选的《中国近代文论选》。在该书前言中,编者承认了近代小说理论界有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分野,且将王钟麒系于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之下。稍后一些,王先霈、周伟民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也将王钟麒的小说理论系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之下加以讨论。第一次确立王钟麒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理论代表人物之地位的,是颜廷亮1980年撰写的《晚清小说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一文。在该文中,作者提出王钟麒“实实在在是个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尽管颜廷亮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文章中改良派的影响看来较多”〔7〕。其后,颜廷亮撰写了《晚清小说理论发展新阶段的一个标志——晚清革命派关于小说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论述》、《晚清革命派关于小说政治方向问题的理论》、《晚清革命派小说理论的历史地位》等系列论文,并获得了解志熙、高申鹏等研究者的应和,从而确立了晚清革命派小说理论流派研究。颜廷亮1996年出版的《晚清小说理论》一书,就是根据改良派和革命派来分布章节,王钟麒自然被归入到革命派中。刘良明、李晓莲、朱殊等著《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设“资产阶级革命派”专章,专门探讨以徐念慈、黄人、黄小配弟兄、陆绍明、王钟麒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理论。
目前来看,学界一般认同王钟麒“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理论家”的定位,从王钟麒的个人经历看,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不但为《警钟日报》、《国民日日报》、《江苏》等宣传革命的报刊撰文,而且历任《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革命报刊主笔;参加了以鼓吹排满革命为风旨的国学保存会的活动,是该会的正式会员;1909年加入著名革命团体南社,一度被选为该会的词选编辑员;因为撰文痛骂断绝人力车夫生计的洋人,遭到军警的通缉,四处避祸;与同盟会众多会员关系密切,于右任、马君武等,都是他的知交好友;辛亥革命期间爆发后,革命党人为光复南京,组织了江浙诸省联军司令部,王钟麒是该司令部秘书部的秘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王钟麒又被聘为总统府秘书处的秘书。从王钟麒的生平经历来看,即便他在晚期撰文反对过二次革命,但立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这也多出于政见的不同表达,并不代表他就背叛了革命,从一个革命者变成反革命者。凡此种种,从政治派别看,王钟麒是一个“排满革命家”,这是毋庸置疑的。另外,迄今为止也仍然有人主张,王钟麒未始不可归于改良派。因为从王钟麒撰写的几篇重要的理论文章来看,《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剧场之教育》都发表在《月月小说》上,《月月小说》由改良派人士创办,自然是改良派小说理论的刊布阵地。由此,在改良派人士创办的小说刊物上刊布文章,此人必归于改良派。更何况还有这样一个评价指标,那就是在看待小说与社会生活之关系的问题上,王钟麒与梁启超等改良派一样,都颠倒了小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客观地说,两种主张都有立论依据,也都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主张将王钟麒归入“革命派”的,显然有以政治派别研究代替小说理论派别研究的倾向,正如“南社既系革命文学团体,其小说理论家当然也是革命派,其小说理论当然也就是革命派的小说理论”〔8〕的表述显然有失公允一样,以是否参与了革命派的社会活动来决定王钟麒的派系归属,同样有武断之嫌。因为在近代历史上,很多小说家的政治立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林琴南算是典型的个案,王钟麒在后期也有摇摆的迹象。主张将王钟麒归入改良派的,很明显犯了先验主义的错误。在小说理论领域,经常发生这样的现象,被划归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小说理论家将文章发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章上。例如经常被看作革命派代表人物的金松岑,就曾将《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一文发表于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上。至于以小说决定社会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决定小说,来判定王钟麒的改良派派系归属,本身就是很荒谬的。文艺理论观点本不应与政治派系划归一谈,主张同一政见的人,其文艺观点不必尽合,这已经被近现代无数的例证证实。回到小说与社会生活的决定关系这个问题上来,辩证何者决定何者,本来就是辨析这个具体的理论问题过程中要走的必然理路,人们对小说艺术的认识,就是在这样的探讨中一步步清晰起来的。
在王钟麒的归派问题上,还有另外一种思路。《近代文学与传播》的作者包礼祥主张按照传媒的归属,王钟麒可以定为“国粹学派(革命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的成员还包括陆绍明、章太炎、黄世仲、刘师培、王国维、周树人、周作人。他们以《国粹学报》、《中外小说林》、《中国日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天铎报》等为媒介。包礼祥进一步说明,该派的特点是“既视小说为传播锐器,又把小说作为文学来研究,从发扬宣传国粹出发,重视小说史的学术研究。”〔9〕但是这又存在一个问题,包礼祥划分的另一派别“小报(商业报)派”中,《月月小说》是该派的主要传媒之一,王钟麒“小说界巨子”地位的奠立,恰恰依托的是《月月小说》,他的几篇重要的小说专论,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如此推论下去,王钟麒归入“小报派”亦无不当之处。可见,以媒体归属来分派,未始不是一种好的方式,但是由于交叉、重叠现象难以避免,它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个案。
综上可见,无论采取哪一种归派方式,都难免有可供攻击的漏洞。所以,论者认为,在具体分析到某一位理论家时,我们实不必纠缠于他的政治派别,更不能以政治派别研究代替文艺理论研究。这种判断放在王钟麒身上尤其适用。改良派也好,革命派也好,或是国粹学派也好,都只能说明王钟麒的小说理论体系中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倾向,这不是界定其小说理论优劣的客观依据,更不能以此决定其在小说界地位之轻重。我们要做的,就是立足于其理论文字本身,解读他在中国小说理论近代化的过程中实际起到的作用和应有的地位。
〔1〕如王运熙主编的《中国文论选·近代卷》收录《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剧场之教育》,黄霖、韩同文选注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收录《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历代小说史论》,陈平原、夏晓虹选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收入《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
〔2〕如王运熙、顾易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近代编第三章第四节即为“王国维与王钟麒、黄人的中国古典小说论”,刘良明的《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第四章第四节为“王钟麒与陆绍明”,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第七章第五节为“狄葆贤与王钟麒”。
〔3〕颜廷亮、赵淑妍.《南社作家王钟麒的小说戏剧理论和创作》.《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85页.
〔4〕张恺.《“南社”的文艺理论家王钟麒》.《江淮文史》,1996年第6期.第99页.
〔5〕〔7〕颜廷亮.《晚清小说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问题》.《西北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第72页、75页.
〔6〕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著.《中国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64页.
〔8〕颜廷亮.《晚清革命派小说理论的历史地位》.《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第56页.
〔9〕包礼祥《近代文学与传播》.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