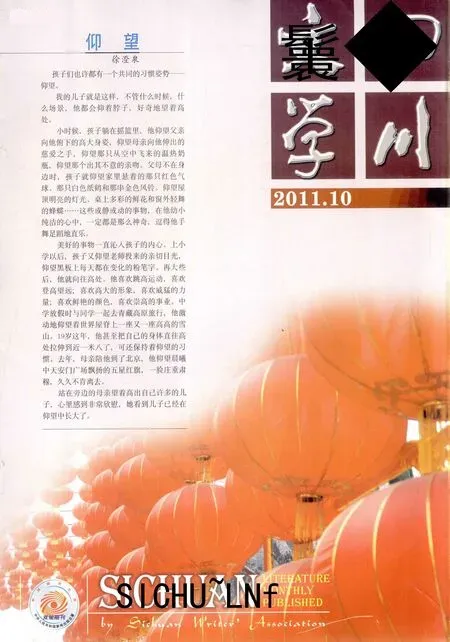彭山,无限的局部(二题)
□聂作平
彭山,无限的局部(二题)
□聂作平
象耳寺品茶
松柏入云,斑竹滴露。夏日清晨的象耳山,太阳将出未出,远近的山峦间游动着一缕缕淡淡的花香。应该是栀子花。开了一宿的栀子花,仍不知疲惫地把它淡定的香味揉进湿润的空气里。你伸出手,似乎能擒得住一些芬芳。此时,象耳寺便近在咫尺了。抬起头,能看到它那高耸的檐牙如同一只兽的脊梁,隐隐地埋伏在一片翠色的竹树中。
与川内众多知名的寺庙相比,象耳寺既无巍巍大山渲染名胜,也无滚滚长河衬托威仪,但这座藏在成都平原南缘众多高岗和低山中的古寺,却自有一种宁静的神韵。它就像一位清静自持的隐者,在滚滚红尘的纷扰之外,保持着自身的矜持与气节。
从小巧精致的彭山县城前往象耳寺,峰回路转,沿途多是川中寻常可见的稻黍和村落,人间烟火的气息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扑面而来。在距古寺还有十来里路的地方,必须乘船溯流而上。那条弯弯曲曲的河汊,夹岸都是苍翠的小山。竹树,山峰和村落的影子落在清澈的水底,原本平如镜面,偶尔一只翠鸟疾速地从天而降,飞快掠过水面,水底的竹树,山峰和村落便细碎了,模糊了,像是一张被揉皱了的风景画。
象耳寺因其托身的象耳山而得名。层峦叠嶂的象耳山,如同一头大象把鼻子伸进太白湖饮水,而就在神似象耳的地方,象耳寺拔地而起——这是一座虽然袖珍,却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寺。可以说,近似大象的地貌虽然原本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但当初的佛教信徒们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修建这座香火鼎盛的寺庙,却和这种地貌密切相关。以佛教观念来看,大象是吉祥神圣之物,据说释迦牟尼的母亲就因梦见六牙白象入怀而生下释迦牟尼,是故佛教又名象教;至于被信徒们广为供奉的普贤菩萨,其坐骑也是一匹白象。因而,在象耳山上修建寺庙,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在象耳寺,被唐代诗人描述过的这种景象乃是鲜活的现实。当阳光透过树梢照射下来,夏天的喧哗与炎热,仿佛已被那十里太白湖和远远近近的群山以过滤的方式通通谢绝。悠扬的钟声虽然就响在隔壁,听上去却像隔了大老远的距离。
就在这座古寺,高僧来过——据记载,隋朝的法泰,唐朝的道会,宋朝的圆觉和清代的大耳,都曾在象耳寺静修。同样是这座古寺,文人来过——宋朝诗人兼画家文与可(也就是留下了胸有成竹典故的那个人)曾在象耳寺多次盘桓,并为象耳寺写下一首诗:转谷萦岩路始穷,隔林遥望一门通。溪山俱在见闻外,台殿尽藏怀抱中。像阁罘崽明海日,轻幢璎玲撼天风。
如今,古人的脚步已成空谷绝响,但这座历尽沧桑的古刹还在,古刹前后宜人的风景也还在。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进入古寺之际,初升的太阳有一种异样的温暖和瓷实。寺中僧侣不多,香客亦稀,却更以这种略显冷清的寂寞,彰显古刹风骨。
游罢寺庙,接下来的重要事情是喝茶。
彭山古称武阳,历来就以盛产好茶而闻名。汉代文学家王褒留下的一纸买卖奴仆的字据里,为我们保存了两千年前彭山即为著名茶市的明确记载。在这纸字据里,有所谓“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的说法,由此既可以断定,当时饮茶已是民间普遍习惯,而武阳即彭山的茶市则远近闻名。
茶是今年春天的明前。色泽微黄的茶水,散发出一阵淡淡的茶香,恰似来途时闻到的那股栀子花的味道,同样的淡,同样的若有若无,却叫人能从那份淡和那份若有若无之中,品味到一种欲罢不休的魅力。
坐在大雄宝殿一侧的过道里,眼前是黛色的青山,更远处是同样黛色的湖水,耳畔偶尔回荡着断续的钟声与杜鹃的啼鸣。朋友们止住了说笑,天地间便是浑沌初开一般的沉静。天下名山僧占多,与峨眉青城相比,象耳山只能算小有名气,但我以为小有名气的象耳山,它的含英吐华,它的淡如禅境,其实并不比峨眉或青城更差。如果硬要说差的话,那就是它的规模过于小巧,但小巧同时也意味着精致,就如同眼前这盏连名字也没有的清茶,它比那些广而告之的名牌,少了一份喧嚣,却多了一份自在的山野之气。在这个过于快餐和浮华的时代,这气,城里人已经很难寻觅得到了。
放眼宇内,如同象耳山和象耳寺这样的非著名景区,其实并不少,但少的是如同我等的闲情与闲心。当你天天念叨着时间就是金钱,当你吃着盒饭加着夜班,当你不得不用记事本来提醒自己每天要干的甲乙丙丁的工作,你能想象得出开一小时的车再坐半小时的船,到一座山中的古寺喝一杯非名牌的清茶吗?
那茶,便在你的忙碌之外,远了,去了。
江口镇怀古
四川江河众多,水网密如蛛网。这众多江河中,我以为,对四川历史文化影响最大的,首屈一指便是岷江。尽管与其它几条大江大河相比,岷江的长度和水量都不能名列第一,但它造就了成都平原,而成都平原,则造就了名闻遐迩的天府之国。可以说,四川的精华集中于成都平原,而成都平原的精华则集中于岷江两岸。
彭山的面积不到五百平方公里,算是一个小县。岷江结束了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之旅后,便一头扎进了彭山的怀抱,将彭山分为了东西两岸。历史上,彭山的县治几度在东西两岸搬迁,但无论如何搬迁,总是与岷江唇齿相依。
如同岷江流经的众多地方,都因得地利之便而催生出城镇与繁华一样,江口镇也是岷江的产物。准确地说,是岷江两水分流之后又交汇的产物。原来,岷江流到成都附近,一分为二,一为府河,一为武阳河,两河在各自行进一段路程之后又合二为一,人称下岷江。这二水合一、下岷江开始的地方就是江口。
在两千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岷江一直是四川最重要的交通网络,而地处两水交汇处的江口,自然得天时地利,从而跻身四川历史最古老的城镇行列。今天的江口镇已然彻底衰败,但这种衰败,却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深入历史的线索。那窄窄的石板街,仿佛还回响着昔日走南闯北的水手和商人的脚步声,那高高的吊脚楼,依稀还能透过岁月的迷雾,看到那曾经高挂的大红灯笼,和灯笼下鳞次栉比的商铺。
作为成都与乐山之间最重要的水陆要津,据史料记载,江口极盛时,这个只有一条沿江而建的狭长街道的古镇,竟有多达五十个以上的码头。从上游运往下游的是洋布,烟草,药品,大米,从下游运往上游的是盐巴,烧酒,草纸,鸡鸭,蚕茧。每天在这里集散的船只多达三四百艘,而来往的从业人员更是多达四五千人。因了水陆码头的重要,江口除了是货物集散地和交通要津外,这里丰富的物产也形成了一系列知名品牌,如江口草纸,江口船钉,江口大头菜,江口晒芋…… 那些一辈子在江口大地上劳作的人们,虽然他们的行踪可能最远就到过咫尺之遥的彭山县城或是稍远些的眉州城,但他们的产品却代替他们走遍了巴山蜀水。明清之交,张献忠的运输船从这里的江面经过,被当地武装击败,船只沉没,大量财宝随之没入江水。至今,仍然不时有人从这片平静的江水中捞出金银。
随着公路和铁路交通的发达,人类的行走与运输不再依赖江河,那些因水而兴的城镇便一下子成为明日黄花。江口镇也一样,它那曾经人来人往的码头渐渐荒芜了,祭祀河神祈求平安的龙王庙,也只剩下了风中的残垣断壁。至于那些曾经在大红灯笼下出没过的面孔,不论是孔武有力的水手还是富态自得的商人,抑或写满沧桑的江湖豪客,他们就像太阳升起之后河滩上的一团团雾气,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还有一些更加坚硬的东西,固执地遗留下来,成为岁月曾经垂青过这座古镇的有力证词。
江口镇外那密集的汉墓就是证词之一。四川境内,汉墓遗迹颇多,这从另一个角度反证出,当我强汉之时,四川虽然远为边地,却也繁荣异常。汉代盛行的丧葬方式是依山掘洞,著名的郪江汉墓就是其代表,而江口镇外的汉墓,虽然从规模和数量上比郪江汉墓稍逊一筹,但其出土的文物却以其精致而著称。比如那被郭沫若称为天下第一吻的男女相拥浮雕,比如描绘男女交媾的画像砖,无不以其栩栩如生的造型,给我们这些两千多年后的来者一种震撼:就在这里,就在这方岷江滋养的土地,我们的祖先曾经像我们今天这样:爱过,恨过,笑过,哭过,来自于尘土,复归于尘土,天地间除了史料上的只言片语,除了口耳相传的民间记忆,便只有这些无言的崖墓为他们的生存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