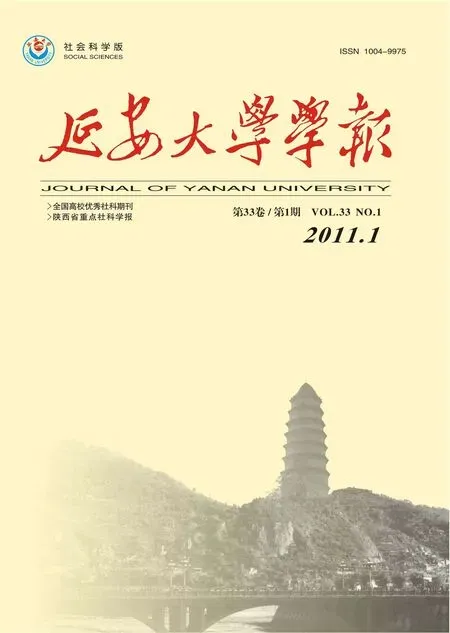中国传统农民的生存安全追求
——以陕西洛川居生村为例
樊志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陕西杨凌 712100)
居生,是陕西省洛川县杨舒乡的一个小村落。笔者生于斯长于斯,二十岁后方离它远游。由于能回家的机会少了,关于故乡的回忆反倒多了。小时混沌、朦胧的印象和记忆,随着年岁的增长越发显得清晰、明暸。细理思绪,许多经历的事情竟与自己钟情的研究领域息息相关。若能将少小见闻置诸相关专业、知识背景下去重新分析、认识,亦不失为了解传统农业、农村与农民的有效途径之一。当然动笔之冲动,也不排除特有的情感因素。若不留下些许文字,谁会关注到僻远的山乡、平凡的百姓,岁月的进程也会淡漠了我们的记忆。随着城镇化与非农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当年熟知和常见的东西也将逐渐消失。我写我的家乡、我的父老兄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中国的农民立传。
“居生击死”乃军事述语,以居生为村名或许涵含着先民们追求平安的良好愿望。研究中国农民历史的学者,将较多的精力放在了对农民贫富问题的关注上,而忽略了其生存安全的保障问题。若果安全出了问题,家身性命难保,纵有万贯家财也尽付流水。中国古代农民的农业生产所得,在维系基本生存与缴纳国家赋税后,比较大的份额都花费在了自身安全的保障方面。尤其在边远地区与战乱时代,保护性命与财富不受侵夺更具重要意义。
居址的安全选择
村落居址的选择,首先考虑的是环境与自然因素。因为居高易旱、处下易涝、依山易崩、濒水易洪,一旦遭遇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便成灭顶之灾。诗有公刘迁豳,选择居址的记载。“相其阴阳,观其泉流”的话头,意味着陵水高下必得其宜。中国古代大凡有一定历史而且颇具规模的村落,往往是规避了不安全因素之结果,它是凝聚着先民智慧的安全选择。
居生村座落在洛川县西南隅,隔洛河与黄陵县毗邻。据堪舆家说,该村大背景是北依柯山南临洛水,得山南水北之阳;该村小环境是于高平处选凹形低地择居,有四方辏附之效。故居此地者必大宜子孙、谋事有成、安居乐业,如此说法给居生村平添了几份神秘色彩。过去偏颇地认为风水是迷信数术之一种,缺乏比较客观的认识与评价,其实它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先民们环境选择的经验与知识。钱大昕《恒言录》卷六认为“古堪舆家即今选择家,近世乃以相宅图墓者当之”。农业民族安土重迁,最为看重的就是生前居址及死后葬地。前者事关他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后者体现的是事死如生及对先祖魂灵之敬畏。大凡居住于北回归线以北的农业民族,对居址葬地大致有着相似的选择。它们一般都位于山之南水之北,呈坐北面南向。山南、水北为阳,秦都居渭水之北、嵕山之南,山水俱阳故谓之咸阳。这种地势向阳避风,是风水学里的绝佳形胜之地,也是农业民族生活居址、死后葬地之首选。如果山的两翼外伸,中间内收,则成典型的箕形地势 (陕西人称之为岰里),向阳避风效果更佳。这样的风俗习惯自古迄今一脉相承,凡是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一点。居生先民卜居于兹,也是遵奉了这一基本原则。在仙姑河与洛河交汇处,黄土高原的三块塬面呈“品”字形地势逶迤相联,居生村恰在其中。除了村西南有一涧水直通洛河外,由西北、东南两翼合抱成一弧形封闭低地。每当冬春二季,居村外则寒风怒号、朔气凛冽,入村中则风平浪静、春意盎然。
居生村人户近百,自笔者记事以来没有发生过较大的环境与自然灾害,这在黄土高原灾害频发区是很少见到的。居生村地处海拔千余米的黄土塬面上,虽高而毋近旱,这或与当初村址选择有关。雨后四方径流齐汇村中二塘,池中戏水成为儿时最快乐的事情。先民们因地制宜于此开凿池塘 (中国北方称之为“涝池”),既资生产、生活之用又可弥补风水不足。即使以现代水工科技考量,居生的涝池设计亦独具匠心。当四方来水相汇村中后,于戏楼广场南侧设四“V”型水门以迎。“V”型设计口阔尾狭,可拦大型漂浮物不入池,水少则兼收并蓄,水多溢洪旁流。水出石门沿石砌阶梯而下,浪翻白,流有声,然后经数米跌水落入塘中。夏日雨后,这里是戏水观瀑的绝好去处。池塘有二,一曰“滗泥池”,二曰“清水池”。二池以渠相联,来水经“滗泥池”稍事沉淀后再入“清水池”。“滗泥池”设置有精巧的溢洪设施,池水超过一定水位即由溢洪道排出。池塘周围是窑场的世界,砖瓦陶器皆烧治于此,入夜之后窑火映红天际;池塘边是妇女和儿童的天堂,秋山响砧杵,牧童骑牛泅,顿增几分祥和气氛。在黄土高原水资源相对比较匮乏的情况下,有容量数万方的池水以调剂余缺,基本上可以做到水旱从人。不过若遇暴雨,也容易发生问题。某年因降水量太大、太集中,致使“清水池”溃决,使下游一村落无辜遭受飞来横祸。双池失一,村中耆老或谓不祥,其实它反映的是黄土台原地区因水土流失而渐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此后每逢雨期,村中老少最为担心的莫过于“滗泥池”能否容得来水。若有渗漏、管涌、溃塌,必举全村之力共同应对,如临大敌。池塘容水量有限,余水多由数十米土崖直泻深沟,故有大雨必有崖崩、滑坡发生。据长者相告,村南沟壑在他们记事时仅宽数尺、深丈余,玩伴们常以往返跃越为趣。而我辈见到的南沟已是临崖俯视深不见底,隔沟喊话必尽全力。沟壑切蚀,逐渐危及村中道路、房舍,基于安全考虑于是渐有迁村之议。
居生新村选择在村东比较宽阔的塬面上,地近交通干线,有就近农作之便。但是生产、生活用水全凭一口深约 60m的水井供给,村民农事之余,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村北深沟取水或去邻村拉水。后来虽然有了机井,老百姓买水做饭尚要精打细算,买水饮畜则被认为奢侈。择居黄土高原不考虑水的因素,生产生活举步维艰;考虑水的问题,则必须应对水土的侵蚀与流失问题。居生村在水的问题上,遇到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难题。
院落的有效设计
小农是中国古代农村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形态,有效的院落设计与建设是小农安全的第一道屏障。
黄土高原老百姓的居室,一般有窑洞和房厦两种。窑洞有在平地以砖、石箍成者,窑址多是经主人择选的宜居之地。由于比较多的考虑了方位、安全诸因素,砖 (石)窑往往要投入较多的人、财、物力。家有窑洞之大小与多少,成为判断主人财富和身份的重要因素。农村谈婚论嫁,除却察家风、审容貌诸程序外,是否有 (砖)石窑洞也是婚姻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依地形在山麓、崖边、砭畔挖洞入住者,谓之土窑。黄土堆积有先后、质地有疏密,所以在不同地层挖窑洞也大有学问。距地表近者,土质比较疏松,投工用料也比较省捷,但容易发生渗陷、坍塌;距地表深者,土质比较缜密,若遇礓石土层费工费时不亚于箍砖 (石)窑,但这类土窑比较坚固耐用。
陕西八怪中有房子半边盖的说法,当地把两边盖的称房、半边盖的叫厦。凡盖房者一般都是南、北向,而盖厦者一般都是东、西向。何以盖厦流行于关中与陕北地区?其一曰条件制约,当地木材短缺,尤其是檩、梁类大材不易获取,只好退而求其次,因材制宜盖半边房;其二曰风水使然,南北向箍窑盖房,依东西两边院墙相向盖厦,有聚气凝神之效。以上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更有可能的是基于院落安全护卫的考虑。房子两边盖,外侧屋檐前伸降低,易给匪贼劫窃之机;厦子半边盖,既有之院墙上加砌山墙,客观上有增高御敌之用。
居生民居中赵姓基本上都是砖窑,樊姓除了前述旧院落有若干砖窑外,居土窑者不在少数。村中盖房者,一为庙宇;二为祠堂;三为富户。庙宇、祠堂乃祭祀、聚会场所,故用大材以增大空间。这类地方除却神像、香火并无若干财货,匪贼亦不敢擅入此地亵渎神灵。富户有财力,故亦有购巨材以盖大房者。但凡盖房者皆增垫台基以升起架,既显巍峨气势亦防窃贼飞檐走壁。一般百姓大多是南向以箍砖 (石)窑三、四孔,然后东、西两厢各盖厦子数间。若有余力,再依南端门墙北向盖厦,以为磨房、厕所或杂用。以上建筑形成了一个外高内低的组合空间,有效地提高了住户的安全系数。
居有其屋是农耕民族的最基本需求,但是能否抵御自然与人为的不安全因素,往往和基建设计与投入具有很大关系。黄土高原精巧的民居院落设计,是在历史与自然的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安全保障功能的强化是其特色之一。
国家的保护功能
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对峙、冲突的非常时期,国家力量是否有效的防御与保护,对边远地区百姓的生存安全是尤为重要的。
文物考古界在陕西发现了数量很大的宋明城堡遗址,这些城堡遗址大多分布在宋与西夏、明与蒙古族接壤的陕北地区。它们呈串珠状向内地延伸,其间以道路和烽火台相连接。烽火台作为陕北至关中的主干驿道及其支线上的通讯设施,在延安各区县呈网状分布,几乎构成宋明陕北文物的主体。这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对峙情形下,在前沿地带留下的军事遗存。主干驿道或称之为“官塘大道”,所以老百姓至今仍将因车马行人碾踩而起的细土叫作“塘土”。主干驿道沿线的烽燧大概每十余里即有一座,相望点燃的狼烟可以确保前线与朝廷间军事信息的快捷传递。洛川县城南北农田中残留的烽燧遗墩,曾成为幼年去县城读书时辨向、认路的标志之一。
以往的军事史对主干驿道上的主干烽燧关注的比较多,而忽略了支线上网状散布的烽燧群的功用,从而缺失了对古代战争的全面了解。少数民族的进犯目标固然在于京师重地,但是最终能抵达者毕竟是少数。他们往往以对沿途涉战地区的劫略与破坏,迫使中原王朝做出某些退守与让步。中国古代的民族矛盾、冲突与战争,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往往以涉战前沿与民族过渡地带最为严重。如何应对残烈的战争破坏,保护军事前沿地带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网状烽燧群的建造是一大发明。若遇险情狼烟四起,一方面有陷敌于汪洋大海的震慑之效,另一方面亦有预警避险之用。
黄土高原多梁峁地貌,梁是川原之间的条形接续地带,峁乃梁上之丘形高地。由于地形破碎,一般百姓择居梁峁者较少。但是梁峁间沿等高线建造的阶梯式农田,往往成为黄土高原的一道景观。虽然近现代以来人口剧增,但仍有大量梯田处于弃荒状态。是何时何人垦辟了这些土地?作者虽颇为熟知陕北史地,但仍难得其解。后求教于文物考古工作者,他们认为大多为宋明时期军屯、军垦遗迹。军屯以服务于军事为目的,以便于据险筑城、择高设燧、临塞驻军为原则,一般不可能太多地顾及是否宜于农业开发的问题。而梁有沟通川原之便,峁有望远预警之优,于是就成为屯垦与设置烽燧的首选地带。居生村东亦有一首尾低浅而中部高隆的山梁,在山峁的最高处筑有一方形土台,长期以来被视为山神祭坛。环台依次修筑了面积可观的梯田,近代以来虽有地狭人众的村落寄种于此,春来秋回形成颇具特色的“吊庄”经营,但垦耕面积仅占已成梯田什之二三。该山梁具有众望所归的地形优势,川塬间数十里皆在其视野之内,并与周围村落的民间防御工事之间存在着某种呼应关系。这些年赴陕甘各地考察,发现凡有高亢地貌者亦多有夯土台墩,乃知此种情形或为通例、这类建筑多为烽燧。于数村之间择高地以建烽燧,形成了联动预警和互保机制,可以有效避免战乱时期遭受大范围的劫略与破坏。
汉唐之间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般是由不同的产业结构所导致的,表现为“农国”与“行国”的矛盾与冲突。匈奴、突厥等民族具有浓郁的游牧经济特征,他们没有太强烈的“地著”观念。追逐水草丰饶、牛羊肥壮是牧民的基本祈求,而季节转换、气候变化、国力强弱往往成为决定他们来去移徙的关键因素,农牧分界线也随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实力之消长而南北移动。秦汉隋唐时期的民族矛盾与冲突虽然甚为惨烈,但对峙方式往往是间歇性的。一场大的战事过后将意味着较长时段的相安无事,这也为北方相对脆弱的生态与植被提供了更生的机会。唐以后的辽、金、西夏诸国虽然在民族构成上与两宋王朝有所区别,但在经济结构上却与呈现出明显的趋同倾向。少数民族的农业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南北政权的对峙形式。由于互为“农国”,在北方地区的民族对峙形式也由间歇性对抗发展到持续性对抗。
可持续的军事对峙,保障了生存安全却破坏了生态环境,某些代价甚至是无法弥补的。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宋以后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生产结构趋同、对峙方式持续很可能有直接关系。
村社的合力应对
中国古代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乡绅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农村长期保留着聚族而居的习惯,在儒家的宗法制度与礼乐文化的影响下,村社共同体也承担了乡村社会某些日常秩序与治安的维护功能。由于国家基层行政职能的缺失,一方面村社势力容易与中央集权产生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又需要利用村社力量维持应对社会治安问题。对村社势力的控制与利用,构成了数千年中国乡村治理中难以两全的命题。
首先,是宗族的抚育赡养、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功能。宗族是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世代相聚在一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作为基层的社会组织结构,为中国农业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农村宗族制度有三个基本要素,即祠堂、族谱和族田。待我记事时族田已不存在了,原来由族田收入用于祭祀的相关支出,改由家族轮流承担或集资分担。但是续族谱仍在进行,娶妻生子登录族谱成为严肃、庄重的宗族活动。族谱记录宗族的起源、繁衍、迁徙,并通过对人物、事件的褒贬以规范族人行为和实施教化功能。祠堂是宗族活动的中心,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行使宗族权力的地方。居生有樊、赵两姓,大人年节相见互问安好揖礼有加,但祭祀活动多隐含攀比、较劲意味。在以传统小农经营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个体农户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是比较弱的,宗族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变个体为群体之功用。在各宗族内部随着人丁的增加,实际上即使同族之间平时联系、走动也不一定很频繁,甚至也会为一些零琐事情产生矛盾与冲突。但逢外来压力与威胁时则必阖族应对。尤其是在与异姓或邻村在水源、田地、山林等问题上发生纠纷时,宗族力量强弱往往成为胜负的决定因素。
国家政权对宗族势力的心态,大约随着国势强弱而变化。在国力强盛的时候,一般侧重于对宗族势力的控制;在国力虚弱的时候,一般侧重于对宗族势力的利用。秦汉时期地方宗族豪强势力干扰政令,与中央集权形成尖锐的矛盾与冲突,故常遭遣散与打击。而魏晋北朝时期战乱灾荒频仍,当国家基层行政难以正常履行职能时,宗族共同体在抵御异族入侵、保障社会生产发展方面发挥了某些正面作用。宋明以来大量出现的乡规民约,一方面是为了约束规范族群的行为,另一方面主要是为了应对危及族群的社会问题。
其次,是民团组织的武装自卫、治安维护功能。《水浒传》中有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祝家庄不仅拥有自己的武装,并且相邻的鹿家庄、李家庄实行了三庄联防。乡村农民拥有自卫武装,这对国家而言是一股异己力量。但民团的建立是得到统治者认可的,它在某种程度上补充和延伸了国家机器的某些职能。民团是乡村治安恶化的产物,尤其是国家政权不能给老百姓以有效保护的情况下,农民以自我武装的方式来应对外来侵扰。民团基本上属于防御性的武装组织,其职能主要是抗击土匪。土匪绑票勒索、打家劫舍,是旧中国危害乡民生命财产的一大祸患,这种状况在县以下农村尤为突出。居生赵姓有排行老七者曾在军队当过连长,回乡后以财富相号召,组织民团自任团长。有人认为民团这种民间武装组织,兼具对内的防御性与对外的劫掠性特征。赵团长对内尚有“兔子不吃窝边草”之良知,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庇佑村民不受外来势力欺凌。某些盗匪虽常觊觎居生村民财富而不敢枉动者,皆有慑于赵团长之声威。同时他也凭借武力,对外干过一些劫掠、仇杀的勾当。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洛川地处陕甘宁边区南缘,为出入延安之必经通道。毛泽东曾称“(介子河)河南、河北两个世界”,由于红、白势力错综复杂,故洛川之乡绅官宦大多都与国共双方都维持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可谓“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
民团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靠乡民自筹,以户为单位根据耕地数量和家庭人口按比例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粮。在有些地方也有完全由富户承担民团经费者,他们因此而掌握了民团的领导权,民团性质也就由农民自卫组织演变为地主武装。民团经费对农民而言是一种额外的经济负担,而且这种负担与社会秩序的混乱程度成正比,盗匪愈严重农民的负担也就越沉重。中国古代每逢乱世,农业生产遭受的破坏尤为严重。究其因由大致有三:一是正常的生产进程无法维持;二是苛捐杂税负担太重;三是将大量的人力、财力用于应对不安全因素。
多样的防御工事
居生村的民间防御工事数量众多,规模宏大、类型复杂,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景观。这里有贯通全村的地道(当地称作窨子);村东村西各有一处依山形建设的山寨;还有规模巨大的城池。
居生村东西南北向有四条道路与外界相联,千百年来由于车马碾压、行人踩踏与风雨冲蚀的交互作用,形成黄土高原颇具特色的“路壕”(村民俗称胡同)景观。“路壕”之浅深短长,成为判别村落历史年代的重要依据。居生村的四条胡同,除北胡同稍显浅短外,其余三条皆以深遂悠长而著称。冬夏行走于胡同中有避暑遮风之效,而每逢雨天四方径流沿胡同汇聚于村中池塘,这些均曾被视为是居生“风水”好的有力佐证。其实胡同也具有重要的防御功能,胡同乃入村必经之地,于四方胡同出入口设卡则可御敌于村外。村西由于路壕切割形成一楔形土梁,俗呼“土牛”。“土牛”由西向东缓降入村,村民筑墙以续“牛尾”,逶迤数里气势雄伟。牛首作为村西制高点,构筑简易工事,兼具护卫功能;牛尾实为崖畔堞垛,以防人畜失足跌落。
幼时看《地道战》,始知地道之神奇功用。不过冉庄的地道是用来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居生的地道是用来对付土匪的。陕北农村习称地道曰“窨子”,实际上地道与窨子或有些许差别。地窨一般指 L形竖洞地窖,它原来是农民用来贮藏农产品的。后来发现遇到危险时可作藏身之用,于是地窨就成了个体农民最原始的避难所。地窨有入口无出口,可以藏身但无法逃逸。多家地窨横向贯通也就成了地道,地道是村民联防而形成的地下工事。地道有入口有出口,既可藏身又可逃逸,尤其是敌匪占领地面、把守入口的情况下,可以避免更大的伤亡。地道在村中有若干隐密入口,出口则通向野外或有设防的寨堡之中。地道是村民在日积月累中形成的地下防御工程,但是它投入的人力、物力是相当大的。居生村东西绵延数里,南北亦有数条侧道,若以 2m高、1.5m通计高、宽,单土方量即已近万。地下施工多有不便,这对一个只有数百口人的村落而言工程量是相当惊人的。
居生村东、村西又有两座寨堡。它是选择黄土高原三面绝壁的土梁,在与塬面联结处作地堑断面而形成的一种防御设施。村东寨堡比较简易,地面并无若干建筑物,在崖壁上凿出洞穴以作栖身之地,这种寨堡只作临时预警、短期逃难之用。村西寨堡规模宏大,由地堑掘洞百余米而入寨。寨中房屋栉比鳞次,各有归属,俨然是村落的再复制。寨中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若遇险情则移粮食牛豕什物入寨,可作长久坚持计。可以做到贼近则入寨守御,贼专则出入耕作。据老者相告,清末陕甘回变一支途经居生,围此寨数日而不下,全村生民性命得以保全。后来有贫穷或子嗣多者,无力于村中再修房舍,只好以寨中房舍为家。寨堡也就从战时的临时居所,逐渐演变成为正式的聚落。
筑城坚守,则是民间防御工事的最高层次。赵姓乃居生富户,他们聚居的村东一带依山势成数排建筑,首尾相接构成所谓的环形院落。“环院”入口处有巨型门楼一座,来人不需下马落轿即可径达馆舍。入门有一广场,皆以砖石漫地、饰花卉、置盆景,乃客流缓冲地带。西侧为赵氏祠堂,择高台以示庄严,建广廈以显气势。逢年过节赵氏门人长幼咸集,通过祖先祭拜以增强族群的凝聚力。广场正北为客舍馆驿,曲尺形阶梯将落差数十米的五孔窑洞、数十间瓦房联成一气,客舍装饰极尽富丽。赵氏祠堂后是颇为神秘的府库所在,高墙四围、小门小窗,建筑以厚重坚实见长。赵氏家业兴盛时广置田产,甚至将农地买到了邻村周边。解放后历数十年人丁增长,居生村人均土地仍达十亩左右。赵氏又广设门面字号,关中、陕北皆有产业经营。“日进斗金”虽稍显夸张,但起码相当富庶殷实。清末兵匪之患日趋严重,赵氏虽有高宅大院仍难保平安。于是有筑城之议,赵姓一族在村东北侧崖边筑城一座。城址呈正方形,边长百余米,城高十余米。城堡东边临崖,西、北边挖成宽深各数十米的壕沟,南墙正中辟一砖券洞为唯一出入通道并与环院相联。城垣四角各有凸出角楼一座,券洞内设门数重,门间横开耳洞以伏兵守城。然城堡建就,赵姓鼎盛时期似乎已过,偌大城中只有北半部被利用,而南半部几乎处于空闲状态。有好事者谓该城破坏了风水,赵氏之衰自此始。其实城堡乃冷兵器时代的防御藏身场所,枪炮火器逐渐普及后其防御功能便大打折扣。以家族之力以建万余平方米之城池,固然是为了保障族群安全,虽家赀万贯亦是不小负担。在中国传统农村,生存安全开支甚至会影响到族群的兴衰,恐非居生赵姓一例。
我没有定量计算过居生的村民间为了生存安全而投资、投劳的总量,这对一个小的村落而言几乎是做了不可能的事,但是他们毕竟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费正清先生在他的《中国新史·自序》中谈到中国人的“生存耐力”问题,认为只有它能够救大家 (世界)。联系到我的父老乡亲为了生存安全的超额付出,我深以为费氏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