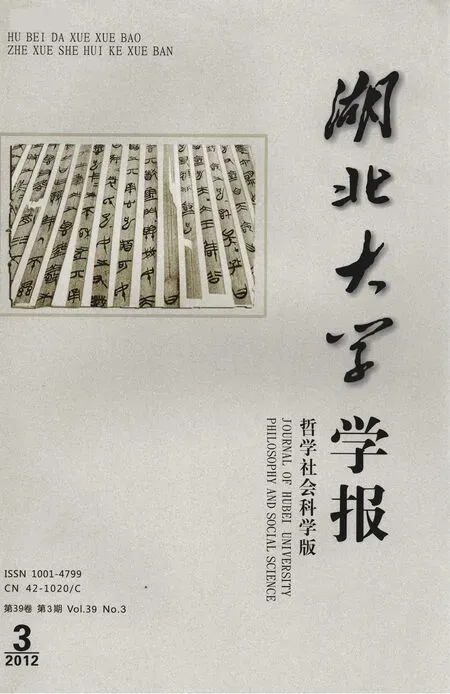威廉·福克纳荒野-旅行小说的原型解说
刘国枝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威廉·福克纳荒野-旅行小说的原型解说
刘国枝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界的荒野-旅行小说中,福克纳对圣经原型的激活可以在整体构架上抽象为一个三元并存的模式,该模式是福克纳荒野神话的深层结构,由此转换生成了形态各异的多部荒野-旅行小说;而三元模式的中间调节项因为其居中的位置,一方面言说着历史的前后牵连,使人物象征性地经历了过去、现在并指向未来,另一方面喻示着地理的内外贯通,使人物不仅保有“南方人”身份,更成为“美国人”和“人类”的一分子,所以,该调节项可以视为福克纳整个世系中所有单部作品的通约性陈述,其所深蕴的既是关于南方的同一个故事,也是整个人类追真求善历程的微缩。
荒野-旅行小说;原型;三元模式;中间调节项
在作为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圣经》里,“荒野”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意象,据统计,在20世纪中期由国际宗教教育学会主持编译的《标准修订版圣经》(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中,wilderness一词在《旧约》里出现了245次之多,在《新约》中也出现了35次[1]13。在这种高频率所渲染的前景里,以色列人逃离埃及之后、进入迦南之前为时四十年的荒野之行,则在《圣经》的整个象征系统里尤为重要。从整体上看,四十年的荒野流浪是神对以色列人信仰的考验,是对他们叛教的惩罚,与此同时,由于以色列人是上帝拣选的民族,他们在流浪途中,在野兽嚎叫的荒野,又一直受到上帝的眷顾,所以,荒野既是一种惩戒性力量,又是安全、自由和希望所在。荒野从来不曾失去其严峻、凶险的特性,唯其如此,作为伊甸园变体的迦南才成为人受难后的最高报偿,对人发出永恒的召唤,亦因如此,以色列人的荒野之行便成为后世文学中旅行主题的源头和范式。
对美国历史和文化而言,“荒野”一词更是积淀了特殊而深远的意蕴,美利坚民族的孕育和形成正是始于移民始祖的荒野之旅。当首批移民为逃离欧洲的宗教迫害而登临新大陆时,他们的精神行囊中不仅珍藏有对于美丽新世界的虔诚预期,还携带了基督教关于重建人间天国的神圣使命。这种精神遗产在美利坚民族的心理中积淀下来,不仅使荒野成为美国文化中“最有力量的词语之一”[2]24,还催生和鼓励了美国文学的荒野传统,从最字面的意义上说,美国文学就是诞生于荒野地上的文学。早期的荒野无疑是“试炼场”,是征服、改造、驯化的对象,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拓殖的深入,边疆日益退却,特别是独立革命的胜利大大激发了美利坚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在这种语境下,北美大陆上原始浩瀚、生机盎然的荒野褪去了邪恶或含混的宗教色彩,而成为美利坚共和国所独有、“让旧世界望尘莫及”的财富,成了滋养美利坚民族性格的“文化和道德资源”[1]67。随后的浪漫主义运动也推波助澜,不仅保持着对于精神荒野的探索热度,更强化了对于物质荒野的崇拜之情。到19世纪中期,荒野保护开始成为一个“全国性话题”[1]96,但1890年的荒野普查仍然宣告了边疆时代的结束。这样,早期拓荒者的子孙们远离了荒野的物质威胁,却转而承受着工业文明对于人的精神的挤压和围堵,在怅然回首之中,自然的荒野愈发成为人们怀旧意绪中的伊甸和天堂。
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伟大旗手威廉·福克纳既是拓荒者的后代,又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浸润,因此成为20世纪美国荒野文学的集大成者,他对荒野文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创作了著名的“荒野三部曲”(wilderness trilogy,又称“大森林三部曲”,即《古老的部族》、《熊》和《三角洲之秋》),更在于他立足自己家乡那邮票般大小的土地所创造的约克纳帕塔法本身就是一个被间距化、神话化的荒野世界,作家所呈现的正是关于荒野向文明进化(或曰在文明面前退却)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性浮沉的史诗性画卷。鉴于福克纳受基督教影响至深以及“荒野”一词所承载的原型意蕴,本文拟对作家荒野-旅行小说中的相关神话因子进行探查和盘点,以揭示其原型模式,进而挖掘其潜藏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圣经原型盘点
所谓荒野-旅行小说,简而言之,是指通过荒野旅行来牵引故事情节的小说,在本文中,具体指福克纳的七部作品,即《我弥留之际》(1930)、《圣殿》(1931)、《八月之光》(1932)、《押沙龙,押沙龙!》(1936)、《去吧,摩西》(1942)中的“荒野三部曲”、《坟墓的闯入者》(1948)和《掠夺者》(1962),其中,《我弥留之际》实际写作于1929年,《掠夺者》则完成于1961年,离作家去世之日不到一年,这三十余年的时间跨度充分体现了作家对荒野题材和主题的深度关注。
批评家们早就发现,福克纳在作品中借用了大量的神话和原型,有统计显示,作家对圣经神话、典故、象征、母题等的直接和间接运用达到379处之多[3]356。当我们以福克纳的荒野-旅行小说为全景,分别从作为小说主要构件的场景、人物、叙事结构以及对旅行具有标识意义的意象等四个层面介入时,不难发现各层面均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圣经原型:
1.通过对作品中类型场景的清理发现,福克纳虚拟世界中的场景既经过了历时的变迁,也维持着共时的三位一体:其一是以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原始森林为介质、未受现代文明污染、超然于工商业社会之外的“原生荒野”;其二为以乡村和小镇为表征、居于文明社会和自然荒野之间、因两者抵牾互渗而生成的“混融荒野”;其三是以位于约克纳帕塔法县之外的喧嚣都市为象征、作为现时生活的外在参照和终极警示的文明社会。这三元场景呈现出与《圣经》中的天堂(伊甸园)、炼狱(荒野和现世境遇)和地狱的精妙对位,它们是《圣经》中关乎人类的三层次世界景象的置换。
2.就人物而言,有三类人物被明显地前景化,其中,由自然的绅士(如“大森林三部曲”中的山姆·法泽斯)、天真的孩童(如《坟墓的闯入者》中的契克和《掠夺者》中的卢修斯)和具有大地母亲特质的年轻女性(如《八月之光》中的莉娜·格罗夫)集合而成的“伊甸式人物”往往凸现出“原始”和“纯洁”的品性,他们是堕落前的亚当和夏娃的象征,是引发、支持和维系伊甸园梦想的力量;与此相对的“反伊甸式人物”则在简单的信念、规划或目的的驱策下,背离人类的古老美德,任自己蜕化为教化的工具(如《八月之光》中的海因斯和麦克依琴,《圣殿》中谭波尔的家人)、欲望的奴隶(如《押沙龙,押沙龙!》中的萨德本)或机械人(如《圣殿》中的金鱼眼),因而成为伊甸园梦想的破坏力量;在这两类人物之间,在他们所形成的紧张窘迫的关系场中,还游离着一群“替罪羊”[4]99~103,他们各自以一己之躯承担起种族、阶级或家庭的罪孽,因而成为平缓冲突、恢复秩序的力量。
3.通过对复现频率高、负载明显主题强度并对旅行结局形成预设的标识性意象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以马、熊、大车等为代表的“助推意象”喻示着旅途中的强大助力,使主人公不仅完成世俗意义的荒野之旅,还在精神意义的人生之旅中实现向上的攀登和跨越;而洪水、大火和黑屋则以各自蕴蓄的巨大张力而成为浮雕似的阻隔意象,它们干预和破坏着行程的推进,宰制着人物的命运;路与桥是旅行中最基层和最恒久的意象,不仅可望沟通荒野与文明、乡村与城市、过去与现在,还可以隐喻种族、阶级、性别栅栏的跨越,它们在言说沟通之艰难的同时,更申述着沟通的必要。
4.弗莱认为U形结构既是《圣经》的具体叙述单元,也是《圣经》的宏观叙事模式[5]220。福克纳在自己的荒野-旅行小说中,对这种U形叙事结构进行了挪用和变形,分别呈现出三种图式。其一为表达“再生性沉降”题旨的“完满的U形”:主人公离开类似伊甸园般的环境,经过荒野之旅而完成某项使命,其命运曲线也随之上扬,因获得积极的赏酬而实现象征意义上的再生(如《坟墓的闯入者》和《掠夺者》)。其二为勾画“大厦的坍塌”图景的“断裂的U形”:人物从一种相对较好的状态下降,由于恶的泛滥、深重而无法再度上升,陷入并终止于U形曲线的底部(如《押沙龙,押沙龙!》和《圣殿》)。其三为“倒置的U形”,彰显现代人一方面因为恶的不绝而反复沉落、另一方面又在德性上奋力自拔的西绪弗斯式命运(如《我弥留之际》和“荒野三部曲”)。
由此可见,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界的荒野-旅行小说中,福克纳对圣经原型的激活可以在整体构架上抽象为一个三元并存的模式,即除了二元对立的关系(分别用X和X-表示)之外,还存在一个介乎两者之间的调节项(用Y表示),如下图:

二、三元模式解说
在以上三元模式中,每一横列涉及一个与阐发主题至为相关的层面,其中,场景、人物和叙事结构是作品的重要构件,共同搭成作家神话大厦中不可或缺的支架,而相关意象则对荒野旅行的结局具有标识意义。每一纵列中的各项也具有同质性,其中,X与X-代表两种截然对立、永恒冲突的力量,Y项的存在成为两者的中介和调节;作为承接两股敌对力量的中间项,Y项的意义因X和X-的高度对立而得到彰显。这个三元模式正是福克纳荒野神话的深层结构,由此转换生成了形态各异的多部荒野-旅行小说。
从纵向上看,X-列以工商主义和工业文明的畸形发展为指向,体现为各种恶行败德的集合,这是一个深度堕落的世界,具有明显的不可救赎性,因而承载着作家毫不容情的强烈批判,传达了作家对人类文明过度进化的远虑。与此相反,X列所涵括的因素则与人类的童年生活、与堕落之前的无邪状态相联结,具有天真、美好、善良、祥和等品质。然而,这里也不是作家的价值偏倾所在。福克纳虽然对原生荒野怀有毕生的不舍情结,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森林是他摆脱繁重的世俗之累,接受心灵休整和疗养的世外桃源,也是他的主要人物之一艾萨克·麦卡斯林的朝圣殿堂和精神故乡,但是,他还深知,荒野的消亡是可以预见却不可避免的宿命。在他看来,任何东西不管看起来多么美好,都不可能恒久不变,因为一旦停滞下来,放弃运动,就宣告了自身的死亡,荒野也是如此,它是“因为变化而必须毁灭的美好而辉煌的东西”,“是人类过去的一部分,是人类遗产的一部分,可是已经过时而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6]277。荒野的悖论也是人类童年生活的悖论,正如作为伊甸园变体的原生荒野不得不失落一样,人必定要成年,必定要从纯真无邪的童年时代进入成人世界令人失望的喧哗与骚动;同样,历史要发展,社会必然要从蒙昧走向理性、成熟和文明。所以,骡、马、大车等虽然是旅行中的助推意象,却因其附着于农业社会的属性而必然让位于作为工业文明象征的汽车。这充分表明,在叙事结构上由自然女性和懵懂少年所贯彻的救赎方案虽然在表面上洋溢着乐观之气,其深层却涌动着悲观的潜流,它们终究走不出自身的神话,因此在现世生活中沦为虚置。
当我们将视线从约克纳帕塔法社会暂时抽离,而远眺圣经世界时,一个类似的三元模式会清晰地浮出:人始而栖居伊甸乐园,继而堕落尘世,经由末日审判之后再归于天国或坠入地狱;上帝是最大的善,撒旦是最大的恶,人被置于上帝和撒旦这两极之间,既无法获得完满的神性达成至善,也不会发展成全面的魔性陷于至恶;人有幸被神“拣选”,却不幸成为神的“受试”,一边是神对人毫不妥协的虔信要求,另一边是神所释放的恶的试探,人注定在“大信”与“小信”/“不信”之间游移……这种三元模式的架设将基督教的原罪、惩罚、救赎等核心命题精妙地包孕其中,集中表达了对于人的本质、处境、归宿的关注。与此同时,透过这一组组三元关系,我们还不难看出,虽然基督教“将最高的正义和终极的价值寄托于彼岸”,其“希望在于乐园和天国,使人的起点和终点都立足于另一个世界”[7]119,但归根究底,对“彼岸”的注目所传达的正是对“此岸”的关怀,是对伊甸园之后、末日审判前的人的现世命运的激励和预警。以此回顾福克纳作品中的三元模式,则X和X-两个纵列成为正反两面借镜,使迷雾笼罩中的Y列的意义豁然开朗——这一纵列正是作家对伊甸园梦想失落后的人的现时命运的汇聚呈现,它生动描摹了现代人生存境况的有限性、相对性和悲剧性,集中表现出现代人所承受的压迫感、迷茫感、焦虑感、孤独感、荒诞感、怀疑感、失落感和错位感;正是在这里,一生都在冲突中寻平衡、在混乱中建秩序、在矛盾中求真理的福克纳寄寓着至为深沉的关切。
三、中间项的意蕴
对福克纳来说,伊甸园之梦的失落具有个人、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所指。首先,作为一位贵族世家的子弟,他有过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童年,而在离家附近的森林中度过的时光更加添了其伊甸性质。但是,那段日子却在上学之后以及父母之间“莽汉+淑女”式婚姻组合所发出的不和谐音中无可挽回地逝去,而森林本身的日渐缩小也成为梦想失落的协奏。随着自己的成年尤其是成名,当他对历史与现在、传统与现代、艺术追求与家庭责任之间的抵牾感受愈来愈切时,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时光也就愈来愈显地成为已经失落的伊甸时代的客观对应物。其次,就家族历史而言,作家的曾祖父一度创造过眩目的辉煌,但是那种辉煌未能延及后世,到父亲一代已经家道中落,由于昔日的荣光在现今生活中无从复制,便只能在传说和想象中被无限擦亮和寻回,以补偿作家的失落意绪。再次,在南方人的保守浪漫主义“记忆”中,南方曾经是一幅宁静祥和的田园牧歌图景,到处阳光明媚,人们相处和谐,黑人奴隶得到白人主子的仁慈看顾而衣食无忧。但是,那一切却因为南北战争而随风飘逝,留给南方人的是“一种来自创伤性经验的集体潜意识:一种破灭理想的记忆,一种昔日传统的召唤,一种末日将临的危机感”[8]464。即使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经济的复苏扫掉了战后的贫困,“社会的、经济的”旧南方已经“死去”之后,“文化的、心理的”旧南方仍然“顽固地‘存活’着”[8]463,而存活下来的就是在南方人的怀旧情感中被神话化、伊甸化的战前经济繁荣的旧南方。作为一位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有良知的作家,福克纳敏锐地洞察出神话与历史的错位,内心涌动着难言的困惑和焦灼,因而通过约克纳帕塔法世界的创制,在对不肯死去的过去的反复寻访中,对其核心的神话内容进行了证伪或纠偏,并借此考量和深省现代南方人的生存窘状。正因如此,混融荒野便以其界线的含混、价值的杂糅、容量的巨大而成为作家至为倚重的表达媒介。
罪与救赎是基督教的两个基本概念,人类始祖对神意的悖逆生成了人类必须世代沿袭背负的原罪,原罪的发生不仅招致伊甸园的失落,还成为人本体化的生存规定:任何人都是罪人之一,而不是唯一的罪人。与此同时,人作为负罪之身,只有通过赎罪才能获救,才能重归神的怀抱和重返原初的家园。福克纳生活于美国南方的圣经地带,对基督教的原罪观和救赎观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感悟,但是他不是一位形式化的基督徒,对他而言,“坚韧、自豪、勇气、同情心和牺牲精神最终具有一种与基督教相关的意义”,他的宗教“本质上是基督教人道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斯多葛式基督教”[9]124,因此,他思想和创作中的原罪和救赎观虽然保有神道主义形式,却填充着人道主义内容。在他看来,私有制和奴隶制构成了南方的原罪,它是人对自然以及对人所犯之罪,旧南方不是一方纯洁的净土,而是一个被玷污、注定要被剥夺的伊甸园,南方必须为此受罚和赎罪,南北战争就是南方受罚和赎罪的顶级形式。所以,他一遍遍地深度追溯南方的过去,在其中,他所关注的不是内战前南方社会的所谓快乐时光,更无意将其树为让后世效仿的典范,他反复展现的是正在走向崩溃的传统,不断探究的是传统崩溃的根源,在各种复杂的根源之中,最为根本的是人的贪欲,这种贪欲在传统形成伊始就已将传统败坏,不仅将南方变成违反天理和人性的奴隶制的温床,还进一步鼓励了种族主义与清教主义的结盟。因此,南方的传统、历史本身就意味着罪孽的生成以及为赎罪而作的努力或因罪而受的惩罚,这就为替罪羊的存在提供了依据:形形色色替罪羊形象的出场是对人的罪性本质和处境的正视,他们既是罪孽的必然产物,也述说着赎罪的必要。由于替罪羊既可以是带罪之身,也可以是无辜之人,这种兼容性身份赋予他们一种精神优势,使他们得以通过自身的替罪而呼唤着伊甸式人物和反伊甸式人物的和解,促成混乱的中止和秩序的回复。
从意象层面看,路与桥是旅行至为关键的要素,人在旅途预示着两个地点的接通和一段距离的跨越,这既可以是地理空间的距离,也可以是心灵旅行的距离,因而在象征意义上还指代现实与希望之间的距离,而后者“常常被美国人解释为‘使命’”,他们据此而“一代又一代地把自己奉献给实现未来希望的事业”[10]33。从这个视点切入,则可以看到福克纳对圣经文学和美国荒野文学所沿循的“选民-使命”程式的置换变形。正如《圣经》中的人物俯首于看不见的上帝的意志一样,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居民也顺服于作家通过他们跌宕起伏的命运来使历史产生意义的意志,而使他们的受难与该县历史上的重要时刻相链接。不过,路与桥所导向的未必是迦南乐土的入口,福克纳的选民(罪民)在经受磨难之后,未必能达到理想的应许之地。
如果说叙事结构层面的完满的U形在救赎启示上沦为虚幻,断裂的U形言说着彻底的无望,那么,倒置的U形所指向的则是一个被无限延宕的迦南。福克纳虽然沿袭了使命程式,却从自身以及整个南方的历史出发,刻意改写了使命实现过程中的“负罪-赎罪/受罚-救赎”的路径,而将救赎环节消隐。这种屏蔽归途的操作源于作家深沉的负罪意识和对现代道德状况的忧思。一方面,在福克纳看来,南方传统价值和道德体系的崩溃与土地(家园)的丧失密不可分,而传统价值和道德体系的崩溃又直接招致了大家族的颓败和人的堕落,这种因果相生的链条使南方人不可能回到战争没有发生时的状态,不可能返回那种“自以为很幸福,自以为没有烦恼和罪孽”的“田园之梦”,而必须“承担起这些烦恼和罪孽继续前行”[11]49。另一方面,在来势凶猛的工业化和工商主义的冲击下,由于价值度量衡的缺位,南方人在愕然中陷入迷途,步履踉跄。面对这种两面作战的困境,唯一可行的应对便是endure,也就是“忍受”或“苦熬”。Endure是福克纳为自己的子民设定的一个通往生命奥秘的关键词,为此,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所有作品中,他不厌其烦地对人的坚韧精神进行了阐发,忍受苦难的能力是他反复称颂的古老美德之一,在他的笔下,谦逊的黑人、坚强的女人、贫穷的白人大多具有这种品质,所以能够苦熬下去。这表明,“忍受”是承担试炼、度过难关的密码,是约克纳帕塔法居民在混融荒野中自我保存的基本能力。只不过此处的“保存”已经失去了精神的内涵,而退化到了生物性水平,因为南方是犯下杀弟之罪的该隐——在这里,萨德本、麦卡斯林等大家族令人发指的种族主义罪孽自不待言,就连一向蜗居在荒崖之上、与外界少有往来的本德伦一家在送葬途中也不放过欺凌黑人的机会——而南北战争是上帝在南方躯体上烙下的标记,这个记号虽然肯定了南方的生命保全价值,却否定了它的道德价值。于是,南方人所期待的伊甸园变成了他们的流放地,受难便成为他们无从摆脱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在福克纳亲手绘制的约克纳帕塔法地图上,“两条碎石土路像十字架一样在县城杰弗生相交”[12]7,对于将基督教象征运用得炉火纯青的福克纳而言,这十字架般的土路无疑是南方负罪和受难身份的显性提示。因此,在低迷的生存状态中,南方人只好再次滚动西绪弗斯的巨石,怀着渺茫的希望去迎接生命的下一轮短暂升腾。
作为三元模式中的中介或调节项,Y列所呈现的人的本质、处境、无从止歇的斗争和探求,是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集中表达。同时,这种居中的位置一方面言说着历史的前后牵连,使人物象征性地经历了过去、现在并指向未来,另一方面喻示着地理的内外贯通,使人物不仅保有“南方人”身份,更成为“美国人”和“人类”的一分子。因此,Y列可以视为福克纳整个世系中所有单部作品的通约性陈述,其所深蕴的既是关于南方的同一个故事,更是关于美国乃至全人类的同一个故事。
四、结语
威廉·福克纳身为美国南方文学的伟大旗手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通过对《圣经》中荒野之行母题的启用和多种圣经原型的激活,而将自己的人物推上移民始祖所选择的荒野路,使他们经历迷途的考验,探寻人性的归途,从而使自己的作品不仅成为美利坚民族文化心理的投射,还成为整个人类追真求善历程的微缩。
[1]Nash,Roderick.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3rd Edition[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2]Williams,David R.Wilderness Lost: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Mind[M].Selingsgrove:Susquehanna University Press,1987.
[3]杨金才.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三卷[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刘国枝.论福克纳小说中的替罪羊群像[J].湖北大学学报,2010,(4).
[5]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Gwynn,Frederick L.,Joseph L.Blotner,eds.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M].New York:Vintage Books,1965.
[7]杨慧林.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8]虞建华,等.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9]Brooks,Cleanth.On the Prejudices,Predilections,and Firm Beliefs of William Faulkner[M].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
[10]埃默里·埃利奥特.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M].朱通伯,等,译.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
[11]Hoffman,Frederick J.&Olga W.Vickery,eds.William Faulkner:Three Decades of Criticism[M].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0.
[12]弗雷里克·J.霍夫曼.威廉·福克纳[M].姚乃强,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
I106.4
A
1001-4799(2012)03-0117-05
2011-06-10
刘国枝(1965-),女,湖北大冶人,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雷 丹]
-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1833—1895年主要汉文西书中议会文化的变迁
- 《休邑土音》音系述略
- 企业信息安全投资的博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