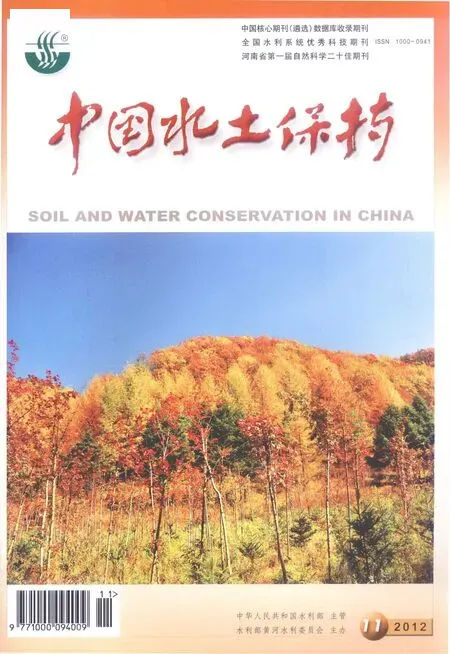基于农户视角的生态移民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探析
时 鹏,余 劲,加贺爪优,鬼木俊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在保护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背景下,生态移民成为解决生态问题和消除贫困问题的重要举措。20世纪以来,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经济活动迅速开展,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渐由地区性、局部性问题演化为全球性的问题并呈逐步恶化的趋势[1]。生态移民工程是历史经验和现实约束条件下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优选择。农户作为生态移民工程实施的主体,其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与如何提高工程实施的内生性成为生态移民研究的热点。本研究对近年来这一领域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论,指[基金项目]中日农户经营状况比较研究项目(K332020019);国际合作“陕南移民的互动联关经济计量模型的引进及应用”项目(2012KW-19)出其存在的不足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以期能推动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在经济利益条件下,成本-收益自然是影响农户搬迁意愿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自然资源的特殊性,产权界定困难,生态移民工程具有外部性,单纯从农户自身利益出发,补偿不足及安置补偿对于安置后收入的滞后效应可能导致搬迁动力不足[2],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因此,非成本-收益因素对农户意愿的影响也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另外,当外部条件相同时,农户自身特征及资源禀赋条件也会对搬迁意愿产生重要的影响。
1 成本-收益因素对农户生态移民意愿产生的影响
英国地理学家拉文斯坦(E.G.Ravenstein)最早对人口迁移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动机是人口迁移动机中的主要成分;根据布朗(Brown)和摩尔(Moore)提出的人口迁移决策模型[3],生态移民农户意愿的形成取决于政府诱导力、生态压力及农户预期,而这三者都最终可以归纳入成本-收益决策之中:政府诱导通过土地政策、户籍政策、资金支持等手段可以增加农户迁移后的收益,降低由于移民搬迁而产生的费用;生态压力主要受到迁出地的推力、迁入地的拉力及中间阻力的影响;最后,在充分了解移民政策及迁入地条件的基础上,农户形成对于迁移后生活水平的预期。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托达罗模型分别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关系和发展经济学的概念,认为人口迁移是在市场条件下获取市场机会的个人理性选择,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迁移理论,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是迁移的最终目标。在国内,李惠(1993年)通过对中国30个省(市、区)之间人口迁移的效益值进行计算,表明人口净迁移与效益值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4];施国庆、陈绍军(1994年)对水库移民的各种费用与效益进行了介绍,探讨了水库移民系统经济评价的理论与方法[5]。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用于研究移民农户意愿时曾饱受非议(Cernea,1998 年)[6],这并非是该方法本身的缺陷,而是由于许多成本并未考虑在内。生态移民的成本,既包括房屋、树木、水井、青苗、土地等有形损失,也包括传统劳动技能的损失、社会关系网络的破坏等无形损失,可将其归纳为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3种损失[2],前人的研究多集中在实物资本的损失方面,而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损失的研究较少。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实施生态移民搬迁后安置点离原有住房较远,搬迁农户尤其是老年人及身体状况较差的年轻人,不能适应新的以打工为主的生活方式,在收入水平下降的同时基本生活消费品也不能自给自足,生活费用大幅上升,给农户生活造成一定的困难。另外,搬迁后原有的分散居住方式得以改变,集中居住方式使责任与信任、信息渠道、规则与制裁等社会关系得以重新界定,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有所下降。在我国,生态移民工程涉及到迁入地区宅基地与迁出地区耕地之间的流转置换,土地作为农户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成本及补偿价值的确定关系着农户搬迁的意愿与可能性。目前,我国实行土地产权的两权分离,从产权经济学的视角看,在土地的未来预期收益上升从而使土地的价格上升、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有一部分利益存在于公共领域[7],不同权利的所有者利用掌握的部分产权去竞取这部分价值的结果是产生利益纠纷,最坏的可能是这部分租值完全耗散甚至由经济利益的分配导致了不公平,会直接引发农户的强烈不满进而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导致工程实施的失败;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村委会、开发商可能凭借其不对称的权力和垄断地位将补偿价格置于市场竞争的价格之下,以攫取农户的供给剩余为代价,扩大自身的消费剩余。已有的文献较少对土地价格确定及由此带来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2 非成本-收益因素对生态移民搬迁意愿产生的影响
生态移民有政府和农户两个决策主体,属于诱导式移民[8],一旦迁移愿望纳入国家政策允许范畴,农户只需寻找政策允许的条件并创造相应的条件就可以实现迁移[9],此时非成本-收益因素与成本-收益因素同样起到重要作用:移民参与、信息公开、宣传教育等因素既不影响农户迁移收益,也不影响搬迁成本,但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它们有可能阻碍顺利迁移;而在收益小于成本时,却可能促进农户迁移。资源环境作为公共产品,从要素需求者的角度看,私人成本小于社会的成本,从而导致资源的过度开采、开发;从生态产品供给者的角度看,由于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单纯依靠个人理性将会导致供给不足。生存的压力、对发展的本能追求以及资源环境的公共产品性质,是生态脆弱地区陷入恶性发展循环的内在原因。生态移民便是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系统和谐发展的重要方式,由于工程实施过程中涉及到各种有形和无形成本,很难保证成本收益之间的平衡,生态移民一开始便具有非自愿的性质,因此非成本-收益因素在促进农户搬迁方面便显得尤为重要。
移民参与是让那些由于搬迁而受很大改变的农户有权过问他们的未来,并参与将要改变他们命运的决策制定。如果农户积极主动地参与,冲突和延误就会减少,避免移民后返迁的发生,增加长期稳定[10]。农户是生态移民搬迁的实施者和受惠者,应该充分调动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避免由于强制搬迁和信息问题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增强农户与村、乡、县相关部门的交流沟通,及时就搬迁的方案、耕地的置换等问题达成共识,增加互信,减少工程实施的内生交易费用。对任何移民计划的成功实施来说,非政府机构和公众参与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从规划阶段开始到实施的每一阶段,都必须有非政府机构和移民的积极参与[11]。陶传进(2000年)认为,非成本-收益因素对农户生态移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即移民参与、宣传教育和动员、利益分配的公正性[12]。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宣传国家政策和大政方针成为变被动移民为主动移民的重要经验[13],它能调动农户移民搬迁的积极性。
已有的文献较少将农户家庭成员、亲邻好友、已搬迁农户的态度等社会压力因素纳入到非成本-收益决策模型之中。在农村,人伦信用较商业信用更为普遍,调研中我们发现,家人、村民、亲朋的支持能对农户生态移民搬迁意愿产生重要的影响:当农户家庭有学龄子女及婚龄男子时,由于交通不便给孩子上学和男孩娶亲带来诸多困难,家庭成员多数支持会促进移民搬迁的实施;已搬迁户的成功搬迁减少了潜在搬迁农户的组织试验成本,减少了后者搬迁的风险,因此当前期搬迁成果得到肯定时,潜在搬迁农户的生态移民积极性也得到极大提高。
3 农户特征对生态移民意愿产生的影响
在政府政策协调和提供诱导的前提下,生态移民潜在农户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于是否搬迁具有自主的选择权[8],农户自身特征及家庭资源禀赋对农户的搬迁意愿产生影响,只有某些特定的人可能成为迁移者[14]。唐宏(2011年)等采用Logistic方法对新疆三工河流域农户的生态移民意愿及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家庭人口数、人均纯收入、主要收入来源、非农收入比重和参与退耕情况是影响农户搬迁意愿的主要因素[15],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和有过迁移史的农户易于迁移[8]。孙田野、马才学、郭洁雯(2011年)对三峡库区农户自身特征和农户资源环境禀赋对移民意愿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搬迁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居住位置和居住方式,居住在地质灾害易发地带的农户、居住分散的农户有较强的搬迁意愿,户主年龄与搬迁意愿呈倒凸关系,中年户主更倾向于搬迁;土地面积越大的农户越不愿意搬迁;房屋结构和基础设施是农户看重的重要因素[16]。在理论方面,户主性别、个人的心理素质、健康状况也会对农户的搬迁意愿产生影响,而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尚不足。调研中我们发现:一般说来,农户在生态移民搬迁这一重大问题决策过程中并非单纯地由户主一人决定,家庭妇女由于较多居家务农及喂养牲口,家庭日常开销也由其支付,从而搬迁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妇女影响较大;妇女较男性保守、承受风险能力较差,与男性相比妇女的搬迁愿望较弱;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户预期在搬迁后可以迅速地适应非农生产方式,因此搬迁愿望也较为强烈,但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户一般倾向于在原住地从事劳动强度较小的农业劳动。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外部条件和农户特征的角度对农户生态移民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以传统的成本-收益方法作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但仍存在缺陷;在实现非自愿移民的自愿迁移前提下,改进后的成本-收益方法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加入模型,但模型涉及变量却难以量化,不易应用。另外,在考虑风险的条件下,农户的未来预期效用不再是收入函数在时间上的积分,农户的规避风险特征使得总收入效用值降低,以往的研究并未将风险因素考虑在内。在非自愿移民中,农户此时不再单纯地考虑由于移民带来的成本收益,非成本-收益因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概念虽在分析生态移民意愿中有应用,但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较少且没有统一的理论框架作为支撑。最后,从农户特征的角度,区分了不同农户家庭人口结构、文化程度、收入结构、资产状况等因素的不同对农户意愿产生的影响,更加微观和具体,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然而,以往的文献中并没有研究农户的行为态度、周围人的态度、农户资源约束条件、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等对农户意愿产生的影响。近年来,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等研究领域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逐渐被引入农业经济研究领域,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结构方程模型已经在相关文献中得到成功应用,这一方法或许可以成为今后研究生态移民农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方向。
[1]张小明.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研究[D].陕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5-15.
[2]盛济川,梁爽,施国庆.中国农村非自愿性移民自愿迁移的经济分析[J].西北人口,2009(3):8-13.
[3]段成荣.人口迁移研究:原理和方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11-13,57-59.
[4]李惠.人口迁移的成本、效益模型及其应用[J].中国人口科学,1993(5):47-51.
[5]施国庆,陈绍军.水库移民系统经济评价研究[J].水电能源科学,1994,12(3):200 -205.
[6]Cernea M.The Economics of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Questions and Challenges(Directions in Development)[M].Washington D C:World Bank Publications,1998:23 -56.
[7]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78.
[8]张小明,赵常兴.诱导式生态移民的决策过程和决策因素分析[J].环境管理与科学,2008(5):180-185.
[9]阎蓓.新时期中国人口迁移[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232-271.
[10]迈克尔·M·塞尼.移民·重建·发展: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研究(二)[M].水库移民经济研究中心,译.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67-80.
[11]S·阿斯撒那·沙达尔.沙罗沃工程移民的实施、管理和监测[C]∥水库移民安置国际高级研讨会文集.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23-33.
[12]陶传进.工程移民搬迁动力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0(6):105-111.
[13]辛文,焦成宾.三峡工程四川库区十年移民工作回顾[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213-255.
[14]佟新.人口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52.
[15]唐宏,张新焕,杨德刚.农户生态移民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疆三工河流域的农户调查[J].自然资源学报,2011(10):1658-1669.
[16]孙田野,马才学,郭洁雯.基于Logit模型的非自愿性移民迁徙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1):1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