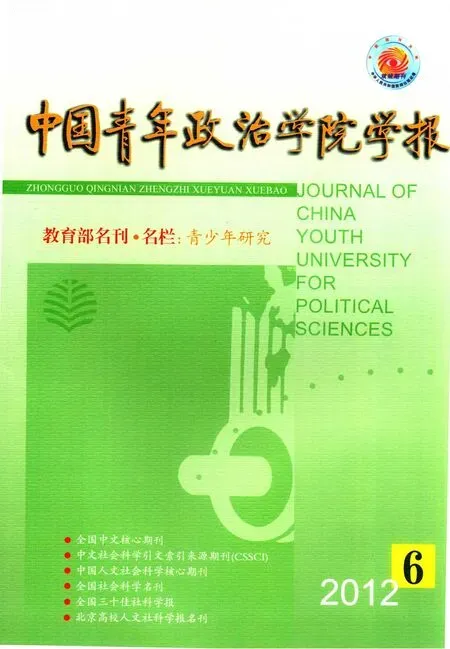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青团青年动员合法性研究
刘新玲 顾方园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科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一、青年动员的概念
青年动员是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动员。因动员主体的不同,对社会动员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从现代化的角度,认为社会动员是在社会变迁的自然过程中,社会成员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的主动或被动的变化,体现了社会动员的自发性。该观点以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等为代表。另一种认为,社会动员即社会发动,动员的主体多为政府或政党,甚至是极具号召力的领袖人物,通过各种发动,以实现一定的政治或经济目的。这一观点更侧重于具体目标的发动过程,偏重于一种人为性的动员。
青年动员从广义上说是现代化进程中,青年在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发生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可以是社会变迁中自发性的社会动员,也可以是人为的发动。对于共青团这个动员主体而言,在不同时期,为实现其历史使命,通过政治、文化、教育、活动参与等方式,影响青年的态度、价值观、行为等方面,促使青年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就是共青团青年动员的过程。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青年动员
1919~1949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头上压着“帝、封、官”三座大山,整个社会都处于剧烈的躁动之中,各种社会运动、革命运动层出不穷,同时也导致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一系列变迁。身处从近代向现代社会演进中的中国青年,时代自然地赋予了他们历史使命感,这一时期青年动员的表现有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青年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广大青年亲身经受地主、买办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亲眼目睹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和掠夺,对国家的落后挨打有着切肤之痛,热血青年无不胸怀悲愤与忧虑,决心奋发自强,拯救中华。正如斯大林在1926年分析中国革命前途时所讲:“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深刻而敏锐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尖锐而痛楚地感觉到必须和这种压迫作斗争”[1]。
第二,广大青年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和封建专制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了20世纪初的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试图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之路,结果都走不通,这一探索过程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
然而,中国社会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型中,自发性的青年动员表现出自身的局限性。(1)狂热、摇摆和不彻底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小农经济占很大优势,民族资产阶级十分软弱。处于这种社会现实中的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虽在政治上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但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又容易陷入迷惘,发生摇摆。毛泽东在分析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时曾说:“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2](2)缺乏理论指导和组织性。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对于农民和工人中的青年来说,由于自身知识和信息的缺乏,斗争与反抗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救国只不过是一种朴素的愿景,没有科学的理论作为行动指南,更没有完善的策划与组织领导。这样,自发性的青年动员虽然有着无数热血青年的参与,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在中国从近代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带领最广泛的青年实现其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的现代性转变。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青团青年动员的合法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发性青年动员的局限性给共青团青年动员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性与合法性。所谓合法性是指动员被青年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青年动员合法性的建立,必须依赖一套能够让青年自愿服从并认可的动员内容、动员过程和动员方式,这是共青团成功实现动员并维护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
(一)动员内容的合法性
1922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作为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青年团这一时期的最主要目标就是动员最广泛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带领青年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青年团一大文件中明确指出,青年团组织的明确奋斗方向和目标要与党的奋斗目标保持一致,以便更好地协助党完成民主革命任务[3]。中共三大也提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变为对主义的宣传,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4]。这些政策成为青年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奋斗目标的指南,得到了团员和青年的普遍认同,顺应了从近代向现代社会转型中青年的政治诉求。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青团根据每一阶段历史任务的不同,其动员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大革命时期,青年团以发动团员和青年积极投身工人运动为主要内容。通过组织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反抗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契合了青年工人的革命愿望。土地革命时期,共青团动员青年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拿起枪杆子参加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统治,这既符合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的要求,又满足了青年农民的经济利益。抗日战争时期,共青团成为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亡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青年同日本侵略者和国内卖国投降势力作斗争,团结各界青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共青团青年动员的任务是把解放区的进步青年组织起来,用他们的革命热情和觉悟去引导和带动广大一般青年,为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积蓄力量。
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青年的广泛参与是不可缺少的。而共青团青年动员在不同时期的主要内容紧扣革命任务,目标明确且具体,对引领思想、凝聚青年、增强青年对革命的认同、加速现代社会转型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共青团对青年动员的人为性引导与组织,正是因为符合当时社会革命的期待,符合青年的政治追求,与广大人民大众利益相一致,才赢得了青年的广泛认同和自愿服从,从而为合法性的青年动员奠定了内容基础。
(二)动员过程的合法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发性的青年动员,并未有效地发动青年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共青团用政治动员的方式,促成中国青年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锋。这一过程包括:通过各种方式向青年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将革命教育、阶级教育深入到具体实践中;帮助青年明确斗争的方向,形成共同的革命信仰,激发青年的斗争热情;领导并组织他们投身革命、反帝反封。这一动员过程的合法性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宣传教育是人们意识形成的客观局限所迫。列宁提出“灌输论”的时候,正值俄国受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变种的经济主义影响。经济派迷恋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满足于分散状态和经济斗争,忽视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否认党的领导,导致初创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使党进入一个混乱、瓦解、动摇的危机时期。
针对上述情况,列宁提出灌输革命理论的重要性。他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5]因此他认为,信息渠道缺乏,工人自身没有文化,缺乏自觉吸收思想理论信息的能力,需要理论大师把社会主义思想传授到工人群众中去,使先进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提升工人运动。这从根本上阐释了宣传教育方式在革命动员中的合法性问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条件同样有限,青年亦是如此。先进的思想并不能自发地在青年头脑中形成,只有通过各种宣传引导,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灌输给青年,才能建构青年对革命思想的集体认同感。因此,宣传教育是动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方式。
第二,唤醒激发可以存续青年热情,建构价值认同。产生政治运动和革命的关键是如何把个体化的行为转化为群体的行为。在自发的青年动员中,往往是针对突发性事件集合起来的有志青年所表现出的激情,而这也就将其弱点显露无遗。当刺激性的事件得到解决,大规模的激情就会消失,集体爆发出来的激情又会回归原始状态。青年不可能在自发的动员中保持持久的激情,因此,共青团在动员青年的过程中,就必须解决把少数的、刺激性的激情凝结为集体的、持久性的激情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对青年灌输革命思想,通过阶级意识增强青年对剥削阶级的仇恨,引导他们认识到要改变生存危机乃至国家危机,不是日常反抗,也不是简单的学生运动,而是凝聚起来加入革命,切实构建起广泛而统一的革命认同感。
第三,组织参与凝聚了青年的革命力量。宣传教育与唤醒激发仅仅形成了革命情绪高涨的状态,还需要有人来把高涨的情绪引向实际的革命行动。共青团的青年动员和自发的青年动员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组织,能够将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结成各种团体,并指导青年动员的整个进程。如通过“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学生救国会”等社团,共青团有效地组织广大青年参与革命斗争,有计划地实现革命目标。
动员过程是动员主体与客体互动的必要途径,直接关系着动员的广泛性和有效性。共青团青年动员的过程,启迪了当时懵懂的青年,建构了青年对革命思想的集体认同感,存续了青年的革命热情,组织参与凝聚了青年的革命力量,为合法性的青年动员奠定了过程基础。
(三)动员方式的合法性
合法性中的权威总是源自于民众的服从、信任与支持,所以合法性理论一般都致力于探讨一种秩序、规范或行动是否以及如何能够赢得民众。由此可见,共青团青年动员的合法性不仅包含内容的合法性、过程的合法性,还应包括方式方法的合法性。一种动员其内容即使完全符合民意,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其过程也合乎逻辑,但如果动员的方式方法有问题,这种社会发动最终也会因为难以将权威内化为社会成员内在的信仰和服从而失去其正当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青团通过文件、通告传达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具有权威性和号召性;通过标语传单、街头演讲启蒙处于懵懂状态的青年,具有感染性和鼓动性。通过文化娱乐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年,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和渲染性。这些动员方式适合当时千百万青年,使动员目标内化为青年参与革命的自觉性。
1.文件、报刊、通告等成为当时青年动员最有力的武器
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各种斗争和战争的环境中,客观条件很差,利用文件、报刊、通告的发行,传递党政各种公文成为一时之选。19世纪30年代的党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是党、政府、军队以及中国共青团刊发重要文件的重要渠道。其先后出刊240期,至少刊发了各级、各类公文473则,内容涉及各种命令、条例、指示、宣言、总结、布告等[6]。这对于动员青年参加革命,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文件、报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青团动员青年的重要途径。1923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中国青年》,就青年关心的学习、组织活动、婚姻恋爱、失学、失业等问题开展讨论,批评不健康的思想和风气,指导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培养青年的革命人生观。在编排上,文字流畅,笔锋尖锐犀利,并配有漫画,成为最受青年欢迎的刊物。共青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的各种刊物,既承担了战时的宣传和动员工作,也总结了青年运动的实践和组织建设理论,为教育和引导青年发挥了巨大作用。
2.标语传单、街头演讲、宣传队是启蒙青年的有效方式
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标语传单和街头演讲作为直观、醒目、通俗易懂的方式,是启蒙对革命还处于懵懂状态的青年最有效的途径。特别是面对突发事件时,共青团组织进步青年分发传单、街头演讲,通过激昂的语言、亲切的称呼,不仅对青年学生面对国难所产生的激愤给予正面引导,而且鼓舞各界青年的抗战热情,使他们自愿加入到共青团组织领导的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之中,从而保证了青年动员的持续性和深入性。
上海“五卅”惨案后,青年学生冒雨上街游行演讲,散发《泣告书》、《同胞们,赶快罢市罢工抵抗》、《告中国巡捕》和《上海市民速起反抗外人残暴》等动员“三罢”斗争的传单五六十万张。这些让人热血沸腾的语言,唤醒了民众,促成上海二十余万工人罢工,5万学生罢课,大部分商人罢市的景象[7]。
3.文化与娱乐相结合,传播文化知识,宣传革命道理,提高革命热情
斯诺认为,为了有效地动员群众,需要在大多数场合将动员主体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进行改造,将其与动员对象的直接利益或情感联系起来[8]。共青团为了能使青年动员不断深入,将宣传革命思想与提高青少年文化水平结合起来,使青年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党的革命纲领,接受抗战教育。抗日战争时期,共青团创办了青年夜校、冬学、识字班等,编写了许多通俗且富有鼓动性的识字课本,把识字和政治、娱乐结合起来,通过开展识字先锋员和模范识字组活动,在青少年中掀起学习文化的热潮。共青团还通过举办歌咏、秧歌、游戏等娱乐活动,以及组织时事研究小组、开办图书室、流动图书馆等形式,把进步文化带到农村,有效地推动了农村根据地移风易俗、破除迷信的新风气的形成。
4.注重组织建设
有效的组织建设培养了开展青年动员的领袖和骨干,为青年动员的合法性奠定必要的人才基础。共青团作为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通过培养领袖和骨干,保证了在革命道路上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土地革命时期,为了配合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各级共青团组织根据党的相关文件和指示,积极发动团员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培养青年军事骨干。
据不完全统计,黄埔军校学员中就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五六十人,约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在国共合作时期,先后到黄埔军校学习的青年团员达五百余人。共青团还号召他们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举办的六届讲习所中,培养了721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全都是18~28岁的青年,其中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9]。这些经过培训的团员,成了国民革命的骨干力量,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夺取北伐战争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共青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动员所采用的方式,符合这一时期青年的特点和社会现实,唤醒了处于迷茫状态的青年,引导他们将革命信念转化为革命行为,自发地投身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去。
结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青团青年动员是具有合法性的青年动员,它拥有让青年自愿服从、认可的动员内容、过程(机制)、方式的合法性基础,赢得了青年的普遍认同和追随。共青团青年动员弥补了自发性社会动员的缺陷,成功地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与青年的发展目标相结合,通过政治动员,不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及路线,形成了青年自觉的革命理想,从而影响了青年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变,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斯大林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33~334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35~636页。
[3][7][9]李玉琦:《中国共青团史稿1922—2008》,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年版,第40、74、20 页。
[4]团中央办公厅:《中国共青团团史简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77~78页。
[5]《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6]韩 云:《“红色中华”的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载《青年记者》,2011年第5期。
[8]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