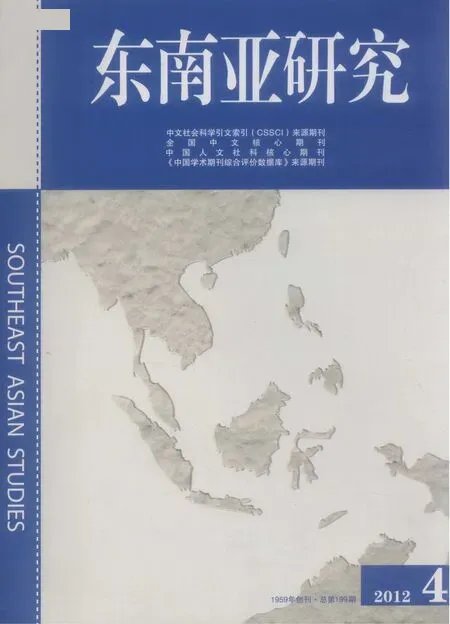东南亚的政党与国家
(新加坡)王赓武著 吴宏娟译 吴金平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新加坡;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州510630)
东南亚的政党与国家
(新加坡)王赓武著 吴宏娟译 吴金平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新加坡;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州510630)
政党;民族国家;西欧;后殖民时期的东南亚
当欧洲的封建王朝承认其领土内拥有共同文化和历史的人民可以自组国家的时候,政党就变得日益重要。这些政党尽管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但都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裕、强大和统一。随着英国、法国、荷兰等帝国势力的撤退,这一模式被带到世界其他地方。在东南亚,帝国势力撤退后留下的国家既没有共同文化也没有相似历史,因此,许多由当地政治领袖创建的政党就试图利用国家机器来建构民族国家。本文主要考察这种“引进”的民族国家模式在东南亚如何催生各种各样的政党,这些政党又为何需要强大的国家来塑造未来的民族。各种经验表明,在民族国家中能发挥影响力的政党,对正努力将自己看作新生民族的人们及其生活,可能起着分化与破坏作用。
一 引言
在过去的200年里,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全世界占有支配性地位。为了不自外于世界主流,任何国家都必须或者最终走向民族国家之路。有人认为,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制度正受到全球化进程的巨大挑战。但是,仍有无数例子表明,民族国家是所有外交关系的基础。尽管地区主义与全球化的冲击不小,民族国家制度仍保持高度的适应性,毫无式微之象。本文集中考察民族国家的一个方面,即二战后政党在东南亚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它同时也在思考,这种作用是否总是有益的?政党是否也可能使业已存在的分歧永久化,甚至进一步破坏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
1945年,民族国家在东南亚还是一种新生事物。二战结束时,东南亚有一些或多或少可与日本、韩国这样的同质化国家相比较的原生民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越南,另外还有泰国、老挝和柬埔寨。至于其他地方,则未发现一丝一毫民族国家的痕迹。东南亚政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放弃殖民时期的国家架构,努力去寻找一种能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例如印尼和缅甸;另外一种是,保留帝国势力遗留下来的国家架构,并试图通过自己的政党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就像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因此,与欧洲或世界其他地区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建立的民族国家相比,东南亚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关于政党的权威研究中,他只是考察了政党在原生民族以及那些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里的作用,而对于还没有建立民族国家的地区的政党,却并未涉及;同样地,他也没有论及那些在殖民者离开之后才开始民主化的后殖民国家[1]。
在“还没有建立民族国家”,或者“在殖民者离开之后才开始民主化”的东南亚后殖民国家里,1945年以后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政治形态。第一种是,政党之间完全互不信任,政府凌驾于政党之上,只允许“王室”政党存在,例如某一时期的泰国和文莱、军人主政的缅甸以及1998年以前的印尼。第二种是,主张革命的共产党获得胜利,例如越南和老挝,柬埔寨也差不多如此。第三种情形出现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现在的泰国、印尼和柬埔寨。在这些国家,尽管不同政党对于民主的理解不同,但都有着强烈的民主诉求。在这些案例中,一个、两个或者更多政党,包括多党联盟,都有其实践国家建构的空间。
1945年,东南亚的领导人都在庆祝战争结束与殖民统治在东南亚开始终结。虽然这些前殖民帝国都力图重返东南亚,但它们当中有些已更清醒地意识到:其重返东南亚将是暂时的。对于反殖民者而言,由国际联盟向联合国的转变意义非凡,它象征着对民族国家这一世界体系的重申。这样,一整套可供未来的民族国家用以对照自身的标准被建立起来了,以一种能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方式去“认可”与“被认可”具有了可能。
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都意识到,它们继承的只是国家的某些形态,但还远不是欧洲经典模式的民族国家。不过,每一个国家都成立了政党或者可能发展成政党的组织。每一个政党的领导者都希望自己的政党成为治理国家的工具,最终塑造国家的命运。在他们看来,这些政党肩负着终有一天把他们的国家建设成为成熟的民族国家的使命。
那么,政党是什么?莫里斯·迪韦尔热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脱胎于西欧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由传统意义上的组织演进而来。而传统意义上的组织由享有共同利益的人们组成,他们行动一致,并对其所在社会施加政治影响。根据这一定义,在1945年的东南亚,尚未存在这样的政党。事实上,东南亚语言中的“政党”一词是由英语“party”翻译而来的。至于翻译的方法,有的是在当地语言中寻找大致等同的词语;而在很多地方,则只是简单的音译,用当地语言的拼法拼写出“party”的读音。用前一种方法翻译,一些被选用的当地词语本来就有其特有的意义,甚至可能与欧洲“政党”中所内蕴的民主假设相矛盾。例如越南语中用以表示“政党”的词语,就来自日语和汉语中的古词语“dang”。而在这两种语言中,“dang”的原始意义都与“派系”有关,其构词隐含秘密与共谋之意,与欧洲“政党”概念中的民主假设是直接冲突的。
迪韦尔热的研究考察了当时已知的各种政党及其结构,以及政党制度在19-20世纪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虽然在东南亚并没有出现所有类型的政党,但是迪韦尔热呈现出来的这幅政党“全景图”对于东南亚已经出现的政党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参照。不过,还有许多可能的情况是迪韦尔热还没有考虑到的,并且这些“可能的情况”在亚洲新的政治条件下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迪韦尔热没有将政党与国家建构联系起来,也即,在尚未建立民族国家,而其政党领导人又希望通过政党塑造国家未来的地方,政党发挥的是什么作用,迪韦尔热对此并没有研究。他没有论及一种可能性,即一个国家(nation)可能并不仅仅是民族国家 (nation-state)或者国家民族 (state-nation),还可能是政党国家(party-nation)。他也没有注意到,欧洲的一党制国家是法西斯和共产党为了改变主流的民主政党而建立的,而在亚洲的一些国家,类似的政党从一开始就在其力所能及之处掌握了主动权,而一旦它们掌握国家权力并且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国家就开始形成。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欧洲的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接受被任何执政党控制,而不会建立自己的政党,而在亚洲,只要一有机会,军队就会趁机建立自己的政党。
二 政党与国家建构
本文并不准备讨论政党的概念在东南亚的全部内涵,在此笔者将集中探讨几种主要类型的政党,并且直指一个问题:这些政党对其誓要建立的那种国家产生了什么影响?首先,这些政党从何而来?有一些可追溯到20世纪早期,而更多的是1945年以后才成立的①最早参与管理国家的政党是1907年成立的菲律宾国民党 (The Nacionalista Party)。其领导人马努埃尔·奎松 (Manuel L.Quezon)是东南亚地区第一位发表下列观点的人:“当我开始忠诚于国家的时候,就不再对政党忠诚了”。见Teodoro A.Agoncillo,Filipino Nationalism,1872-1970,Quezon City:R.p.Garcia,1974.。政党组织主要有三种来源,但关注一些政党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如何改变其结构和功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造成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那些政党领导人试图领导和管理的国家的国情,特别是他们在建构新国家的过程中将要发挥的或没有发挥的作用。
东南亚最早出现与最普遍的是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包括宗教的或者种族的地方性团体、对当局表达不满的协会,以及反映各种社交与知识分子聚会观点的非正式社会团体等。荷属东印度群岛有几个明显的例子①最好的例子是成立于1908 年的至善社( Budi Utomo) 和成立于1911 年的伊斯兰商业联盟( Sarekat Dagang Islam,后称“Sarekat Islam”,即“伊斯兰联盟”) 。但是,这两者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相反,1914 年由荷兰人授意发起的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 Indonesian Social Democratic Association) 实行一种新的政治领导,并最终于1920 年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个共产党———印尼共产党。见Ruth T. McVey,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Ithaca,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5; Akira Nagazumi,The Dawn of Indonesian Nationalism: The Early Years of the Budi Utomo,1908 - 1918,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1972; Deliar Noer,The Modernist Muslim Movement in Indonesia,1900 - 1942,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这些团体并没有像政党那样组织运行,因为在其成立之时,其所在的地方尚未具备民主的可能。然而,在一些关键时刻,一些团体开始在政治上变得积极,经常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团体联合,在全国范围组成更大的组织,以施展它们的政治抱负。它们虽然代表的是存在已久的深深植根于传统社会的利益,但其逐渐发展成能更有效地发出自己声音的社团机构。但是,这些团体还只是“原生政党”组织。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为了在讨论国家事务的会议上陈述观点,东南亚一些主张以欧洲现代国家为榜样、走欧洲政党发展之路的地方出现了新的政党。在欧洲,一些政党是从早期 (19世纪之前)上层社会群体之间为争夺权力而建立的“前现代”政党发展而来的,但它们最终都顺应民主意识的觉醒,适应正在变化的政治形势而做出改变。在法国大革命后的一个时代里,许多欧洲政党完成了其现代转型[2]。与前述这些政党不同,18世纪末北美13个殖民地对英国统治的反抗最终导致了一种独特的平民主义政党的产生,这也是后来现代政党的主要模式之一。类似的例子也出现在19世纪的澳大利亚。在那里,英国《1832年改革法案》发展起来的模式衍生出了许多典型分支[3]。
美国和法国革命也促使了其他类型政党的产生,而这些政党成了现代革命党的先驱。这种政党,无论是以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其他名义,都自认为比早期的政党更民主,并且常常以人民的名义推翻压迫性政权来夺取权力。在19世纪欧洲的民主化进程中,这些政党对政府构成了挑战。革命者们认为政府的所谓民主有名无实,政府由代表着中产阶级以及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所控制,而这些政党是为了剥削在英国和法国产生的工人阶级而建立的。因此,革命党必须纠正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必要的话,在可能的地方,使用武力②第一个革命党产生于17 世纪的英国,接下来的产生于法国和美国革命之中。之后的亚洲政党,例如中国孙中山创建的革命党,不是效仿法国,就是效仿美国。但是,1917 年之后直到20 世纪80 年代,俄国革命催生了一批新的政党。见Christopher Hill,The English Revolution:Three Essays,London: Lawrence & Wishart,1949; Georges Lefebvre,The French Revolution,2 vols,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62 - 1964; Gordon S. Wood,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 Y. : A. A. Knopf,1992; E. H. 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 1923,London: Macmillan,1950.。
在回顾1945年以来东南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之前,政党的性质与作用值得更密切关注。在大多数国家都被卷入的国家建构的背景中,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这些政党是什么样的?它们在这些国家里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为了建构国家,政党对国家机器的利用或改变达到了什么程度?政党又是如何改变其性质以适应国家变化的?本文仅仅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初步考察,其他更大的问题,笔者将只是简单涉及。例如,笔者本应该从国家的文化、社会和宗教方面去探寻政党性质的历史根源。而且,把“经济增长改变了政党的性质及其所处的环境,使它们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变得脆弱”作为贯穿全文的主要思路,也应该是重要的。然而,笔者主要关注的是,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是如何改变或者彼此维持的。
三 革命党与国家建构
在已形成的众多类型的政党中,笔者选择了三种过去50年里在东南亚地区占支配地位的政党,它们都在国家建构中发挥了作用。第一种是革命党,第二种是军队主导的政党,第三种则是在那些或多或少民主化或者追求民主的国家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政党。在每一种案例里,政党都与国家有着一种独特的关系,而这个“国家”可能业已存在,也可能尚未建立,或者是政党要参与建立的。
在二战后短短几年内组织得较好且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尼与越南的革命党。它们学习欧洲政党的民主模式,在反殖民和自治运动中诞生。在这两个案例中,日本和中国的宽松民主政党在政党的组织方面对其有一定影响,日本于1942—1945年间占领印尼则对苏加诺 (Sukarno)的政党最终领导反抗1945年荷兰殖民者重返的军事行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的不利条件下,一个赋予军队特殊地位的革命党就这样产生了。与印尼不同的是,越南当时已经具备了建立一个独特国家的种族与文化基础。于是,越南革命党控制并且利用国内民族主义运动,先后反抗法国与美国的殖民统治,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4]。相比之下,印尼还强烈地需要糅合几个潜在的民族要素,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当务之急是给予这个新国家一个可靠的身份认同,这是激发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共同体”观念最迫切、也是必须的步骤[5]。
印尼和越南都曾经走过共产主义道路,共产党在这两个国家的出现都很早。在越南,共产党取得了胜利。除了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了中国大陆的帮助,中国大陆从国民党统治转向共产党的胜利,越南革命也走上了这样的道路。在1955—1975年这20年战争期间,越南共产党在其周围聚集起了一批小的政党及民间团体。现在,它以一个大联盟,也即越南祖国阵线 (The Vietnamese Fatherland Front)的名义统治国家。这样,越南共产党视自己为国家的代表,并且为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创建了相应的国家架构。相反,印尼共产党失败了,因为它未能展现革命战争所需要的建设国家的热忱,相反,它运用以阶级为基础的国际主义辞令,与自认为是革命的真正领导者的民族主义武装分子展开争论。最后,印尼共产党发现自己被其不能控制的国家结构与想象的民族共同体所排斥——在这两者的形成过程中,它没有起任何作用。
东南亚地区还不乏像印尼共产党这样最终失败的例子。其中最有名且实力最强的是马来亚共产党,它与中国、印尼、越南、泰国以及沙捞越的共产党都有联系。尽管其民族主义的对手从来都不怎么强大,马来亚共产党也极力宣称自己的最终目标是民族主义,却还是成为刚刚开始国家建构的多元社会的牺牲品。一个地方如果不具备形成国家的要素,政党及其军队再有勇气,做出再大的牺牲,都不足以弥补这一缺陷,马来亚共产党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太晚了[6]。
在泰国和菲律宾,还有一些作风温和却值得注意的共产党,而缅甸则有革命党。越南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为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其他地方建立类似政党提供指导,特别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 (The Khmer Rouge)和老挝的人民革命党 (The Lao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7]。此外,国际主义思想促使它们在亚洲向中国或者越南寻求帮助,而后来发生的事件迫使它们,特别是缅甸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改变了方向。这些国家的政党都接受了国外共产党的帮助与支持,其中唯独老挝借助“手足情深”的越南共产党的帮助夺取了政权。这些政党是没有能力夺取国家政权的,不过,这些政党的激进主义事实上已对各自国家政府建构新国家的努力造成了影响。至少,它们为反殖民主义的产生做出了贡献,还在各自国家激起了工人与农民的平等主义意识与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这些政党的实践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尚未具备形成国家要素的地方,为了建构国家,革命党应该首先转向民族主义运动。
四 军事政权与国家建构
第二种政党是军队主导的政党,即便它们实际上不是由军队建立的。在欧洲,军队主导的政党还称不上一种特定的政党类型,而更多只是政党在发展中的暂时偏差①在拉丁美洲,欧洲殖民者建立起了牢固的军事政治。对于这个现象,目前已有很多很好的研究。例如,Abraham F.Lowenthal和J.Samuel Fitch编辑的Armie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N.Y.:Homes&Meier,1986)一书就是对这一内在问题的有用调查。而美国在菲律宾部分地方的统治似乎及时遏制了这种类似的趋势。。但是,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军队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即使不能直接掌控国家,也要求自己的声音能被听见。这种军事政权出现得很早,甚至在民族主义开始获得广泛关注之前就出现了。那就是在泰国,1932年军队帮助推翻了绝对的君主统治。新政权以“新泰国”之名建立,此后在其控制中央政府的努力中经历了诸多沉浮起落。在与官僚体制的配合中,军队其实并不一定需要政党。1945年以后,军队虽然被迫建立或者支持一些政治组织,但这些政治组织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支持。20世纪70年代以后,军队统治制度不得不让位于民主制度。军队统治失败的原因涉及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一个接受更好教育的社会的出现,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强大的中产阶级建立起了一套新的国家标准。这是军队精英们不愿意接受,更不准备去实现的。改变的压力来自于军队领袖们所不能控制的外部事件,但最终导致其垮台的,是他们自己不能领导国家去适应变化。相反,那些能够调整自己去适应变化的政党,得到了国内外的认同[8]。这种得之不易的认同目前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
然而,在缅甸,截至20世纪60年代,军人控制了整个国家,并且试图取缔此前所有的政党。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权力体系,并以此统治了这个国家40多年。有意思的是,军队领袖们给保证其权力的组织冠上各种各样的名目。总的来说,他们避免使用“政党”一词,强调其所要扮演的一种在他们看来超越政治的民族角色。然而,很明显地,它们就是政党,而且实行的是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后,缅甸军方被迫重开“党禁”大门,并受到来自全国民主联盟 (The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的直接挑战,但军队领袖们还是坚持认为,国家的命运太重要了,不能交到政客及其政党手中。正是以国家与国家团结的名义,军人掌控着这个国家。可以说,对于军人而言,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民族国家,也不仅仅是由国家塑造的民族。尽管并没有成立自己的政党,但他们集体所做的,就像是统治一个政党国家——所有一党制国家所致力要做的事情[9]。
军事政权在印尼的发展可以拿来与上述国家做一比较。1965年以后,印尼由军队掌权,但其发展轨迹却有所不同。虽然不像泰国、缅甸那么明显,但是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军队主要官员充当着专业集团党的根本基础,而该组织是苏哈托政权建立的,它发挥着执政党的作用。不过,与泰国和缅甸一样,印尼当局也极力淡化专业集团党作为政党的观念,将其塑造成一个代表所有人的民族精神的团体。另外,虽然从来没有大肆宣扬,印尼当局的潘查希拉思想代表的就是专业集团党已经着手建构的国家的本质。这是专业集团党为保证其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掌握所做的一种努力[10]。
这些军事集团是否称得上一种特定类型的政党,目前还存在争议。不过,事实表明,只要形势需要,军队精英们是有能力组成政党的。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二战前的泰国,就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影响。日本军队以天皇的名义掌握了国家政权,颠覆了新生的民主制度[11]。另一方面,泰国军队也没有寻求民主支持便以“新泰国”的名义夺取了国王的权力。在缅甸,由于民主政党的分裂与软弱,军队宣布接管国家,紧接着便开始建构他们自己的权力制度。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一种制度一点也不需要政党参与其中,但是,对1945年以后的东南亚而言,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这些军事集团就是军队主导的政党,要求在国家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五 民主政党与国家建构
最后,第三种政党就是民主政党,它们的存在需要或多或少的民主条件。目前东南亚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政党。菲律宾1945年独立后的几年间,出现了试图像美国那样实行两党制的自由党和国民党。但是,一些激进的政党对它们形成了挑战,其中包括无法接受这两个政党所代表的狭隘阶级利益的工人和共产主义组织。而且,由于成员的流动性以及政党路线存在诸多交叉之处,这两个政党之间的差异逐渐被模糊了。不久之后,费迪南德·马科斯 (Ferdinand Marcos)从自由党转向国民党实现了“一党”的跨界和交叉,最终导致了这种双重性与两党制的终结。可见,两党制在菲律宾受到质疑,以至于被不断涌现的短命政党或为了赢得选举而暂时组成的政党联盟所取代[12]。
有证据表明,在菲律宾,西班牙的政治传统并没有完全为美国的政治传统所代替,而且,受拉丁美洲政治运动影响,军事政变也变得频繁。但是,美国殖民遗产仍然影响很大,民主制度在菲律宾生存了下来。菲律宾的国家建构似乎并不依赖政党,组织完备且实力强大的社群组织,尤其是天主教会,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然而,其他由少数民族(例如摩洛穆斯林)或者经济实力强大的华人领导的力量,恶化了政党政治的问题,而政党政治曾一度被国家寄予厚望。例如,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党 (The LAKAS Christian-Muslim Democrats),这个由前总统拉莫斯 (Ramos)创立的政党联盟,表现出了学习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取得成功的联合执政模式的迹象。
这使笔者联想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实行的政党制度。它们都宣称这两种政党制度是借鉴英国议会制度而来的。1945年,这两个地方政党制度的开端并不起眼。当时,英属马来亚各地的种族骚乱和武装暴动加速了英国殖民者离开的步伐,但建立政党的有意义的尝试却主要是受外部影响。其中,有来自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影响,也有来自印度国大党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的支持,更近一点,还有与当时已经开始自称“印度尼西亚人”的荷属东印度群岛民族主义者的联系。不过,殖民当局对马来封建君主和贵族的支持以及不断增长的移民贸易利益延缓了当地政党的建立,同时也削弱了国家认同的形成。所以,当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获得独立时,关于应该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众说纷纭。这些说法要么互不相干,例如不同族群的不同理想,要么目标相反,例如上层阶级及工人阶级各自的政党。此外,英国通过英式教育为整个马来亚培育人才的努力对于塑造新的国家精神而言,也显得杯水车薪,并且太迟。而且,这样的做法事实上也对在方言学校就读的学生起到了离间效果,深化了种族与阶级隔阂。1961—1965年,以一个新的、更大的马来西亚联邦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统一马来亚联合邦及新加坡殖民地的努力失败后,这两个国家的政党制度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马来西亚,由三大公共政党组成的政党联盟于1957年领导国家走向独立,从此开始了对这个国家的统治[13]。后来的国民阵线 (The Barisan Nasional,BN)是在最初三个政党的基础上扩大而成,并试图让更多的反对党也加入其中。目前国阵由超过12个政党组成,其中有些非常弱小,甚至是分裂的。至于剩下来的反对党,它们也尝试组成另一个政党联盟,以战胜国阵。最近组成的反对党联盟已经对执政党构成了严重挑战。就“只有另外成立一个政党联盟才有希望打败执政党联盟”这一点而言,马来西亚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党类型,即联盟政党。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事物,但是在东南亚地区,还没有别的政党联盟比马来西亚的政党联盟存在时间更长,而且,除了内部的一些政治斗争,也没有别的政党联盟比其更稳定。当然,更没有哪一个政党联盟像马来西亚政党联盟这样,一心一意地要建立一个以“在马来人土地上的马来人至上 (Ketuanan Melayu)”为宗旨的民族国家。
事实上,国民阵线作为政党的性质是由马来人领袖认为可行的国家类型决定的,而这种类型的国家之所以可行,主要依据在于马来西亚的人口结构。也就是说,政党联盟这一途径,并不仅仅是为了无限期地保持某一政党或者政党联盟的执政地位,而是为了保证一种关于国家形态的构想能够有机会以非暴力、不流血的形式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党联盟制度本身就是更令人满意的,组成联盟的每个政党都是一种理想的政党,或者其政治家相对其他政党更无私、更廉洁。到目前为止,这种制度使国家的建构者可以克服多元社会传统可能导致的分裂倾向。因此,马来西亚的发展道路显示了,东南亚地区的特定政党可以将国家置于政党之上,而其成功取决于一个强大的、能够使行政体系有效运行的国家制度[14]。
在泰国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主化进程中也能找到可以与此做一比较的政党联盟。在泰国,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联盟类型的政党先是取得国家权力,尔后在选举中落败,存在时间最多不过几年。即便是平民主义的泰爱泰党 (Thai Rak Thai party),也不得不通过与其他较小政党组成联盟来统治国家,然后被另一个同样不稳定的政党联盟推翻。到目前为止,以君王为象征、得到官僚精英支持、但强调民主政治的泰国,已陷入全面瘫痪状态[15]。这使得泰国政党的立场更接近于欧洲那些既不为国家建构所需要,亦不对国家团结起关键作用的政党。因此,它们可以自由地代表地方的或者其他小集团的利益。
现在讨论1998年以后印尼政党的作用还为时过早。目前印尼有如此多的政党,而各党成员改变党籍的现象似乎相当频繁。印尼新的总统制度建立在普选的基础上,总统不得不长时间依赖有相同政见的政党联盟。不管怎样,这可能是必须的。很简单,因为任何单一的政党都没有足够的人力去统治一个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家,也无法代表其复杂多样的社会群体利益。不过,如果可以将马来西亚视为榜样,那么联盟政治不失为一种典范。很难说这样的一种联盟是否稳定,但是更难想象的是,单一的政党能够独自或者与其他单一政党一起建构一个大多数印尼人想要的国家。为此,需要一套权力影响广泛的国家机器。这提醒我们,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机构,将会长期处于混乱无序且脆弱的状态。对于印尼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强大的国家机构的缺失将导致其政党难以形成建构新国家所必需的粘合力。因而印尼面临的巨大困难在于,它既不是国家民族,也不是政党国家,而被迫在想象中飞跃成为民族国家。或许,仅仅为想象中的国家所鼓舞,印尼的领导者们就会知道印尼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拥有什么样的政党[16]。
至于新加坡,其情况与东南亚地区其他任何国家完全不同。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 (People's Action Party,PAP)一开始是欧洲很多国家都有的那种左翼社会民主党,但是,1961年以后,它开始从大众型政党向精英政党转变。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复杂的,外部的政治压力包括越南战争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解释。不过,从政党的领导能力这个角度来看,人民行动党敢于改变路线,建立一种有助于巩固权力的国家结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改组后的人民行动党吸取了欧洲类似政党的教训,不过更直接的教训可能来自其他地方,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的组织严密、根植于革命党的精英政党。因此,与马来西亚的联盟政党相比,新加坡政党的发展道路无疑是截然不同的[17]。
英国试图为其殖民地和保护领地建立的马来亚殖民国家,就这样创造了两种如此不同的政治制度,并且其两个部分分别由国民阵线和人民行动党这两个不同的政党主政,这几乎让人难以置信。不过,在1961—1965年间,人民行动党确实企图在它支持的马来西亚联邦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中协商得到一个特殊的角色,但是,对其而言,与一个它不能也不准备加入的政党联盟共存,其中的矛盾可想而知。事实上,合作的失败使人民行动党寻求独自开拓一条新的道路变得更加必要,而这条道路通向的是它能保卫的国家。人民行动党与至少6个反对党共存 (还有一些仍登记在册但不再活动的政党)。从1965年开始,为了保证其建国计划持续推行,人民行动党利用它所继承的强大国家政权的一切手段,击败了反对党。目前,新加坡这个国家似乎仍在其既定轨道上,而掌权的人民行动党决心要保证这条道路的畅通。人民行动党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似乎是可行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小岛国,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新加坡人口的种族构成中,有一个明显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族群——华人。忠贞不二的人民行动党已经为新加坡的未来做好了不止40年的规划。如果说东南亚地区有一个主要由单一政党建成的国家,那么,那一定就是新加坡[18]。
上述案例提醒我们,政府的民主制度是可以由不同类型的政党来推行的。在此我们可将柬埔寨包含在内,尽管其政党比不上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的,也很可能不会发展出自己的政党制度。柬埔寨政党的混合性非常明显。柬埔寨人民党 (The Cambodian People's Party)仍然保持着其革命传统,民族团结阵线 (The United National Front)或者说奉辛比克党 (Funcinpec)则是保皇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平民主义的奇特混合物。还有一个以其领导人森朗西 (Sam Rainsy)的名字命名的森朗西党。只要柬埔寨继续沿着现在这条通向民主的道路前进,那么这些不同的政党终将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集合起来。柬埔寨政党证明了它们与外国殖民者遗留下来的民主制度进行合作,并且对其加以改造以满足自己特定需要的能力。接下来使它们为人称道的是,它们衡量建构国家所需要东西的方式,以及它们如何利用所继承的国家架构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接着,它们可能会宣布成为具备民主合法性的政党,以使自己变得更加有效与独特[19]。
六 结论
东南亚的政治领导人,包括其反对者,都将欧洲的政党模式视为衡量一个政党成功与否的标准。莫里斯·迪韦尔热及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即使还算不上“指南”之类的,但也就如何组织政党,及其应该或者不应该做什么等问题,提供了指导。然而在实践中,许多政党发现,它们都不得不各自面对“未经教科书批准就出现”的新挑战,包括所期望的国家尚未存在这样的关键性事实。当这些政党为了保证生存而临时灵活调整自身的时候,借鉴欧洲政党模式其实对他们帮助不大。那么,关于前面提出的问题,即政党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国家所要发展的道路及时实现,笔者已经说明了,这也取决于非殖民化后遗留下来的国家架构的状况。对于殖民时期的国家制度遗产,东南亚地区的人民是接受还是拒绝以之为建国的基础?他们是否认为这是保卫国家所必需的?对于目前的国家情况,他们是否认为既不是“民族”,也不是“民族国家”,而更像是一个必须以国家形象来塑造民族的“国家民族”?
通过考察执政党的性质,这些问题可能会得到解答。无论如何,要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做出概括与归纳似乎不太可能。在独立时就确认存在原生民族的地方,例如越南,是民族决定其所需要的政党类型,以确保民族团结以及为国家服务。但是,在尚未存在民族而不得不从零开始建构国家的地方,就像东南亚其他的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印尼、马来西亚和缅甸,各种不同的政党或者政党制度都有可能出现。在这些案例中,问题主要在于哪个政党会成功夺取国家权力并且利用国家制度推动国家朝着自己想要的那种形态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和印尼的革命党发挥了非常不同的作用。越南劳动党(The Vietnam Workers'Party),也即现在的越南共产党,很明显地独自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其他所有政党,或被破坏,或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与其合并。由此看来,单一政党可以宣称代表国家,而确定符合新的国家需要的国家形态则是这个政党的责任了。
而在印尼,革命催生了很多政党,它们都认为,政党在未来印尼国家塑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鉴于将要组成的印尼国家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构成的复杂性,这样的发展是颇为符合现实需要的。取得胜利的革命党可以选择像1965年之后那样采取军事途径,或者反映多种族与多中心的多样化要求,走上民主道路。而当时印尼作为一个民族尚未成形的事实也要求,不同的利益在国家制度中得到适当的体现。没有一个单一政党可以独自承担建构国家的工作。目前,印尼人民在两种不同的政党之间获得了平衡,但是,有趣的是,如果这两种政党混合,以军人为民主制度之首,会不会也行得通?但问题在于,印尼大多数领导人所理解的国家目标的性质实际上能否塑造出一种能长久统治国家的政党?到目前为止,对于印尼来说,还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有足够长的时间利用国家制度去确定其想要建构的国家类型。
如果我们转向讨论不稳定的军事政党,那么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政党是否应该一直控制军队?或者军队是否应该操纵政党?在越南,就像中国一样,政党控制军队依然是一个信条,并且很可能会持续下去。而军队操纵政党,在东南亚的其他地方更加普遍。我们已经看到,军队是多么频繁地成功操纵了政党,即使它事实上并没有控制政党。军队对政党的操纵总是不稳定的,即使在缅甸这样的已被军队控制了很长时间的国家。而如果专制军队对权力的滥用激起了愤恨以及强烈的民主反对,军队的所谓建构国家的口号也就不足信了。
但是,是否那些坚持民主的政党在国家建构中就做得更好呢?目前在泰国活跃的政党并不像欧洲的任何政党。直到21世纪,它们都还是太年轻、太反复无常,因此,除了推进国家机器实施的或者平民大众要求的政策之外,做不了多少事情。到目前为止,在泰国南部以及东北部的国家建构中,它们做得并不比军事政权好。更有甚者,许多泰国人都不认为执政党是为国家服务的。很多人怀疑,它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政客们以国家利益为代价中饱私囊的工具。不过,在菲律宾,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相反的趋势。菲律宾的政党可能满足了特定社会集团的需求,也符合某种选举民主的标准,但是,它们也削弱了许多国家制度的作用,其中包括那些致力于发展经济与维持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制度。由于不能有效实施国家制度,菲律宾政党也在那些已经在国家建构进程中被忽略的群体中失去了威信,特别是南部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如果说,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是国家繁荣所必需的,那么,菲律宾政党体制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掌握国家前进缰绳的两个政党似乎都表现得比较好,但是,对它们来说,是什么构成国家,这仍然是个不易解决的难题。因此,核心问题就在于,控制和培育国家制度。通过国家制度,政党可以明确什么是它们可以或者不可以向人民传达的,而这又是政党巩固其威信和合法性所需要的。如果它们能够有规律地做到这一点,那么它们就赢得了建构国家所需的时间。不过,没有人会知道,这两个国家最终各自建立起其所期望的国家还需要多长时间。
东南亚地区的政党种类几乎与国家数量一样多。但是,没有一个与西方传统的政党相似。在那些民族意识已经形成或者即将形成的地方,政党表现得更像一个准备好去完成这项任务的组织;而在民族意识尚未形成的地方,政党则有一系列可以扮演的角色。它们要么描绘未来国家的蓝图,要么防止已开始出现的国家分裂,要么为终将出现的国家创造更好的条件。很多东西取决于政党能否充分利用时间将其努力完全付诸实践。然而,正如前文案例所显示的,政党所能利用的国家架构的状况才是最主要的因素。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对比是鲜明的。当继承下来的国家架构软弱无力时,政党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并且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保证事情完成。反之,政党就能很快取得很大的成就。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变量,例如多元社会里的种族融合、贫富差距的悬殊、外界压力的强度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状况有多复杂,对于政党来说,与其为不可预测的国家建构去努力,不如为既有的特定民族服务,那样会更有好处。这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东南亚地区的大多数政党仍然在国家建构的道路上摸索着。与此同时,东南亚地区想要建立自己国家的人们,应该将目光越过政党而看得更广更远。实际上,他们已经以积极参与更大范围组织的行动来付诸实践了。通过培育民主生态环境,他们不仅有机会直接为国家建构做出贡献,还有机会使将来政党角色合法化。
【注 释】
[1]Maurice Duverger,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translated by Barbara and Robert North),3rd revised edition,London:Methuen,1969(first published in 1954).
[2]Guido De Ruggiero,The History of European Liberalism(translated by R.G..Collingwood),Boston:Beacon Press,1959(first published in 1927).
[3]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new translation by George Lawrence),N.Y.:Harper& Row,1966;Seymour Martin Lipset,The First New Nation: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Y.:Basic Books,1963;Rudolph M.Bell,Party and Fac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1789 -1801,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73;Dean Jaensch,Power Politics;Australia's Party System,St Leonard's:Allen& Unwin,1994.
[4]David G.Marr,Vietnamese Tradition on Trial,1920-194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William J.Duiker,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Boulder:Westview Press,1981.
[5]George McT.Kahin,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2;Benedict R.O'G.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Verso,1983.
[6]最近出版的著作有:Chin Peng,My Side of Histor,As Told to lan Ward and Norma O.Miraflor,Singapore Media Masters,2003,而C.C.Chin与Karl Hack编辑的 Dialogues with Chin Peng:New Light on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2004)一书则为早前的研究增加了另一个维度。
[7]Thomas Engelbert and Christopher E.Goscha,Falling Out of Touch:A Study on Vietnamese Communist Policy towards an Emerging Cambodian Communist Movement,1930-1975,Clayton: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Monash U-niversity,1995;Martin Stuart-Fox,Laos:Politics,Economics and Society,Boulder:Lynne Rienner,1986.
[8]Suchit Bunbongkarn,The Military in Thai Politics,1981 -1986,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87;Donald F.Cooper,Thailand:Dictatorship or Democracy?London:Minerva Press,1995.
[9]Aung San Suu Kyi,Freedom from Fear,and other Writings,N.Y.:Viking,1991;Josef Silverstein, Burmese Politics:The Dilemma of National Unity,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Robert H.Taylor,The State in Burma,London:C.Hurst,1987.
[10]Leo Suryadinata,Military Ascendancy and Political Culture:A Study of Indonesia's Golkar,Athens,OH.:Ohio U-niversity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1989;Damien Kingsbury,Power Politics and the Indonesian Military,London:Routledge-Curzon,2003;Angel Rabasa,The Military and Democracy in Indonesia:Challenges, Politics, and Power, Santa Monica:RAND,2002.
[11]Herbert P.Bix,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N.Y.:HarperCollins,2000;Peter Wetzler,Hirohito and War:Imperial Tradition and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in Pre-war Japa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8.
[12]Jennifer Conroy Franco,Campaigning for Democracy:Grassroots Citizenship Movements,Less-than-democratic Elections,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the Philippines,Quezon City:Institute for Popular Democracy,2000.
[13]Cheah Boon Kheng,Malaysia:The Making of a Nation,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2.
[14]Francis Loh Kok Wah and Khoo Boo Teik eds.,Democracy in Malaysia:Discourses and Practices,Richmond:Curzon Press,2002;Diane K.Mauzy,Barisan Nasional:Coalition Government in Malaysia,Kuala Lumpur:Marican & Sons,1983.
[15]Pasuk Phongpaichit and Chris Baker,Thaksin:The Business of Politics in Thailand,Bangkok:Silkworm Books,2004;Likhit Dhiravegin,Political Attitudes of the Bureaucratic Elite and Modernization in Thailand,Bangkok:Thai Watana Panich,1973.
[16]Bob S.Hadiwinata,The Politics of NGOs in Indonesia:Developing Democracy and Managing a Movement,N.Y.:Routledge,2002;Edward Aspinall and Greg Fealy eds.,Local Power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Decentralisation and Democratisation,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3.
[17]R.K.Vasil,Governing Singapore:Democrac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Singapore:Allen & Unwin,2000.
[18]Chan Heng Chee,The Dynamics of One Party Dominance:The PAP at the Grassroots,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76;Lee Kuan Yew,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The Singapore Story,1965 - 2000,N.Y.:HarperCollins,2000;Garry Rodan ed.,Singapore Changes Guard:Soci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rections in the 1990s,Melbourne:Longman Cheshire,1993;Lam Peng Er and Kevin Y.L.Tan eds.,Lee's Lieutenants:Singapore's Old Guard,St.Leonard's:Allen & Unwin,1999.
[19]Sorpong Peou ed.,Cambodia: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Aldershot:Ashgate,2001;The 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uthority in Cambodia(UNTAC):Debriefing and Lessons,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ingapore August 1994,Bost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5;David P.Chandler,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Politics,War,and Revolution since 1945,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D733
A
1008-6099(2012)04-0004-10
2011-06-11
(新加坡)王赓武,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原所长。
[译校者简介]吴宏娟,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杂志社编辑;吴金平,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
原文载于Millennial Asi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India:Association of Asia Scholars,Vol.1,No.1,2010,pp.41-57。本文经王赓武教授授权翻译并审阅发表。
【责任编辑:王 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