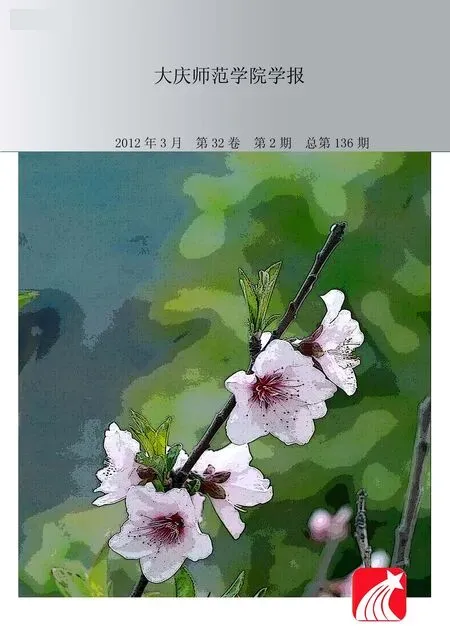浅析切·米沃什的佛教思想
张 昊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北碚 400715)
波兰诗人切·米沃什是一位复杂而矛盾的诗人,他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称其“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他命途多舛,见证过大屠杀也见证过集权统治,做过社会主义者,也做过社会主义的逃亡者,战争中他加入过抵抗组织,战后做过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之后又从社会主义波兰逃至法国,再之后在美国定居并任教,1981年时又回到波兰,最终在波兰的克拉科夫辞别人世。
这些复杂经历大致可以归结为两次重大的事件——战争和流亡。其中,被迫强加的战争几乎摧毁了整个欧洲的文明和一代人的理想,同时自然也带给人们深刻痛切的反思;而流亡的经历则使得他能够摆脱思想和写作上的束缚,能够更为自由、客观地审视和记录历史和现实。与此同时,有着如此纷繁复杂的经历,切·米沃什的思想体系也注定是繁杂丰富并且充满矛盾的。尤其是当涉及个人精神领域基石的宗教思想时,他的思维体系中往往包含着诸多不同的宗教思想和宗教元素。“路易斯·埃瑞巴恩形容米沃什既是诗人也是哲学家,既是东方人也是西方人,既是过去的人也是现在的人,既是孩子也是先知,既是雅各也是赞美诗的作者”[1]。
作为一个有着超越视野和长远眼光的诗人,米沃什不会也不可能将自己限定在单纯某一种宗教之中,更不可能将自己限定在单纯某一种排他性宗教之中。从某种角度来说,他这种复杂包容的宗教思想和他“通过神学对话,尤其是佛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对话,结出了普世性的硕果”[2]67的佛教有着一定程度的相合之处。当然,米沃什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单属于某一种宗教,只能说在多种神学思想中,他更倾向于哪一种。
一、对天主教的失望
出身天主教家庭的米沃什是个不折不扣的天主教徒,但是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险将人类拖入灭绝边缘的冷战的20世纪,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来说,都不啻为一场深刻透骨的精神危机,因此哲学家阿多诺才会痛切地感叹:“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而米沃什恰恰就生活在奥斯维辛的所在地——被称为“世界的阴沟”——波兰,他目睹了身边大批的犹太人被驱赶入集中营和毒气室,也目睹了几乎将整个华沙城夷为平地的“华沙大起义”,对于人性的残酷丑恶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因此他写过一段和阿多诺相似的话:“无疑存在着两个欧洲,并且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第二个欧洲的居民们,命定坠入了20世纪的‘黑暗中心’。我不知道怎样一般地谈诗。我谈诗,必然会谈到它与特定时空环境的关系。”[3]220
因此,他愤恨地谴责人类:“一群令人厌恶的猴子,做着可怕的、愚蠢的鬼脸,他们相互交配、尖叫、杀戮。在20世纪,人给人造成了如此数量庞大的死亡,我们怎么能再来赞美人?人的所作所为既配不上学童的纯洁形象,也配不上获取有关灵魂的最高知识的能力。”[2]192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米沃什对于“全能上帝”的信仰必然也要受到极大的动摇。他甚至曾经引述哲学家伊曼纽尔·勒维纳斯的说法,声称1941年为上帝“抛弃”我们的时间[2]36。如此一来,他诗歌中经常出现的那些痛苦的怀疑乃至质问:“上帝不会为善良人增加羊群和骆驼/也不会因为谋杀和伪证带走什么。/他长久隐匿着……”(《忠告》)“在不幸中赞美上帝是痛苦的,/想着他不会行动,尽管他能。”(《在圣像前》)也就不足为奇。
事实上,经历过一系列荒诞吊诡的残酷现实之后,他更加倾向于做一个怀疑论者。当然,他反对的并不是天主教或者上帝本身,而是那些假借真理和正义的名义所施行的各种丑恶暴行,是那些冒着正义之名行不义之实的人。他痛切地控诉道:“去做弥撒本该具备坚定的信念,本该具备一种意识,即我们生命中的所作所为符合宗教对我们的要求,但所有热衷于去教堂的人都配得上‘伪君子’和‘法利赛人’的称谓。”[2]78-79因此,在《二十世纪中叶的肖像》中,米沃什把那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虚伪之至的人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一只手放在马克思的著作上,他私下读着《圣经》”的古怪复杂行为,实在是让人生厌,而实际上也多是这样的人大量存在,才使得深为诗人重视的天主教变得混沌,不再纯洁,沦为一些人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他所反对、所厌恶的正是那些身在教堂,心里想的却是“朱莉娅的奶子, 一头大象/黄油的价格, 或新几内亚”(《神学论文》)的假道学和伪信徒。
二、盘根错节的神学体系
诗人的家乡维尔诺,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也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城市。历史上,它曾经属于沙皇俄国,曾经归属于波兰,曾经属于立陶宛大公国,曾经归属于苏联,还曾被纳粹德国占领过,现在则作为首都归属于立陶宛。与此同时,在宗教上,维尔诺是立陶宛的天主教中心,也被犹太人称为“北方的耶路撒冷”,同时还拥有东正教、新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教派。城里有几十座犹太教堂和四十座天主教教堂。这种多元化的、宽松的宗教形态使得身为天主教徒的米沃什从自身的宗教文化背景上排除掉了天主教自身狭隘的排他性宗教思想,对于各种其他宗教、教派都能采取一种平和客观地评判态度。
所以,当米沃什谈到城市的精神面貌时说城市里“有一种宽容的无政府主义,一种使凶猛口角罢休的幽默,一种有机的群体感,一种对任何集权的不信任”[3]221。而实际上,他对任何的狭隘都是深有抵触的。海涅曾说:“没有比狭隘的民族主义更有害的东西了。”而20世纪狭隘民族主义最可怕、最有害的例证也莫过于纳粹德国。亲眼目睹纳粹暴行的米沃什自然更不可能选择狭隘主义,更不可能选择狭隘主义的神学观。相反,他的神学体系呈现一种复杂的矛盾状态。他一会儿说“不管怎样,我发现适合自己的是一种怀疑论的哲学”,不一会儿又声称:“我不停地念叨‘相信上帝’,可心里清楚/ 自己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冷待本性》)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他在1987年的一次访谈中所引用的一位波兰诗人的话:“上帝同意我做无神论者。”[4]这个简短的语句,充分展现了他身上宗教与以唯物论为代表的理性与科学所构成的强烈悖论。
事实上,对于自己的思想体系,米沃什有过一段简短的叙述:“我是一个理想国的居民,这个理想国与其说是存在于空间,还不如说是存在于时间。构建它的是以前的圣经译本、圣歌、柯哈诺夫斯基、密茨凯维支以及当代诗歌。”[2]210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米沃什所推崇的是“以前的圣经译本”,也即是未受污染的、充满原初基督教精神的宗教。而这个存在于时间之中的理想国中的构建元素也都是一些人性中所共通的东西,他所期许的理想宗教因此也必然是那些能够排除狭隘的共通因素。所以,在米沃什的宗教思想体系中,除了天主教的影响外,摩尼教、佛教,以及以斯威登伯格、伯曼和布莱克为代表的神秘主义思想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多样化的宗教思想共同构成了米沃什盘根错节而又包孕丰富的神学体系。
三、对佛教的推崇
佛教对米沃什最大的吸引是它的普世情怀,这样的一个大慈大悲的包容性宗教,对于神学体系盘根错节,信仰陷入深刻矛盾的米沃什来说不失为一剂良药:“明摆着,我被佛教的法言所吸引,因为我生命中所经历的困苦——生灵的困苦——正是悉达多王子普世情怀的核心关照。佛教大慈大悲,将一种神圣体验带给那些无法在自己与各圣经宗教之矛盾、自己与一位人格神之间达成妥协的人们。”[2]67当然他对佛教精神内核之外的东西同样也是抵触的,他对那些庙宇堂皇、“法相庄严”的“形式佛教”并无好感,其抵触情绪并不亚于他对受污染的天主教,他所推崇的依然是改良型的保留有原初佛教精髓的纯粹佛教。所以,他说:“另一方面,我对不设寺庙,只设沉思中心的美国佛教兴趣浓厚。佛教并不敌视其他信仰,它并不排斥同时属于天主教、新教或犹太教的东西。它通过神学对话,尤其是佛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对话,结出了普世性的硕果。”[2]67
另一方面,佛教中对于技术文明、技术思维的反抗,也让米沃什十分着迷。因为他对技术思维是十分抵触的,尤其是带给人们残忍的“物竞天择”哲学的生物学。他认为生物学是“科学之中最邪恶的一门。它削弱了我们对于人类的信念,妨碍人类去追寻那更高的召唤”[2]56。他认为如果生物学影响人类的仅仅是科学数据还可以接受,可是生物学作为一种哲学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类观察世界的方式,进而被大众所简单化、庸俗化。生物学的邪恶,正是在于其“拆毁了人与兽之间的栅栏”,因而,“一旦我们与其他种类的生灵之间的分界被打破,那至高的王权便受到怀疑。这时,在进化的过程中,产生自无意识的意识就变得靠不住了。从这时开始,相信一个不朽的灵魂,好像就变成了一种僭越之举”[2]57。失去了宗教信仰的制约,人们过于相信和崇拜“强力”,甚至让其拥有了完全的权力,在这种“上帝之死”的语境之下,强力崇拜最终在20世纪导致了灾难深重的后果:“他们自己给自己派给自己一项艰巨的任务:用实践来证明我们服从于强力关系的人类必有其逻辑后果,他们通过建造奥斯维辛集中营证明了这一点。”[2]57
所以,米沃什倾向于佛教,是因为它有一种对自然的偏好和清静平和的状态。这种与自然的贴合是对于粗暴简单的技术文明的反驳,能够重新恢复人与自然的亲和,让那些被技术思维、技术哲学遮蔽的自然美感能够重新被感知。因为“佛教的思维方式与技术文明的思维习惯刚好相反。技术文明讲究速度,电视镜头一闪而过;佛教思维的兴趣在于维护自然状态,因为它致力于此时此刻”[2]187。米沃什还引用了“用深心”一词,认为这一个词包含了佛的所有教义。“它意味着一种专心致志的状态,即善意地对待自然和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注意到自己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所有细节,不会因为分心而与之擦肩而过。”[2]187米沃什认为,佛教的“用深心”可以作为一种平衡力量来抵消浮躁语境中的分心倾向,最终成为一种对单维技术哲学世界的反抗。
结 语
作为一个经历过大屠杀和几乎整个20世纪人类灾难史的诗人,米沃什的宗教思想必然是复杂的,但是承袭自家庭和生活环境的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思想使得他注定不可能彻底反叛天主教和上帝的影响。20世纪的人类灾难使他得以对人性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也使他能够对上帝有一个清醒深刻的认识。而源自故乡维尔诺的多元化和宽容精神,又使得他能够比较宽容客观地看待各种宗教,吸收各宗教中那些普世性的东西来构建其盘根错节的神学体系。因此,主张宽容,具有“普度众生”的强烈普世情怀的佛教,强烈地吸引了在各种排他性宗教中陷入矛盾挣扎的米沃什。这种与自然贴近的包容性宗教也使米沃什找到了一种对抗近代以来以生物学为代表的技术哲学的途径,让他能“用深心”观察世界,与世界对话,最终得到了他的青睐和推崇。
[参考文献]
[1] 西川.米沃什的另一个欧洲[M]//切斯瓦夫·米沃什.米沃什词典.西川,北塔,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13.
[2] 米沃什.米沃什词典[M].西川,北塔,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
[3] 米沃什.拆散的笔记簿[M].绿原,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
[4] 王家新,沈睿.历史、现实与诗人的探索——米沃什访谈录[M]//王家新,沈睿.二十世纪重要诗人如是说. 全小虎,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456-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