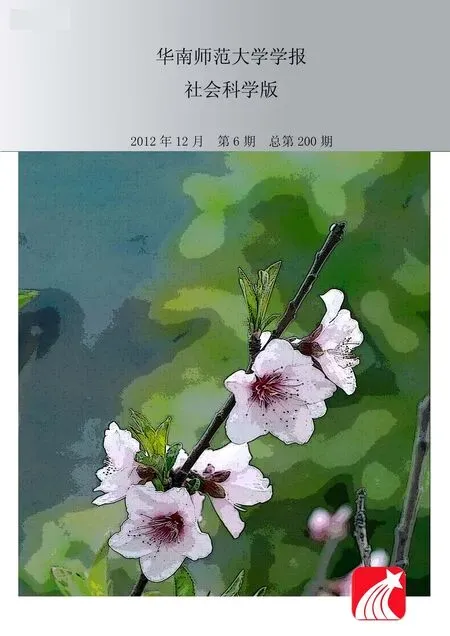中国古代女性医护者的被边缘化
李 志 生
(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1)
在儒家的性别理论中,男女有别是最重要的支柱之一。《礼记·内则》曰:“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然而在中国古代,妇女在产育子嗣和罹患疾病时,必然涉及到身体。如此,在中国古代妇女的医护过程中,如何贯彻男女有别思想?社会性别制度又对中国古代的两性医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文将从中国古代医者体制的角度,以社会性别理论来考察女性医护者被边缘化这一问题。[注]对中国古代女性医护者的研究,主要有郑金生:《明代女医谈允贤及其医案〈女医杂言〉》,载《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费侠莉:《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梁其姿:《前近代中国的女性医疗从业者》,见李贞德、梁其姿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妇女与社会》,第355-37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衣若兰:《三姑六婆——明代妇女与社会的探索》,(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李贞德:《唐代的性别与医疗》,见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第415-44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程锦:《唐代女医制度考释——以唐〈医疾令〉“女医”条为中心》,见《唐研究》,第12卷,第53-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李贞德:《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台北)三民书局2008年版;陈昊:《读写之间的身体经验与身份认同——唐代至北宋医学文化史述论》,北京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社会性别(Gender)是美国学者琼·斯科特提出的理论。它考察的是社会对男女两性的建构以及在这一建构中,男女所处的差异性位置。社会性别理论强调:“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分。”[1]168而这一命题又可区分为四方面:象征性表述、规范性概念、社会制度和主体认同。依此,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医者体制,是由男性统治者和士大夫依据儒家的男女有别理论而建立的一种社会医学制度;男女医者在这一体制内,被赋予了不同的职责和位置;男女两性医者,也在认同这一体制的前提下,或尽力对其维系,或尽量与之靠近,或被体制打压。总体而言,对比男女两性医者的社会地位,女性医护者明显被边缘化了。
本文所称的“女性医护者”,特指具有现代社会所认同的医术者 。虽然中国自古巫医不分,但以数术为主的女性医护者(如卦姑、师、婆),本文不予讨论。中国古代的女性医护者主要有四类:一是官府太医令属下的女医,此类女医主要见于汉、唐两代,她们大略知悉医典和医方,谙熟医术,按脉诊疾,用药治病;二是女儒医,她们出自官宦书香之家,在家族内受到较系统的医学教育,熟谙医典和医方,按脉诊疾,用药治病,有医籍出版;三是士人家族女医,她们也出自官宦士人之家,熟谙医术,按脉诊疾,用药治病,但不谙医典;四是下层女医及其他妇女健康护理者。其中最重要的是产婆,她们游走于户外。在不同程度上,第一、三、四类女性医护者,都受到了正统医者体制的排挤;第二类女儒医,则在力求靠拢正统医者体制。因此,她们能够被正统医者体制所接纳和承认。
一、中国古代的正统医者体制
中国古代的正统医者体制,是在唐宋时期逐渐形成的。从战国到秦汉,在长期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产生了《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四部重要医书。它们的出现,标志了中医学术体系的形成,后来也成为了最重要的中医医典;它们的出现,对中国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李建民总结说:“相对于神仙、房中术偏重选择明师、祝由等仪式性医疗偏重语言、动作的演出,中国医学是‘以文本为核心’的医学。《内经》、《难经》等‘经’在汉代或许还称不上所谓‘经典’,但无疑具有‘正典’概念下的‘规范’或‘标准’意义。典籍在此有着‘社群规范性的功能’……。也就是说,医学文本具有建立师徒系谱、区别我群与他群的作用”;“强调读医书以习医的风气,使医学一变为士大夫之业。”[2]6、15
到唐代,已出现医者须读以医典为主的医书的看法。唐初名医孙思邈,在其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中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3]1-2孙思邈认为,要想成为“大医”,必须精通以四部经典为主的医书。关于医书对医者的重要性,宋代医家史崧更明确说:“夫为医者,在读医书耳,读而不能为医者有矣,未有不读而能为医者也。不读医书,又非世业,杀人尤毒于梃刃。”[4]
唐宋时期,“儒医”的观念也逐渐出现并形成,此类医者既通医书,也精儒术。孙思邈在述完“大医”必读的医书后,继续阐述说:“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旺,七曜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3]1-2宋代臣僚更直接以“儒医”来概称具有儒学学养的医者:“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5]2217明代肖京则进一步认为,作为儒医,既应博通经史,还要身行俱嘉:“尝稽秦汉以后,有通经博史,修身慎行,闻人硕儒,兼通乎医者,精究玄机,洞明至道,每见立言垂教,后学凛为法程。”[6]511
由此,从唐代开始,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念:熟谙以四部经典为主的医书,是成为“大医”、“儒医”的首要条件;同时还须兼通经史等其他文化知识,且行止亦须无瑕。自唐宋以后,在这一正统观念的支配下,女性医护者被置于了劣势地位。中国古代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都远逊于男子,女性医护者主要以技艺实践见长,医学理论及通经博史并非其优势;下层女性医护者游走于户外,这也与儒家所提倡的“男女有别”观念相左。由此,由男性建构起来的强调读医书兼通经史的观念,也成为男性士大夫歧视女性医护者、女性医护者被边缘化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古代的四类女性医护者
(一)太医令属下女医
在唐宋时代,熟谙医书为男医特权的思想,不但体现在观念上,也贯穿于制度中。唐代设太医署,下辖四类医师:“(太医署)太医令,掌诸医疗之法,丞为之贰。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皆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各类医师所读之书为:“诸医、针生,读《本草》者,即令识药形,知药性;读《明堂》者,即令验图识其孔穴;读《脉诀》者,即令递相诊候,使知四时浮沈涩滑之状;读《素问》、《黄帝针经》、《甲乙脉经》,皆使精熟。”[7]299关于太医署医师所读医典,《天圣令·医疾令》也记:“诸教习《素问》、《黄帝针经》、《甲乙》,博士皆案文讲说,如讲五经之法。私有精达此三部者,皆送尚书省,于流内比校。”[8]578由此,《素问》、《黄帝针经》和《甲乙》三部医著,是唐代太医署医师习医时最重要的经典。太医署医师及自学精通此三经者,均可参加科举考试并入仕为官。关于医师参加科举考试的方式和内容,《唐会要》记:“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制:‘自今已后,有以医术入仕者,同明经例处分’。”肃宗乾元三年(760),右金吾长史王淑也奏:“医术请同明法选人,自今已后,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十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已下放。”[9]1525
由此可知,唐代太医署医师的教习,是比照国子监科举诸生的培养方式而设的,其考校也是按科举制中的明经或明法之科而定;另有“私达”三部医经的士人,也可入仕为官。唐代的医师培养和入仕,完全被纳入了其时的官僚体制中,医师也成为了官僚体制内的成员。宋代医师的培养,大体与唐代类似,相关的令文集载于《天圣令·医疾令》中。
相较之下,在唐代女医的培养中,无论是女医的出身、教习地点和方式还是学成后服务的对象等,都与男医有别。关于唐代的女医教育,《天圣令·医疾令》为我们留下了一条极为珍贵的材料:“诸女医,取官户婢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无夫及无男女、性识慧了者五十人,别所安置,内给事四人,并监门守当。医博士教以安胎产难及疮肿、伤折、针灸之法,皆按文口授。每季女医之内业成者试之,年终医监、正试。限五年成。”[8]579依此,大致可知如下诸点。其一,唐代教育系统设有女医科,但它于“别所安置”,与太医署下四科医学生应别为两系统,具有特殊性。其二,女医取自“官户婢”。“官户婢”当为官户和官婢的合称,均属贱民;而“诸医生、针生、按摩生、咒禁生,先取家传其业,次取庶人攻习其术者为之”[8]577,身份为良人。其三,女医被“别所安置”。所谓“别所”,可能是后宫尚药局侧造别院安置。如此,女医是为后宫服务而培养,所以比照宫女,要求她们“无夫及无男女”。其四,与太医署男医的培养有别,女医的教习并不包括读医典和医方,只是医博士“按文口授”治疗“产难及疮肿、伤折、针灸”的相关医籍、医方。如此规定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排斥女医的性别和贱民出身;二排斥她们未来的行医内容——安胎产难等;三受限于这些“官户婢”的文化水平。但医博士需对她们“按文口授”医籍,这又保证了女医的基本医学理论被控制于正统医者体制内。其五,相较于男医,女医的考试相对简单,女医仅有季试和年终试,而男医则分别有月试、季试和年终试。[注]本段论述,参考了程锦《唐代女医制度考释——以唐〈医疾令〉“女医”条为中心》、李贞德《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陈昊《读写之间的身体经验与身份认同——唐代至北宋医学文化史述论》。综上诸点,医学理论水准较低、且出身低贱的唐代女医制度,使这些女医处于了边缘地位。
太医署下设女医,在汉代已可见到。汉代最著名的女医是淳于衍,她也是隶于太医署的。《汉书·孝宣许皇后传》记,淳于衍在宣帝许皇后临产罹病时入宫为其疗疾,霍光之妻托她借机杀死许皇后。淳于衍谓霍光妻曰:“药杂治,当先尝,安可?”淳于衍后来“捣附子,赍入长定宫”,“取附子并合大医大丸以饮皇后”,而将许后毒杀。[10]3966在《汉书》中,淳于衍被称为“女医”、“女侍医”、“乳医”。对此,颜师古《汉书》注曰:“乳医,视产乳之疾者。”[10]2953关于女医,清人著《钦定历代职官表》指出:“汉时又有此等女医,同隶于太医令,以备诸科之一,特史未详其制耳。”[11]卷三六不论汉代女医的制度如何,但如下诸方面是清楚的:汉代太医署女医的服务对象是后宫,女医为后宫患者疗疾、开具处方,但不负责配药、制药。由此推测,她们对相关的医方应较为谙熟,这些都与唐代太医署女医相似。但她们也有不同于唐代女医之处,淳于衍是已婚之妇,居于宫外,这与唐令所规定的女医“无夫及无男女”且常住宫中不同。
(二)女儒医
中国古代的另一类女医——女儒医,在对医典的谙熟、其他理论素养、诊疗水准和医著撰作上,都不逊于男儒医。但在20世纪前,此类女医凤毛麟角,谈允贤和曾懿[注]曾懿(1852-1927)生活的年代已超出了本文的时间范围,但因其接受医学教育的渠道、行医的方式等,仍具有中国古代正统医者体制所承认的女儒医特点,故也将其含括于此。是其中的佼佼者。
谈允贤(1461-1554),江苏无锡人。关于她的家世、接受医学教育的过程、内容和行医情况等,在其所著《女医杂言·自序》中都有详述。她出生于世医之家,曾祖、祖父都以医名于其时。史记其祖父“以医药济人,衣食常不给”[12]420;其伯父、生父应科举,入仕为官,故其世医之学,乃由祖母接传;其生父和祖母教之以医经及儒文诗史:“(父)亚中府君先在刑曹,尝迎(祖母)奉政府君暨大母太宜人茹就养。妾时垂髫侍侧,亚中府君命歌五七言诗,及诵女教、《孝经》等篇侑觞。奉政喜曰:女甚聪慧,当不以寻常女红拘,使习吾医可也。妾时能记忆,不知其言之善也。是后读《难经》、《脉诀》等书,昼夜不辍。暇则请太宜人讲解大义”。婚后,她亲为子女诊疾调药;祖母去世,痛而大病,亦是自己“强起检方调治,遂尔全瘳”。因其高超的医技和女性的身份,“相知女流眷属,不屑以男治者,络绎而来,往往获奇效”。至五十岁时,“谨以平日见授于太宜人及所自得者,撰次数条,名曰《女医杂言》”[13]。谈允贤的《女医杂言》,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个人医案之一。
谈允贤的个人经历,特别是她对于医典的掌握,契合了唐宋以来对儒医的基本要求。因此,她也颇为其时的男性士大夫所称赞,还成为了其家族的骄傲。谈允贤的侄孙谈修在重刻《女医杂言》的跋语中就说:“余在龆龀,目睹其疗妇人病,应手如脱,不称女中卢扁哉!”[13]卢扁,即战国时的名医扁鹊。将谈允贤比于扁鹊,可见其时之人、特别是族人对她的推崇。
另一位卓有成就的女儒医是曾懿(1853-1927)。曾懿的祖辈世代为农,至其父谈咏时,方举进士为官;卒前,官至江西吉安知府。曾懿的母系家世则极显赫,家族的文化素养也很高:曾外祖左辅官至湖南巡抚,工诗擅文;曾外祖、外祖都有文集传世;母左锡嘉、姨母左锡璇,并为清代才女,皆有诗文集传世,且曾懿的同辈表亲也是才女迭出。曾懿不但厕身于家族的才女之列,且是其中的翘楚。她的兄长称赞她有绘画、书法、诗词“三绝”;缪荃孙更夸赞她:“古今才媛,不可多得之遇,以一身兼之,则又独异也。”[14]除此而外,她还对女子教育、医学多有研究,有《古欢室诗词集》、《女学篇》(附《中馈录》)、《医学篇》等著作传世。
曾懿对医典和医家颇为熟谙,这从她的《医学篇》自序便可看出:
自神农尝百草以治病,迄于汉晋《灵枢》、《素问》、《肘后》诸书,代有传人。降及后世,仲景谓医中之圣,其所著《伤寒诸方》,后学家莫不奉为准绳。故医方集解,通行于世,其中张子和、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四大家,皆有偏胜处,张、刘善于攻散,李、朱一偏于补阳,一偏于补阴,……。近世徐灵胎、叶天士、吴鞠通、王士雄、费晋卿诸医士,皆能运化古方,以治今人之病,……。其最切时人之时病者,莫如吴鞠通之《温病条辨》一书。[15]
在此,曾懿不但缕析了医典的传承,对前代和当代诸家名医的医道所长,也颇有见地。关于学医经历,她说:“懿本女流,性又不敏,只因弱岁失怙,奉母乡居,而家藏医书,复甚齐备,暇时流览,心窃好之。”曾懿是在其家门的熏染下涉入医门的。除了医学,曾懿也广涉其他知识:“懿幼承母训,夙好金石词章之学与图画……”[16]曾懿认为,若非“博览群书,抱用世之才,不足以语医也”[15]。她的医学理论素养甚至远超于许多男儒医,所以她能够以自己的理论和经验辨别诸家理论与医方,并最终于五十四岁时撰成医书《医学篇》。曾懿的这一医著,同样受到了男性士人的赞扬。曾懿之子曾为母亲的《女学篇》向张百熙索序,张百熙在读过《女学篇》和《医学篇》后为其《女学篇》所作的序称:“盖叹夫人之襟抱宏远,议论明通,不独今之女界无此完人,即求之《列女传》中,亦不可数数觏。”[16]曾懿无疑也成为了曾氏子孙的骄傲。
(三)士人家族女医
除谈允贤、曾懿等少数熟谙医典和医方且有医著出版的女儒医外,中国古代还有一些来自士人家族的女医。她们的医方和医术或源自家族,或受术于他人;她们为人疗病,多有成效;但她们对医典或名医理论却未必谙通(史书对此未有记载),这也是她们与女儒医最重要的区别。
四明宋氏长于妇科之学。宋林皋在明代万历年间撰成医书《宋氏女科秘书》,他在书序中记道:“唐开元时,始祖广平公璟,精于医门,吏有疾,见之堂下,察色而知之,审治之,若中鹄也,世莫不称神焉。夫人余氏,窃其术以行于世,虽闾阎小民之妇,靡不被其泽,而其传耑于妇女一科。宋建炎初,有祖讳钦者,由进士,任七子城,使扈驾南迁,卜居四明,嗣后有以科名并于朝者,有以医术呜于时者,医与政,若院使,世世相承,代不乏人。”[17]1按宋林皋的记载,其家族的妇科之技肇启于始祖母余氏。余氏是唐玄宗朝著名宰相宋璟之妻,宋璟“精于医门”;而余氏的妇科技艺,则是从丈夫那里“窃”之而来。
另一位杭州冯氏妇人,也长于妇科之术。宋高宗建炎时,曾入宫为孟太后疗疾,她的医术也是源于家族之术。清修《浙江通志·杭州府》记医者郭昭乾:“昭乾自祥符初由汴徙杭州,多隐德,施子未常倦。有异人乞斋,郭膳之。潜遗牡丹花三朵,覆几上而去。追询之,曰:‘若累世隐德,故来相报。花上书妇人症十三方,若子孙世世用之无穷。’如法试之,无不奇验,遂为妇人医。郭氏之以医名,自昭乾始,三传至曾孙时义。高祖建炎元年,孟太后疾,召医,时义以母冯氏应召,依牡丹方治之,脱然愈。封安国夫人,赐田、赐葬、赐药碾如铁舟,然又赐第海昌,赐国姓,至今称赵郭里。”[18]卷一九六郭昭乾家传的妇科医方来自他人之授,其家族的医技多在男性之间传承;其孙媳冯夫人的医术,也应学自家中习医的男性成员;但冯夫人的入宫,无疑光大了郭家的名医地位。
宋代还有一位擅治皮肤病的张小娘子。宋人洪迈《夷坚志》记:“秀川外科张生,本郡中虞候。其妻遇神人,自称皮场大王,授以《痈疽异方》一册,且诲以手法大概,遂用医著名,俗呼为张小娘子。又转以教厥夫。”[19]828张小娘子擅医皮肤病,她的医术源自他人之授,她又将自己的医术传授给了丈夫。
明代歙县有名医程邦贤,他的儿科医术承自其父。受此家门医术的影响,其妻蒋氏和子媳方氏也都长于儿科。蒋氏不但精通一般的儿科疗法,还能施行外科手术:“一日,邦贤他出,有村妪抱初生七日儿至,粪门无孔,腹胀垂绝。蒋询其出胎能饮,知非脏腑有隔,特谷道未分耳。暗袖刃,酌分毫刺之,胎矢随出;仍用绵捻蘸蜜,令时通润,以防复闭,儿得无恙。”方氏的医术更为精湛,声名甚至超过了家族中的男医:“(方氏)外诊婴儿,求治者日盈,坐计所全活,岁不下千人,遂致道路啧啧,有女先生胜男先生之称。”[20]卷五一六
在史料记载中,中国古代精通医方、医术的女医一般出自士人家庭,而她们的医术则多学自男性。这从文本的话语上,实已设定了她们的次等地位。另外,此类女医虽医术高超,且其中的许多人还是家族医学的发韧者,并得到了族人的称赞,但并未如谈允贤、曾懿般受到男性士大夫的赞赏。其原因之一,便是以儒医的标准考量,她们的身上缺少了如谈、曾般的文化素养,特别是对医典的熟谙。明代吕坤有感于地方医制不振,提出地方医官须“令四境行医人等,不分男妇,俱委佐贰,会同医官考试,各认方科,分为三等。上等堪以教习授读医书;中等不通文理,令记单方;下等止许熬膏卖生,不许行医”[21]1133。依照吕坤的分类标准,再对照如上所举的士人家族女医之例,士人家族女医应属于吕坤所说的中等行医之人,即“不通文理”者。而在这类女医之下,还有许多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医护者。宋末元初以后,她们被归入了所谓的“三姑六婆”或“三婆”中。
(四)下层女医及其他妇女健康护理者
“三姑六婆”一词,首先由元初的赵素提出。[注]参见衣若兰:《三姑六婆——明代妇女与社会的探索》,第1页。他在《为政九要》中说:“官府衙院宅司,三姑六婆,往来出入,勾引厅角关节,搬挑奸淫,沮坏男女。三姑者,卦姑、尼姑、道姑;六婆者,媒婆、牙婆、钳婆、药婆、师婆、稳婆。斯名三刑六害之物也。近之为灾,远之为福,净宅之法也。犯之勿怒,风化自兴焉。”[22]336而元末明初陶宗仪关于“三姑六婆”的文字则更为人所熟知:“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也。盖与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奸盗者,几希矣。若能谨而远之,如避蛇蝎,庶乎净宅之法。”[23]126在“三姑六婆”中,药婆、稳婆是具有实际医疗技能的女性医护者。按清人褚人获的解释,“药婆”指“捉牙虫,卖安胎堕胎药之类”[24]1164-1165。她们身处街巷,为人疗病、卖药或帮助妇女堕胎,以此谋生;其中有些人或也精通方脉,但大多数人则不辨方脉。在明清士人笔下,她们有时也被称为“女医”。“稳婆”也称产婆,即为人助产者。在中国古代的民间,一些妇女是身兼数业,像《金瓶梅》中的王婆即如此:“原来这开茶坊的王婆子,也不是守本分的。便是积年通殷勤,做媒婆,做卖婆,做牙婆,又会收小的,也会抱腰,又善放刁”[25]。另外,明代后宫也会不定期地择选“三婆”入宫。所谓“三婆”,是谓奶婆、稳婆和医婆。关于医婆,明人沈榜的《宛署杂记》记:“故事,民间妇无得入禁中者,即诸宫女已承恩赐名称,其母非得旨亦不入,惟三婆则时有之。……医婆,取精通方脉者,候内有旨,则各衙门选取,以送司礼监会选,中籍名待诏。入选者,妇女多荣之。”[26]83沈榜所称“三婆”中的医婆是精通方脉者,但她们杂厕于其他诸“婆”中,故也被归在了下层女医之列。
至明代时,下层女性医护者是男性士人挞伐的重要对象。吕坤在《实政录》中就说:“女医师婆,一毫不明,每向庸医买残坏丸散,更不问治何病疾。妇女小儿诸症,先寻此等之人,前掐后捏,乱灸胡针,下过药、拔火罐、打青筋、送鬼祟。”[21]978另一位明人李东阳也对京师的女医批评道:“京师有女医,主妇女孩稚之疾。其为人不识文字,不辨方脉,不能名药物,不习于炮炼烹煮之用,以金购大医,求妇女孩稚之剂,教之曰:‘某丸、某散,某者丸之,某者散之。’载而归。人有召者,携所购以往,脉其指,炙其面,探药囊中与之,虽投以他药,弗辨也。”[27]404。吕坤和李东阳对女医的检视实际是在以“儒医”的标准进行考量;对她们的批评,集中于她们的“一字不识”和不谙医方、药剂。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下层女医中的许多人是具备一定医技的,她们也颇得到很多人的欢迎。李东阳也记道:“妇女之爱其身若子者,举其躯付之无疑焉”,“有疾者,皆乐而求之。”[27]404这些下层女医拥有实际诊疗技能,但欠缺医学理论素养。这也正是士人与下层女医的矛盾所在。
产婆也以经验见长,以其技能服务于孕产妇。她们中的许多人出自下层,以此谋生。在正统医者体制建立前的酝酿期隋代,产婆就已开始受到男医的责难。如隋太医博士巢元方即认为,“产已死而子不出候”的原因之一,就是“傍看产人抱腰持捉失理”而“令产难”[28]。唐宋时期,对产婆的指责更多见于医书中。武后朝户部尚书崔知悌的《崔氏纂要方》言及产妇死亡的原因说:“其产死者,多是富贵家,聚居女妇辈,当由儿始转时觉痛,便相告报,傍人扰扰,令其惊怖,惊怖畜结,生理不和,和气一乱,痛切唯甚。傍人见其痛甚,便谓至时,或有约髻者,或有力腹者,或有冷水噀面者,努力强推,儿便暴出,畜聚之气,一时奔下不止,便致运绝,更非他缘。”[29]924此处的“女妇辈”,就应包括产婆。唐后期妇产科医生昝殷的《产宝》也对“产时看生人”批评道:“旧方:胞衣不损儿者,依法截脐,而以物系其带一头,所有产时看生人,不用意谨护,而率挽胞系断其胞,上掩心而夭命也。”[30]21北宋杨子建在其所著产科名著《十产论》中则直接批评“收生之人”的医术低劣:“收生之人,少有精良妙手,缘此而多有倾性命。”[31]463
元明时,男性士人对产婆的认识呈正负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产婆严厉批评,如上举赵素和陶宗仪对“三姑六婆”的批评;另一方面则是一些男医对产婆工作的尊重。明代名医薛己就在自己的医著中提到从产婆处学习经验:当产妇胎衣不出时,他“常询诸稳婆”;他还亲自为一位稳婆怀孕的女儿诊疾,称此女“勤苦负重”[32]863、947。另外,明代名医武之望和万全也在他们的医著《济阴纲目》和《万氏妇人科》记载了产妇在生产遇到问题时稳婆的重要作用。[注]武之望:《济阴纲目》卷四《临产门》,见苏礼主编:《武之望医学全书》,第168-169页,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万全:《万氏妇人科》卷三《产后章》,第40-43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医婆和产婆因出身下层,欠缺医学理论,且游走于户外而饱受士人批评,但她们的不可或缺,也为男医所深知和承认。
在中国古代的妇女医护史中,始终贯穿着男女有别的性别观念。中国古代的医学体制是一种男性体系,它对应着男外/女内的社会性别分工理想,也呼应着儒家士大夫读书出仕以治国的理想。宋代以后对儒医的要求,实际指向的就是男医。由于性别的原因,中国古代的女子受教育机会少,因此女医侧重的是经验而非医典与医论。在男性正统医学体制下,理论水平不高的女医,无疑就被边缘化了。而这一点也契合了儒家性别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女人的从属性——在“从人”的理论下,女人必须弱于男人、女医必须劣于男医的认识必然出现。虽然如此,中国古代的女性医护者却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其原因在于男女有别的另一层含义,即男女身体或空间上的隔离。在男女有别的封建礼教下,男医诊治女患者遭遇了严重的阻碍与困难,其结果是极大促进了女医与女患者的联系。如李东阳所说:“非女医之所治者,虽名家术士未尝信之。”[27]404像谈允贤这样精通医典、医术高超且知悉女性心理的女儒医,更是受到了女患者的追捧。谈允贤的弟弟谈一凤称:“乡党女流得疾者,以必延致为喜”[13];朱恩《读〈女医杂言〉》也谈到了女医受欢迎的原因:“妇人医妇人,则以己之性气,度人之性气,犹为兵家所谓以夷攻夷,而无不克。”[13]从女患的角度而言,女性医护者不但不存在于边缘,反而是她们的生命重心所在。这实际上衍生出了中国古代的另一类女性文化——女性医学文化。
参考文献:
[1] 琼·W.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
[2] 李建民.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校释.李景荣,等,校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4] 史崧.编.灵枢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5]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
[6] 肖京.轩岐救正论.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3.
[7] 李隆基.大唐六典.李林甫,注.东京:广池学园事业部,1973.
[8] 天一阁博物馆,等.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
[9]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
[10]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永瑢,等.钦定历代职官表.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广雅书局校刊本.
[12]裴大中,等,修,秦缃业,等,纂.光绪无锡金匮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3]谈允贤.女医杂言.明万历十三年(1585)锡山谈氏纯敬堂刻本.
[14]曾懿.古欢室诗词集.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长沙刻本.
[15]曾懿.古欢室医学篇.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长沙刻本.
[16]曾懿.古欢室女学篇.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长沙刻本.
[17]宋林皋.四明宋氏女科秘书.上海:中医书局,1955.
[18]嵇曾筠山,等,修,沈翼机,等,纂.浙江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洪迈.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1981.
[20]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石印本.
[21]吕坤.吕坤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
[22]居家必用事类∥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23]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
[24]褚人获.坚瓠己集∥清代笔记小说大观(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5]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8.
[26]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
[27]李东阳.怀麓堂集∥四库明人文集丛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8]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
[29]王焘.外台秘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30]昝殷.经效产宝∥中国医学大成(28).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31]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
[32]薛己.薛氏医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