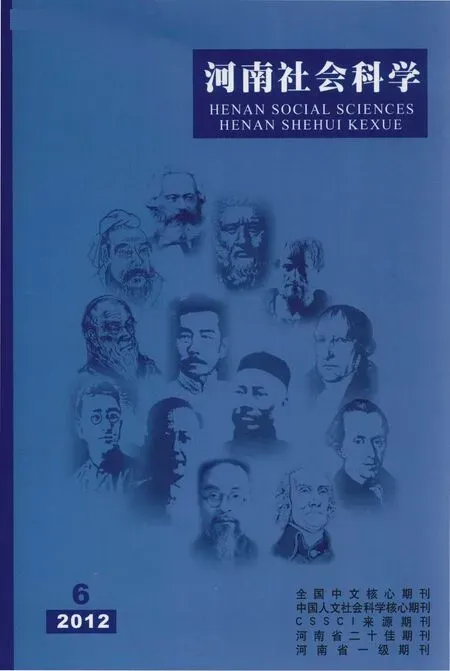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女性主义表现及其特质
施志渝
(上海政法学院 外国语学院,上海 210701)
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女性主义表现及其特质
施志渝
(上海政法学院 外国语学院,上海 210701)
女性主义作为人性发展的一种哲学和思辨理念,在各个方面都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前进和发展。20世纪以来,西方女性主义在政治上的诉求深刻地影响着其在人文领域的表现,就是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的激荡和融合,20世纪西方文学发展也深受女性主义影响,尤其是在存在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相互转化中这种表现尤为明显。分析这种女性主义的表现和特质,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文学和更广阔意义上人文学科的转变。
西方文学;女性主义;存在主义;生态主义
一、前言
女性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整体,受制于男权社会话语权和伦理体系的束缚,一直是沉默的、被动的甚至是无言的群体。女性对于男性和家庭的依赖,又固化和强调了家庭、婚姻、爱情等范畴对其的禁锢与限制。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幸福的家庭、美满的爱情,成为表现女性存在的主要特征。这类特征无论是在男性作家那里还是在女性作家那里,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女性价值的家庭化和附属化,使得社会对女性的定位和要求完整无缺地进入到文学领域。女性自身的抗争和反叛,从未超出过爱情、家庭和婚姻的范畴。“第二性”和男性的影子折射出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崎岖挣扎的艰难背影。
西方文学进入20世纪以后,人性的诉求超越了“文以载道”的局限,新文论要求的“中性”及摒弃价值评价成为主流。文学的叙事也由从男性的角度来看女性变为由中性的角度来看女性。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开始突破家庭、婚姻和爱情的局限,开始抒发女性对于社会的抗争。随着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思潮的崛起,由女性角度来看待女性,成为西方文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女人的自我意识不是由她的性征专门确定的:它反映了取决于社会经济组织的处境,这种处境反过来又表明了人类所达到的技术发展阶段。”[1]20世纪的西方文学,流派林立、思潮迭起,人文领域的急剧变化和社会制度的激烈变革,使得没有一个文学流派可以统领文坛的发展方向。随着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的兴起,西方文学中的女性主义特征开始滥觞。
二、西方文学中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从叛逆到超越
20世纪的西方文学从19世纪的浪漫主义中挣脱出来,热衷于表现存在、内在、自我等现实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意识,反叛、荒诞和痛苦都是文学作品惯用的表现手法,意图打破“物”或“物质”对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压迫与束缚作为女性主义的第二波浪潮,存在主义在话语权和思想的底层掀起了对20世纪西方文学的冲击。
存在主义哲学自萨特和海德格尔起,以“超越”“他者”和“内在性”等概念为核心,为存在女性主义提供了理论根基。以此为基础,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和玛丽·戴利的《超越圣父上帝》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巨著横空出世。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基本论点是:第二性或附属性的女性特质并非天生,而是男权社会强加并以理性为旗帜固化的行为。“我们可以用女人自己的女性意识去解释女人,但这并不比说她是一个雌性更令人满意。因为她是在取决于社会(她是其中的一员)的环境中,取得这种意识的。”[1]因此,超越男性和理性,就成为女性追求的首要目标。“对女人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既要拒绝这样逃避现实,又要在超越中寻求自找实现。于是,要做的事情是,通过所谓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态度,看看在她面前会展现出怎样的前景。”[1]波伏娃所说的这种前景,就是女性超越“他性”、“内在性”,并突破男权社会规定的女性角色的抗争过程。
19世纪的女作家,如夏洛蒂·勃朗特、简·奥斯汀等,被认为是“在以男人为中心的房子里生活”,从而“在她们的作品中往往充斥着封闭和逃跑的形象,疯狂的自我”[2]。“女人的无能导致了她的毁灭,因为男人从他为致富和扩张而进行设计的角度去看待她。”[1]反叛是这一时期女性作家表现的主题。
在存在主义的理论体系里,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建构史,也是男性的自我意识、个体意识付诸于社会、组织、家庭和女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女性被束缚、被淹没甚至没有声息。女性的价值由男性来评判,家庭和繁育后代成为女性存在的主要理由。打破“房子”生活的第一步,就是对家庭的反叛。通过对男——女、内——外社会分工的颠覆,打破了男权社会赖以生存的文化和社会基础。从简·奥斯丁到艾丽丝·沃克,19世纪以来,女性作家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她们打破了由男性来观察女性的传统,开始了从中性角度来观察女性。她们的创作淋漓体现了女性对世界的认识、体验、评价和反叛,全新的女性形象(如简·爱)已经将“伟大的母亲”“天使”和“贞女”等形象彻底粉碎。感情丰盈、血肉丰满和自我追求的女性形象彻底否定了男权文化对女性强加的评判。
在波伏娃的作品里,女性的形象已经简单地从反叛男权和社会,转化为追求独立、自我和精神解放。对于女性观察的角度,也已经不仅仅从中性或中立的角度进行,而是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待女性。她们独立、有思想,不受任何人的摆布,自由地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这也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在文学创作中回应存在主义的特质与表现。
“你们知不知道,在一年的过程中有多少本书写的是女人?你们知不知道,有多少本书是男人写出来的?你们是不是意识到,你们或许是天地万物中被讨论得最多的动物?”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凌厉地质问着女性,“在所有诗人的作品之中,妇女都像烽火般燃烧着——在剧作家的笔下,有克吕涅斯待拉、安提戈涅、克娄巴特拉、麦克白大人、菲德拉、克瑞西达、罗莎琳德、笞丝狄蒙娜、马尔菲 公爵大人;还有在散文作家的笔下,有米勒芒特、克拉丽莎、蓓基·夏泼、安娜·卡列尼娜、爱玛·包法利、盖芒特夫人——在脑海中这些名字纷至沓来,而且她们绝不会使人想到妇女‘缺乏个性和特色’,确实,倘若妇女只存在于由男人所写的虚构作品之中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想象妇女是最为重要的人,千姿再态,既崇高又卑贱,既光彩照人又令人沮丧,既美艳绝伦又极端丑陋,像男人一样伟大,有人认为甚至比男人还要伟大。但这是虚构中的妇女。诚如特里威廉教授所指出的,实际上妇女是被关起来,在屋里被打来打去”[3]。
由此,法国女性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说道:“男人们说有两样东西是无法表现的:死亡和女性。那是因为他们需要把死亡与女性联结起来”,因此呼唤女性:“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美杜莎的笑声》)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强大冲击力,催发了一向沉睡中的女性性别意。女性主义角度的女性,是她们向束缚自己的男权社会挑战的最佳视角。她们的写作深及女性精神的底层,精神的解放和自由使她们能从更基础的意义上解构男性对女性的认定和遮盖,她们的笔下折射的人性光辉冷冷地刺痛着男权社会。
三、西方文学中的生态女性主义:从超越到自然
现代性对20世纪人类的发展侵蚀入骨,后现代性的解构应运而生。生态女性主义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中至今最有活力的派别之一,它的“新全球论”、“关怀伦理”、“生态伦理”直到现在仍是热点词句(罗诗钿,2010)。
1974年,以美国学者密克尔《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专著的出版为标志,“文学的生态学”(Literajy ecobgy)这一概念正是进入文学领域。接着,美国学者克洛伯尔把“生态学”(ecology)和“生态的”(ecological)概念引入文学批评。生态文学由此勃发。
而女性与生态主义的联系,在女性主义看来则是天然的,因为“自然被客体化、被征服,成为了与统治者有着本质差异的‘他者’。女性在男权社会等同于自然,同样被客体化、被征服。在这种意义上,女性和自然成了最原始的‘他者’。”[4]
卡伦.J.沃伦(Karen J.Warren)认为,女性作为男权社会压迫和禁锢的对象,等同于现代社会物质对于自然的侵占和利用。女性和自然之间,天然地存在紧密的联系。女性更容易接近自然、理解自然,而不像男性那样侵占自然的领域。就此意义上讲,自然、和谐和可持续对抗现代物质文明,等同于女性对与男权社会的抨击和反抗。
存在女性主义强调的是“超越”、摆脱“他者”、强调“自我”,实现女性的独立和价值。在生态女性主义这里,超越或者自我,都不能使女性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因为现代物质文明对自然的压迫是结构性和社会性的,属于人的制度构建上的污点。而这种污点恰恰是男权社会强加于自然和人类的。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要求人类社会“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通过对自然的解放来解放女性和其他受压迫的群体(罗诗钿,2010)。
自然与女性的等同,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首要内容。在反叛和超越男性社会的同时,她们提出了构建新型社会结构和伦理的诉求,即人类社会的价值和结构不是建立在把自然和妇女作为资源来统治的基础之上,而是基于一种能使男性和女性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完整保持之上的(罗诗钿,2010)。
艾丽丝·沃克(Alice Waiker)写道:“我们跟它们(动物们)的联系至少像我们与树木之间的联系一样亲密。”而面对来自男性的诘问和责难,女性的回答是“我很穷,我黑乎乎的,我也许很丑,又不会烧菜……不过,我还活在这个世上!”[4]因为“我们常说每个行动都会对其本身造成后果,现在报应来了。你砍光了树木,就肯定会发洪水。”[5]
人类的和谐是女性主义追求的目标,因此“洪水”的寓意更多地是在提醒人类社会关注现代物质文明对于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压迫与侵蚀。解决这一难题的思路,就是生态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多样性。因为单一性正是男性社会对女性和自然的统治与侵占。而单一性的文化寓意,正如查伦·斯普瑞特耐克(Charlene Spretnak)所说:“欧洲世界观的父权主义核心是一种文化恐惧,即害怕自然和女性的创生能力,如果不受文化父权们的管辖,将会是混乱无序的、席卷一切的。”[6]
传统文化观对男——女两性的分割,对于自然的盲目自大和优越感,人为地割裂了男——女、人——自然的和谐纽带。男性社会通过物质化自然和人类社会结构,制造出二元制的价值观念,并以此来束缚女性对自身的认知和对自我的追求。在二元制思想中,对立的两面中前者要优于后者,也就意味着男性对女性的占优,人对自然的占优。由此,沃克断定,超越男权社会二元制的概念,是解放女性和自然的必然之路。
生态女性主义并非简单地强调自然、强调和谐。在她们看来,仅凭女性、种族、自然等力量,根本无法改变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构成,作为“他者”和对立存在的社会地位也无法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强调多样性、反对单一性,成为她们解构人类社会的主要立足点。
四、融合与激荡:西方文学中的女性主义
存在女性主义强调“超越”“女性气质”,追求“自我”;生态女性主义提倡“女性特质”,要求自然和和谐,从本质上看,都是要求重新审视和建构人类社会,打破男权和物质性对于女性的压迫和束缚。正是基于这一点,两者相互激荡与融合,共同促进了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罗诗钿,2006)。
女性气质是存在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主要分歧点。在存在主义看来,女性气质纯粹是男性强加于女性的观点,是男性对女性的审视而非女性自身的要求。“如今之所以不再有女性气质,是因为它从来没有存在过”;“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的”[1]。男性对女性气质的塑造通过不断的固化和发展,最后演变成为女性的自觉意识,进而成为女性追求“自我”的最大障碍。男性对女性气质的塑造一方面满足了“作为个人私欲的要求”,另一方面通过伦理和精神延伸,更加固化了人类社会结构中男性的占优地位。因此,波伏娃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必须“超越”这种“内在性”,实现“自我”的存在,才能摒弃“他者”的地位,成为和男性一样的平权者(罗诗钿,2006)。
生态女性主义则并不回避女性气质的问题,正如自然对于人类而言存在独特性,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也存在自身的特质。如女性的平和、爱心、怜惜等特征,对应的正是自然对于人类关怀的部分。因此,她们强调,女性气质本身就是对男性社会的反叛,女性气质与自然、生态和社会的和谐面相连,能够对男性的“野蛮征服”和“粗暴超越”形成制约和抵抗,从而拯救自然、社会和女性本身。
需要强调的是,女性气质本虽然是存在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分歧点,但如果深入分析这种分析,则会看到两者的融合与殊路同归的趋势。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所要超越的是被男性所规定的女性气质,是反对从男性角度来看待女性,要求树立女性本身的特点即“自我性”。而生态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女性气质,是女性天然的、不带雕饰的特征,是未经过男性化的女性气质。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存在主义超越以后所存在女性“自我性”。
结构与解构的不断碰撞、西方哲学思潮的不断变革,引发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勃发和女性主义作家的兴盛,无不在告诫世人:男性社会的压迫和侵占已经成为历史,女性的觉醒和对自我意识、自身存在价值的追求将反抗任何敢于歧视和压迫她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思想。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赞叹道:女性主义作家既塑造妇女应有的形象又使作家通过写作成为反抗的妇女来抵制这个男权世界。小说创作的本身就是生活在父权中心文化内部的妇女进行的颠覆性活动。男性以往所固有的对女性非天使即妖魔的说法也将渐渐隐退于女性与日俱增的独立、平等的女性意识之后。女性作家们运用手中的笔纠正了传统男性作家笔下扭曲的女性形象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颠覆了男性中心的话语表达构建了女性新的话语权,谱写出一曲曲女性反抗父权、自强不息的动人诗篇极大地促进了人类两性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存。而建立在爱和理解基础上的人类两性的和谐共存将使世界变得美好使人类获得真正生存的意义[7]。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总是先由社会思潮的变革引发。西方自启蒙时代开始,通过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冲击与洗礼,女性和女性的形象、地位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一方面冲击着旧有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不断解放着人类本身。男权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经历变革与分离,男女平等、女性选举权、女性受教育权等,不断提升着女性的地位和话语权。男权文化的弊端虽多,但它却催生和滋养了女性主义文化。而女权主义思潮又极大地影响了女性的现实存在,影响到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们较多地仍然是运用现代哲学、逻辑性、社会学的理念来解构、剥离和评价男性主义世界。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与西方哲学社会学理论的进步紧密相连。无论是存在女性主义还是生态女性主义,它们对现代性、物质性和男权的消解,并不能成为构建新型的人——自然、男——女结构的基础。但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理论毕竟不完善,像如何克服女性自我传统的心理障碍及意识束缚,女性主义虽然已经影响并改变着西方文学的发展,但消费角度的女性文学作品,仍然是旧有文学模式的沿袭,即便是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并为完全消除男性视角的特征。进入后现代语境的西方文坛,一面是创造消费与社会认同的传统套路的文学作品,另一面是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作品的孤芳自赏或无人问津,其实质,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变革所引发的思想和价值的多样化,而多样化,恰恰是女性主义挑战男权社会的主要武器。女性自我解放,必然是人类自我解放的组成部分,怎样打破物质对自然、社会对人类的禁锢与压迫,任重而道远。
[1][法]伏波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美]约翰·克罗·兰色姆.新批评[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3]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北京:三联书店,1989.
[4]吴良红.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紫色》[J].河南社会科学,2011,(5):162—165.
[5]Griffin,Susan.Woman and Nautre[M].San Francisco:Harper and Row,1978.
[6][美]法尔克,等.冲突与解构:当代西方学术术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7][美]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三联书店,1997.
I109
A
1007-905X(2012)06-0088-03
2012-03-15
施志渝(1957— ),男,山东莱州人,上海政法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责任编辑 姚佐军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