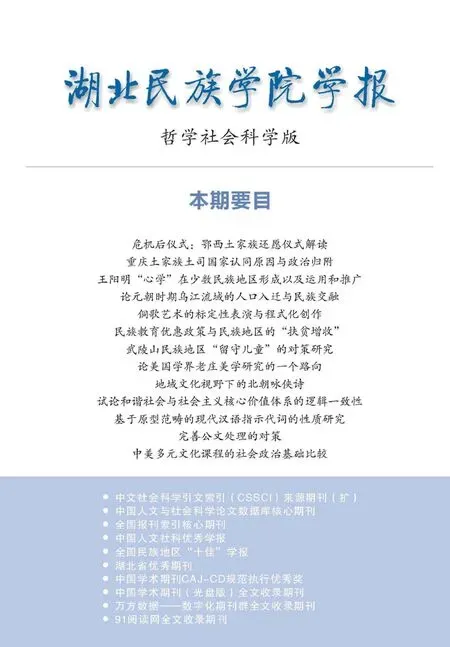论元朝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入迁与民族交融
张世友
(重庆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重庆401331)
论元朝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入迁与民族交融
张世友
(重庆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重庆401331)
元朝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因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地理区位,长期成为无数外来移民入迁定居之地。在元朝政府强制遣送和政策吸纳等综合性行政策略的共同推进之下,大批中原人口通过各种途径陆续移迁到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而且更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元朝时期;乌江流域;人口入迁;民族交融
乌江流域地处中国西南边疆腹心地带,贯穿贵州、云南、湖北、重庆三省一市,幅员8万多平方公里,气候呈垂直分布,生态环境平衡有序,矿产、水利和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世代杂居着苗、土家、彝、仡佬、侗、布依、白等30余种少数民族。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尊称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蒙古汗国建立后,即开始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向外频繁发动战争。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1276年灭南宋,1279年消灭南宋流亡政权,结束了宋辽金时期的分裂状态,又一次统一了全中国。元朝对中国的统一,结束了500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各族人民又可以在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息和发展社会生产,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特别对于西南边疆的乌江流域地带而言,因其再次被纳入到了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历史版图,大元朝廷为强化其中央集权和体现封建朝廷的威仪,不惜在设置行省机构、推行土司制度和建立站赤驿道的基础上,同时辅之以强制遣送和政策吸纳等各种手段,移居流迁了大批中原人口至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些举措不仅有力达成了大元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而且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各民族之间的互通、交流和融会。
一、军事入驻与民族政治的重构
元朝时期,封建朝廷为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力量,维护蒙古贵族特权,一直习惯以武力征伐的特殊形式,将蒙古移民作为征服者和统治者分散于各地。地处西南边地的乌江流域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当然也未能幸免,尤其流域上游水西地区的乌蛮部落亦奚不薛,曾多次遭到元朝政府的不断派兵征讨。《元史》卷122《昔里钤部(爱鲁)传》有载:“(至元)十四年(1277年),忙部、也可不薛叛,以兵二千讨平之。”同书卷 10《世祖七》又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癸已,爱鲁将兵分定亦乞不薛。”而同书卷11《世祖八》记载则更为详细:“冬十月丁丑,以湖南兵万人伐亦奚不薛,亦奚不薛降。……壬辰,亦奚不薛病,遣其从子入觐。帝曰:‘亦奚不薛不禀命,辄以职授其从子,无人臣礼,宜令亦奚不薛出,乃还军。’”可见,经过这次征讨,亦奚不薛是以降告终。但好景不长,元政府对亦奚不薛的大规模讨伐行动初定之后不久,至元十九年(1282年)亦奚不薛再次叛乱。据《元史·昔里钤部(爱鲁)传》载:“十九年,也可不薛复叛,诏与西川都元帅也速答儿、湖南行省脱里察会师进讨,擒也可薛送京师,仁普诸酋长皆降,得户四千。”[1](卷122《昔里钤部(爱鲁)传》)藉考有关文献,亦奚不薛此次复叛一直延续到至元二十年(1283年)才为元朝所平定,并在其地设立政权机构进行管理。《元史·世祖九》有记:“二十年夏四月庚寅,敕药刺海戍守亦奚不薛。……秋七月,丙寅,立亦奚不薛宣慰司,益兵戍守。分亦奚不薛地为三,设官抚治之。壬申,亦奚不薛军民千户宋添富及顺元路军民总管兼宣抚使阿里等来降。班师,以罗鬼酋长阿利及其从者入觐,立亦奚不薛总管府,命阿里为总管。”[1](卷12《世祖九》)
可以肯定地说,元朝统治者以军事入驻的移民方式引发的穷兵黩武,非但从一开始就没有收到良好的统治效果,相反却引发了乌江流域各地民族的起义不断。据近人研究,“仅就公元1280至1290年的十年中,彝、苗、僚、罗氏鬼国各族的起事粗略统计,就达七次之多。”[2]而这其中,当数元成宗大德四年至七年(1300~1303年),由宋隆济和蛇节(又称“奢节”)领导的苗、仡佬、彝等族人民大起义最具影响。据《经世大典·招捕总录》载:“大德元年(1297年),八百媳妇国(今泰国北部纲怕省景迈、昌莱、喃邦诸府之地)与胡弄攻胡伦,又侵缅国,车里告急,命云南行省以二千或三千人往救。二年(1298年),八百媳妇国为小车里胡弄所诱,以兵五万与梦胡龙甸土官及大车里胡念之子汉纲争地相杀,又令其部由混干以十万人侵蒙样等,云南省乞以二万人征之。四年(1300年),梁王上言,请自讨贼,朝意调湖广、江西、河南、陕西、浙江五省军二万人,命前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刘深率以征。”[3]629大军进至顺元,“纵横自恣,恃其威力”,骄横跋扈,肆意征派,并“驱民转粟饷军,谿谷之间不容舟车,必负担以达。一夫致粟八斗,率数人佐之,凡数十日乃至。由是民死者亦数十万,中外骚然”。大德五年(1301年)四月,官军令雍真葛蛮(在今贵州开阳县境)“出丁夫、马百匹”,限期缴纳。这于是激起民变,土官宋隆济率苗族、仡佬族等民众直接起义,“攻贵州,杀散普定、龙里守令军,烧官粮,杀张知州”。[1](卷156《董文炳传》)对此,清人毕沅在《续资治通鉴》卷194中亦有记载:“六月丙戌,宋隆济率苗佬、紫江诸蛮四千人攻杨黄寨,杀掠甚众。壬辰,攻贵州,知州张怀德战死,遂围刘深于穷谷中,梁王遣云南省平章绰和尔、参政布埒齐将兵救之,杀赋酋撒月,斩首五百级,深始得出。”大德五年(1301年)八月,水西土官之妻奢节因刘深威逼其“出金三千两,马三千匹”,大为不满,遂以“朝廷远征,供输烦劳”为辞,带动乌撒、乌蒙、东川、芒部等地民众起兵响应宋隆济。又《元史·哈刺哈孙传》同样记载有序:“刘深次顺元,深胁节求金三千两,马三千匹。蛇节因民不堪命,举民围深于穷谷,首尾不能相救。”[1](卷136《哈刺哈孙传》)很明显,这次宋隆济、蛇节起义是因元军征讨八百媳妇国而起,起义从新添葛蛮开始,蔓延顺元及水东、水西,进而扩大到四川马湖、永宁及云南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武定、威楚、曲靖、普安,“西南半壁为之震动”,元朝调湖广、四川、云南、陕西四省兵力镇压,历经四年才告结束,不仅使征“八百媳妇”的两万官兵,只剩十之一二,纵横自恣的统兵官刘深受诛,而且迫使朝廷免除顺元、思州、播州等地一年税粮,并罢征“八百媳妇”。
而除却此次事件,时乌江流域的渝东南少数民族也曾有过激烈反元军士入驻的抗争。据《元史·杨大渊传》载:“(至元十二年,杨文安)功鸡冠城,谕降守将杜赋;又招石马、铁平、小城、三圣、油木、牟家、下隘等城。”“(至元)十五年(1278年),(杨文安)进兵攻绍庆,守将鲜龙迎敌。二月,潜遣勇士,夜以梯冲攻破其北门,鲜龙大惊,收散卒力战,兵败就擒。”[1](卷161《杨大渊传》)继续往后,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还爆发有今渝东南酉阳、秀山境内的“九溪十八峒蛮”起义。据《元史·李忽兰吉传》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奉旨与参政曲里吉思、佥省巴八、左丞汪惟正,分兵进取五溪洞蛮。时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蛮僚叛服不常,往往劫掠边民,乃招四川行省讨之。曲里吉思、惟正一军出黔中,巴八一军出思、播,……十一月,诸将凿山开道,绵亘千里,诸蛮设伏险隘,木弩竹矢,伺间窃发,亡命迎敌者,皆尽杀之。遣谕诸蛮酋长率众来降,独散毛洞潭顺走避岩谷,力屈始降。”[1](卷162《李忽兰吉传》)不难看见,本次参加起义的不仅有土家族、苗族,而且还有众多的其他少数民族,他们几乎占领了今湘鄂渝黔边区的绝大部分地区,元军最后通过任命四川行省参政曲里吉思为主将,并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军事征讨方才平息了这场当地少数民族反抗元廷军士入驻的斗争。
二、遣调屯垦与民族经济的助推
元朝时期的屯垦制度起于战争需要,据《元史·兵志三·屯田》:“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之。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又据《经世大典·屯田篇》载:“国家平中原,下江南,遇坚城大敌,旷日不能下,则困兵屯田,耕且战,为居久计。”[3]642这说明,元军镇守各地,往往就地屯田,以解决自身的部分粮饷问题。而在广大的乌江流域地区,元政府甚至有专门设置的屯垦管理机构,以加强对军民屯田的日常监控。譬如,泰定四年(1327年),元廷就曾以马思忽为云南行省平章,“提调乌蒙屯田”[1](卷 30《泰定帝二》)。 另据 《元史· 兵志三》和《元史·地理志四》的记叙,元朝在今乌江流域和与之毗连地区屯田的规模还不算小,其基本情况大致如下:乌撒宣慰司(领乌撒路、东川路)有军民屯200户,田数阙载;梁千翼军屯(先在乌蒙地区,以后迁新兴州),先有1000人,以后减为700人,有田3789双;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军屯有5000人,田1250顷。又据《元史·英宗一》:延祐七年(1320年)再开普定路屯田,分乌撒、乌蒙屯田卒2000人赴之。另据《元史·刘国杰传》:元大德五年(1301年),因土官宋隆济、蛇节率众反叛,时湖广行省平章刘国杰于是在行省西部南北3000里的地域,一共又设置了38处屯戍,并遣将士守之,“由是东尽交广,西亘黔中,地周湖广,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诸蛮不能复寇”。[1](卷162《刘国杰传》)
除军屯而外,大元王朝在乌江流域地区还通过政府出面进行户口清查,对“各地清查出不少漏籍人户,往往就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在当地建立民屯。”[4]300时《元史·昔里钤部(爱鲁)传》有记:“至元十年(1273年),平章赛典赤行省云南,令爱鲁疆理永昌,增田为多。十一年(1274年),阅中庆版籍,得隐户万余,以四千户即其地屯田。”[1](卷122《昔里钤部(爱鲁)传》)与此同时,在流域下游地带亦同样有些许民屯建立。根据《元史·兵志三》的记叙:“绍庆路民屯: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于本户未当差民户内,签二十三户,置立屯田。二十年(1283年),于彭水县籍管万州寄户内,签拨二十户。二十一年(1284年),签彭水县未当差民户三十二户增入。二十六年(1289年),屯户贫乏者多负逋,复签彭水县编民一十六户补之。为户九十一。”[1](卷100《兵志三·屯田》)
元朝政府在乌江流域地区通过遣调军民大肆开展屯田垦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当地少数民族小区域的闭关自守,进而改变了当地经济、政治上的落后状态。在蒙古贵族们看来,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非立屯之地”,但却因其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3]642,所以也就不能不在乌江流域的一些地方开展军民屯田。屯田垦殖这一行为本来是元朝政府对该区域内的封建领主、奴隶主和部落贵族的统治范围内有效巩固自己统治的一种手段,但它却促成了当时一部分地方封建地主经济的产生。尤其是行省的官吏们从军屯、民屯户中直接汲取经济和军事的力量,不但加强了对各少数民族中的封建领主、奴隶主和部落贵族的统治区的政治控制;而且最重要的是元朝政府不断从军、民屯田的据点出发,更一步步扩大了行省对乌江流域地区各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
元朝时期的封建统治者在乌江流域遣调军民屯田,这是前所未有之事。它对在乌江流域地区确立地主经济,稳定郡县政权,推动农业生产,均起到重要作用。屯垦制度的实行,也使乌江流域之内的民族经济开发得以提速,地方经济很快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通道。以乌蒙屯田为例,元延祐五年(1318年),朝廷曾专门命行省官刘元亨兼领屯府一事。在他的严格经管之下,“尽其水土之利,公有余而足以用众,私均赡而不敢自私,又通其医药、市易、祷祠、游观之用,几不异于中州”,三年不到的时间,屯田地区“稳然不可动之势成矣”[5](卷13《福建总管刘侯墓碑》。又元延祐年间(1314~1320年),在官吏刘济的整顿之下,地处乌江流域上游的乌蒙、乌撒等屯田一带地区,也已出现了“府中储积多如山,陂池种鱼无暵干,几闻春硙响林际,仍为窳蔬流圃间”的兴旺景象[6](卷3《题蒙泉吏隐图》)。 另据元李源道《为美县尹王君墓志铭》所记,云南少数民族官吏王惠任威楚屯田大使时,同样亦是“增粮万石”。
三、留居戍守与民族成分的融变
蒙古帝国建立以后,为实现迂回包围南宋并达到天下一统,1252年蒙哥汗命令其弟忽必烈统率十万军队进攻云南。1253年蒙古大军兵分三路进入云南,消灭了大理国。1254年忽必烈还师,留大将兀良合台镇守云南,并以云南为据点征服西南邻近地区。至于乌江流域地区,蒙古大军的留居中心主要是大定(今贵州大方县)。据史料记载,大定自元初伊始就有蒙古族迁留。《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记云:至元元年(1264年),赛典赤出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至元七年(1270年)赛典赤“分填四川”。另有资料显示,“元代在今四川和重庆地区也设有陆站48处、水站84处,驿站官员和站户多由蒙古人或回回人充任。”[7]43当然,元代设于各路、府、州、县录事司及非蒙古军队中执掌大权的达鲁花赤,除了大多数由蒙古人担任外,个别回回、畏吾儿、乃蛮、唐兀等色目人也可担任。各路还设有同知,也可由回回人担任。譬如,早在至元二年(1265年),朝廷就曾下令:“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1](卷6《世祖三》)
从另一层面看,伴随站赤驿道的开通,元军深入乌江流域腹地,随军伍而来的汉人亦渐次增多。“元朝经常在贵州用兵,历次征战,每有汉人随之而来,落籍贵州者往来有之。”[8]347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至元十六年(1279年)三月,以兵3000戍小龙等处安抚司[1](卷10《世祖七》);十八年(1281年)三月,遣兵戍守黄平、镇远等处[1](卷11《世祖八》);二十年(1283年)四月,遣人屯守亦溪不薛险隘地[1](卷12《世祖九);二十七年(1290年),列乌撒路军屯[1](卷16《世祖十三》)。 《元史·石抹按只传》亦载:至元十八年(1281年),石抹按只也被朝廷遣派,“领诸翼蒙古、汉军三千戍施州”。[1](卷154《石抹按只传》)又据《元史·兵志三》:延祐三年(1316年),因云南行省言:“乌蒙乃云南咽喉之地,别无屯戍军马,其地广阔,土脉膏腴,皆有古昔屯田之迹,乞发畏吾儿及新附汉军屯田镇遏。”[1](卷100《兵志三·屯田》)朝廷于是再置立乌蒙军屯,发畏吾儿和新附汉军1000人置立屯田。
对于这些戍守乌江流域的外来兵士,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无法返回原地,从此便留在了当地,其中大部分的兵士逐渐融合到了当地民族当中,但亦有部分保留住了其民族特征、民族意识,而成为了今天乌江流域地区的蒙古族,色目士兵则在与其他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成为了今天乌江流域地区的回族[9]363。所以,在今天乌江流域的湖北、重庆、“贵州不少地方,至今仍有元代迁来的蒙古族、回族与白族人口的后裔。”[10]譬如,今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咸丰县的唐崖土司,也就是当时的蒙古族南下之后,因留居此地而后成为土司,并融入了当地社会,接受了当地的文化[11]。更有甚者,有的蒙古人因为王朝倾覆,而不得不主动改姓(用汉姓),并易名隐居或迁移他方。例如,今贵州大方县的蒙古族余氏,原是居住湖北麻城县的蒙古贵族,明初改姓弃官避难入四川,以后辗转进入贵州[12]。据《余氏家谱》载:“我余氏之视奇屋温,胡人也,……号蒙古铁木真。……不料,红巾贼作乱,改铁为余,四散各处。”再有今重庆彭水县亦有一支蒙古族人,他们“住在太原乡香树坝村,为谭姓。据《谭氏族谱》记载,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二晚,朝廷中有人托付心腹谭国知(化名谭国明)带着铁木耳十子中的铁满四等七人,装扮成汉人,改姓谭,逃出大都,远走河南灵宝以北隐居。次年二月初二,他们来到洛阳桥边,插柳为记。后又迁入湖北麻城县孝感乡高街珍珠石马头居住。由于明军搜捕,明洪武四年(1371年)四月,他们再迁至四川万县三稹里龙王坝。于当年八月十五日夜,兄弟几人共议七言诗八句:‘本是元朝帝王家,洪(红)兵(巾)赶散入西涯。红阳岸上各分手,凤凰桥头插柳桠。一姓改为几样姓,几姓分居百千家。要想兄弟同相会,一梦云游海推沙。后人记得诗八句,五百年前是一家’。从此,七兄弟分手。他们虽改为谭姓,但那几句诗却代代相传,且只传子不传女,只传内不传外。谭满四与妻黄氏曾落业于忠州,又迁至巫山县,再迁往石柱县沙子关。他们的长子元龙及其子宗贵,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迁徙到彭水县谭家堡(今属太原乡)定居,至今全家已繁衍达300余人(不包括外嫁女性)。”[13,14]734-735
四、自发流移与民族文化的荡涤
元朝时期乌江流域的外来移民,虽绝大多数是在蒙古军队的武力威胁下被迫入迁,但也有一部分属于自发流移之徒。有元一代,由于乌江流域的站赤设置,与内地交通因统治的需要而得以全面恢复,较之于前朝时期有较大的发展;而与周边各国,也由于有中央王朝为强大的后盾,政治交往频繁,经济交流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元朝置驿起初的目的是“宣布政令,通报军情急事”[15](卷19421《站赤六》),但驿道开通以后,官民行走和蛮夷入觐亦可利用,给行人提供了很大方便。《元史·世祖十一》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云南行省平章纳速剌丁奏准数事,首条即是“弛道路之禁,通民来往”。
伴随着交通的愈益顺畅,不仅促成了边疆与内地的政治联系,客观上增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对祖国的向心力,使乌江流域地区出现了“远夷蚁附,烟火相望,千里无间,既富且庶,诸蛮朝贡,络绎不绝”的繁荣景象;而且交通的整治,也为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社会文化的交流制造了便利条件。譬如,天历年间(1328~1330年),因乌江流域毗邻的中庆路学毁于战火,官府即刻就派人“乘驿持镪五千缗”至江南购礼乐之器,另持千缗到成都购买服装,很快恢复了路学[16](卷8《中庆路·学礼乐记》)。而姚安路总管高明在“缮官舍、葺邮传”的同时,也凭借畅达的交通“近聘荆益关陕之士以为民师,远购洙泗濂洛之书以为民学”[17](卷20《升姚安路记》)。 此外,大量站赤驿传的设立和顺畅发达的交通,还直接为外地移民进入边疆,以及扩大边疆诸族的文化交往创造了有利环境。譬如,元代有大批汉人、蒙古人、色目人以军人、官吏、商人等身份来到乌江流域,这其中就有不少人落籍当地而被视同土著。有记载显示,时流域相邻的威楚地区(今云南楚雄一带),已是“多旧汉人,乃元时迁徙者,与夔人杂处”[16](卷2《楚雄府·风俗》);而紧邻的中庆地区(今云南中东部一带),更是“土著之民,不尽焚人而已,有曰白罗罗(属今彝族)、曰达达(今蒙古族)、曰色目,及四方之为商贾、军旅、移徙曰汉人者杂处焉”[16](卷1《云南府·风俗》)。另据相关记载,“至元二十年(1283年),从常德、辰州、沅州、靖州等地调往乌撒淘金、思州采炼朱砂水银的万户民工,即经由东西驿站抵达。”[8]310至元末明初,流域中的重庆地区也陆续迁入了三路回族同胞:一路是西北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回族同胞,因经商等多种原因陆续迁来重庆;二是由湖北等地迁入重庆;三是由广东、江南等地迁入。从而开始形成重庆的回族[7]249。
各种自发流移的外来移民,齐聚尚处“蛮荒”的乌江流域,跟进而来的先进技术自然刺激了当地社会生活的大发展。加之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廷诏谕四川行省“抚治播州、务川西南诸蛮夷,官吏军民各从其俗,无失常业”[1](卷10《世祖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廷又诏谕思州宣抚司“因阅户惊逃者,使各安业”[1](卷17《世祖十四》);大德七年(1303年),元廷再免思、播二州粮税一年;次年因乌撒、乌蒙、益州、忙部、东川等路饥疫,并赈恤之[1](卷21《成宗四》)。这些举措,无疑对乌江流域生产的恢复、社会的安定和文化的繁荣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基础。所以,在社会繁荣发展、文化激烈碰撞的同时,这些移迁汇聚到乌江流域的外来民众除了在本民族交际中使用本民族语言外,往往还能在与相邻民族交往中听懂以至能讲相邻民族的语言。而那些散居于土司辖区的汉人,更是大量吸收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分,日渐“夷”化。
另外,鉴于元代在各行省所在地均设立儒学提举司,统管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置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各路设儒学教授一员及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1](卷81《选举志一·学校》)。在这种政策的利好刺激下,当时整体文化还比较蒙昧的乌江流域地区于是迎来了一次文化发展的契机,尤其地处流域北部腹地的播州,它们首得风气之先,儒学一时兴盛不衰。《大元一统志·播州军民安抚司》有记:“(播州军民安抚司)宦户、儒户与汉俗同”,《遵义府志·土官志》亦记载有:杨汉英为元播州宣抚使,“急教化,大治泮宫,南北士来归者众,皆量材用之”[18](卷31《土官志》)。 再往后,不仅流域上游黔西的普安路、普定路等地有了儒学的建立,至皇庆时(1312~1313年),隶属湖广行省的顺元路也建立起了儒学,并以贵州著名教育家何成禄为教授。
总而言之,元朝因以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执掌地方各级政权的官员、镇守将领及军士主要均是蒙古、色目和归附汉人。外地进入者多带有幕僚、随从、家属,往往定居当地,子孙繁衍。同时随着西南地区与内地交流的频繁,还有一些汉人、色目人商贾和平民也从外地进入,数量多寡不一。元朝时期乌江流域地区的人口入迁,“不仅给地处西南边陲的蒙昧地区注入了新鲜血液,引进了充足的劳动力,带来了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而且把内地先进的政治思想意识,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经济发展理念也移植到了新开拓的区域。”[19]同时更把国家因地域统一而形成的整体一统观念带到了西南边地,将边疆民族与内地民族之间的交流由两个政治团体间的民族交流转变成为同一国家的民族交往,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罗友林.元代贵州宋隆济、蛇节起义[J].贵州民族研究,1984(4).
[3]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4]方铁,等.中国西南边疆发展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5](元)虞集.道园学古录[Z].明嘉靖四年(1525)刻本.
[6](元)陈旅.安雅堂集[Z].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7]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重庆民族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8]侯绍庄,等.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9]王文光,等.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0]古永继.元明清时期贵州地区的外来移民[J].贵州民族研究,2003(1).
[11]王平.唐崖覃氏源流考[J].贵州民族研究,2001(3).
[12]荣盛.贵州省余姓蒙古族籍试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5).
[13]东人达.成吉思汗在西南的后裔[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14]彭水县志编纂委员会.彭水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15](明)解缙,等.永乐大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6](明)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Z].明景泰六年(1455)刻本.
[17](明)刘文征.(天启)滇志[Z].明天启五年(1625)刻本.
[18](清)郑珍,等.遵义府志[Z].遵义市志编委会1986年重印本.
[19]张世友.论历代移民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经济推动[J].贵州民族研究,2011(6).
C956
A
1004-941(2012)04-0022-05
2012-06-28
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伦理文化与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研究”(2011YBYS091);重庆师范大学启动基金项目“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伦理思想研究”(10XWB00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乌江流域历代移民与民族关系研究”(06XMZ005)。
张世友(1969-),男,重庆垫江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历史文化、中西伦理思想。
责任编辑:谢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