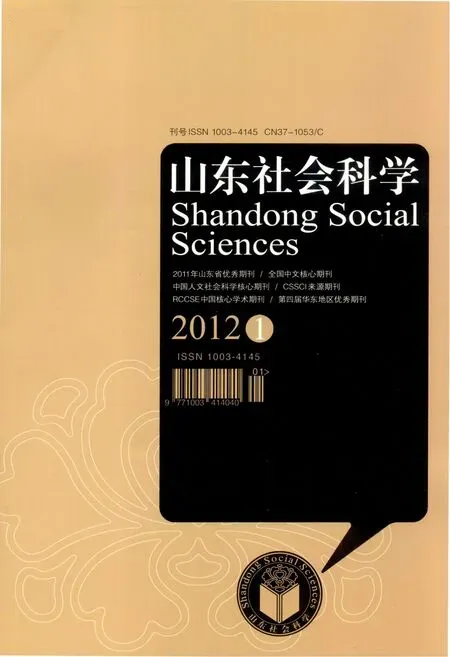反乌托邦文学与元乌托邦理论
曲 宁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汉学院,吉林长春 130117)
反乌托邦文学与元乌托邦理论
曲 宁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汉学院,吉林长春 130117)
乌托邦文学与政治哲学中的乌托邦理论有着很深的渊源,它们共同探讨着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永恒理想。但到二十世纪,无论在文学还是政治学说和运动中,乌托邦都面临危机。本文拟就西方现代极有影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以及诺齐克的元乌托邦理论对这种乌托邦的危机略做探讨。乌托邦的危机是人们对它精神理想向度做出错误的理解,妄图加以现实化的结果。反乌托邦文学正是对其可能后果的预见,而元乌托邦理论则是从政治哲学角度对传统乌托邦理论的反思和提升。
反乌托邦文学;罗伯特·诺齐克;元乌托邦
一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界于文学文本和政治哲学文本之间,也同时在这两个领域中带来深远的影响。在文学中,它一度掀起了同类创作的热潮,以致形成一种亚文类——“乌托邦文学”。在政治领域,它的影响就不止限于文本层面,更直接或间接地促生了一系列的乌托邦实践运动。
在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乐观主义的推动之下,乌托邦文学和乌托邦政治运动同时达到了顶峰。由于有了公有制、民主制等方面的实际操作经验——当然更多的是教训的积累,这一时期的乌托邦文学的描绘趋于具体化。我们在早期乌托邦——比如莫尔的乌托邦或斯威夫特的慧骃国里听到的更多的是对国民自由平等富足程度的描述,而十九世纪的乌托邦文本中则颇可见到各种可资实践的策略措施。这一时期的乌托邦文学俨然打算成为社会改革的指导手册。然而,就是在政治与文学齐头并进、跨越世纪之界,信心十足地向现实的乌托邦迈近的时候,乌托邦本身被宣布终结了。
这种终结也同时应验在政治与文学的两个向度上。前者体现为二十世纪中几种社会规划的挫折——法西斯国家造成的灾难是其中最可怖最惨痛的例子之一——以及随之而来的学者对乌托邦性质的批评反思;后者则以反乌托邦文学的出现为表征。在那里,弥漫于传统乌托邦文学中的那股对理想国的热情讴歌、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不见了。萦绕于其中更多的是对人类未来走向的恐惧和彷徨。当乌托邦不再是人人向往的天堂和避难所,而更像是对现代人类发展趋势的反讽的时候,乌托邦就不再是乌托邦,而沦为“反面乌托邦”。
二
苏联作家叶·扎米亚京的《我们》(1924)、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和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1948),被誉为现代西方的“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三部小说都从某一个侧面描写了一个成为现实的“乌托邦”。这些国度以各自的方式演绎着它们对自由、平等、和平、安定等乌托邦理想的解读,或误读。
前两部作品都在某种程度上兑现了传统乌托邦构想中富足安定的承诺,然而又在深层次构成了对乌托邦愿景的扭曲。《我们》中的世界是一个以数学般的完美秩序为统治核心的世界。它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化为符号,像数字一样按部就班地服从国家最高秩序的安排。《美丽新世界》则建立在现代生物学理论之上。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精神极度匮乏的世界把人的孕育和抚养过程社会化、生产线化,人为地干预胚胎和幼儿的发展方向,使未来的成人别无选择地各司其职、安分守己。与二者相比,《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国甚至并不费心粉饰“理想社会”的假象,只以政治谎言裁成极权主义独裁者的新衣,裹在社会破败、狂乱、可怖的躯体之上。独裁党“英社”的统治口号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实质是:通过不尽的无实质战争持续消耗过剩产品,使民众堪堪挣扎在生存线的边缘,无心过问权力归属,推行愚民政策,使民众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甘受“英社”统治。这是作者奥威尔对当时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极端化推演。
虽然有侧重点的不同,但从实质上看,这三部曲又有着深刻的共性——它们所预演的未来世界,都违背了乌托邦传统上自由、平等的基本追求。在《我们》中,社会是封闭在绿色大墙之内的严密机器,秩序高于一切,个人以成为机械零件为致福,争取一呼一吸都与集体同步,而绝对不能以爱、个性、自由思想这类“灵魂”的东西威胁秩序。凡有这样的异端分子出现,要么被推上极刑台液化处理,要么就要接受“幻想去除手术”,除掉灵魂。《美丽新世界》把等级制度进一步固定下来,并以社会分工的国家规划代替了人的自由选择,以由睡眠教育和条件反射训练灌输出来的社会角色意识取代了个性思想的养成。为了防止人们发现平等和自由的缺失,国家使人们沉溺于各种物质享受当中,甚至怂恿人们吸食毒品,而把精神上的爱情、亲情以及纯粹艺术等有关人性的东西摒除在自己的玻璃围墙之外。《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国不屑于打什么社会进步的旗号,反而故意制造贫穷,制造战争,制造国家、阶级上的隔绝。同其他统治者不同,“英社”不屑于宣传什么积极价值,无需通过让个体获得某种形式上的自我实现感的方式来达到维护现状的目的,相反,它相信只需把一系列的反面措施推向极致——24小时电屏监控器、无孔不入的思想警察、匪夷所思的残酷刑罚等手段营造极度恐怖的思想禁锢氛围,就能扼制任何有可能危及极权统治的个体思考。为了根除这种“思想罪”的隐患,“英社”还彻底改造了语言,把这一思想的载体严格限制在党的政治话语模式之内,从而使反抗思想无所附丽而自行消亡,最终实现个体性思想与党性思想的完全同一。于是,在《一九八四》的世界中,人不但在社会行为上没有任何自主自由可言,就连自己头颅之内的小小空间也不属于自己了。
这些未来的反面乌托邦无不漠视乌托邦传统所标举的人的基本权利。它们甚至怂恿了某种形式的国家暴政,使国家机构有权以社会的名义牺牲个体,以稳定的名义牺牲自由,肆意剥夺人的权益乃至生命。国家或说权力取代了人,成为一个社会的躯体,而个体的人则沦为喂养国家这个庞大的吸血怪物的奴隶和食料。
然而以上这些可预见的黑暗未来之所以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不仅仅在于它们对乌托邦思想的背反,更在于它们推行各种暴政的借口正来自于某些传统中的乌托邦构想。《我们》中全社会步调一致的生活秩序可以溯源到《太阳城》等乐于具体规划乌托邦内作息时刻表的传统文本;早在《乌托邦》羊毛衣服比粗布衣服更受尊重之类的细节中,就暗藏了社会分工的不平等具有合理性的潜台词;傅立叶等人的著作中流露出的享乐主义倾向或许正是《美丽新世界》中无节制的物质享受的灵感来源;而传统乌托邦设想大多倾向于自上而下地实现乌托邦,于是就强调了国家政权在其中的作用,这种强调已经不详地预示了《一九八四》中“英社”的极权角色。最根本的,由于“乌托邦”在传统乌托邦文本中意味着无与伦比的完美性,它也就具有了人类社会终极形式的意味。于是,乌托邦也就同社会结构的稳固画上了等号。为了这种稳定,为了避免后续的革命,乌托邦的推行者就有借口不惜牺牲人的基本权利。反面乌托邦三部曲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这种倾向——《我们》的大一统国把自己安全地置于绿色围墙的保护之内;《美丽新世界》中的世界国用玻璃大墙把自己文明世界同“野蛮世界”隔开;《一九八四》则通过篡改历史、封锁信息把人民同过去、同共时的世界相隔绝。这种种形式的隔绝,是各种暴政的前提、手段、与结果。三部曲中这些意味深远的细节都警示着,当乌托邦的实践者要把社会闭合在一个固定的形式内,当他们要把历史冻结在某一时刻时,乌托邦就成为反面乌托邦。
以上述三部作品为代表的反面乌托邦文学,从不同角度批驳了十九世纪以来乌托邦理论中的科学乐观主义、批驳了以社会结构稳定的名义牺牲个体自由的倾向。放到历史背景中看,它们有着特定的时代针对性,我们可以把它们解读为对社会主义苏联、发达工业国家或战后英国等这些自诩为某种乌托邦实践的社会模式加以讽刺的寓言。但是另一方面,当我们把这些作品纳入到整个的乌托邦思想传统中时,又会发现它们都具有相当的历史超越性。它们是发自乌托邦思想内部的对乌托邦传统的整体性反思。它们对人们以往看待乌托邦的方式提出了总的质疑,承认对乌托邦的传统误读和误用需要对二十世纪人类社会诸多劫难承担起若干责任。它们暗示我们如要使乌托邦思想的生命在未来仍能够延续,就应该给这一思想本身以一个全新的、更为清醒的定位。
三
我们传统中对乌托邦的本质有哪些误解,又应如何重新界定乌托邦呢?乌托邦思想在政治哲学领域的继承者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深刻的思考。罗伯特·诺齐克的元乌托邦理论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例。我们此处就略引他的观点,看一看乌托邦思想是否能够像凤凰一样,在被宣告终结之后仍浴火重生。
我们在“反面乌托邦三部曲”可以透视到传统乌托邦规划中这样的偏颇:它们往往以某种(数学的、生物学的、或政治经济学等等的)对世界的认识为最终真理,并以此为据,构建自己的国度。这就意味着一种理念要意识形态化,使自己在精神领域占据排他性的垄断地位。为实现这种垄断,又势必要寻求某种社会模式的稳定性、封闭性,从而会导致不同形式的国家暴政。
同样,罗伯特·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也将矛头指向打着“平等”这样的乌托邦传统旗号的国家规划中隐含的不正义倾向。他指出,为实现平等的目的而人为设计的国家模式很容易形式化,而逐渐形成一种独立性,成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国家机器,成为一种国家的异化。
为纠正这种倾向,任何社会模式都应以维护个人的权利为出发点。而国家应该回归到它的自然状态,也即本性的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体,即“最弱意义国家”,除这种保护作用以外,国家不应有更多权利。“最弱意义上的国家把我们看作是不可侵犯的个人——即不可被别人以某种方式用作手段、工具、器械或资源的个人,它把我们看作是拥有个人权利及尊严的人,通过尊重我们的权利来尊重我们;它允许我们个别地,或者与我们愿意与之联合的人—起地——就我们力所能及地并在与其他拥有同样尊严的人的自愿合作的援助下——来选择我们的生活,实现我们的目标以及我们对于自己的观念”。
在他看来,他所说的权利最受限制的国家是道德上可取的国家、道德上唯一合法的国家、道德上唯一可以忍受的国家,正是“能最好地实现无数梦想家和幻想者的乌托邦渴望的国家。它保存了我们从乌托邦传统中所能保留下来的全部东西,而把这一传统的其余成分分别留给我们个人的渴望”。这是一种元乌托邦状态。诺齐克所倡导的元乌托邦不是某种特殊的乌托邦构想的实现,而是一种包容了各种乌托邦实验的社会“结构”。并且这一结构也并不包含任何静止的意味,而是某种或某些社会性团体向着理想化的不断地自我更正、相互融合的结果,即一种自然进化的产物。
诺齐克元乌托邦理论值得我们思考之处在于,他强调了乌托邦理想实现具有动态性,是一个不断演进修整的进程,甚至不排除其中包含的永远变动的倾向,从而纠正了传统乌托邦设想的固化偏颇:无论莫尔的作品还是其它乌托邦文本只是对某种特定的理想社会模式作为描述对象,他们“把一个完善的社会作为他们的目标,因此,他们描述的是一个静止和严格的社会,没有任何改革的机会或发展的希望,这一社会的居民亦无任何机会自己选择新的社会类型”。
诺齐克的元乌托邦理论恰好符合于学者们近来对乌托邦理论的整体反思。有学者指出,之所以近代的乌托邦运动频频失败,而且有些努力衍生出反乌托邦的恶果,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乌托邦的本质的认识是错误的。“乌托邦之为乌托邦,在于其根本精神向度,乃是对人类政治生活的正义永无止境的追求。”“乌托邦与政治现实是对立的,乌托邦是政治现实的否定,政治现实则是乌托邦的终止。而乌托邦运动则是在乌托邦精神召唤下形成的现实政治运动,乌托邦从观念到实践的这一转型,充满了悖谬和困惑之处。由于乌托邦运动中的乌托邦已经现实化,因而不能与乌托邦观念简单地等同,乌托邦运动的失败,并不是乌托邦观念本身的失败,相反,是很大程度上背弃了乌托邦观念,走向现实化的结果。”乌托邦的现实化即是反面乌托邦,是工具合理性对价值合理性的置换。
传统乌托邦构想的通病,很大程度上在于不加批判地肯定人们现有的想象力,认为人们完全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性”来构建自己的乌托邦化社会。这一假定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在现有的非乌托邦世界,我们的思考必然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塑造和灌输,我们对理想生活方式的设想,是遭意识形态污染过的,在很大程度上要回护现有社会秩序,因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想象。另一方面,即使人们能做出超越性的想象,那么在把这一特定想象加以实现的过程中,又把它固定化,形成了一种新的闭合体。后一种情况,我们在“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中已见实例,前一种情况,则对应于现在这个想象力匮乏、日趋保守的世界。那么我们如果才能避免传统乌托邦的这两种误区呢?诺齐克的元乌托邦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道路。
诺齐克的元乌托邦社会结构中每个理性成员都有对其他即存或可能的团体知情的自由,以及选择离开现有团体迁移到其他团体的自由,只要他认为那里能够实现他的最大价值,即做出最大贡献,并能获得最大回报。这意味着任何玻璃围墙或消息封锁都将是违法的。不批判这种被动想象,闭合的社会形态就不可能被打破,就不可能形成堪称“乌托邦共同基础”的开放的社会结构。因此,当哈贝马斯宣称乌托邦终结的时候,并非乌托邦本身终结,而是指那种试图把乌托邦现实化的运动和对乌托邦本质的误读应该终结了。
诺齐克在他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的确重申了乌托邦理想作为理想的本质。元乌托邦不是某种排外的社会形态,不像《我们》、《美妙的新世界》中表现的那种包裹在玻璃围墙之内的脆弱国家,更不像《一九八四》中被囚禁在语言的牢笼中的铁幕国家。相反,它是一个格外开放、包容、具有充分的动态性的“结构”,它不受任何政体或政策的限制,只负责维护每个个体成员的人的权利。除了正义,它不追求任何功利目标。它充分考虑到每个成员的个体差别,不会以“社会进步”或“国家利益”等名义剥夺人的情感和个性,相反,它尊重每个成员选择生存状态的自由,不会使“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中描绘的人的异化成为现实。在那里,每个人都能够完成自己的最大实现。
四
可以说,反面乌托邦文学与当代乌托邦理论延续了乌托邦传统中文学同政治两领域相辅相成的关系。反面乌托邦文学警醒我们不要对乌托邦文本所描画的美好世界形成拜物教式的盲从。因为具象化的乌托邦的存在价值只是对现有社会现实进行对照与批评。同样,现代乌托邦哲学也告诉人们,乌托邦思想的真正价值正在于它的否定性。乌托邦是人类永不受束缚的想象力的代名词。一个真正的乌托邦主义者是一位浮士德,他不达到人类的致福就永不满足。另一方面,他又超越了浮士德——他不会在任何一幅看似完美的图景前停驻他无尽追索的脚步,相反,他会亲手将闭合的幻景拆解开来,向更为广阔的可能性敞开怀抱。从这个角度说,乌托邦也就是人类的终极自由,它深深植根于我们的人性之中,任何政治势力都无权,也无力将它终结。
I106.4
A
1003-4145[2012]专辑-0008-03
(责任编辑:宋绪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