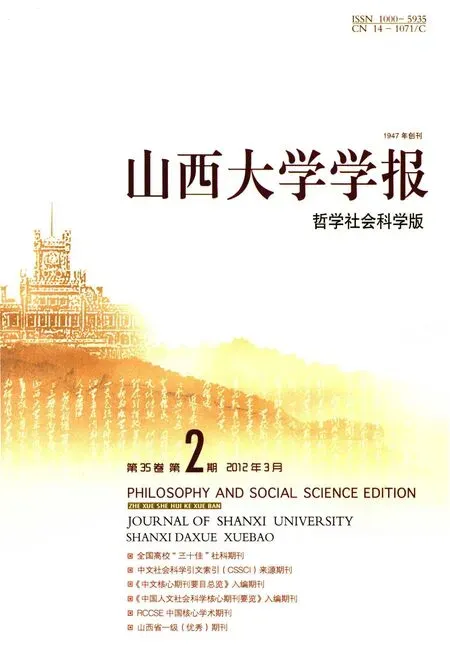印度教复兴改革与印度民族女神的塑造
谢 勇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上海 200241)
一 印度教中女神崇拜及其特征
在印度教的万神殿中,男性主神无疑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吠陀教诸自然之神到印度教的三大精神主神,他们都占据着无以匹敌的显赫地位。然而,因为印度教众神具有类似希腊罗马众神的“神人同形同性”的特征(虽然表现更为复杂和怪异),俗世的阴阳相济就必然在圣界得以体现。同时,印度教把力量归因于妇女,特别是母亲,这自然导致了印度教女神崇拜。[1]因此,众多的女神必不可少,并且从吠陀教诸自然女神到印度教诸精神女神,她们大多作为男性主神的配偶或情人。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女神的诸多面向。一些女神出身高贵,生于圣界,如萨拉斯瓦蒂、普利提维、帕尔瓦蒂、乌莎斯等,而一些女神则生于尘世,如拉克希米、杜尔伽、迦梨等;有些女神是已婚的,如萨拉斯瓦蒂、拉克希米、普利提维、黛维等,有些女神是独身的处女,如杜尔伽、迦梨、乌莎斯等。已婚的女神大多慈善,未婚的女神大多凶暴,这与男性神的慈悲形成对比。同时,同一个女神通过不同化身可以呈现不同的面貌。毗斯诺(Vaisno)和迦梨是女神的两个不同面向,可以粗略描述为温柔和凶狠。印度教万神殿中诸神的区别建立在性别上,男性神一般仁慈,女性神一般凶狠,除非通过婚姻被驯服。[2]221这增加了女神属性的复杂性,也说明在印度教万神殿中女神处于从属和依附的地位。已婚的女神大多贞洁,而处女则多色欲,“毗湿奴偶像象征着拥有女神的神明,而女神装扮优雅,其淫荡的魅力和放荡的面容激发了情欲思想”[3]240,因此常常被印度教信徒作为情人或配偶的想象对象。而杜尔伽和迦梨因为同时呈现仁慈和恶毒两个截然不同的面貌除外。据信,宇宙在迦梨的子宫内,她的皈依者采取了孩子对母亲全方面热爱的态度,但是女神作为死亡和毁灭的象征有另一个可怕的面貌,在象征中她表现为卡利,黑暗者,佩戴着牺牲者滴血的手和人头。[4]215杜尔伽也是如此。所以,呈现慈悲面貌的女神喜欢素食,凶暴女神则喜欢血祭;有些女神出现在吉祥的仪式上,如萨拉斯瓦蒂、拉克希米、帕尔瓦蒂等,而另一些女神则出现在危机仪式上,如黛维、杜尔伽、迦梨等。
除了一些自身的属性外,女神还有一些社会属性。有些女神有偶像,如杜尔伽、迦梨有形象鲜明的偶像,有些女神则没有偶像;有些女神是乡村神,有些属于都市神,而杜尔伽和迦梨则二者兼具;有些女神是地区神,只属于本地信徒,与其他地区的信徒无关,有些女神仅为婆罗门种姓信仰和崇拜,另一些则只能由非婆罗门种姓信仰和崇拜,但是有些女神却属于全体印度教徒,不分地区和男女,如杜尔伽和迦梨。无论印度教女神有多少面向,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夏克提。夏克提是女性性力,是神圣的女性创造力,在印度教中也意味着神圣的力量或权力,是原始宇宙能量,被视为穿越宇宙的动力,是女神独有的力量。信徒崇拜女神事实上就是在崇拜夏克提。对女神(事实上是对夏克提)的专注崇拜极易形成巴克提(Bhakti)①在印度教中指宗教献身的术语,意为虔信,即信徒忘我投入到神圣崇拜中,多使用于一神论的印度教中,笔者注。,一旦投入到巴克提中,信徒就完全进入了忘我境地,处于宗教狂热中。在Seranvali(黛维的化身)崇拜中,重点是夏克提内的巴克提。它能够被称为一种“现世的”巴克提,与“来世的”巴克提相反,在这种巴克提中,世俗和精神的界限被模糊了,即,爱、虔诚和放弃是重要的主题,但是从不与物质满足的渴望分离。在黛维的崇拜中,“隐秘的献身”和“无私的献身”的界限,或者宗教先验的和实践的面向并非一目了然。[5]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巴克提是比较易于形成统一和同一的观念与事实的。“巴克提意识形态包含了印度教传统中的其他所有价值,并且通过将印度教理解为‘一个拥有一致性和统一性的宏伟的建筑’,从而提供了一个综合的框架。”[6]
当然巴克提与女神崇拜并非完全没有差别,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崇拜者对神性的态度。“在传统的Krsna(克里希纳)巴克提中,信徒有各种心态或心境面对克里希纳,包括Madhurya(性爱的情人)、Vatsalya(父子)、Sakhi(朋友)和Dasya(主仆)。用这种类型学标准看,最适于黛维巴克提的是Dasya Bhava(主仆态度),也许其次是父子态度,这是在崇拜小女孩或Kanya(童身)的女神的前提下。有趣的是,在克里希纳的意识形态中,没有将信徒描述为孩子、将神模式化为父母的心态。然而,这是最准确描述信徒与女神的心态,她是母亲,所有信徒都是她的孩子。也许这就是性爱的情人心态明显远离黛维巴克提的原因。将自己视为女神的情人或配偶将破坏乱伦禁忌。[7]159在此基础上,女神就可以避免像过去成为信徒的意念中的情人或配偶,而神圣化为主仆或母子的关系,成为服务与被服务关系,或血亲的长幼互爱关系。印度教复兴改革者正是在此基础上成功塑造了民族女神——母亲和祖国的形象。
二 印度教复兴改革与印度民族女神的塑造
女神观念固着于物质的动力在Sakti Pithas(夏克提所在地,即力量所在)的神话和仪式中得到进一步表达。地球本身作为女神的形象,更特别的是,印度土地作为女神的形象在印度传统中是古老的、普遍的。同样的,像山脉、河流、湖泊和洞穴等某种地理特征是神的显现的观念是一个伟大的遗产。[7]32这些地理圣物已经变成崇拜女神的形象物,当它们和特殊的神或圣人经常联系在一起时,本身就成为神圣的地点。在某个时刻,女神崇拜是与正式的Pithas(所在地,住所,是女神身体的神圣部分)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印度教复兴改革者们在塑造印度民族女神时十分清楚女神形象在印度教徒心目中的象征意义,即地球、土地、丰饶的生产力,最终这些模糊的描述均指向一个具体的高大形象——母亲。
印度最早将女神指称为母亲和祖国的著名人物是邦基姆·钱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rjee)。印度教所谓的偶像崇拜经历了巨大变化,这个过程真正开始于邦基姆·钱德拉,他将大多数流行的印度教女神作为民族进化的不同阶段的象征。[8]36他使用卡利(母亲女神)作为祖国的象征,并且在小说《Anandamath》中表明印度教的Sannyasa制度(弃绝世俗生活追求解脱)能够获得关于弃绝概念的新意义,即为了民族服务而不是个人解脱。[9]邦基姆·钱德拉关于女神——祖国的描述,在印度引发了深刻的政治思索。“在那个时期的文学史中,你们会发现孟加拉的光荣。孟加拉被升华为母亲。杜尔迦只是孟加拉的人格化。”[10]57另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女神崇拜的集中化趋向,即专注于杜尔伽和迦梨女神,这是因为两个女神完全符合印度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的要求。首先,她们纯洁、独身;其次,她们具有普遍化特征,属于不同种姓、地区的所有印度教徒;第三,她们都能够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慈悲和凶暴,吉祥和危机。而印度也正需要这种对信徒慈悲,能够出现在民族的吉祥仪式中,同时对敌人凶暴,也能够出现在民族的危机仪式中的女神。因为在邦基姆·钱德拉看来,印度此时对英国殖民者剩下的只有愤怒了。“就像在《Durga Mahatmyam(杜尔伽的光荣)》中所描述的,女神唯一可以辨识的情绪是愤怒——黝黑,无情和嗜血。她是从至高神处浮现的女神。她是他们的愤怒。”[2]221对迦梨和杜尔伽女神的崇拜被后来的民族主义者所承袭,甚至独立后仍然如此。
然而,政治思考并没有立即转化为切实的政治行动。印度大起义后的印度殖民政府给予了印度更多的政治让步,导致印度民族主义者与殖民者进入了一段“政治蜜月期”,直到孟加拉分治运动方才结束。1905年,印度总督寇松的孟加拉分治是印度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英印的不平等的“蜜月”结束,对抗政治代替了合作政治。国大党的温和派逐渐失去了垄断地位,甚至一度让位于激进派。这个时期的政治运动的另一个特征和本质是印度作为母亲女神的光荣,这与向许多神与女神祈祷的印度教实践相关。激进派提出了印度自治的政治主张,并进行了大量鼓动印度教群众的运动,利用印度教作为宣传手段,印度教民族主义由此诞生。“向母亲致敬Bande Mataram”是他们的口号,而母亲就是祖国印度,并且迦梨和杜尔伽女神则是其化身。孟加拉的恐怖主义集团是这次运动的先锋,而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 Ghosh)是其核心领导人。
奥罗宾多将印度教思想与民族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国家,土地是民族唯一的外部实体,是其Annamaya Kosh,是全部肉体;大众,成百万居住在民族实体并使其活跃的人是Pranamaya Kosh(民族的生命体)。这两个都是Gross Body(粗身),是母亲(祖国)的物质显现。”[11]141他认为要唤醒印度民族的主体印度教徒,必须从印度教文化中寻找力量。“现在必须唤醒的不是英国化地区的人民,西方驯服的学生,这将注定重复欧美成败的循环,而是必须唤醒古代不朽的夏克提,恢复其最深刻的自我,达到光明和力量的最高来源,并且致力于发现其达摩的完全意义和更宏大的形式。”[11]157奥罗宾多在他的消极抵抗和革命的计划中渴望动员孟加拉社会中的各个集团,他利用民族主义的宗教理论,特别是利用夏克提象征主义,利用印度教卡利崇拜的肖像,并且采用民族主义哲学证据(这是基于现代主义者,商羯罗吠檀多哲学的新印度教解释)。民族被描述为卡利女神的化身,并且民族主义者被视为她的献身者。[12]奥罗宾多的政治吠檀多与韦维卡南达的行动吠檀多十分相似,只是他的哲学被更明确地应用于政治行动。奥罗宾多把韦维卡南达的新吠檀多概念(神是人类灵魂的集合)发展成为一个更复杂的理论(神是个人、总体人类和人类共同体的化身),因此,他提倡这个概念,民族本身是神的化身,即卡利女神。
奥罗宾多对夏克提象征主义的使用和政治吠檀多理论得到了孟加拉杰出的激进政治家的回应。比平·帕尔(Bipin Pal)(孟加拉极端主义派的第二个最重要的领导人)也强调夏克提象征主义,尽管他的宗教背景是毗湿奴派。[12]他清楚地认识到民族主义化的印度教神明对印度政治革命的重要性。[8]38当比平·帕尔赞扬迦梨女神的时候,他“继承了罗伯斯庇尔的传统,将美德和恐怖结合起来”[13]14。他几乎完全使用夏克提象征定义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恐怖主义的宗教象征主义主要是夏克提,而不是Jugantar偶尔提到的克里希纳参加马哈拉施特拉战争的毗湿奴传统,这是为了创造Dharmarajya(正义王国)来为印度自由进行民族主义斗争的目的服务。[14]200女神也被视为暴力和革命的象征,死亡和毁灭的象征,这是再生必需的,革命的暴力行为据说是母亲神圣的演出。[15]对卡利和杜尔伽的传统的山羊和水牛的动物祭祀给革命以宗教的象征意义,革命被召唤,以在祖国母亲面前牺牲压迫者和他们自己的鲜血来把她从羞辱和堕落中解脱出来。[16]101-102用于孟加拉反对分治运动中的宗教习语来自于对湿婆配偶夏克提的崇拜。在这个崇拜中,湿婆是永恒不变的神源。在湿婆的宇宙展示或者行动原则中的夏克提形成了一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善与恶,生与死,创造与毁灭似乎是真实的。杜尔伽通常拟人化为夏克提的仁慈方面,就像在她与魔鬼宇宙战争的著名传说中一样,这象征着对邪恶力量的征服。[4]190-193
奥罗宾多之后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迅速发展,最终成为与印度民族主义分庭抗礼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他们在民族女神的塑造和深化上甚至没有跃出孟加拉分治时期形成的阶段,或者可以这样说,奥罗宾多及极端主义领导人已经完成了民族女神的塑造。日后的印度教领导人更多的是在实践民族女神观念,女神已经完全幻化成印度祖国母亲,他们宣传和团结印度教群众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民族国家献身,即使提出了“印度教特性”的最著名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领导人萨瓦卡尔(Vinayak Damodar Savarkar)也不例外。在萨瓦卡尔看来,夏克提就是印度教的武器,迦梨就是象征。[17]369随着政治思想的逐渐成熟,在萨瓦卡尔的观念中,偶像的民族女神完全变成了崇高的民族国家。在其著名的《1857年印度独立战争》中,他大声疾呼:“印度母亲从沉睡中苏醒,冲上去摧毁奴隶制度。”[17]518作为印度教徒,即印度民族国家的成员,应该为祖国奋斗,忍受苦难。“以那些因为呐喊‘母亲万岁和Hindusthan Hinduonka(India for Hindus)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被鞭打或者被警棍殴打的印度教统一者为例。他们在警棍打击下继续呼喊‘母亲万岁’和‘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许多勇敢的人死在折磨之下。”[17]276对萨瓦卡尔而言,这些爱国的印度教徒的整个生命都弥漫着对母亲的神圣之爱的存在意识,在印度教特性的序列中肯定有其应有的地位。“由种族、血统、文化和民族性构成的人们拥有几乎所有印度教特性的要素,并且被暴力赶出我们的起源地——只要你全心全意地热爱我们共同的母亲,将她不仅视为祖国(Pitarbhu)而且视为圣地(Punyabhu),你就会被接受为印度教徒。”[17]536印度独立后,印度母亲女神崇拜得以延续。
世俗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也接受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关于印度女神—迦梨和杜尔伽—母亲—祖国(民族国家)的逻辑。哈尔·比拉斯·萨尔达(Har Bilas Sarda)在一次集会上号召为印度女神、印度母亲牺牲,实现解脱:“在高尚的理由中有价值地死去或者‘让母亲的乳汁显出光辉’是他们的渴望。”[18]8甘地完全接受了“向母亲致敬”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口号:“那么,当我们反对所谓的法律和秩序的支持者的侵犯而保证正义的统治时,我们的时刻就到了。在观念的推动下,我反对孟加拉政府侵犯我们的结社权利,并且违反我们‘向母亲致敬’的信念。”[19]89这样的态度甚至引起了印度穆斯林的反弹,他们的领袖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们命令或者允许在所有公共场合吟唱向母亲致敬之歌,恢复印度教主权的象征和憎恨穆斯林。甚至国大党统治的省份的一些集会用向母亲致敬之歌作为开始程序。”[20]129-130
三 印度民族女神塑造的影响
印度教民族女神的塑造是印度教近代历史中的一次伟大创举。在纷繁的印度教万神殿中形成共同朝圣、共同崇拜是相当困难的,从数世代的印度教复兴改革的成败可见一斑。印度女神—迦梨和杜尔伽—母亲—祖国(民族国家)的模式,即女神、杜尔伽和母亲,变成与国家同一,而国家则是更大的女神和母亲,对于在印度教群众中形成平等观念、统一观念、民族国家观念,形成共同体意识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正如一个女神的崇拜者所说的,“在母亲的宫廷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7]77对女神的朝圣可以让信徒产生共鸣,产生最初的共同体意识。朝圣者离开他们熟悉的俗世家园而冒险到神圣地带,在这里能够更直接地与女神交流,仪式活动承担了更强烈的中介特征。就像维克托·特纳(Victor Turner)指出,去朝圣也有启蒙性质,在圣地,朝圣者从熟悉的地方到陌生之地,重新融入熟悉的环境,这是在经历一个转变。在圣地花费的时间类似于启蒙的“阈限”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的通常规范暂停,朝圣者经历了与其他朝圣者的“同感”。[21]166-230在圣地,人们有机会与其他类型的人相遇和融合。这些人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联系,地位和等级被暂时搁置一旁。在一个团体中,像这样的圣地中,……座位与种姓无关。女神神庙在任何时候都有低等种姓的顾客,神庙从未拒绝不可接触者。朝圣者经历了统一和友情的感觉。[7]77在这里,宗教的等级差异消除了,甚至那些通常不与低种姓共餐的高种姓印度教徒在德维的Langar(共餐仪式)中也是如此,因为女神的神性是纯洁的,不会被污染。[7]77这是因为在女神神学中隐含着一种共同因素。“暗含在女神神学中的是一种一元论。物质和精神在这种一元论中虽然存在差异,在夏克提(活跃的女性创造之源)中却是一致的。然而,与男性神湿婆和毗湿奴相关的湿婆和毗湿奴神学都认识到夏克提是神性的积极面向,是对不积极面向的补充,性力派神学将与伟大女神同一。夏克提理解为最终实在本身和所有实在的整体性。”[7]31
事实上,民族女神的实践的确推动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激发了印度教群众献身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情,成员把自己看做年轻的Sannyasin(放弃家庭和职业去服务卡利女神象征的民族)一员。[22]25在给年轻干部开始任何使命的理论和勇气前,常常是先给予卡利女神以牺牲。[22]27同时,民族女神在动员各个种姓投身祖国自由斗争中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孟加拉反分治运动时期,激进领导人为了在农村高等种姓中制造统一意识而利用夏克提象征主义。高等种姓作为一个整体是夏克提,他们接受吠檀多哲学观,因此,奥罗宾多的政治吠檀多被解释为将受过英语教育的精英的民族主义观与宗教象征和吸引农村高等种姓的制度整合起来的企图。很明显,他想在政治上动员地主,以及利用他们在农村中的影响获得耕种者的支持,或者至少是默许。[12]尽管新的受过英语教育的精英在19世纪晚期发展了一个单独身份并且凝聚成一个集团,这个精英的成员在农村地区保持与低等种姓的联系也是事实。受过英语教育和农村高等种姓集团的重要沟通渠道之一是一个共享的宗教取向。
[1]David Smith.Hinduism And Modernity[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x.
[2]Lawence Babb.The Divine Hierarchy:Popular Hinduism In Central India[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
[3]Swami Dayanand Saraswati.The Light Of Truth[M].New Delhi:Sarvadeshik Arya Pratinidhi Sabha,1984.
[4]Heinrich Zimmer.Myths And Symbols In Indian Art And Civilization[M].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46.
[5]Mandelbaum David G.Introduction:Process and Structure in South Asian Religion[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66,68:1174-1191.
[6]Mandelbaum David G.Toward a coherent study of Hinduism[J].Religious Studies Review,1983,9(3):207.
[7]Kathkeen M Erndl.Victory To The Mother:The Hindu Goddess Of Northwest India In Myth,Ritual,And Symbol[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8]Bipin Chandra Pal.The Spirit Of Indian Nationalism[M].London:The Hind Nationalist Agency,1910.
[9]Bankim Chandra Chatterjee.Anandamath[M].Bengali By Aurobindo And Barindra Ghosh.Trans.Calcutta:Basumati Sahitya Mandir,1907.
[10]Das C R.India For Indians[M].Madras:Ganesh&Co,1917.
[11]Sri Aurobindo,Peter Heehs.Nationalism,Religion,And Beyond:Writings On Politics,Society,And Culture[M].Delhi:Permanent Black,2005.
[12]Barbara Southward.The Political Strategy Of Aurobindo Ghosh:The Utilization Of Hindu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Bengal[J].Modern Asian Studies,1980,14(3):353-369.
[13]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M].范慕尤,杨 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14]Majumdar B.Militant Nationalism In India[M].Calcutta:General Printers And Publishers,1966.
[15]Rowlatt Sedition Report[R].Calcutta,1918:67,Ix.
[16]Kali Charan Ghosh.The Roll Of Honour:Anecdotes Of Indian Martyers[M].Calcutta:Vidya Bharati,1965.
[17]Vinayak Damodar Savarkar.Selected Works Of Veer Savarkar:4vol[M].Chandigarh:Abhishek Publication,2007.
[18]Har Bilas Sarda.Speeches And Writings[M].Ajmer:Vedic Yantralaya,1935.
[19]Gandhi M K.The Pilgrims’March:Their Messages[M].Madras:Ganesh&Co,1921.
[20]Khan Durrani F M.The Meaning Of Pakistan[M].Lahore:Sh.M.Ashraf,1944.
[21]Cf.Victor Turner.Dramas,Fields,And Metaphors:Symbolic Interaction In Human Society[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
[22]Jogesh Chatterji.In Search Of Freedom[M].Calcutta:K L.Mukhopadhyay,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