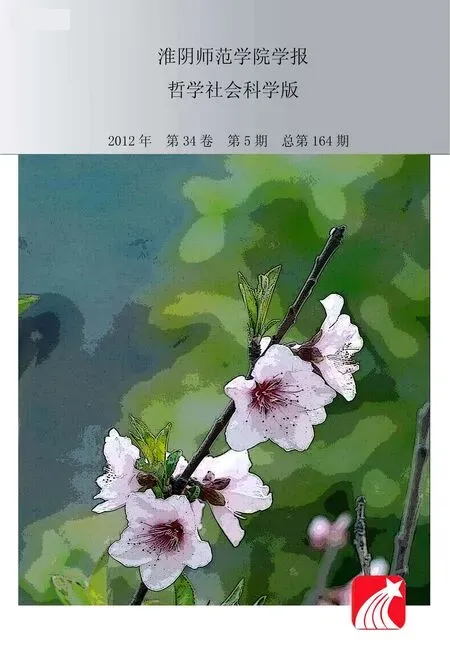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校勘发微
杜甫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之一。早在宋代,即有众多学者对杜诗进行辑佚、校勘、辨伪和注释工作。元、明两代,杜集鲁鱼亥豕,讹误窜夺的情况已非常严重。到了清初,随着杜诗热和注杜的兴起,注家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对杜诗文字进行正本清源的是正考异。朱鹤龄在继承前人校勘成果的基础上,集腋成裘,取精用弘,对杜诗文字校勘作出了杰出贡献。
朱鹤龄(1606—1683),字长孺,自号愚庵,吴江松陵人,明末诸生。入清后绝意仕进,以笺注为业。一生著述等身,被《四库全书》所著录者有《尚书埤传》、《禹贡长笺》、《诗经通义》、《读左日钞》、《李义山诗集注》、《愚庵小集》六部著作。他是明清之际江南遗民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李颙、黄宗羲、顾炎武并称“海内四大布衣”,是清初著名的经学家和乾嘉学派的先驱之一。他的《杜工部诗集辑注》(以下简称《辑注》)是清初最著名的杜注之一,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本文拟就其校勘方面初献刍荛,求正方家。
一、底本和校本
关于《辑注》的底本,朱鹤龄在卷首交代:“愚素好读杜,得蔡梦弼草堂本点校之,会萃群书,参伍众说,名为《辑注》。”[1]卷首识语选用宋代著名的注本之一蔡梦弼《草堂诗笺》作为底本,而参校他本。宋代杜注虽多,但大多为集注本,质量不高。蔡注为宋代三个单家注本之一,作为底本是合适的。
关于校本,《凡例》第三条曰:“集中讹字最多,朱子欲如韩文作考异而未果。今遍搜宋刻诸本及《文粹》、《英华》对勘,夹注本文之下,以备参考。”所谓宋刻诸本,即朱氏“得阅其全注”的另外两家赵次公、黄鹤注本,以及吴若本;总集有宋人的《唐文粹》、《文苑英华》。吴若本是《辑注》参校的一个宋本,但情况较为特殊。从源流上看,它是与杜诗祖本二王本最为接近的本子,大体保存了二王本的本来面目①参见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前言”的考证及第14页《赵注宋代源流示意图》。。二王本久佚,故吴若本价值不言而喻。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白文本,突出特点是面目清净,除了为数不多的“公自注”,它是没有注释的。加之它当初编校时占有资料有限,刻成后又流传不广,因此几乎没有遭到臆改和窜夺,又悄悄躲过了元明两代的污染,一直到清初为钱谦益获得。第二,它在杜诗校勘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个系统。它以“樊作”、“刊作”、“晋作”、“荆作”、“一作”等标明杜诗异文来源的做法,为后世注家效仿,从南宋的蔡梦弼,到清代的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杨伦,各家注本均采用这种做法,可见影响之巨。但吴若本的缺点也毋庸讳言,即它只是简单的对较和罗列,取舍方面没有吸取丰富的考辨成果。朱氏与钱谦益有过一段合作注杜的时期,从吴若本中迻录了大量异文。另外,钱谦益还藏有蔡梦弼《草堂诗笺》高丽刻本,如《信行远修水筒》“何假将军盖”,“盖”字高丽刻本作“佩”,亦为《辑注》吸纳[1]517。
其实还不止这些,《辑注》对宋代姚宽《西溪丛语》、龚颐正的《芥隐笔记》、陈岩肖《庚溪诗话》、程大昌《雍录》、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等笔记也多有取资,如《芥隐笔记》“杜诗古今本不同”条曰:“王仲言自宣城归,得杜甫诗三帙,有南唐澄心堂纸,有建邺文房印、沈思远印及勅赐印,笔法精妙,殆能书者。试考一二诗,多与今本不同,《如忆李白》诗:‘白也诗无数,飘然意不群。清新庾开府,豪迈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话斯文。’”今《辑注》“白也诗无敌”,“敌”下注:“《芥隐笔记》云:南唐本一作‘数’”;“俊逸鲍参军”,“俊逸”下注:“芥隐云:一作豪迈”[1]35。吸收了《芥隐笔记》关于此诗的两条异文。可以说,朱氏最大限度搜集到各种杜诗宋本,为杜诗校勘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继承与别裁:正文和“公自注”的校勘
《辑注》的校勘内容,相对而言可分为继承宋人校勘成果和自己的考证两个部分。
宋人校勘又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吴若本的所谓“樊作”、“刊作”、“晋作”、“荆作”等,这些在《辑注》中基本保存。二是宋注和宋人考证。宋注以赵注为主,如《北征》“惨淡随回纥”,下标异文:“一作鹘”,《辑注》:“赵曰:‘随回鹘’,当以‘回纥’为正。德宗元和四年,始请易号回鹘,言捷鸷犹鹘然。”[1]147赵次公的校勘多结合诗意、史实、文献、音韵、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考镜源流,思虑缜密,体现了精湛的校勘艺术①参见武国权《赵次公〈杜诗先后解〉研究》第二章第三节《杜诗校勘》(硕士论文)。,故多为《辑注》继承。《秋兴八首》其五“几回青琐点朝班”,“点”下注:“一作照,非。”则引用宋代著名学者楼钥的考证:“楼钥曰:点与玷通,古诗多用之。束皙《补亡》诗:鲜侔晨葩,莫之点辱。陆厥《答内兄》诗:复点铜龙门。杜诗‘几回青琐点朝班’正承用此也。”[1]530这些引用,其实也暗含了朱氏的辨析。
杜诗三千五百多处异文,朱氏几乎均作一一辨析,最为精彩的是朱氏别出心裁的考证部分。这些考证按内容的性质,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一)依照史实。1、《过宋员外之问旧庄》“零落首阳阿”,“首”字下注:“旧作守,误。”《辑注》曰:“按《新书》:‘之问,汾州人。’《旧书》则云:‘虢州弘农人。’首阳与虢州相邻,故有庄在焉。赵次公引河东蒲坂之首阳,误矣。”[1]82《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得云字》,“补阙”,一作“遗补”。《辑注》曰:“时贾至为中书舍人,严武为给事中。两院,谓拾遗、补阙也,作‘遗补’是。”[1]1403《石犀行》“嗟尔三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三”字下注:“蔡云当作五。”《辑注》曰:“按《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水经注》、《成都记》,皆云李冰作犀牛五头,后来止二犀可考,其三头已不存,所谓‘缺讹只与长川逝’也,缺,损其数;讹,易其处也。”[1]282
(二)依照地理。1、《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秦山忽破碎”,“秦”字下注:“一作泰。”《辑注》曰:“秦山,谓终南诸山。登高望之,大小错杂,如破碎然。泾渭二水从西北来,远望则不可求其清浊之分也。黄鹤本作‘泰山’,引宣和间樊察《序雁塔题名》为证,谬矣。”[1]392《喜达行在所三首》“莲峰望忽开”,“莲峰”下注:“《英华》及《正异》俱作‘连山’。”《辑注》曰:“按公自金光门出,西归凤翔,不应走华阴道,当以‘连山’为正。”[1]1273《柴门》“巨渠决太古”,“巨”字下注:“黄作巴”(黄指黄鹤本)。《辑注》曰:“按‘巨渠’恐当作‘巴渠’。”《水经注》:‘清水出巴渠县东北巴岭南獠中,即巴渠水也。西南流至其县,又西入峡。’又曰:‘巴渠水南历檀井溪之檀井水,下入汤溪水,汤溪水又南入于江,名曰汤口。’夔州居荆蜀之中,吴盐、蜀麻所会。”[1]631按三例考证,精审可据。《四库提要》评价朱氏《禹贡长笺》“旁引曲证,亦多创获”,亦肯定其地学造诣,可谓的评。
(三)依照训诂。1、《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章罢凤鶱腾”,“鶱”字下注:“一作骞,非。”[1]21又《赠比部萧郎中十兄》“风雅蔼孤鶱”,“鶱”字下注:“他本作骞,误。”《辑注》曰:“按骞、鶱,音义各不同。骞,去乾切,马腹热。鶱,虚言切,飞貌。”[1]342《九日寄岑参》“所向泥活活”,“活活”一作“浩浩”。《辑注》曰:“《诗》注:活活,水流声。”[1]773《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旌旂日暖龙蛇动”,“旂”字下注:“俗作旗,非。”《辑注》曰:“《周礼》:交龙为旂。《释名》:旂,倚也。画作两龙,相依倚也。”[1]156
(四)依照出处。有时异文皆无明显格碍之处,若寻得杜诗用字出处,自然最佳,此校勘甚难者。如《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燃脐郿坞败,握节汉臣回”,“握”一作“秃。”《辑注》曰:“《竹坡诗话》: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书少陵诗一卷,如‘握节汉臣回’乃是‘秃节’,‘新炊间黄粱’乃是‘闻黄粱’。杨慎曰:《后汉张衡传》:‘苏武以秃节效贞。’公正用此。”[1]126此处引用宋人周紫芝的记载,又引明杨慎的考证,似乎凿凿可据,但朱氏终觉不妥,《杜诗辑注·补注》曰:“‘秃节’虽有据,按《左传·文三年》:‘司马握节以死,故书以官。’作‘握节’为正。”[1]126此处考虑了出处,其实也兼顾了对仗,“握”对“燃”,皆动词。此前后的改易斟酌,可见校勘之不易。
(五)依照杜集。此即所谓的本校。1、《郑典设自施州归》“登顿入天石”,“石”字下注:“他本作矢,非。”《辑注》曰:“入天石,言石势之参天也。公《瞿唐》诗‘入天犹石色’可证。旧本讹作‘矢’,须溪云:‘暗用李广射石没羽事。’此喜新之见,笺杜诗正不宜尔。”[1]7062《陪李金吾花下饮》“细草称偏坐”,“偏坐”下注:“一作偏称。”《辑注》曰:“公尝使‘偏劝’、‘偏醒’、‘偏秣’,此云‘偏坐’,言偏宜于此坐也。”[1]62这些细微的区别,若非熟稔杜诗,是难以考订的。
(六)综合校勘。有时一字之勘定,需要结合多种因素综合考虑,而每位注家学识有深浅,所据有异同,故见仁见智,聚讼纷纭。但朱氏往往广征博引,考据翔实,如下两例。1、《游龙门奉先寺》“天阙象纬逼”,“阙”字下注:“《正异》作窥。”《辑注》曰:
《庚溪诗话》:“按韦述《东都记》:‘龙门号双阙,以与大内对峙,若天阙然。’此诗‘天阙’,指龙门也。王荆公谓对属不切,改为‘天阅’。蔡兴宗《正异》谓世传古本作‘天窥’,引《庄子》‘以管窥天’为证。皆臆说。”杨慎曰:“古字‘窥’作‘闚’,天闚、云卧,乃倒字法耳。闚天则星辰垂地,卧云则空翠湿衣,见山寺高寒,殊于人境也。”按用修之说,盖主兴宗。然《丹阳记》载王茂弘指牛头山两峰为天阙,见《文选注》;禹疏伊水北流,两山相对,望之若阙,见《水经注》,皆确据也。况此本古体诗,何必拘拘偶对耶?[1]1
其实“阙”字异文有八种①详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游龙门奉先寺》附考。,朱氏仅就最似合理、影响最大的两种驳之。山谦《丹阳记》有“天阙”之说,《水经注》亦喻山为阙,可见“天阙”早有所本。此处考证从史书、地理和诗律方面综合考证当为“阙”字,确凿无疑。2、《投简梓州幕府兼简韦十郎官》“幕下郎官安隐无”,“隐”字下注:“一作稳。”《辑注》曰:
按《说文》:“隐,安也。”义与“稳”通。《通鉴》:“玄宗遣中使至范阳,禄山踞床不拜,曰:‘圣人安隐?’”注:“隐,读曰稳。”又唐帖多写“稳”为“隐”,作“隐”正得之。[1]387
这个考证也十分精彩,从训诂、史书和法书实物三个方面考定“隐”字。
杜甫的自注,也叫“公自注”,包含不少问题,成因较为复杂,既有传抄刊刻的错误,也有注家引用时将旧注和杜甫自注混为一体导致的错误,更有注家伪造自注以自圆其说的情况,因此《辑注》对“公自注”十分谨慎,细心辨析。《凡例》曰:“千家本公自注语,向疑后人附益,考之多王原叔、王彦辅诸家注耳,未可尽信。今取类于公注者,以原注二字系之,旧本所无俱削去,其旧云自注而千家本不载者特标数则。”方法主要有:(一)依据善本。如《八哀诗》之《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慷慨嗣真作”,《辑注》曰:“是言邕与公论及审言诗而叹伏之,非指历下亭唱和之作也。《千家注》本此句下有公自注‘甫有和李太守诗’。考旧善本俱无之,今削去。”[1]565(二)依据史实。如《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得溪字》,九家本、阙名千家本题下有所谓“公自注”曰:“池在府内,萧摩诃所开,因是得名。”《辑注》曰:
《元和郡县志》:“摩诃池在州城西。”《通鉴注》曰:“《成都记》云:‘摩诃池在张仪子城内,隋蜀王秀取土筑广子城,因为池。有一僧见之,曰:摩诃宫毗罗。盖胡僧谓摩诃为大宫,毗罗为龙,谓此池广大有龙,因名摩诃池。’”或曰萧摩诃所开,非也。池今在成都县东南十二里。[1]455
这里辨明“摩诃”乃梵语而非人名,则所谓“公自注”显系后人附会添注。(三)综合考虑。如《对雪》“有待至昏鸦”,旧本该句下有“公自注”:“何逊诗‘城阴度堑黒,昏鸦接翅归’。”《辑注》曰:“按二语今《何记室集》不载。公《复愁》诗‘钓艇收缗尽,昏鸦接翅归’,不应直用成句,且昏鸦亦常语,何独于此释之?必出后人假托。今流俗本所云‘公自注’者,多此类也。”[1]814此例综合考虑了文献、诗歌内容及自注的一般规律,驳斥有力。
《辑注》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联绵字。联绵字由两个音节连缀而成,每个音节不能单独表示含义,一般没有固定的写法,如“踌躇”可以写成“踟躇”,也可写成“踯躅”,这是汉语独有的语言现象,但古人对此并不十分理解,所以《辑注》在这方面徒然花费了不少笔墨,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乐动殷胶葛”,“胶葛”下注曰:“旧作樛嶱,荆公、欧公定为胶葛。《正异》作嶱嵑。”[1]104又如《醉歌行》“春光潭沱秦东亭”,“潭”字下注:“一作澹。”《辑注》:“《江赋》:随风猗萎,与波潭沱。善曰:潭沱,随波之貌。富嘉谟《明水篇》:春光潭沱度千门。”[1]60实际上此类正文、异文的考辨意义不大。相反有时却错过了勘定的机会,如《义鹘行》“飘萧觉素发,凛欲冲儒冠”,“欲”字下注曰:“一作烈。”[1]174其实“凛冽”是双声词,对叠韵词“飘萧”,十分妥帖。检宋各本以及《钱注杜诗》、《杜诗详注》,亦无一本以“烈”为正,说明这是古代一个普遍的问题。另外《辑注》也存在少数的漏校、误校现象,兹不举例。
三、成就与影响
朱鹤龄《杜诗辑注》是清代第一个对杜诗进行全面校勘的注本①较《杜诗辑注》稍早出版的钱谦益《钱注杜诗》基本以吴若本为主。参见邓绍基《关于钱笺吴若本杜集》,《江汉论坛》1982年6期。,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客观而言,宋人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如大多异文均在宋本中有所著录,考辨也取得很大成绩,为其提供了借鉴的基础。就主观而言,一是重视。朱氏《辑注》目的是要提供世人一个正本清源、简洁无误的杜注本,所以他在清理杜诗文字方面不遗余力,许多注文就是关于一字一词的斤斤考辨。二是勤奋和认真。朱鹤龄大概是杜诗学史上对杜诗文字用力最勤且最认真的注家,他广泛搜集杜诗宋本,认真核对,注明来源,比较优劣。钱谦益说他“订一字如数契齿”[2],确非虚语。一般认为,宋人校勘用力甚勤,清人校勘既勤且精,是不无道理的。三是学、识、才。校勘的最终目的是保证文字的正确或少误,没有学识才,不免空谈。朱氏是清初著名的经学家,精通文字、音韵、训诂,对史学、地学亦甚有造诣,本人又擅文词,《愚庵小集》是被《四库全书》著录的清代少数文集之一。因此他在校勘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实非偶然。
朱氏的校勘成果为仇兆鳌《杜诗详注》所继承。仇兆鳌评价朱鹤龄《杜诗辑注》曰:“坊本多字画差讹。蔡兴宗作《正异》,朱文公谓其未尽,当时欲作考异,未暇及也。近日朱长孺采集宋元诸本,参列各句之下,独称详悉。”[3]仇氏除了对少数的校勘表示异议外,几乎完全以《辑注》为文本。《详注》面世后,因其考据精审,资料广博,号称杜注集大成。其实除校勘外,在年谱、编年、考证、笺评等诸多方面,《辑注》也是《详注》最主要的依据对象,当然这非本文讨论的范围。《详注》成为今日的通行本,《辑注》功不可没。
钱谦益的著作在乾隆期间遭到禁毁,《杜诗辑注》因冠钱序而阑入抽毁之目,除了乾隆间金陵三多斋的一次翻刻,一直若有若无地存于天壤之间。直到上世纪30年代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详细介绍了钱、朱的注杜之争,《杜诗辑注》才逐渐回归人们的视野,但大多学者也只是依据《杜诗详注》得以窥其一斑。本文所举的有些例子,因《详注》未引,就不为人知。直到1976年日本吉川幸次郎编辑《杜诗又丛》本,据万卷楼刻本影印,由日本中文出版社出版,《杜诗辑注》逐渐扩大影响。2009年3月,韩成武先生据康熙间金陵叶永茹万卷楼刻本和中科院藏本点校,由河北大学出版社排印出版,此部巨著才正式面世。细细对照阅读,方知此书校勘的巨大成就,不仅此著之不朽也。杜诗自杜甫身后至清初《杜诗辑注》付梓刊刻,历经整整九百年(770—1670),虽有众多学者为之甄别校勘,辛勤不懈,然谬误如扫落叶,旋扫旋生,至朱氏始以其渊博之学识和翔实之考据,集历代之大成,存真汰伪,定于一尊,沾溉学林,功莫大焉。
[1]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
[2] 钱谦益.吴江朱氏杜诗辑注序[M]//杜工部诗集辑注:卷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
[3] 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M].北京:中华书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