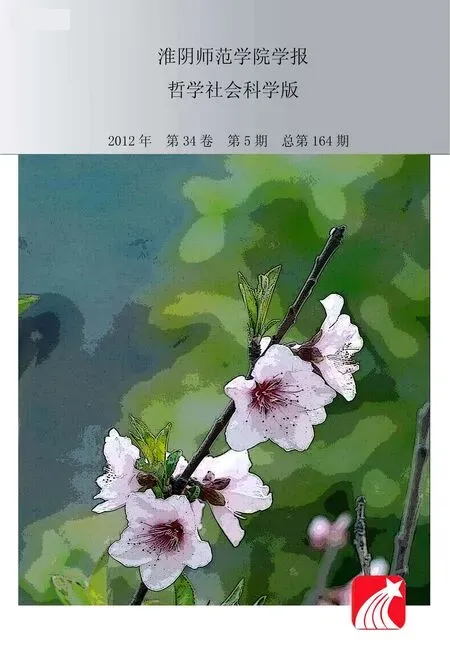诗僧齐己及其论诗诗
朱大银
(巢湖学院中文系,安徽巢湖238000)
齐己(864—943?),俗姓胡氏,名得生,长沙人。《宋高僧传》卷三十:“秉节高亮,气貌劣陋。幼而捐俗于大沩山寺,聪敏逸伦,纳圆品法,习学律仪。而性耽吟咏,气调清淡。有禅客自德山来,述其理趣,己不觉神游寥廓之场。乃躬往礼讯,既发解悟,都亡朕迹矣。”曾栖居长沙道林寺和庐山东林寺。后梁龙德元年(921)后,受荆州节度使高从海挽留,一直居龙兴寺。齐己为唐末五代著名诗僧,与当时诗人如贯休、虚中、曹松、李洞、方干等交游。与诗人郑谷酬唱尤勤,今集中有《和郑谷郎中看棋》、《乱中闻郑谷吴延保下世》、《永夜感怀寄郑谷郎中》、《寄郑谷郎中》等唱和诗共十八首。齐己是苦吟诗人,写诗尚琢炼,但不入僻涩一途。五代人孙光宪评其诗曰:“趋尚孤洁,词韵清润,平淡而意远。”[1]所作诗由门人编为《白莲集》十卷。齐己又是晚唐五代著名诗论家之一,著《风骚旨格》一卷,又《玄机分明要览》一卷(今佚)[2]。
齐己《贻惠暹上人》诗曰:“经论功余更业诗,又于难里纵天机。”[3](谨按:本文所引齐己诗均出自《全唐诗》,下文不再注出)所谓“业诗”云者,当然不仅仅指写诗,同时还包括读诗及论诗。在唐代缁流诗人当中,齐己可谓是对诗歌思考最为殷勤的一位,不仅留下《风骚旨格》诗话一卷,而且他的论诗诗无论质、量都大有可观之处。通观齐己的诗作,其论诗诗主要有《山中答人》、《谢王秀才见示诗卷》、《览延栖上人卷》、《还黄平素秀才卷》、《寄郑谷郎中》、《贻王秀才》、《逢诗僧》、《因览支使孙中丞看可准大师诗序有寄》、《吊杜工部坟》、《谢武陵徐巡官远寄五七字诗集》、《读李贺歌集》、《读李白集》、《谢荆幕孙郎中见示乐府歌集二十八字》等,另外还有不少散见的论诗诗句也包含了丰富的诗论内容。
齐己论诗主要从两个方面立论,即诗教与禅理,下面分别论述之。
一、从诗教立论
所谓从诗教立论就是以儒家诗学理论为出发点,发扬自《诗大序》以来的诗统观点。受儒家思想影响,齐己写了不少颇具诗教价值的作品,尤其是他的乐府体诗如《猛虎行》、《西山叟》、《苦热行》等都沉痛地披露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很具有白居易等中唐诗人“新乐府运动”诗歌的讽喻精神。就齐己论诗诗来说,其内容包括相辅相成的三个侧面:
(一)推举“风雅”。
齐己《君子行》诗:“圣人不生,麟龙何瑞?梧桐不高,凤凰何止?吾闻古之有君子,行藏以时,进退求己;荣必为天下荣,耻必为天下耻;苟进不如此,退不如此,亦何必用虚伪之文章,取荣名而自美。”这里齐己倡导为诗为文不“取荣名而自美”,要发扬圣人之道,就是要求诗歌要继承“风雅”传统。齐己论诗举“风雅”不遗余力,其《风骚旨格》论诗首标“六诗”:一曰大雅,二曰小雅,三曰正风,四曰变风,五曰变大雅,六曰变小雅;他称赞陈陶诗说:“一室贮琴尊,诗皆大雅言。”(《过陈陶处士旧居》)称赞宋杜诗说:“宋杜诗题在,风骚到此真。”(《游道林寺四绝亭观宋杜诗版》)其他如“满箧新风雅,何人旧岁寒”(《赠卢明府闲居》),“取尽风雅妙,名高身倍闲”(《酬尚颜》),“同流有谁共,别著国风清”(《送彬座主赴龙安请讲》)等诗句都可见出齐己论诗对“风雅”的推重。
齐己身处乱世,到处满目疮痍,对“风雅”的推重,是齐己从儒家思想出发,发而为诗教呼声的。齐己的诗教动机与他对世道丑恶一面的态度是互为表里的,他在《自题》诗中说:“未尝将一字,容易谒诸侯。”可见他与权贵公侯是格格不入的,原因是齐己厌恶他们的贪得无厌,齐己把他们比作只会吞钱的“扑满子”:“只爱满我腹,争知满害身?到头须扑破,却散与他人。”(《扑满子》)不仅刻画形象而且入木三分。
(二)对当代“风雅”诗人的赞叹与哀鸣。
与他推重“风雅”诗风相表里,齐己在论及当代诗人时,大多从“风雅”诗教出发,赞叹他们能在世风日下的时代依然继承诗歌“风雅”传统,哀叹他们因为坚守“风雅”而受到的种种不幸。《渚宫谢杨秀才自嵩山相访》诗:“惆怅雅声消歇去,喜君聊此暂披襟。”正因为“雅声消歇”,作者才觉得杨秀才独守“风雅”的可贵,又《偶题》诗:“时事懒言多忌讳,野吟无主若纵横。君看三百篇章首,何处分明著姓名。”正道出了艰难时代“风雅”诗人坚守传统的孤独。《酬西蜀广济大师见寄》曰:“犹得吾师继颂声,百篇相爱寄南荆。卷开锦水霞光烂,吟入峨嵋雪气清。楚外已甘推绝唱,蜀中谁敢共悬衡。应怜无可同无本,终向风骚作弟兄。”与末世“风雅”诗风消歇相联系的是“风雅”诗人命运的乖舛。齐己在诗中常常从诗人偃蹇潦倒的身世出发,把他们的遭际同时代悲剧联系起来,在流露出对“风雅”诗人命运同情的同时指出了诗人不幸的社会根源。《经贾岛旧居》诗:“先生居处所,野烧几为灰。若有吟魂在,应随夜魄回。地宁销志气,天忍罪清才。古木霜风晚,江禽共宿来。”又,《寄松江陆龟蒙处士》云:“万卷功何用?徒称处士休。闲攲太湖石,醉听洞庭秋。道在谁开口,诗成自点头。中间欲相访,寻便阻戈矛。”前诗中“地宁销志气,天忍罪清才”两句语气极为深沉,更是对贾岛命运多舛的哀鸣;后诗首联的设问增加了陆龟蒙虽有万卷诗却地位低微的悲凉色彩,“道在谁开口,诗成自点头”一联交代了陆龟蒙是坚守传统的“风雅”诗人,尾联尤具匠心,在不经意中揭露了时代给诗人带来的灾难。这种把个人遭际与家国命运连在一起描述的好处就在于使悲剧显得更为深沉,也更加有痛定思痛之感。
齐己在表达对同时代“风雅”诗人的同情时,喜欢用“冤”、“恨”等极具悲愤情感色彩的词汇,以便于宣泄内心愤怒的情绪。《读贾岛集》云:“遗篇三百首,首首是遗冤。知到千年外,更逢何者论。离秦空得罪,入蜀但听猿。还似长沙祖,唯余赋鵩言。”又,《哭郑谷郎中》:“朝衣闲典尽,酒病觉难医。下世无遗恨,传家有大诗。新坟青嶂叠,寒食白云垂。长忆招吟夜,前年风雪时。”这里“遗冤”、“遗恨”一类的哀鸣,都可以从“还似长沙祖,唯余赋鵩言”两句中得到正确的解释。就是说,哪怕像贾岛、郑谷这样一些“有大诗”的“风雅”诗人,又能如何呢?还不是就像汉代贾谊一样,郁郁而终。齐己内心这种随着对“风雅”诗人生不逢时遭际同情而产生的愤懑,又常常借对南朝诗人鲍照的咏叹表达出来。《寄益上人》诗曰:“风骚味薄谁相爱,攲枕常多梦鲍照。”钟嵘《诗品》论鲍照曰:“嗟其才秀人微,故致湮当代。”同时,鲍照诗中也充满了乱世失路文人的感愤,齐己正是借鲍照“才秀人微”之身况以及其诗中的感愤来为自己以及同时代苦难诗人鸣不平的。另外如“社客无宗炳,诗家有鲍照”(《送东林寺睦公往吴国》)、“社思匡岳无宗炳,诗忆扬州有鲍照”(《荆渚逢禅友》)等诗句,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三)尊白居易。
齐己诗集中论及唐代诗人的颇多,如李白、杜甫、李贺、王维、孟浩然、贾岛、孟郊等,但论及最多的还是白居易,这自然与白氏的诗教、禅理立场有关,也正因此,齐己才引白居易等“风雅”诗人为同调。齐己论白居易或从禅思出发,如《登大林寺观白太傅题版》诗说:“九叠苍崖里,禅家凿翠开。清时谁梦到,白傅独寻来。怪石和僧定,闲云共鹤回。任兹休去者,心是不然灰。”但更多的还是从儒家思想出发,赞美白居易诗歌中的风雅比兴诗教品格,如《送僧游龙门香山寺》:“君到香山寺,探幽莫损神。且寻风雅主,细看乐天真。”又《贺行军太傅得白氏东林集》:“乐天歌咏有遗编,留在东林伴白莲。百尺典坟随丧乱,一家风雅独完全。常闻荆渚通侯论,果遂吴都使者传。仰贺斯文归朗鉴,永资声政入薰弦。”两首诗都是以白居易诗歌“风雅”特征为重点发而为议论,赞扬了白居易诗歌的教化作用。又齐己认为可准上人的诗颇传风雅精神,堪与白居易诗比肩,《谢西川可准上人远寄诗集》诗中曰:“江上传风雅,静中时卷舒。堪随乐天集,共伴白芙蕖。”齐己对白居易诗歌风雅的大加赞誉与同时代诗人皮日休(834?—883?)《七爱诗·白太傅》中“谁谓辞翰器,乃是经纶贤。歘从浮艳诗,作得典诰篇”所论是相一致的,都是出于主张儒家诗教的社会目的。此外如“钱郎未竭精华去,元白终存作者来”(《谢秦府推官寄丹台集》)、“叮咛与访春山寺,白乐天真在也么”(《送僧归洛中》)等诗句都流露了齐己对白居易及其诗歌的赞叹之情,这背后的心理原因也只有从齐己对白居易讽喻诗歌诗教特征的认同方面来求得。
二、从禅理立论
与齐己颇有往来的诗僧尚颜《读齐己上人集》曰:“诗为儒者禅,此格的惟仙。”[4]齐己《怀金陵李推官僧自牧》诗也说:“秣陵长忆共吟游,儒释风骚道上流。”又如“日用是何专,吟疲即坐禅”(《喻吟》)“坐卧与行住,入禅还出吟”(《静坐》)齐己很喜欢将“禅”、“诗”并举,禅与儒是影响齐己修行最主要的两种思想。上文说过,齐己对诗思考最为殷勤,事实上,他对“禅”以及“禅”与“诗”的关系的思考也最为殷勤,认识也极为深刻,可以说远在唐代其他诗僧之上。对于齐己这方面的诗论内容,我们可以从两个侧面来论说。
(一)“诗”、“禅”相通。
与皎然所持“诗情聊作用,空性惟寂静”[5]的禅宗观点不一样,齐己认为“诗”、“禅”是互通互济的。齐己《夏日草堂作》诗中说:“静是真消息,吟非俗肺肠。”又《荆门寄怀》说:“神凝无恶梦,诗澹老真风。”还如“道性宜如水,诗情合似冰”(《勉诗僧》)、“诗心何以传,所证自同禅”(《寄郑谷郎中》)等,在齐己看来,“禅”、“诗”相通,二者之间恰如水与冰的关系,具有同一性质,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而已。齐己在《寄郑谷郎中》诗中说:“还应笑我降心外,惹得诗魔助佛魔。”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他的《夜坐》诗尤其能体现齐己对诗、禅互通互济关系的领悟,诗曰:“百虫声里坐,夜色共冥冥。远忆诸峰顶,曾栖此性灵。月华澄有象,诗思在无形。彻曙都忘寝,虚窗日照经。”诗中“虫声”、“峰顶”、“月华”都是自然物象,而“性灵”、“诗思”都是由主体对物象参悟而得,齐己从认知来源上说明了禅、诗互通一理之特征。
(二)禅之“悟入”与诗之“吟出”。
齐己所谓“入禅还出吟”实际是指出了“禅”与“诗”各自不同的获得方式,禅是靠“悟入”而得,直见本性,无须用文字说出,也无法用文字说出;诗则不然,诗在通过感物而性情鼓荡之后要表现为文字声音等实实在在的可见可感形式,所以是“吟出”。齐己从自己禅僧兼诗僧的身份出发,认为诗歌创作有两个极为艰辛的过程:一是对物象的穷搜旁讨,是感悟过程,二是诗歌本身的精深而且合于自然,是苦吟过程。
上文说过,齐己认为“禅”、“诗”一理,从源泉上说都是对自然物象的参悟而获得。诗歌既然是由自然物象参悟获得,则主观能动的积极参入则必不可少,齐己反复强调诗人参入自然物象而获得诗思的过程,《清夜作》诗:“不惜白日短,乍容清夜长。坐闻风露滴,吟觉骨毛凉。”又《谢王先辈湘中回惠示卷轴》诗:“少小即怀风雅情,独能遗象琢淳精。不教霜雪侵玄鬓,便向云霄换好名。”这里,作者自道感物、作诗之苦,由此也可知齐己是一位苦吟诗人。这种主体对自然物象的穷搜旁讨过程又是一个主体心灵对物象积极干涉的过程,所谓“诗句闲搜寂有声”(《寄蜀国广济大师》)说的是于那些哪怕是极为细小的物象所求得的诗思翻动。这又是一个艰难的主观活动过程,所谓“功到难搜处,知难始是诗”(《贻王秀才》)、“经论功余更业诗,又于难里纵天机”(《贻惠暹上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过程更要求诗人能把万物摄入自己的诗思之中,并且穷形尽相,入细入微,毫发无遗,正如齐己在《闲居》诗中所说:“微寒放杨柳,纤草入风骚。”又如《中春感兴》诗说:“春风日日雨时时,寒力潜从暖势衰。一气不言含有象,万灵何处谢无私。诗通物理行堪掇,道合天机坐可窥。应是正人持造化,尽驱幽细入垆锤。”这里,“道合天机坐可窥”是坐禅得道的过程,也就是“入禅”过程,“尽驱幽细入垆锤”是穷搜万物而获得诗思的过程,也就是“吟出”的过程,再看《寄酬高辇推官》诗:“道自闲机长,诗从静境生。不知春艳尽,但觉雅风清。竹腻题幽碧,蕉干裂脆声。何当九霄客,重叠记无名。”说明自然界中任何一草一木、一动一静都可以成为“入禅”与“吟出”的材料。
齐己认为真正能于自然物象中穷搜旁讨而获得诗思的诗人更是“仙手”、“高手”。《禅庭芦竹十二韵呈郑谷郎中》诗曰:“错错在禅庭,高宜与竹名。健添秋雨响,干助夜风清。雀静知枯折,僧闲见笋生。对吟殊洒落,负气甚孤贞。密谢编栏固,齐由灌溉平。松姿真可敌,柳态薄难并。映带兼苔石,参差近画楹。雪霜消后色,虫鸟默时声。远忆沧洲岸,寒连暮角城。幽根狂乱迸,劲叶动相撑,避暑须临坐,逃眠必绕行。未逢仙手咏,俗眼见犹轻。”表面上看,这是一首咏芦苇的诗,作者从声色、长短、时令等方方面面加以描写,可谓穷行尽相;同时作者又注入了自己深厚的主观情愫,尤其以“错错在禅庭,高宜与竹名”领起全诗,使诗歌通篇既浸染了禅思又充满了诗情,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关键在最后两句,所谓“未逢仙手咏,俗眼见犹轻”不仅是对于禅家而言,同时也说明了错错芦苇只有在能穷搜旁讨、穷行尽相的“仙手”中,才能得到诗艺的表现。又,《寄谢高先辈见寄二首》其一:“穿凿堪伤骨,风骚久痛心。永言无绝唱,忽此惠希音。杨柳江湖晚,芙蓉岛屿深。何因会仙手,临水一披襟。”诗歌誉诗人高辇为“仙手”并且希望能与他一起乘兴于江湖岛屿,披襟吟咏。之所以称高辇为“仙手”就是因为能“穿凿”万物,运物象于诗思之中。又《谢高辇先辈寄新唱和集》曰:“敢谓神仙手,多怀老比丘。编联来鹿野,酬唱在龙楼。洛浦精灵慑,邙山鬼魅愁。二南风雅道,从此化东周。”可知在齐己,“洛浦精灵慑,邙山鬼魅愁”是诗人穷搜物象的理想程度。齐己论诗极推李白、李贺,就是因为认为他们是穷搜物象的“高手”,《谢荆幕孙郎中见示乐府歌集二十八字》:“长吉才狂太白颠,二公文阵势横前。谁言后代无高手,夺得秦皇鞭鬼鞭。”其中“夺得秦皇鞭鬼鞭”一句正是指出“二公”运万物于胸次的高超本领。又《酬湘幕徐员外见寄》诗:“诗同李贺精通鬼,文拟刘轲妙入禅。”“精通鬼”就是说李贺感物之幽深与细微。齐己论诗诗中有《读李贺歌集》、《读李白集》两首读诗诗,都是从二人牢笼万物而刻画精深方面来评论他们各有诗歌特征的。《读李贺歌集》曰:“赤水无精华,荆山亦枯槁。玄珠与虹玉,璨璨李贺抱。清晨醉起临春台,吴绫蜀锦胸襟开。狂多两手掀蓬莱,珊瑚掇尽空士堆。”《读李白集》云:“竭云涛,刳巨鳌。搜括造化空牢牢。冥心入海海神怖,骊龙不敢为珠主。人间物象不供取,饱饮游神向悬圃。锵金铿玉千余篇,脍吞炙嚼人口传。须知——丈夫气,不是绮罗儿女言。”所谓“玄珠与虹玉,璨璨李贺抱”以及“搜括造化空牢牢”、“人间物象不供取”云云,都是就二人诗歌牢笼万物、刻画细微而言的。
诗人感物生情的过程其实只是获取诗思的过程,营造意境,形诸篇什,在齐己看来则是一个苦吟过程。这是一个与禅悟完全不同的过程,所以齐己说自己的苦吟是“禅外求诗妙,年来鬓已秋”(《自题》)。齐己屡屡提及这个过程的艰辛,如《寄谢高先辈见寄二首》其二:“诗在混茫前,难搜到极玄。有时还积思,度岁未终篇。片月双松际,高楼阔水边。前贤多此得,风味若为传。”纵有诗思翻动,就是难以成篇;又齐己《酬光上人》诗曰:“禅言难后到诗言,坐石心同立月魂。应记前秋会吟处,五更犹在老松根。”吟诗而达于五更,无怪乎比“入禅”更难了。
齐己认为苦吟过程应该包括章句音律之难与得“极趣”之难两个方面,并反复强调,正因为作诗有诸多难事,所以要苦吟。《永夜感怀寄郑谷郎中》诗:“展转复展转,所思安可论。夜凉难就枕,月好重开门。霜杀百草尽,蛩归回壁根。生来苦章句,早遇至公言。”见出齐己为锤炼章句用功之勤,诗中“至公”是指郑谷,郑谷也是苦吟诗人,曾为齐己《早梅》诗“昨夜数枝开”句改为“昨夜一枝开”而成为“一字师”,于此亦可见郑谷、齐己二人苦吟之一斑。齐己《山中答人》诗说:“谩道诗句出,何曾著苦吟。”说明齐己认为苦吟是赢获诗名不可少的条件。在《谢王秀才见示诗卷》中齐己鼓励王秀才说,只要“低摧向苦吟”就“何虑未知音”。齐己认为作诗又有音律之难,《酬微上人》说:“古律皆深妙,新吟复造微。”又《览延栖上人卷》诗中说:“今体雕镂妙,古风研考精。何人忘律韵,为子辨诗声。”都可见出齐己于诗歌音律形式探索之勤。齐己认为诗有“极趣”,并且认为诗有趣而至极,则诗可合于自然。“趣极同无迹,精深合自然”(《谢虚中寄新诗》),又说:“趣极僧迷旨,功深鬼不知”(《寄还阙下高辇先辈卷》)。齐己认为诗之“极趣”同于禅之“至悟”,是遗万象而于冥冥中搜得的“淳精”。《谢王先辈湘中回惠示卷轴》诗曰:“少小即怀风雅情,独能遗象琢淳精。”又说:“冥搜从少小,随分得淳元。”(《孙支使来借诗集因有谢》)这里“淳精”、“淳元”就是指诗歌超出文字章句等形式之外的一种总体韵致。正因为诗之极趣通于禅悟,所以齐已说:“禅玄无可示,诗妙有何评。”(《逢诗僧》)这种趣极之境界只有在冥寂中“搜”得、“扣”得,也就是说非下苦功夫而不可求得,这也是苦吟内容的一个方面。齐己《酬微上人》诗说:“搜难穷月窟,琢苦尽天机。”又《寄曹松》诗曰:“旧制新题削复刊,工夫过甚琢琅玕。药中求见黄芽易,诗里思闻白雪难。扣寂颇同心在定,凿空何止发冲冠。夜来月苦怀高论,数树霜边独傍栏。”诗歌反复强调为诗之难,难就难在“扣寂”、“凿空”,而“扣寂”、“凿空”之目的就在于获得“思闻白雪”这样的诗歌极趣。诗之趣至极,则诗歌不仅精深,而且是浑化无迹,合于自然。具体地说,即在于既能运万象于胸次又能遗万象而得真淳;既能于冥寂中穷搜旁讨,炉鎚锻炼,又能不露痕迹而归于平淡。齐己在论诗诗中往往用“清”、“淡”两种风格来诠释这种趣极而浑成的诗歌审美特征。《荆门寄怀章供奉兼呈幕中知己》:“神凝无恶梦,诗澹老真风。”又《览清尚卷》说:“格已搜清竭,名还着紫卑。”又如《寄匡阜诸公二首》其一曰:“争学忘言住幽胜,吾师遗集尽清吟。”齐己认为唐代诗人中诸如王维、孟浩然、孟郊、贾岛、姚合等人诗作最具清淡浑化的审美特点,齐己对他们多有称道,如“贾岛存正始,王维留格言”(《寄洛下王彝训先辈二首》)、“贾岛苦兼此,孟郊清独行”(《览延栖上人卷》)、“高韵双悬张曲江,联题兼是孟襄阳”(《题玉泉寺》)等。《还黄平素秀才卷》诗曰:“求己甚忘筌,得之经浑然。僻能离诡差,清不尚妖妍。冷澹闻姚监,精奇见浪仙。如君好风格,自可继前贤。”忘筌浑然,僻而不诡,清而不妖,这正是齐己诗歌“趣极”或者说是“清淡”境界的精髓所在。齐己是苦吟诗人,诗歌不入僻涩刻苦一路,他的诗歌于冷峭中显平淡,意境清幽,这与他的诗论主张是一致的。
齐己是唐代诗僧中的代表人物,“禅”与“诗”是他精神的两大支柱。齐己的修行思想不止于禅宗一端,兼有儒、道,受此影响,齐己论诗诗内容大致有两个方向,其一是本儒教论诗,尚“风雅”、重诗教,其二是本禅宗论诗,认为“禅”、“诗”一理,都是从自然万象中悟入;但诗歌还有一个“吟出”的过程,是一个苦吟过程,更须从冥寂中遗落万象去搜得;齐己认为诗有极趣,诗趣至极方可合于自然,才可达到浑成清淡之境界。
[1] [清]董诰,等.全唐文[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5535-5537.
[2]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597.
[3]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第84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9576.
[4]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第84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9602.
[5]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第81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9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