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的文化情怀——评《我与父辈》
/ 江苏_晓 华
作 者:晓华,本名徐晓华,评论家,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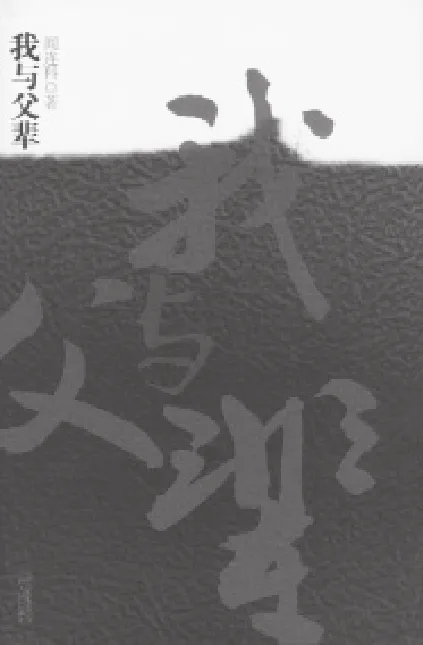
《我与父辈》,阎连科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定价:25.00元。
如果仔细辨别一下,小说家的散文总归有些小说家的影子,脱不了小说家的追求与笔法。读《我与父辈》,我们首先感到的是,阎连科的散文首先是写人的艺术。作品主要写了三个人物:父亲、大伯和四叔,这三个人物各有其性格特点。先看父亲。父亲是内敛的、隐忍的,为了一小块自留地,他披星戴月,领着一家人硬是在山上开荒,捡僵石,挑土担水,垒出了一小块地种上红薯。然而一夜之间,这块付出了全家人心血的土地却要被收为公有,因为农民不准拥有自留地了,父亲的心痛自然可以想见,但他忍了。当“我”急切地想离开多灾多难的家时,父亲虽然知道这对家庭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反对。这是一个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整天与土地庄稼打交道,从未尝试过其他生活方式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除了按乡规习俗、季节轮回去生活,他想不出也没有想过其他的活法,他最奢侈的愿望就是能在自家的院子里放一场电影,然而连这样的愿望最终也未能实现。再看大伯。相比起父亲的老实本分、内敛隐忍,大伯则要外显张扬得多,也许这与他农闲时走乡串村的织袜职业有关。大伯一出场就表露出幽默、顽皮、爽朗和善良的性格特点,一个几个孩子的父亲,一个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却有着一个孩子王般的快乐。大伯鲜明的个性在作者有关他嗜赌的描写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阎连科花了不少笔墨来写这个农民的赌博,因为赌,大伯不断输掉为儿女准备婚嫁的财产,也因为赌,他甚至悔愧到自杀,但是大伯最终还是战胜了一个赌徒难以战胜的赌瘾。其实,比起赌博来,大伯的人生还有更为残酷的地方,儿子不明不白死于部队,女儿又葬身车祸,自己的生意赔了再赚,赚了又赔,几乎血本无归,但不管怎样,大伯都挺过来了。阎连科着重刻画的是在乡间习见的人生祸福中一个农民性格的力量,一个普通人的“尊严”。这种乡村的尊严是一个农民对自己职守的坚持,是对农事的认真,是对乡村道德的践行,是对长辈的孝敬、对同辈的体恤携助和对子女的哺育义务……正是这种尊严,使得大伯这样的普通农民平凡而又伟大。还有四叔。阎连科笔下的四叔温和、文静而落寞,他是父辈中唯一在城里做工人的,但他娶妻生子依然在农村。这种人当时被称为“一头沉”,乡不乡,城不城,既接受了城市文化的熏陶,有着城市人一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节律,但内里的根、生活的牵挂又在乡村。四时节令,春播秋收的农忙,四叔必得像候鸟一样飞回农村的老家,这种内在的矛盾、自卑与身份上的暧昧使得四叔在表面的温文尔雅下充满了孤独与煎熬。阎连科对四叔晚年的生活费墨不少,早年在城里上班加班,为儿子操劳盖房,容不得半点时间来面对自己的内心。只有晚年退休回到乡村,大把的闲暇时间才使得那些内心的孤独与寂寞尖锐地存在于他的生活中,城市已无法返回,而乡村又格格不入,他只得整日靠麻将与酒来打发时光。三位长辈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与人生目标并无多大差异,但就在这似乎相似的生命旅程中他们却以不同的个性方式形成了不可重复的生命轨迹。
相信每一个读过《我与父辈》的读者都会对书中的大量细节留下印象,有些细节甚至让人震惊,刻骨铭心。一般而言,散文从大处来说是叙述与抒情的艺术,描写则是点缀,但对一个小说家而言,没有描写则是不可想象的,而细节在描写中又处在支撑的位置。这也许是《我与父辈》从总体上讲是叙述与细节描写两者关系呈现过程的内在原因。我们也许会记住老师的白色药片,那部用报纸裹着的《红楼梦》,台湾气球带来的“台湾不计划生育”的宣传单,会记住作品目录里阎连科名字下被父亲和家族人反复指点的那一团黑色的污迹,那只掉了油漆、已经钝了的剃须刀,那封告知大伯儿子死亡却丢在大路上的部队来信,还有作者为大伯做的那顿蛋炒饭和三鲜汤……许多细节只能出现在那样的时代与文化氛围中,不可复现。一件衬衣在那个时代是那么重要,它可以象征财富、身份,是社交场的重要符号。当四叔回乡时,那身白底蓝格儿的花衬衣足以牵动全村人的视线,以至于“我”憋不住请求“叔——把你的布衫给我吧”,而对于四叔来说,这件衬衣是珍贵的出客礼服,没了它,四叔出客时只能将身上穿着的白衬衣洗了,等它晾干了再穿上赶路。衬衣的细节出现了两次,它所透出的贫穷、窘境与复杂的心理实在一言难尽。那是个精神与物质双重贫困的时代,因此,有关贫困的细节俯拾即是,可以信手拈来。作品两次写到父亲打儿子,一是阎连科的父亲打他,一是大伯打书成。父亲打他是因为他的顽皮和偷盗,穷不要紧,但不能抢,不能盗,那关乎一个人乃至一家人的名誉。其实,穷是要紧的,一切不幸与不如意的根源都在那个穷字上。大伯为什么那么近乎残忍暴戾地往死里打书成?具体原因作者已经记不清了,在作者的描写中,好像大伯在打的过程中也忘却了原因,因为大伯边打边说的话显然与具体的事情无关,也与被打者无关,所以才那么悲怆,让作者至今难忘:“打死你们我们家的日子就好过了……”“都把你们打死日子就轻轻松松了……”这两句话与乡里医生在阎连科家里说的一句话意思是一样的,父亲的病其实也是因为一个穷字。乡里医生说了一句适用于所有因贫致病、因病致贫、贫病交加的家庭的话:“只要二叔(我父亲)活着,你们家怕不会有好日子过,你们家要日子好了,二叔也能多活几天。”它确实是对那种生活状态中一种因果关系的揭示,而且里面所透出的残酷与不可能作出的选择实在令人不寒而栗,正如大伯的话一样。
其实,面对《我与父辈》这样的作品,讨论它在艺术上的得失是多余的,它是那种质胜于文、因质而忘文的作品。对于这种类型的散文作品有一点要特别地指出来,那就是无论是非散文纯正血统的写作者写出了堪称当代经典的散文作品,还是小说家给散文带来了新的气息、新的元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求,这种欲求之强大几乎到了与自己生命相当的程度,到了还债、赎罪与仪式化的程度,而这种欲望背后的内容又非自己原先的职业文体所能满足。
我相信许多读者都会对阎连科在书中真诚表露的自责与忏悔感到惊讶、感动和钦佩。而且,阎连科的忏悔具有相当强的个人性、日常性,他是从中国日常生活的伦理出发,对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与心理进行的问责与反思。自中国“五四”新文学直到新时期文学以来,其忏悔意识、主题原型与结构模式往往表现为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社会、民众与社会普世价值、伦理的忏悔。这里的知识分子虽然也不缺乏真实的个体,但是这样的个性常常可以被看做是群体的代表,他的行为虽然是个别化的,但他的错误甚或罪过都是普遍的,而且与社会时代存在因果关系。因而,从另一个方面看,他的错误甚或罪过又是可以理解与宽宥的。同时,这一传统所依赖的精神资源或具有形而上的玄学性,或具有现实的意识形态色彩,很少关乎个体的私人空间,实际上,它与个体的现实形象、与在场评价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过去,人们可能从宗教的角度过分强调了忏悔中灵魂的拷问和对形而上的追问,却忽视了人对自我在现实生活中行为的追悔、反省与问责。其实,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大国”,在这样一个太上立德、崇奉日常伦理规范、重视现实人际关系中的评价的社会中,恰恰对自己日常行为的评价是最具难度的。也正是从这种文化特质出发,我以为倒是《我与父辈》表露出一个人忏悔其个体的不可重复性、排他性与代言性,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潜在的辩护理由,直接地以在场的方式给自己以残酷的评价。设身处地想一想,有谁有勇气承认父亲的死与自己有关?阎连科为此给自己开出了三张欠单,一是“没有花那十元钱让父亲看一场他想看的电影《少林寺》”,没钱不是理由,因为他探亲回到部队时身上还有近二十元钱。“如果自己自幼就是那种爱父母胜过爱自己,是那种肯把父亲的吃穿、喜好放在自己心上的人,我会不包那一场电影吗?为什么到了父亲死去之后,才来懊悔这件事情呢?这不也正是要把自己冰冷了的善、爱穿上一层棉衣吗?”“第二笔欠单,就是自己执拗地服役,执拗地逃离,从而在别人以为一切都合乎情理中改变了父亲的命运,使父亲痼疾复发,六年后就别离了这个他深爱的世界。”第三张欠单是直指内心的,阎连科说当他听到医生说出“只要二叔(我父亲)活着,你们家怕不会有好日子过,你们家要日子好了,二叔也能多活几天”的话时,停在他脑海里的便是它的直接含义:“只要父亲在世,我们家(也许就是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那含义就是我对父亲过世的一种预盼,对父亲长年有病受到拖累的一种厌烦,一次逆子私欲的无意识的表白。”“似乎有‘我希望父亲早一天离开人世’”,“想以父亲的死来换取我们家(我)的好日子”等“罪恶的念想”。我不知道这属不属于灵魂范围里的事,但它绝不比任何知识者伟大的忏悔来得容易与轻松。当一个人在真实的世界里以真实的身份面对公众与亲人说出自己内心这样的罪孽时,他应该知道会面临什么,当然,从另一个意义讲,他已作好了接受惩罚的准备,是他自己将自己送上了良心的审判台。这是中国作家忏悔姿态的一次重要转型,我希望它的意义能被广泛地关注。也许,这样的忏悔对一个民族伦理价值的建设与内心向善精神的提升更有作用。
阎连科家族叙事的精神资源来自于中国传统的乡村伦理。《我与父辈》的叙述虽然很纷繁庞杂,但其核心乃在于从中国农村普通人的生与死、人生与命运以及循环往复的单调生活中重申其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是乡村中每一个个体活下去的理由。我们可以发现,阎连科写得最多的是父辈三兄弟如何为子女的成长、婚姻与房子操心,质言之,也就是家族的延续。这种目标的本质即在家族的延续与生命的延伸,一代代就是这样传承下来,上一代人是下一代的榜样与老师,通过生育子女,将个人的有限生命延续到无限的未来之中,从而获得生命的意义。这是个体,也是社会,是现世,更是历史与未来,它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本质的生命观与历史观。由这种本体价值观出发,即使日常的生计,柴米油盐也会获得意义,阎连科笔下的父辈都是那么坚忍,虽然大伯说“人活着也是活受罪,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罪”,虽然四叔说“天下没有一碗好吃的饭”,但是他们都把生儿育女并且帮助他们成家立业当成一项庄严的事业去做。因了这样神圣的目标,个体的许多美德会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养成。他们会觉得忍受现实苦难富有意义,会脱离狭隘的个人利益的局限,会摆脱个人物欲的困扰,也由此安身立命。于是,乡村的社会评价系统也会相应地建立起来。为什么大伯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却是活得最有尊严的人?就是因为大伯在持家置业、儿女婚姻上信守承诺,“显出了他一个农民对卑微的生命认识的高贵与脱俗,显出了大伯在那块土地上,生命的痕迹在命运的道路上,要比别人留下的深刻并光辉”。父亲虽然艰难多病,但他带着儿子愚公移山盖起房子使每一个过路人的脸上“都一律挂着惊羡的神色和默语的称颂”,“把我们家那所宅院和那宅院中盛装着的乡村的人,当成村落建筑和日子的榜样与楷模”。这样的事业在乡村中起着引领风尚的作用,它的意义超出个体与家族而参与到乡村文化的培育与积累之中:“那所宅院和宅院中的日子,的确在那片村落和方圆多少里的村落中,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和声誉,对许多农民的日子起着一种引导和督促。”乡村的许多伦理规范、文化观念与乡风民俗都与这种本体价值有关,如孝,它是生儿育女、家族延续的逆向展开。再如生死观,《我与父辈》写了两代人的死亡,之所以留恋生是因为家族的兴盛:“对一个农民来说,只要活在这个世上,能同他所有亲人同在一个空间生活和生存,苦难就是享受,苦难也就是欢乐。”而坦然地面对死亡,也是因为家族的延续是不会断的。人生是有归宿与去处的,是有来世的,一个现世的人简单地说就是将时间向两极延续,承续着父辈的血脉,并向下传递,他以晚辈的现实存在相信生命将通向无尽的未来,他又以缅怀追思的方式接续着看不见的祖先从遥远的过去向他传递的源远流长的历史。所以,中国人讲究慎终追远,认为死生亦大焉,死与生是同等重要的。大伯要求他死后的丧事一定要隆重,纸扎、社火一定要多,要旺,孝子一定要多,事实上儿女们都照着做了,备极哀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习俗与仪式?为什么要有一座坟墓,一处死者的葬身之地?说穿了,那是对死者生命的另一种肯定,是对那走入虚空的生命与家族历史的挽留,是对自己生之所来的感恩与敬畏,是对自己生命与精神之源的反复确认。有一处坟茔,逝者便与生者同在,也给后者留下了可以凭吊追思的地方。“现在,父亲坟上的柳幡都已长成了树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事情,唯一不变的就是父亲的安息和我对父亲永远不能忘记的疚愧与想念。”
阎连科通过亲情对乡村伦理的这些书写其意义当然超出了叙事本身。他不仅在缅怀先辈,同时也在追怀日渐消逝了的乡村伦理。中国很长的历史是处在农耕文明当中,整个文化价值理念是在农耕文明中孕育成型的,因此,乡村是文化的母体,承载着文化的生产与输送,当社会遭受动乱与重创时,乡村又承担着文化的重建与修复,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但我们现在的文化生态恰恰是文化的源头正面临破败与解体,这是阎连科深层次的忧患所在,他一再诉说他的“焦虑”,然而,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通过父辈的故事,向人们讲述曾经的乡村,曾经的美德。在书中,阎连科反复书写父辈的离去对后代的影响,“长辈年纪再大也是前面挡风的树”,现在父辈一个个离去,“我们家生命的围墙不是有了豁口,而是倒了一堵完整的墙”。它提示人们注意到的不仅是生命消失的自然节律,在特定的语境中,它成了关于乡村、传统文明与精神价值的可怕的寓言:当乡村死去,我们将再无庇护。这是阎连科文化情怀中超越自己与家族的剧中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