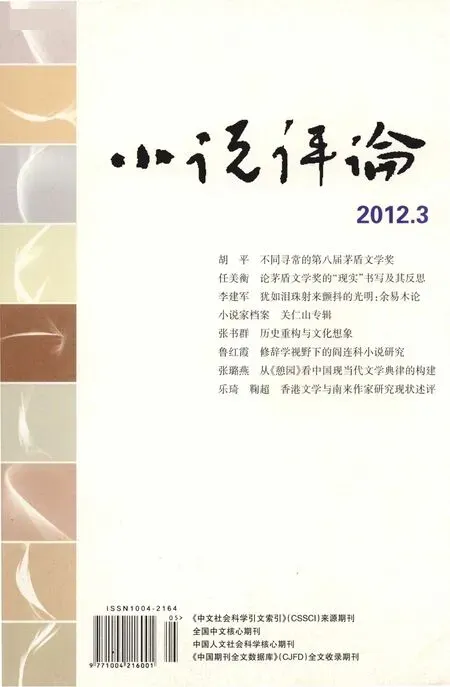现实与寓言的交汇,真实与虚构的对话:关于阎连科《四书》的评论
刘熹
当苏童的《河岸》在叙事后半段脱离了对文革自身的专注,当贾平凹的《古炉》仅仅凝视着一个村的世界,当伤痕、反思的文学创作将文革叙述重复成为一种固定模式,当王朔式的调侃解构导向了文革的消费化叙事,当文革渐渐成为写作的背景,成为一个遥远的文学记忆时,阎连科的《四书》不啻是一个新的开拓。他用寓言式的手法建构了一个悬浮的世界来装置他的文革世界,(也许可以增加对《苍蝇》的映照)阎连科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完整的,透明的世界,我们带着距离观看,思考,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空间来反思,喟叹。也正因为此,《四书》在大框架上就获得了一种反思的深度。
如果说阎连科成功的在文革这个题材上建立了庙宇似的宏大结构,那么在他建筑的庙宇内部,他同样成功的完成了精致的内部构建。是的,这是一部结构精致的书。章节的命名呼应着《四书》这个书名:《天的孩子》、《故道》、《罪人录》和《新西西佛斯神话》既是《四书》的小节,也是四本独立的书名,而四本书中的章节被截取和组合,构成了《四书》这个全新的整体。在《四书》的最终章《书稿》一节,阎连科现身了,讲述这四部书的前世今生:
关于这“四书”中的《罪人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历史史料出版的。而作家的《故道》这部将近五百页的纪实书,直到二○○二年前后才出版,时过境迁,反响平平,无声无息。而《天的孩子》这一本,是我几年前在一个旧书摊上买到的,作者的署名处,写着这样两个字:佚名。出版者是中国典籍神话出版社。唯一没有出版的,是学者那本思考数年、没有写完的《新西西佛斯神话》的哲学随笔稿。
阎连科的此番现身有着双重意义。他让我们更加明晰的察觉到《四书》结构的精致,原来那些不同的叙述方式呼应着不同的著书者,而更重要的是,阎连科的此番现身,让我们从阅读的完整性中脱离,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我们渐渐适应的那些跳跃的、风格不同的叙述,原来以为正在欣赏的小说家先锋的叙述方式,它们不是为炫耀技巧而存在,它们是因为真实而存在。《天的孩子》仿圣经风格的句式,穿插着《罪人录》文革式的口号标语,还流淌着《故道》对育新区细腻的讲述,以及《新西西佛斯神话》充满寓言和哲理的卒章显志,这些风格相异的文字使《四书》不仅仅在叙述一个已经发生的故事,而是指向神秘的远古,指向开阔的初始,也指向似乎一直悬挂在全人类头顶的命运。而小说呈现的寓言式风格被小说结尾的仿真叙述冲击消解了。原来我们看的不是某个寓言,某种神话,我们看到的是一本娓娓道来历史的书,这些历史是我们切身经历的,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印迹。
而阎连科的出现却也宣告了作者的退位。当然,这里的“隐退的作者”不是阎连科,而是我们读者所假象的、将《四书》作为一个整体来创作的作者。我愿意将《四书》看作不仅是由四本相关联的书构成的整体,更是一本由书写作的书。此番感觉就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美丽的妇人从字里行间活了过来,摆脱作家的控制走向铁路、选择死亡。《四书》里的书,互相孕育而生,互相印证阐释,形成书本之间隐秘的对话。《天的孩子》里我们知道了《罪人录》的存在,也知道了“学者”隐秘写成的《新西西佛斯神话》;《故道》中“作家”一直喃喃要写一本书,“我要写一部真正善良的书,不为孩子,不为国家,也不为这个民族和读者,仅仅为了我自己”而这本真正善良的书正是我们一直阅读的章节“故道”——“作家”说“我确定我的书名为《故道》”;《新西西佛斯神话》里西西佛斯承担由上往下推巨石的那座山坡,正是《天的孩子》里“宗教”和“孩子”去镇上献黑沙铁时碰见的那座颠倒重力定律的怪坡,西西佛斯遇见的,爱上的小孩正是“天的孩子”;而“孩子”为了取暖烧掉的所谓禁书,《魏晋七贤》《野草》《唐宋律》《高老头》《罗密欧与朱丽叶》《少年维特之烦恼》《大卫·科波菲尔》《石头记》等,突兀的又固执的在被绚烂的火焰埋葬前,将自己的名字告知读者,譬如一块耸立在黄河岸上的墓志铭。这是一部由书写作的书,当“作家”意识到自己应当用笔记下这一切,不为“孩子”,不为国家,不为红花,不为五星,当“作家”天启般觉得自己创作的作品应当被命名为《故道》时,由《故道》组成的章节才真正显现了魅力,“作家”这个形象才真正变得立体和丰满。如果将“作家”“确定我的书名为《故道》”那一刻作《故道》一书自觉的标志,那么此前的《故道》仅仅是作为《四书》的章节存在,行文中采用的第三视角叙事方式仅仅同《罪人录》、《天的孩子》产生一种补充的效果;而此后的《故道》具备了独立于其它三本书的特质,甚至在《故道》中存活的“作家”也从此具备了肉身。那个只会流水账般记录育新区大小琐事的“作家”突然间唤醒了自己的鼻子,他闻到了“劈柴的木香味,浓得仿佛让人走进了油坊间。从烧柴上滴出的木油汁,一滴滴呈着红色落在火道边,然后又因炙烤和火温,嘭的一声燃起来。那木汁的香味吞进肚子里”;他的耳朵被打开了,他“听见了来自地面碎细吱吱的响,以为那是来自大地和田野夜间必有的声息和细语,尤其在星星高挂、月亮当空、万籁俱静的子夜中,月光和星光落在地面的游移会有那水流似的响,还有这荒野间草长花开在子夜时的神秘响声和语音”,他“隐隐细细地听到我的枕头下有蛐蛐爬动的声响走进我的耳朵里……我听到来自麦田那边麦棵和草根在沙土地下跑动的脚步声,似乎还有你争我夺的扯拽和不安,仿佛那些麦苗、草根在地下打架样;他的眼睛重获了新生,他看到“天上血雨漫舞,如半银半红、一丝丝透明的细柱扭着身子竖在麦地间。脸和地面垂直时,穿过那红白相间的雨帘雨帐朝前看,能看到雨外晴天处的太阳光明彤照,金黄灿然,如燃在大地漫卷在远处的火”。
伴随着感觉的鲜活,“作家”的人性也得到了复苏。事实上不止是“作家”,“宗教”、“音乐”、“学者”、“孩子”、整个育新区的罪人、这些曾经的知识分子都在此后经历着人性的磨练与考验。我仍然愿意将《故道》的自觉作为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育新区的人们还承受着回家的诱惑,他们在红花五星的机制下劳作,生活,互相监视;在对家人的思念和渴望中,放弃自己的常识,放低自己的尊严;在此之前,“孩子”还经历着前往京城的诱惑,像一名初生的婴孩般不顾一切,争报产量,损毁自然,大炼钢铁;在此之前,“宗教”还无法放弃自己的信仰,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和黑色封面的《圣经》是他甘愿用肉身护卫的;在此之前,“音乐”还沉浸在和“学者”隐秘的恋情里,神谕般的梦让她堕落至此,却也找到了心中最爱;在此之前,“学者”还为了给“音乐”挣得永久离开育新区的五星,抛开自己的理性和清高,游离在大众之外;在此之前,“作家”还只受着五颗五星的诱惑,监视同僚,记录言行,讨好“孩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育新区的人们适应了这样的生活,甚至那些逐渐增加的红花五星还带给他们仿佛近在咫尺的希望,和遥远的家的影子。而在此之后,发生在“孩子”帐篷的大火不仅烧毁了“孩子”的奖状,还烧毁了属于育新区罪人们的红花和五星。谎言,猜忌弥漫着曾经有条不紊的育新区;愤怒,嫉妒使这些曾经的知识分子用最粗俗的语言,用最原始的方式惩罚那通过出卖而率先拿到五颗五星、偷偷离开育新区的“作家”。当尿液被自然的视为侮辱的手段,当生殖器被坦然的当作惩罚的武器,育新区的生存环境已经退回到人类初始的蒙昧状态。我们曾经冲破黑暗时代的勇气、我们经历启蒙后的痛并快乐、我们掌握了自然规律时的兴奋、我们探索着科学边界的小心翼翼和宏图壮志、我们改善着人和人之间相处原则的欣慰,这一切被一场映红了天边的火烧为灰烬。罪人们抛却了所有获得的红花五星、他们因承受回家的诱惑而获得的宁静,在这场火光冲天中变为乌有。这一刻催生的谎言猜忌和愤怒嫉妒,亦如《新西西佛斯神话》中的西西佛斯“开始懊悔他在山的那边路上碰到的那孩子,懊悔他对那个孩子的爱”。不同的是,西西佛斯在新的惩罚中重新找到了宁静:“他越过神的惩处看到了山下的禅院和俗世炊烟图。他爱上了这俗世的禅院烟图”,而育新区的罪人们却在继大火之后再次面临着大饥荒的考验。这是来自神的惩罚,“神说话:‘人都狂妄了,让他们白白滴血劳作吧。’”这是对我们无限自信的惩罚,这是对我们热衷现世的惩罚,这是对我们惰性的惩罚,因为“惰性产生从适,从适蕴涵力量”,而这力量是摒弃了独立而理性的思考换得的,这力量源自各种不同的诱惑。
正因为我们不是于惩罚中找到存在意义的西西佛斯,我们置身育新区的罪人们才会在大饥荒中狼狈不堪的挣扎,这是挣扎着活下去,也是挣扎着寻回我们的人性。即使他们选择了吃死尸果腹,至少我们还记得那两个吃后便梳洗整理、上吊自杀、留下道歉信的“文化处长”和“教育部副厅长”;即使“音乐”选择了出卖自己的身体换取以供生存的口粮,至少我们还留意到她总会偷偷的放一半粮食在“学者”的被窝里;即使他们都迷失在饥饿和死亡里,至少我们还有“学者”抛开了此前游离的、边缘的、自我心灵上的放逐,肩负起掌舵人的重责;至少我们还有“作家”,让我们看到了救赎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写下《罪人录》是他原罪的开始,虽然他给了自己足够的理由:只有记下育新区发生的一切,他才有机会离开这里好好写本关于育新区的书,也只有如此他才能够在纸张和墨水严格被控制的情况下记录宝贵的素材。但当他拿着五颗五星在偷偷回家的路上,被育新区的同僚们狠狠打倒在地、狠狠的羞辱,并且毫不怜惜的点燃了他的五颗五星和宝贵的稿纸时,“作家”“却连一点悲伤和怨恨都没有,反而觉得浑身轻松自在得没法儿说”。而他离开育新区,独自生活在旷野中,选择用鲜血浇灌麦棵,这样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讨好“孩子”以得到离开育新区的五颗五星,这也是“作家”潜意识里的愧疚。他无法待在那片被他出卖过的土地上,而他也只有用如此自残的方式平息自己潜在的愧疚。所以当他看到“音乐”的宿舍里有他被偷走的《罪人录》时,当他意识到“音乐和学者对我什么都知道,而我每天还依旧去偷记他们的言行时,我忽然觉得自己是被音乐和学者扒光衣服的人。想到接下来,我必须在黄昏之前面对音乐和学者,有一个想念如一片草中突兀出来的尖刺扎在了我的脑子里,使我的脑里刺疼一下儿,浑身又哆嗦一阵子,紧跟着,我的双腿仿佛抽了筋般颤抖胀裂得让我无法直直地站在音乐的床铺前——我的天!——当我想到我曾经割破十指、双腕、双臂、双腿和动脉去浇血脉时,我竟又想到我应该从我的身上——双腿上——割下两块肉,煮一煮,一块供在音乐的坟前,一块请人吃掉,由我看着那人一口一口噘着我的肉”。作家内心的惭愧只能够用割下自己的肉奉献给学者和音乐才能平息。以肉身的疼痛来表达如此惨烈的赎罪,这是一种洗礼,这是一种修炼,这是一个让作家寻回自己人性的旅程。所以“作家”会选择带领育新区的众人前往未知的归家之旅。虽然前途未知而路途漫长艰险,虽然学者劝慰他们哪儿都一样,可能长途跋涉更加危险,但作家那番赎罪的自白给了我们希望:“这次是我鼓动大家逃走的。这些人,我都在《罪人录》中记过他们许多事,赎罪我该把他们带出去”。
《四书》故事的结尾完结在“作家领着人众往外走”,还完结在因发现黑沙炼铁而早早离开育新区的“实验”带着一家老小复又前往育新区,幻想着那里“地广人稀,春季间万物花开,有吃不完的东西啊”。这个戏剧性的结尾不是钱钟书《围城》中“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的无奈,而是一种对赎罪,或者确切的说,对重新找回独立而理性思考能力的赞美与期待。因为在那片曾经仿若此岸伊甸园的育新区,“孩子”已经完成了耶稣死亡的仪式,而“学者”也化身为守候孩子的教徒。在那片死去的土地上,宛若犹大的“实验”只会跌入深深地狱。
当然,阎连科的《四书》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突然出现的、谦卑的国家领导,比如学者总是喋喋不休的标榜着读书人这个身份。或许就如但丁的《神曲》:地狱和炼狱的描绘那么生动多变,而天堂的美好却显得单一,我们总是无法真切圆融的表达我们感知以外的世界,那是想象力也无法抵达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四书》成为一部非常出色的书,成就文革题材小说创作的新高度。至少他拓展了新的表达方式:那种用寓言和真实混杂的表述手段,那种游离在历史外部,却又深入人性的思考方式。特别是他开创性的将文革与大跃进、知识分子改造融为一体,并将贯穿一致的思考表现在文本中,还别出心裁的将文革造成的苦难具象为不可抑制又压倒一切的饥饿,让无法言说的痛苦用真切的肉身来表达。而更让人掩卷深思的是阎连科对这段历史的疑问和尝试性解答。在他制造的模糊时空中,阎连科探寻的脚步摆脱了对历史的亦步亦趋,也没有单纯的将矛头指向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阶级,他试图解答的是一个整体的,甚至人性的总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