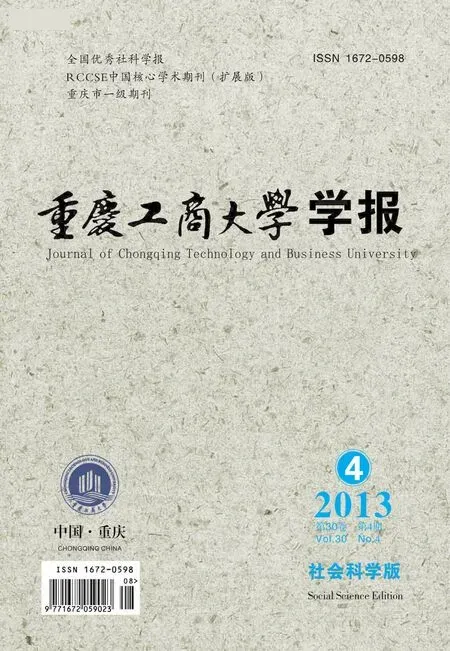以“法”解《庄》:林云铭《庄子》散文评点的本质特征*
李 波
(1.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庆246133;2.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28)
林云铭,字西仲,别署“沤浮隐者”,福建侯官人。顺治五年(1648)举人,顺治戊戌十五年(1658)进士,曾官徽州通判。林氏少时读书颇为用功,王晫《今世说》称:“云铭少嗜学,毎探索精思,竟日不食,暑月家僮具汤请浴,或和衣入盆里,人皆呼为书痴。”(《四库全书总目·楚辞灯提要》)但其一生遭遇颇为坎坷,“毕生颠踬,屡滨于危。”(《挹奎楼选稿·自序》)据四馆馆臣载,1674年,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反清,“云铭方家居,抗不从贼,被囚十八月,会王师破闽,始得释,其志操有足多者。”(《四库全书总目·挹奎楼选稿提要》)后来举家迁居杭州西湖,但一场意外的大火使他家徒四壁,在穷困潦倒中客死他乡。林氏一生著述颇丰,有《挹奎楼选稿》《楚辞灯》《庄子因》《古文析义》《韩文起》《吴山鷇音》等流传于世。
林云铭从小喜欢《庄子》,先于康熙三年(1664年)注成了《庄子因》。后又花了二十多年时间,经过几次修订,于康熙戊辰二十七年(1688)完成了《增注庄子因》一书。是书书前有《自序》《凡例五则》《庄子总论》以及《庄子杂说》二十六则,篇前题“三山林云铭西仲评述”字样。其评点形式有夹注、篇末总评、少量旁批音注以及圈点。董思凝在王夫之《庄子解·序》中说:“近闽人林氏《庄子因》出,而诸注悉废。”[1]可见当时影响之大。现全国各大图书馆大都藏有此书,更能说明其传播之广。此书以较为完备的评点形式对《庄子》散文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解读,雅俗共赏,迎合了时代的审美趣味,不管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超越了前人,故形成了广泛的读者消费群体,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影响一时。综观《庄子因》一书,其解《庄》方法不再以训诂和哲理为主,而是分章析句,层层剖析,逐句逐段点明意旨,探究脉络,体悟文情,将庄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汇”(《增注庄子因·序》)[2]一一析出与读者分享,使读者不仅从中悟到了作文之法,更领略到了《庄子》独具特色的艺术审美特征,大大开拓了《庄子》的审美意蕴,拓展了《庄子》的审美阐释空间。林氏这种以文法解《庄》的方法为人们从纯文学角度研究《庄子》树立了典范,开时代风气之先,在庄子散文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一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是以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通过形象化语言对审美对象作宏观整体把握为主要特征的。南宋以来,科举制度催生了评点这种新的文学批评样式,要求人们更加理性地来总结前人的写作经验,指导士子们写出符合规范而又有技巧的文章。在这种背景之下,评点之风迅速兴盛起来,人们的理性思维逐渐增强,以至影响至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个领域。宋明以来,《庄子》评点亦盛极一时。这种新的文学批评形式使人们解《庄》的思维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理性思维越来越强烈,“法”的观念越来越浓厚。终于在清初,出现了一批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具有较鲜明的以“法”的观念来评点《庄子》的著作。林云铭的《庄子因》即是其中较突出的一个。
对于林云铭《庄子因》的评价,以四库馆臣的观点最有代表性。“支离弇陋,以时文之法读《庄子》。”馆臣的态度固然有些偏激。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林云铭毕竟是一位在八股教育浸淫中长大的古文家,摆脱不了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因此,他的古文理论明显地受“时文”评点的影响,带有“八股”影子。他解读《庄子》,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全章八股文字,俱要还他浑浑成成一篇妙文”(《庄子因·凡例》)[2]。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他明显继承了明清学者所宣扬的带有浓厚八股气息的“文法”理论,来对《庄子》展开批评赏析的。“盖凡读书家,必先识得字面而后能分得句读,分得句读而后能寻得段落,寻得段落而后能会得通篇大旨,及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汇,此不易之法也。”(《增注庄子因序》)他第一次在注文中增设“读庄子法”体例,总结了“以地理之法读庄”“以观贝之法读庄”“以五经之法读庄”等等方法,引导读者“细读”《庄子》。在注解《庄子》的过程中,他归纳了《庄子》中的诸多作文之“法”。如《齐物论》篇“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四句,他评曰:“言与知、知与言是一篇之赈,然言又本于有知,故先提此四句立局,极得振裘挈领之法。”四句看似突兀,与上文不相蒙,但仔细分析发现庄子是由地籁之不齐转到了人情之不齐,此四句实为下文立楔子,统领下文,他称之为“振裘挈领之法”。又如评《齐物论》“瞿鹊子问乎长梧子”一段中的“固哉,丘也与汝皆梦也,予谓汝梦亦梦也”几句:“再着此句方全是文家深一层法,庄文中此法甚多。”本是说别人在做梦,却随口又加一句说自己也是在做梦,意义得到了深化,他称之为“深一层法”。其他如《齐物论》篇“散中取整法”,《胠箧》篇“化板为活法”,《天运》篇“详略变化法”,《秋水》篇“文字埋伏法”“抑扬开阖之法”,还有“倒句法”“翻跌法”“文字倒收法”等等。这些说法虽然有八股气,但颇能抓住《庄子》文章的独到之处和修辞艺术,对读者很好地理解《庄子》艺术特征是非常有帮助的,后来胡文英、刘凤苞等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更多的艺术手法,有的相当精彩。
林云铭以“法”解庄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与当时文艺思潮不无关系。北宋以来,随着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对诗文之“法”的研究。如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提出诗歌写作的“换骨法”与“夺胎法”:“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3]到了明代,由于复古主义文风的兴起,文人们更侈谈“法”。前七子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曰:“古之工如倕如班,堂非不殊,户非同也。至其为方也圆也,弗能舍规矩,何也?规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4]唐宋派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云:“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密则疑于无所谓法,严则疑于有法而可窥,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则不容异也。[5]后七子王世贞更是重视为文之“法”,他在《艺苑卮言》中发表了一段极为著名的言论:“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缀关键,金石绮綵,各极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锦,句有千钧之弩,字有百炼之金。”[6]受明人的影响,清人也极为重视“法”,特别在小说、戏内评点中,已开始将这种“法”的理论运用到了批评实践中。如金圣叹评点《水浒》时总结了“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欲合故纵法”“横云断山法”等多种叙事手法,影响一时。林云铭显然受到上述诗论和文论的影响,自觉以“法”的理论来解《庄》。他“以时文之法读《庄子》”显然是明清以来文艺界盛行的“文法”观念在《庄子》散文领域的一次具体实践,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代表了时代的治学风格。馆臣将其一棒子打死的做法显然有失公允,更何况林氏能够融会贯通,在解其文的基础上,求其意,体其情,多有理论创造与发明,远远超出了时文评点的藩篱,开一代学风。
二
在“法”的观念支配下,林云铭认为《庄子》是“一部有首有尾、有端有绪之文”(《楚辞灯·序》)[7],因此他对《庄子》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分析,“将内七篇逐段分析,逐句辨定,逐句训诂,誓不复留毫发剩义。而外杂篇虽属内篇注脚,遇有神奇工妙处,亦必细加改订,分别圈点、钩截,得其眼目所注,精神所汇而后止。……但以数十年寝食于《庄》,久已稔其大旨,迄今论定,而段落、字句之间,始无遗憾。”(《庄子因·自序》)综观《庄子因》一书,可以看出林云铭已具有了一种较为成熟的文章学观念,尤其是他对庄子文章结构的理解上已较前人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在评点过程中,紧紧抓住庄子文章的主旨,细细梳理文章脉络,不仅使《庄子》内外杂三部分形成了有机整体,亦使每篇文章前后一体,充分显示出了一个古文研究家的独特眼光和理论学养。
(一)对《庄子》内外杂篇关系的独特理解
首先,他承前人之说,认为内篇是一个前后相因的整体,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在《庄子》散文研究史上,分析内篇逻辑关系是学者们普遍重视的问题,他们各从自己的理解出发,对一问题做出了富有个性化的阐释。成玄英、王雱、褚伯秀、释性通、陆西星、释德清等人都对内篇的逻辑关系进行了解析,虽然理解角度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庄子》内篇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有逻辑可寻。林云铭对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承前人之说,但在具体的理解上却颇显出他作为古文家从文学角度理解的独特:“《逍遥游》言人心多狃于小成,而贵于大;《齐物论》言人心多泥于己见,而贵于虚;《养生主》言人心多役于外应,而贵于顺;《人间世》则入世之法;《德充符》则出世之法;《大宗师》则内而可圣;《应帝王》则外而可王。此内七篇分著之义也。然人心惟大,故能虚;惟虚,故能顺;入世而后出世,内圣而后外王,此又内七篇相因之理也。若是,而大旨已尽矣。”(《庄子总论》)从每篇文章的主旨出发,认为七篇具有“相因”的逻辑关系,前人虽有过类似的说法,但林云铭的理解却更能抓住庄子思想的本质,显得更为朴实,更为精练,也更容易让人接受。
其次,在《庄子》内外杂篇的关系上,他认为内篇为全书的宗本,外杂篇对内篇是一种补充、阐释说明的关系,《庄子》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外篇》《杂篇》属《内篇》注脚。”(《增注庄子因序》)在《读庄子法》又说:“《庄子》全部以内七篇为主,外篇、杂篇旨各分属,而总不离其宗。”这一看法是对前人释性通、释德清等人以“外杂篇为内篇蔓衍”说法的进一步发挥。但在具体认识上,林云铭对内外杂篇的关系作了独具特色的理解:
《外篇》《杂篇》义各分属,而理亦互寄。如《胼拇》《马蹄》《胠箧》《在肴》《天地》《天道》,皆因《应帝王》而及之,《天运》则因《德弃符》而及之,《秋水》则因《齐物论》而及之,《至乐》《田子方》《知北游》则因《大宗师》而及之,惟《逍遥游》之旨,则散见于诸篇之中。《外篇》之义如此。《庚桑楚》则《德充符》之旨,而《大宗师》《应帝王》之理寄焉;《徐无鬼》则《逍遥游》之旨,而《人间世》《应帝王》《大宗师》之理寄焉;《则阳》亦《德充符》之旨,而《齐物论》《大宗师》之理寄焉;《外物》则《养生主》之旨,而《逍遥游》之理寄焉;《寓言》《列御寇》总属一篇,为全书收束,而内七篇之理均寄焉。《杂篇》之义如此。若《刻意》《缮性》,义有所属而无味;《让王》《说剑》《盗跖》《渔父》,义无所属而多疵;昔人谓为昧者剿入,非虚语也。《天下》一篇,则后人订《庄》者所作,是全书之后序耳。[2]
在他看来,庄子外篇意义单纯,由内篇相因而来,“义各分属”。而杂篇每一篇的主要思想都是内篇中某一篇思想的发挥,但又同时搀杂了其他篇章的一些理论,“理亦互寄”,其中《刻意》《缮性》《让王》《说剑》《盗跖》《渔父》六篇为伪作,而《天下》篇是后人所作,为全书后序。这样,《庄子》一书即通篇一旨,前后贯通,富有逻辑。明人潘基庆在《南华经集解》中,就将外杂篇分类附于内篇之后,以此说明外杂篇与内篇的关系。林云铭的理解显然比他又更深入了一步,在庄子研究史上颇具特色。
(二)对篇章文脉的用心梳理
南宋以来,随着文章学理论的发展,学者们慢慢发现,《庄子》文章并非无章法可言,而是独立成文,首尾一体,脉络贯穿。从南宋末年林希逸以来,人们就开始用心于《庄子》的行文脉络,以求《庄子》文义畅达,后来的禇伯秀、罗勉道等人也都尝试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但只止于分析个别字句及个别篇章,还缺乏完整的结构意识。到了明代,随着文学观念的增强,《庄子》文章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明初的道学家方孝儒素以宣传道统思想为己任,但读了《庄子》之后也不得不承认:“庄周为人有壶视天地、囊括万物之态,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飘飘然若云游龙骞不可守。”(《张彦辉文集序》)因此明代学者更为用心地研究《庄子》文脉,特别是陆西星,他在细细研读《庄子》之后,提出了庄文具有“草蛇纩线”“藕断丝连”的特点,准确而又形象,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可,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清代,林云铭“以时文之法读庄子”,更为重视“阐发通篇血脉”。他反对那种认为《庄子》一书“无首无尾、无端无绪”的说法,认为这只会使《庄子》“千层雾障,幻成迷阵”(《楚辞灯序》)。在他看来,古文无不可解,哪怕像《庄子》这样“文字中鬼神,独步千古”(同上)的奇书也是如此。所以他注《庄子》《楚辞》都“止求其大旨吻合,脉络分明,使读者洞如观火。”(《楚辞灯序》)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逐句辨定,逐段分析”,对上下文的来路去路、埋伏照应、承上启下处等等一一注出,力使《庄》文“有端有绪”。
首先,他对文中起关键作用的字词的来龙去脉花费了大量笔墨来细细爬梳,这种工作前人几乎没有做过,而林云铭在分析很多篇章时几乎做到了字字有来处,充分体现了他“誓不复留毫发剩义”的良苦用心。如在《齐物论》篇“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一段中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句后分析说:“‘见’字、‘知’字皆自上面‘明’字生来。”在“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句后分析说:“‘照’字根上‘明’字来,‘天’字生下‘天均’、‘天倪’等字,此句最是肯綮,‘因是’两字,是《齐物论》本旨,通篇俱发此义。”又如《人间世》中分析说:“‘气’字、‘心’字看得甚细,下文‘听之以心,听之以气’,与此呼应极灵。”“‘感’字应上‘所感’,‘门’字应上‘医门’,‘毒’字暗应上‘菑人’句”等等,真是不厌其烦。此外,他还不惜笔墨将文中起承上启下的句子、前后遥相呼应的句子与句子、字与句子、段落之间以及篇和篇之间前后的来路都一一作了梳理。如在阐释《齐物论》篇“圣人不从事于务”段时说,“圣人不从事于务”句“起下六句”,“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句“承上六句,与‘不从事于务’句相应”,“参万岁而一成纯”句“顶上‘不就利’四句,生下‘生死梦觉’一段”,“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句“顶上‘有谓无谓’二句,生下‘我与若辩’一段”。又如阐释“分也者,有不分也者”一段说:“此段又从上段‘有言之意’透下,见得圣人虽有言,仍不起是非之意。看他双收‘道’、‘言’二字,应上双起,针线极密,此率然首尾也。”本来看似散乱的地方经其分析前后呼应,针线极密,首尾率然,连成了一片。总之,在林氏看来,《庄》文处处是伏笔,处处是呼应,纵横交织,文章贯通一气。可以说,在《庄子》散文研究史上,林云铭是对《庄子》文脉用力最多,研究最细的人。但也正因为如此,他将《庄子》支解得有些支离破碎,故四库馆臣说其书“支离弇陋”。林氏对《庄子》文脉的梳理虽然不免有些繁琐,但也不乏真知灼见,今天看来,很多地方还是有其道理的。
林云铭没有局限于仅仅对《庄子》文脉作条分缕析的技术处理,他深深地为《庄子》文章脉络隐密、构思巧妙的高超艺术所吸引,故而他在每篇文章之后用诗化的语言将全文的艺术魅力较为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让读者充分体会到了庄子文章的整体艺术特色。如他在《逍遥游》篇末总论中说:“篇中忽而叙事,忽而引证,忽而譬喻,忽而议论,以为断而非断,以为叙而非叙,以为复而非复,只见云气空蒙,往返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陆方壶云纩中线引,草里蛇眠。嘻,得之矣。”又如《齐物论》篇末曰:“文之意中出意,言外立言,层层相生,段段回顾,倏而羊肠鸟道,倏而叠嶂重峦。”又如《在宥》篇:“此篇以无为二字作线。……文之段落变化,顿挫耸秀,议论奇横,理窟精深,笔底烟霞,胸中造化,非读万卷者不敢仰视。”他这种较为完整系统地来阐释《庄子》文章艺术特征的做法,上承陆西星,下开一代学风。不仅使后人对《庄子》文章的批评鉴赏更加系统完善,也使后人更为用心于对《庄子》文章结构的深入剖析。遗憾的是,林云铭与后来的宣颖等人相比,还缺乏“结构”概念,没能将庄子文章内部逻辑层次关系较好地梳理出来。
三
林云铭为学主张要探求作品的“命意之深,寄意之远,措意之巧,抒意之工。”(《古文析义序》)即重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他看来,庄子是天下至文与至理的完美契合,“须知有天地来,止有此一种至理;有天地来,止有此一种至文,绝不许前人开发一字。至其文中之理,理中之文,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因此,他反对那种只追求文章形式,不重主旨的做法,“今人诵其文,止在字法、句法上着意,全不问其旨之所在,此大过也”(《庄子杂说》)。主张在分析文章技巧的同时,更要积极求取庄文之旨。林云铭的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在《庄子》散文研究史上以至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仅就《庄子》散文研究来讲,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他以前,文章形式技巧与义理的分析都是割裂的,注家或只欣赏《庄子》文章艺术,或只重视其哲理思想,即使那些“释义兼评”型的评点著作,也只是义是义,文是文,还没有哪一个学者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庄子》文与理的不可分割,更没有人提出这种文理并重的治学思路。林云铭第一次明确了这种概念。尽管他的评点还没有像后人那样做到文理的水乳交融,但他已经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了。就这一点来说,已功不可没。
林云铭在评点中较好地实践了他的理论。“《庄子》篇中,有一语而包数义者,有反复千余言而止发一意者,有正意少而傍意多者,有因一言而连类他及者,此俱可置勿论。惟先求其本旨,次观其段落,又次寻其眼目,照应之所在,亦不难晓。”(《庄子杂说》)要求在求得本旨的基础上,分析文章形式,因而他十分重视总结每篇文章的立意即中心思想,作为通解全篇的钥匙。如他解读《逍遥游》篇时认为通篇“‘大’字是一篇之纲”,在解读《大宗师》篇时说“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二句是“通篇扼要处”,在解读《缮性》篇时说“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等句是“通篇之纲”,等等。他在注文中对文章具体内容的分析,都是紧扣这个中心思想展开的。如他在《逍遥游》篇开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下说:“总点出‘大’,‘大’字是一篇之纲。”在“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下说:“分点出背之大。”在“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下说:“所覆者广,分点出翼之大”等,并于篇末总评中以“大”为纲对全文进行了归结:“逍遥,徜徉自适之貌;游,即所谓心有天游是也。此三字,是庄叟一生大本领,故以为内篇之冠。然欲此中游行自在,必先有一段海阔天空之见,始不为心所拘,不为世所累,居心应世,无乎不宜矣。是惟大者方能游也,通篇以‘大’字作眼,借鹏为喻。意以鹏之图南,其为程远矣,必资以九万里之风,而迟以六月之息,盖以鹏本大,非培风不能举,况南冥又非一蹴可至者。……至如鹏之适而斥鴳之笑也,诚不异于二虫所云。此无他,小大故也。彼世之一得自喜者,何以殊此?乃宋荣子进矣,以未树而未大;列子又进矣,以有待而未大。惟夫乘阴阳二气之正,御六时消息之变,以游于不死之门,方可为大,即所谓至人、神人、圣人是也。如何徵之?如许由之不为名也,此无名之一证也;藐姑射之不为事也,此无功之一证也;尧之窅然丧天下也,此无己之一证也。皆能用之,以成其大也。然非致疑于大而无用也,故不龟手之药,得其用则大,不得其用则小。居心者视此矣!抑非必求其有用而始为大也,故狸狌、斄牛,或以有用而致困,或以无用而免害。应世者视此矣!大瓠也,大树也,又一鹏也,何不可遂其逍遥游哉?人惟求其大而已。”全文紧扣“大”字,充分表达了其以“大”为逍遥的观点,文理并重。像这种紧扣中心,梳理文意,总结艺术的做法前人是没有过的。林云铭这种文理并重的治学理路开创了庄子研究的新局面,清代的《庄子》散文评点大都是在这一思维下进行的。
四
林云铭博学多闻,涉猎广泛,淹贯经史,精通《庄子》《楚辞》。他自小嗜好古文,尤善于钻研古文精义。陈一夔云:“先生于经史无不淹贯,又探奇于庄、屈,取法于史汉,摹神于唐宋大家,宜其才雄力厚,品格高古,而姿韵悠扬,不愧当代作者。”[8]清初学界对时文与古文的争论十分激烈,林云铭作为一个复古主义文人则极力倡导古文,旗帜鲜明地反对时文。在《古文析义·序》中,他说:“余自束发受书,即嗜古文词,时塾师亦仅取坊本训诂口授,然余终疑古文必不如是作,在后人亦必不应如是读也。比长偶取一二篇,逐字逐句,分析揣摩,反覆涵泳,遂觉古人当年落笔神情,呼之欲出,狂喜竟日。”(《挹奎楼选稿》卷六)由于醉心于古文,林氏对当时的时文以及学者们浸淫于八股求取功名的作法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
余十馀龄学为制艺,即嗜先正诸大家传文,时当明季,风气数变,始而骈偶,继而割裂,终而诡异。余虽不能尽屏时趋,然必以讲贯题旨,理会题神,相度题位,阐发题蕴为第一义,但苦无可与语。尝抚几自奋曰:“文章定价寸心千古,若仅粗记二三百篇烂时文,影响剽窃,逐隊棘栫中,学做誊録生,走笔写就,纵掇上第通显,亦不过如乞儿弄猢狲,扮鬼脸戏,唱几套烂熟曲子,向市井驵僧手中,讨得百十铜钱,途遇群丐,持出相夸,诚可哀也。”(《四书存稿·自序》)
嗣余遁迹西湖,浮沉市肆中,碌碌俗缘,所见所闻,大率较论八股,为猎取科第梯航,不则或诵习词章倡和,以博声气。(《天经或问后集·序》)[8]
林云铭对时文的批判可谓大胆、激烈,表现出了与时文格格不入的态度。在《庄子因》一书中,林云铭亦借解读《庄子》缕缕表达了这种思想。如《外物》篇“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一则寓言故事中,庄子以“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来讽刺那些“辁才讽说之徒”,林云铭评点曰:“近日穷措大抄写数篇烂时文,向邑令投拜门生者,当书此数语示而辱之。”又在《天下》篇篇末说:“此篇为庄子全书后序,明当日著书之意,一片呵成文字。……岂若后世浅儒粗就一篇烂时文,便自署其姓字于上,灾梨以自夸诩,徒以供覆瓿之用,当使古人笑,人人至今齿冷矣。”受小说戏曲评点社会批评思维模式的影响,他将自己对社会风气的批评与不满融入到了解庄中,表达了对时文的强烈反感与蔑视。林氏不趋世俗,“不达时宜”,个性鲜明,“数十年间迫之以患难坎坷,錬之以穷愁抑郁”(《挹奎楼选稿·序》)。但他并没有趋从时俗,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志业,终生以研治古文为乐,“手不绝吟,手不停披”(《挹奎楼选稿·自序》)。在创作诗文、披点古文中寻找着快乐,抒发着不满,寄托着情思。就这一点来说,馆臣及后人对林云铭的看法未免过于武断。
其次,林云铭的这种以“法”解《庄》的治学思想看似极为冷静地理性剖析与直面《庄子》,尤其是条分缕析地对《庄子》文章的技术处理,给人一种浅薄的印象,容易使人产生割裂、繁琐而又空洞之感。其实,我们联系他的遭遇,细细阅读他的一些作品,却发现林云铭评点《庄子》散文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他内心对《庄子》极为感性的情感世界,以及他借解读《庄子》表达自己无可奈何的人生态度。试读他的原《庄子因·序》:
余支离成性,不为事物所宜,于庄为近,故少而好之,久而弥笃。少长,涉猎伭门诸书,私念人生地上寓也,其与几何?逍遥寝卧于无何有之乡,一笠一瓢,此生之事业毕矣。戊子以来,历今十有六载,其间天损人益之洊加,俾畏人之鷾鸸,难以自遂,不得不智效一官,舍鹏飞而从鷃笑,自是以后,为樊雉,为庙牺,为雕陵异鹊,求其俯仰而不得罪于人,此其难者。故有甚忧两陷,螴蜳不得成阴阳之食人,与金木之讯者等。吾友邵是龙善于庄,案牍之馀,为余谈及,余聆之若昆弟亲戚謦欬于藜藋鼪鼬之迳也。急索书竟读之,则见见闻闻,旧国旧都望之畅然矣。夫虚己游世,人莫能害,而流遁决绝为大道所不出,则今日之余祸福淳淳,想与为风雨寒署之序,举不足以滑成,斯其所得于庄者,固不在区区筌蹄间也。但大道日漓,去古渐远,谈庄之家自郭子玄以后,言人人殊,究为鲁遽之瑟,无关异同,使人徒受其黮闇,适得存焉。余考证诸本,参以管见,栉比其词,隐括其旨,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治庄之道,读庄之书,求合乎作者之意而止。异日者,骊龙未寤,腐鼠已捐,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将手此一编,以质于大莫之国,若谓漆园功臣,漆园罪人,呼牛为牛,呼马为马,余何蕲乎而人善之,而人不善之邪?亦因之而已矣,遂以为名。[8]
《庄子因》旧本我们已难以看到,但其原序与今天增本的序文已大相径庭,此序文是其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庄子情结与庄子情怀的真实反映,是他人生态度的真情流露,寄寓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面对世事变化的无奈与悲情,以及对庄子追求精神自由的高度认同。《庄子》伴随其一生,是其感情的慰藉。他在《楚辞灯·序》中说:“余少痴妄,不达时宜,私谓用世可以得行其志,及筮仕后,所见所闻,皆非素习,以故动罹谴诃,每当读骚,輙废书痛苦,失声什地,因取蒙庄齐得丧、忘是非之旨,以抑哀愤。”[8]又在《贺武平卫邑令左迁序》中云:“余曩理新安,亦常执不材鄙见与大吏忤,屡陷于阨,因念齐得丧、忘是非之旨,莫过于蒙庄,取而表章之以俟知己。……然后扬搉蒙庄,处于材与不材之意,相与逍遥于无何有之乡,则梁丽殊器,大用小用,俱可置之勿论。”[8]林云铭的性格与其遭遇使他自觉地追随庄子的人生态度,处处以庄子的“齐得丧、忘是非”为人生信念,以庄子的“逍遥于无何有之乡”为精神追求,道家思想极为浓厚,影响了其一生,因而在《庄子因》中他“以庄解庄”,还原了庄子的本真思想。也许是由于时代的原因,林云铭在评点《庄子》的过程中却将现实生活中自己的种种隐痛深深地隐藏了起来,而通过对《庄子》文章艺术的无比陶醉与欣赏寄托着自己的情思,流露着自己的庄子情怀。尤其是他对庄子“情”的阐发,发人深思,影响深远。
[1]王夫之.庄子解[M].清同治四年湘鄉曾氏金陵节署重刊本.
[2]林云铭.庄子因[M].清乾隆白云精舍刊本.
[3]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一)[M].四库全书本.
[4]李梦阳.空同集(卷六十二)[M].四库全书本.
[5]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八)[M].四库全书本.
[6]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四)[M].四库全书本.
[7]林云铭.楚辞灯[M].清康熙36年挹奎楼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8]林云铭.挹奎楼选稿[M].清康熙三十五年陈一夔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