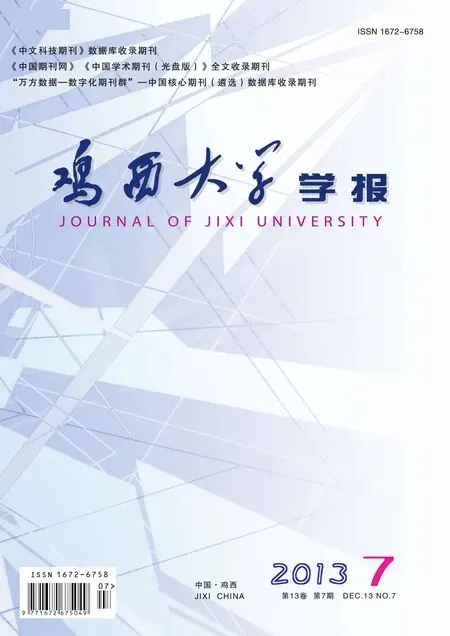从“顺从”“叛离”到“回归”
——探究巴金小说中的“家”情结
彭 弥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从“顺从”“叛离”到“回归”
——探究巴金小说中的“家”情结
彭 弥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从《家》中觉新式的“顺从”到觉慧式的“叛离”,再到《寒夜》中汪文宣欲“守家”而不得的一系列文本呈现,反映了巴金从早期批判“家”的无形束缚和有形捆绑性转向了后期“怀家”“守家”的温情笔调。他的这一叙事转向正是因为受到了“家”情结的牵引而对“家”的温情围困给予了深入的思考。
家;顺从;叛离;回归;围困
有关“家”的话题历来是作家笔下永恒的创作主题。巴金现代小说的创作中,从早期《灭亡》《新生》中的厌家、《家》的弃家、到中期《憩园》的怀家和后期《寒夜》的无家可归,全面展示了“家”情结对中国现代社会中各色人群的影响,也影射出巴金对于“家”的复杂情感和深入思考。巴金笔下的高觉新、高觉慧和汪文宣就突出地代表了他不同时期对“家”的顺从、叛离和回归的挣扎与思考。
一 顺从——依附“家”的无形束缚
在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家族非常重视血缘谱系的延续,侍奉双亲、传承香火、不违祖训等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族情怀。钱穆曾指出:“‘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1]“家”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中人的存在状态、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以小说《家》中高觉新为代表的即是顺从宗法制家庭的典型人物。
从整个高家的结构模式来看,它是一个标准的金字塔形。无数的“砖块”即家族中的成员均按照“三纲五常”和“君臣父子”这些封建伦理规范来排列,各个层级具有严密的等级结构。高老太爷是整个高家的最高统治者,处于塔尖位置,居高临下地统摄着整个高家;其次是由克明、克定、克安、周氏、王氏、沈氏等一支庞大的腐化堕落的集团组成;再者是由觉新、觉民、觉慧等一群年轻人组成,最下层是由鸣凤、婉儿等组成的完全受奴役的仆人组成。
“儒家文化的精髓就在于它把封建制度权利结构伦理化和神圣化,并把人的存在价值规定为这种宗法结构形式的服从和服役,即使掌握了某种权力,也应当服从和服役于这种政治形式。”[2]这在奉行“不抵抗主义”和“作揖哲学”的长房长孙觉新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不过了。为了实现祖父“四世同堂”的心愿,他被迫舍弃了自己的理想和爱情,终止学业,与一个陌生女子结婚生子;为了让祖父安心,他阻止二弟觉民抗婚和三弟觉慧的出走;他明知道所谓的“血光之灾”是无稽之谈,却不敢站出来争辩,以至于让心爱的妻子难产而死。这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熏陶下的孝子,履行了所谓的“孝”,却葬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和梦想。正如黑格尔所分析的,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在家庭之内,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3]觉新已经被封建宗法家庭中的嫡长子制完全异化了,他只是一副懦弱的躯体,毫无自我价值的内核,而完全顺从于伦理纲常和等级制。
此外,梅芬的郁郁而死和瑞钰的难产致死也是顺从传统观念和封建家庭制度的悲剧。巴金在回忆录里说:“父亲的死使我更看清楚了我们这个富裕的大家庭的面目。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压迫像沉重的石块重重地压着。”[4]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家”构成了一种强大的统摄力和束缚力,使家众都顺从于这种力。“家”的利益弱化了个人行为,自我的价值、尊严、个性都处于从属的地位,甚至被无情地践踏。巴金的《家》正是通过觉新、梅芬、瑞钰等人的悲剧批判了这种旧有家庭文化的局限。
二 叛离——冲破“家”的有形牢笼
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从传统文化场中走出的青年一辈理性地认识到家族这个社群对个体存在的威压,转而把西方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奉为精神指南,从而逃离家族牢笼,实行对“家”这座金字塔的突围。觉慧即是叛离者的突出代表。他积极地参加爱国学生请愿,大力支持觉民的“逃婚”斗争,勇敢地同婢女鸣凤恋爱,并强烈声讨长辈们抽鸦片、赌钱、养小妾等腐化堕落行为,最终义无反顾地逃离了封建大家庭。他觉得家“不过是一个‘狭的笼’”,多次坚决地喊道:“我要做一个旧礼教的叛徒。”“我要逃出这个家,再也不回来了”。觉民也在信中表示“……我决定走自己的路,我毅然地这样做了。我要和旧势力奋斗到底。”琴也立志“做一个人,一个和男子一样的”新女性。
正是这些叛离者构成了家族故事的基本叙事主链:“‘他者’因素侵入传统家族空间——家族任务势能被激活,家族人物互相纠结抗衡——稳固的传统家族‘差序结构’受到冲击,家族分裂,叛逆者冲出家族‘围城’。”[5]在这里,叛离就代表了一种意志,叛离者深切地感受到了家族文化的负面影响,叛离意向即突显为他们追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愿望,更预示了传统大家族的衰亡。家族批判就成了一个主流意向。就是觉慧这样的“叛逆新人”给封建大家庭增添了异质因子,加速了封建家族的毁灭,成为了旧秩序的掘墓人。巴金也跟觉慧一样在青春的年纪,靠着青春的热情和鼓舞如饥似渴地阅读过宣扬进步思想的杂志,密切关注着学生运动的发展事态,他还参与创办了新兴进步杂志《半月》等。巴金曾在回忆录中表示:“‘幼稚’和‘大胆’救了我。在这一点我也许像觉慧。我凭着一个单纯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个目标走去: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许我做的事。”[6]正是有着冲破封建大家庭阻力的决心和信仰的鼓舞,使巴金同他笔下的觉慧一样也做了一个大胆地叛逆者,无情地控诉着旧时代和旧秩序的黑暗
三 回归——眷恋“家”的温情诱惑
“叛离既是传统家族没落时所必然出现的图景,也为现代作家重新设置迥异于传统的家庭提供了逻辑起点,‘叛离——寻找——重建家园’是其基本写作模式。”[7]受传统家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难以抗拒“家”的温情诱惑,成为叛离者的无意识牵挂。当青年一代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冲出封建旧家庭的堡垒时,却又因根深蒂固的“家”文化情结所羁绊,导致他们产生悬浮半空的失“根”焦虑,因此,处于文化转型期的青年们宿命式地陷入了个体与家族纠缠不清的两难境地——理智上的摒弃与情感上的依赖,以及行动模式上的出走与心理意义上的回归,“使家族成了屹立于他们生存境遇之上的一座‘围城’。”[5]这类人物以汪文宣为代表,很多论者在比较《家》与《寒夜》时,都认为汪文宣身上有觉新和觉慧的双重影子。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有过开办乡村教育的远大理想,也反对举行结婚仪式,与曾树生自由恋爱并同居,然而这个积极争取个性自由的革新派青年,却在建立家庭后,磨灭了他当初所有的理想,他起初像觉慧一样义无反顾地摒弃了旧有的一切,而后却依然回归于家庭中,甚至像觉新一样卑诺地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汪文宣痛苦地挣扎在母亲与妻子之间,只是想维护这样一个名存实亡的家。
此外,在《家》中也可以看到“家”对叛离者们的温情围困:当觉慧准备逃离家时,觉民还在犹豫,因为这时的他有了琴,还要考虑到姑母,念及这个“家”而暂时舍弃了离家的想法。而且对高老太爷的感情,也并未停留在痛恨和批判上,在高老太爷临死的时候,也描写了温情感人的一幕。我们不得不思考,当初那么执意离开封建“旧”家,奔向社会这个“新”家的觉慧在自己组建家庭后会不会就成了下一个汪文宣呢?而与觉慧一样有过离家出走经历的巴金,回到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老家寻根祭祖并重修了祠堂,说明了“家”情结在他心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位置,“家”具有一种神圣的血缘关系与难以割舍的情感。
四 结语
家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天然感情处所,无论作家以何种眼光和态度看待家,没有人能真正摆脱它的诱惑。家族所营造的亲情氛围对任何人都弥足珍贵。早年的家庭生活和结婚以后的经历使巴金对“家”产生了特殊复杂的情感,他一方面痛斥封建伦理文化和家族制度对人们的摧残,另一方面却也无意识地流露着对普通之家的眷恋和羡慕。在巴金看来,不合理的制度是造成一切不幸和灾难的根源。因此他巧妙地构筑了以“家”为中心的叙事话语语境,借黑暗没落的高公馆作为批判的中心标靶。但是后来巴金也说到:“然而理智和感情常常有不很近的距离。那些人物、那些地方、那些事情,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任是怎样磨洗,也会留下一点痕迹。”[8]说明巴金同样受到了“家”的温情围困。自1946年以后巴金再也没有进行过以反抗封建家长制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了。“因为家庭结构的实质没有变,《寒夜》里所提出的仍然是‘走’出家庭的问题。《寒夜》与《家》所存在的内在的一致性与延续性,正内孕着‘历史循环’的时代悲剧内容:这是巴金痛苦而又深刻的‘发现’”。[9]中国现代小说主要停留在对家的专制性和迫害性的批判上,而“家”繁衍后代、组织生产等基本功能却被淡化遮蔽了。巴金从批判封建大家庭转向对“家”内核的关注,正是受到了“家”情结的牵引而产生了这种叙事转向,进而对“家”的温情围困给予了深入的思考,是对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所揭示的“中国传统之家走向何处”命题的进一步探索。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商务印书馆,1994:51.
[2]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57.
[3]黑格尔.历史哲学·东方世界中国[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164-167.
[4]巴金.巴金全集(第1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398.
[5]李永东.颓败的家族——家族小说的文化与叙事研究[M].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10,2.
[6]巴金.巴金选集(第10卷)[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143.
[7]肖向明.家族文化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J].学术研究,2005(6):134.
[8]巴金.巴金全集(第1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441.
[9]王建平.重读《寒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1):36.
ClassNo.:I206.6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郑英玲)
ExplanationofFamilyComplexRevealedinBaJin'sNovels
Peng M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Sichuan, Chongqing 400715,China)
Those events happened, from Jue Xin’s obedience to Jue Hui’s rebellion described in the novel Family to Wang Wenxuan’s intention to protect the family but failed in Cold Night, reveal the change of. BaJin’s writing thought, which is turned from criticizing from the intangible binding for personalities to the protecting the family . The change of writing i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omplex and it is a reflection of the family value.
family; compliance; renegade; regression; besiegement
彭弥,在读硕士,西南大学文学院2012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1672-6758(2013)07-0088-2
I206.6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