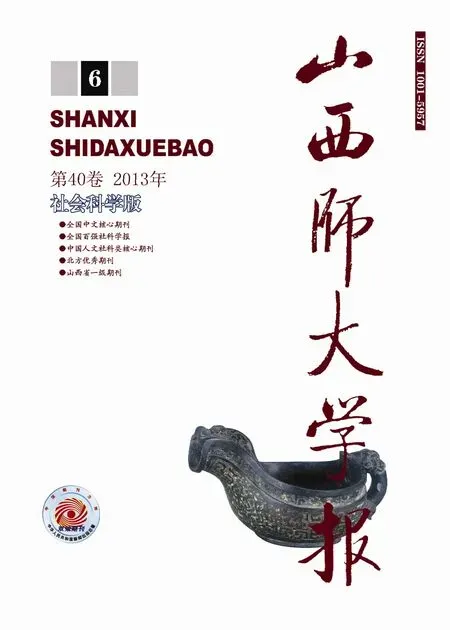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重思想取向
刘歆立
(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郑州450002)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奠基人和重要推动者,根据实际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赋予其民族化的中国形式而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厘定与认识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彰显出的多重思想取向,对当前我们坚定理论自信与进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直面问题的实践取向:重视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毛泽东之前,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革命领袖,在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为使这些思想在中国本土化、大众化而提出了一些接近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概念与革命思想,例如李大钊早期的民彝史观与青春哲学、陈独秀的进化论历史观等。由于这些哲学概念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不够紧密而渐渐湮没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而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哲学范畴与新的理论命题,例如《实践论》中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认识运动的总规律等,《矛盾论》中提出的矛盾普遍性涵义、矛盾问题的精髓等,《改造我们的学习》赋予“实事求是”这一古老的词语以新的思想内涵,等等。这些思想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了崭新的理论形态和理论内容,而且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走向成熟、走向世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理论家的毛泽东,毕其一生反复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与道路。他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我写《新民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1]243可见,毛泽东向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他又始终保持着极力避免犯“不从具体的实际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1]711的错误倾向。在毛泽东眼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却不可能找到“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这种特殊性。这是因为,毛泽东深知拿既有理论剪裁中国革命现实,走“实践服从理论”的唯心主义路线,必然会遭遇“实践的滑铁卢”。教条主义者的屡屡受挫以及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足以证明这一点。
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通过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革命得失成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来反思发展自己的革命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中国国情这种独有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的惊人洞察,“为毛泽东实践哲学的思考和构建奠定了一个实践的平台,使毛泽东能够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与中国的传统哲学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化的实践哲学”。[2]151毫不夸张地说,无处不体现着唯物史观精神与彰显着辩证法光辉的毛泽东诸多著作,例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都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或缺的理论准备,是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活教材,是非哲学著作形式的哲学著作。事实上,也唯有这种来自于革命斗争实践的活的哲学,才带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走出“左”和右思潮造成的理论“死胡同”,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春天,使中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地。因而,后来毛泽东也总结指出:“单有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没有列宁哲学就不能解决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产生的新问题;单有列宁哲学,没有《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中国哲学,同样不能解决中国革命出现的新问题,不能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3]109—110
二、古为今用的本土取向:立足于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尽管产生于西方,但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相通性。而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的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中,顺理成章地将中国历史文化的厚重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间正道熔铸在一起,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4]707,并在不断汲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养分中枝繁叶茂,具有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斯诺在《西行漫记》说道:“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5]65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不仅为毛泽东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的学识素养,而且也为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发生“视界融合”并生成新的哲学视界作了发生学意义上的准备。正如伽达默尔所理解的,这种融合不是同一或均化,只是部分重叠,它必定同时包括差异和交互作用。视界融合后产生的新的融合的视界,既包括理解者毛泽东本人的视界,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视界,但已经无法明确区分了。它们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的一体化关系。不仅如此,毛泽东所开创出的新视界还超越了原有视界的问题和所及思想范围,为中国革命别开生面地发展提供了发展路向。[6]500
可以说,传统文化的影子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俯拾皆是。“实事求是”、“矛盾”、“知行关系”等这些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学范畴均来自于毛泽东对古代词语的直接化用。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指出:“形而上学,亦称玄学。”“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7]300—301通过对传统辩证法的扬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法相结合,使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执两用中”等传统朴素的辩证思维方法,经过毛泽东的继承借鉴与理论创造,从而具有了现代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形态,成为中国人民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还实事求是地肯定了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他指出:“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9]4371955年,当谈到物质的构造时,毛泽东说:“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说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用“一分为二”来表述对立统一规律,是对《易传·系辞上》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辩证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他还将《老子》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的思想概括为“相反相成”一语说明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用孔子的“内生不疚,夫何虑何惧”与苏东坡的名言“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人必疑之,而后馋入之”论述内外因关系原理。引用《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警醒人们“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等等,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湘学既是一种地缘性特征显著的湖湘文化之精髓,也是经世致用的中国文化传统在近代复兴的表现,它以推崇立志的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与主张躬行实践而著称于世。毛泽东自幼成长与浸润于这种地方性的文化传统氛围中受其影响自不待言。传统的经世致用因素转而成为重要的支援意识,构成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的文化基因。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主要是一个考据学的命题,标志的是一种埋头故纸、脱离现实实际的学风;而毛泽东所阐释的‘实事求是’与这种考据学的‘实事求是’显然是大相径庭的。实际上,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命题另有其思想渊源,这就是湘学中的经世务实传统和注重现实实际的实事求是精神:这一传统和精神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使得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能够独具卓识地提出‘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命题。”[10]“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使他主要关注现实和民生,“主要关心的是理论在当下的正确性,而不关心与其他假设进行的抽象的比较。毛泽东想要洞穿这个问题的本质,同时利用全体一致的假设(“大家晓得”)来建立起他对于该问题的系统阐述,并利用中国历史和现代国家中广泛的实例来支持实际的判断”。[11]33
三、心系大众的人民取向:依靠人民力量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把握与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等唯物史观真谛的自觉信仰。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许多新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内容,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首先,毛泽东用中国人民习惯的思维方式与熟悉的话语方式生动地阐述了人民史观的基本思想。毛泽东经常讲到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最大”等名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观点的直接表达。“‘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12]933更是运用中国人民熟识的历史典故来形象地表达“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基本观点的典范。
其次,在实际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毛泽东在1934年1月27日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明确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525—526在明确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具有人民性的同时,继而指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7]139。随后的《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进一步认为:“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4]381,从反面说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
毛泽东还进一步结合中国八年抗战的历史深刻地具体论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他在包含着大量军事哲学思想的《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381,反映了他一贯坚持的人民战争思想;“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4]480表明了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库中找到了指导中国人民正确抗战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这些理论与观点的形成与发展,和他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际需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不开的。与当时其他的一些党的领袖,例如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都狭隘地、错误地把马克思恩格斯讲到的“人民群众”片面化为工人阶级形成鲜明对比。正是由于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充分认识到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的作用,他才不止一次地将党群关系比喻为鱼水关系,强调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对我们党的革命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13]547因而必须明白,“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4]522“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4]522这些看法从不同的理论角度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力量。
再次,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新的实践需要发展出一系列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并把这些体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本原理应用于指导革命与建设。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判断一个政党历史地位的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4]409这个标准可以说是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先声。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即提出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区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等思想。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将这些个人的理论思考转变为指导新中国建设发展的指导思想,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代表中央明确提出使我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即“两个转变”并举的思想。1953年12月由毛泽东最后确定的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把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主体。1956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思想等,应该说都基本体现了革命和建设的时代主题,而变革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是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国家建设和维护与实现全国人民利益的生动体现。
最后,毛泽东著作大量地使用了明白易懂的群众口语与各地谚语,使用了贴近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典故事例。这一特点使毛泽东思想对中国人民来说具有天然的理论亲和力。例如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等口语化的名言,“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闭上眼睛捉麻雀”等形象的譬喻,以及对“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等民间俚语的辨析,等等。
四、实事求是的真理取向:在克服错误思想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客观地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必然要借助于同错误思想路线作斗争才能实现。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轨迹,其之所以始终同“两种主义”作斗争胶着在一起是迫不得已的革命斗争形势需要。例如《反对本本主义》提出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了发展线索与理论内核,并为以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中国化提供了起点和方向。一般认为它是整个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初步形成的标志。[14]242这篇文章的确批评了那种安于现状,不求甚解或只知按本本办事、死抱着旧条框不放的人,认为他们坚持的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想路线,共产党人应当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但纵观全文,整篇文章主旨是提倡把调查研究同坚持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结合起来,而不是刻意地寻找理论敌人进行理论斗争。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教条主义盛行,将脱离中国实际的“国际指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圣化、教条化,全然不顾中国的现实。立三路线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导致革命屡屡受到重创,几乎断送了红军、断送了革命。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高屋建瓴地认识到,无论“左”的教条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都犯了唯心主义错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基本要求,割裂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系,走上了“主观决定客观,理论剪裁实际”的歧路。这种认识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地茁壮成长,一方面也显示了其经受革命斗争实践的试金石考验所显示出的巨大理论力量。
针对立三路线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唯书”、“唯上”导致革命屡受重创的错误,毛泽东坚定他要“踏着社会实际说话”的哲学立场,将问题思考的着眼点聚焦于中国社会现实和人民大众的生活,根据革命的实践需要研究理论问题,事事处处力求实事求是,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路线。基于当时错误路线产生的认识论根源与思想根源,毛泽东立场鲜明地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7]112从哲学立场上,既肯定书本的实用性,又强调不能“唯上、唯书”、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圣化。同时,毛泽东剖析了中国革命中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认识论根源,指出教条主义正是否认了理性认识需要不断经受实践的检验,否认它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而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凝固化和公式化,无法做到有的放矢。
如何纠正教条主义呢?毛泽东从实践决定理论的哲学高度、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纠正了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开头”[7]109—110的唯物主义原则,指出能动性的局限性,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他强调,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是我们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巨大障碍,只有努力做“实事求是”的调查,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唯心主义的危害。毛泽东这种基于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还体现在他对待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问题上。在革命时期,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属于真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前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绝对化,把它视为亘古不变的真理,用“理论剪裁实际”,否认革命理论需要变化、发展;后者则夸大个人经验,否认有什么真正科学的革命理论存在。毛泽东深刻地批判了这两种错误倾向,反对任何把马克思主义凝固化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行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仍将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为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明了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断反思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文章中,他通过对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两个模范乡与汀州市的工作对比,指出汀州市扩大红军成绩极差的原因是对群众生活关心不够造成的,其理论表现出明晰的实践特色。后来,毛泽东思想和左右倾教条主义及经验主义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最终,在实践的推动下获得统治地位,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无不是基于实践的需要,立足于实际的需求,在与错误思想及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客观实际催生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这四重思想取向是一个相互连结并相互促进的整体。限于篇幅,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本文不再展开论述。
[1]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2]王玉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嬗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
[6]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周晓阳.论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J].南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3).
[9]中央党校.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哲学部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10]李佑新,陈龙.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湘学渊源[J].哲学研究,2010,(1).
[11](美)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M].雷伟岸,刘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4]张文儒,郭建宁.中国现代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