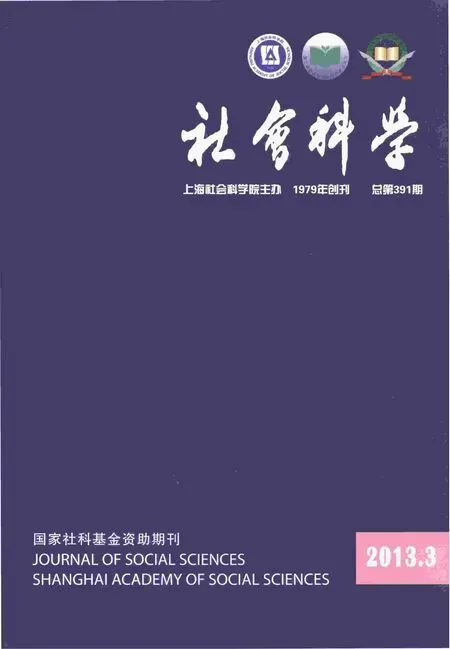实践理性抑或象征理性*——萨林斯对形式主义知识体系的解构与反思
马良灿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苏和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冲击,形式主义关于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念蔓延到各个学科之中,成为主导性学术话语。特别是在经济人类学中,很多人类学家按照经济理性原则来解构部落民族的经济社会生活,将该民族视为追求物欲和私欲的理性个体。这种将初民经济视为资本主义原始版的做法,歪曲了该民族社会行为的本质。在经济人类学领域,再次引发了一场针对部落民族经济社会关系本质的论战,即著名的“形式论”与“实质论”论战。持实质论的人类学家试图延续和重振波兰尼的传统,强调经济行为的社会文化基础,突出文化制度对人们经济社会生活的意义。他们反对将经济理性观念强加给部落民族,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虚构,背离了该民族经济社会生活的真实。
在经济人类学视野中,萨林斯是继波兰尼之后实质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将初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置于同一理论平台,通过对两者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的比照,从三个层面完成了对形式主义的知识论、价值论和理论硬核的解构。首先,从知识论层面,萨林斯对一百多年来盛行于西方学术思想中的实践理性观念进行了系统批判,形成了其关于文化理性制约经济实践、“物质实践由文化构成”的人类学命题。其次,从价值观层面,萨林斯探讨了西方人经济行为逻辑中关于“罪恶”、“利己”、“需求”等观念的宇宙观背景,认为这种以趋乐避苦、利己为基础的功利主义人性观是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原罪,是西方宗教宇宙观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复归。其三,在理论与经验链接层面,萨林斯通过对初民社会中人们经济社会行动的动机、生产模式、经济互动类型、交易方式的系统研究,驳斥了形式主义经济学中盛行的经济理性、理性选择、理性个体等抽象观念,使经济人类学回归到了正确的思想轨道。对萨林斯的新经济人类学思想的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西方经济社会科学认知局限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复杂多变的人类经济社会行动逻辑的理解。
二、对实践理性的批判及象征理性原则的阐释
萨林斯从实质论的学术立场,对功利论和实践论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关系的观念进行了深刻批判。这两种观念主张,文化制度是从物质实践活动及其活动背后的适用利益中逐渐形成的。实践论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形式,功利论强调的是制约物质生产利益的逻辑。萨林斯指出,实践论的主要学术流派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它主张文化理性由物质实践构成,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功利论的主要流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功能主义人类学,它坚持文化是行动者在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活动中积淀形成的,是行动者进行理性选择的主观结果。无论是功利论还是实践论,都是从“实践理性”立场,强调理性计算和理性选择逻辑对人类社会文化的限定,主张经济理性对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宰。从实践理性立场看,“所谓文化因素在那里相对于物质理性是‘外生的’,且典型地被视为其发展的一个‘妨碍’,因此是‘非理性的’”①[美]萨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张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实践理性主张经济理性逻辑对塑造个体人格的意义,这种观念构成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萨林斯明确反对用经济理性的观念来解读文化秩序,反对将文化贬低为个体追逐私利的结果。他指出,西方人错误地将经济理性视为人的本性,将物质追求视为人的目的。这种本末倒置的文化观忽视了经济的文化形式,曲解了象征理性对个体生命的意义。资本主义的商品化逻辑使人们的所有行为和欲求都用金钱来衡量。但这种经济理性事实上根植于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由事物的逻辑——意义属性与人们之间的关系所构成。因此,资本主义的金钱理性,尽管同土著人的物质实践方式不同,“但殊途同归,它只是更大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果”②[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新版前言),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页。。
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实践决定文化形态,它将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性逻辑服从于工作的工具性逻辑,……将社会存在的象征坐标转置成社会存在的结果”③[美]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205页。。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真正的中介因素是以劳动为基础的物质生产逻辑,文化仅仅是生产活动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生成。观念不组织经验,而是追随经验,生产是人们建立各种社会关系的前提。历史唯物主义将人与人的关系,正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简化为经济关系,这显然将人类真实的社会经验事实倒置了,“唯物主义成了‘唯经济主义’的一个变种”④[美]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205页。,人由此蜕变成没有文化个性与社会特质的理性动物。把生产关系消解成生产过程本身时,也就将文化逻辑消解成了工具逻辑,将生产的文化关系转化成了自然的关系。在唯物主义视野中,工具理性得到了伸张,但却以牺牲象征理性为代价。当马克思将人视为“类的存在物”时,人所“从属的‘类’,实际上就是‘经济人’”⑤[美]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205页。。这样,人们所有的社会经济关系都依赖于实践理性,依赖于劳动过程的工具有效性。依照这种逻辑,经济理性的实质不证自明,而文化则是物质实践的副产品。⑥张盾曾对萨林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进行了批判。参见张盾《保卫唯物史观:评萨林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
功利论明确倡导一种经济人的观念,将文化视为一种工具系统,视为满足人们物质欲求的手段。它关注的是个体为实现其利益和目的而采取的行动,“强调客观世界是依主体的需求而调节和定位的”①[美]萨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张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211页。。摩尔根是人类学功利论思想的主要发起人,他强调文化是人类的欲望和需求的产物。马凌诺夫斯基则是文化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与摩尔根相比,马凌诺夫斯基更明确地将文化视为实现人的欲求的工具,认为文化是从实践行动和实际利益中创造出来的②马凌诺夫斯基关于文化及其功能的更多阐述,参见[英]马凌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功能主义仅把文化属性当作表面现象看待,将文化视为满足冲动、欲望、天性和需求的手段,这无疑“用工具理性的刻薄真理消解了象征秩序”③[美]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220页。,扭曲了人类文化的本质。由此,自我利益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宰,文化也被简化成理性行动者从有目的的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副现象。这种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实用主义观念,漠视了人类行为的意义秩序。
萨林斯指出,无论是实践论还是功利论,都使文化理性从经济理性的逻辑中消解了。实践论在将生产看做是满足需要的、自然的、实用的过程时,陷入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论调。功利论强调人们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过程是谋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这种根深蒂固的实践理性观,构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论基础。但实际上,任何既定群体的“理性的”、 “客观的”图式都是“文化性地建构起来的”④[美]萨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张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211页。。甚至在完全相同的物质条件下,文化秩序都可能完全不同。萨林斯反对将文化系统从物质活动中抽离出来,反对经济脱嵌于社会。他批判到,不论是实践论还是功利论,都错误地将文化理性等同于各种适用性,将需求视为文化存在的根基:经济关系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社会关系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精神关系是为了满足经济需求。这种从物质欲求层面来理解文化形式、将文化视为物质环境的产物的认识是错误的。
萨林斯进而倡导一种“象征理性”的新观念。这种观念主张,“人的独特性在于,他必须……根据由他自己设定的意义图式来生活”⑤[美]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2页。。亦即文化是关于人与事物的意义秩序,这些秩序是系统性的,它绝不可能由物质实践随意地创造出来,人们的经济活动是文化系列不开分割的领域,不可能脱嵌于其所处的文化系统。因此,一个民族的经济社会活动只有置于该民族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才能理解,“经济活动是具体生活形式中,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的物质表达”⑥[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新版前言),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2页。。换句话说,人对生活的看法并不受物质条件的限定,相反,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决定着其物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方式,事物与观念、价值观与利益,均是文化的建构物⑦王铭铭:《萨林斯及其西方认识论反思》,载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代译序),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13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决定或者说包容了经济基础”⑧[美]萨林斯:《何为人类学启蒙:20世纪的若干教训》,载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附录),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9页。。犹如波兰尼所主张的人类经济行为应嵌入于社会之中,经济关系应纳入社会整体的脉络中进行理解一样⑨Polanyi,Karl,eds.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Glencoe:Free Press,1957,p.250.,萨林斯指出,象征理性决定经济实践,经济社会关系嵌入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意义秩序之中。这正是他所强调的,应当将“社会放置在历史中,把生产放置在社会中”⑩[美]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220页。。只要物质力量被社会所建构,其行动方式和社会后果必定由文化决定。
萨林斯指出,生产中的物质力量并不包含文化秩序,物质力量本身没有生命,其展开过程和结果只有通过将其与文化秩序的坐标联系起来方能理解。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部落社会,均强调特定的文化制度对经济社会关系的意义。部落社会强调亲属制度对人们经济社会生活的意义,而西方社会则强调生产关系的意义秩序。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也是一个文化系统,其独特性在于经济象征机制是以结构性的方式起决定作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物质基础及其社会存在形式是由它在文化系统中的整合程度决定的。就其对象征理性的依赖而言,西方工业文明与部落民族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西方人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毫不留情地摧毁其他文化形式。他们在追逐私欲的过程中,忘却了一个极为普通的常识,即“社会对自然的主宰,是受社会主宰的”①[美]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页。。
三、对功利主义思想与道德根基的质疑
功利主义为实践理性提供了价值基础。它主张从人的先天性和生物性来解释人类经济社会关系的本质。这种观念认为,人们进行经济社会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这种追逐私利的冲动是个体奋斗的动力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萨林斯指出,这种功利主义人性观源于西方古老的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宇宙观,其强调人性的善与恶,强调人性的堕落与贪婪,强调苦乐与人类苦难的天命价值论。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西方宗教神学思想的延伸,是西方人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社会之关系的现实表达。因此,只有对西方宗教神学关于人性论的认识进行系统批判,才能摆脱功利主义宿命,从根本上颠覆实践理性的价值与文化根基。
西方基督教神学强调人是罪恶之源,是追逐私欲的贪婪动物。人类始祖亚当违背了神谕。亚当偷食禁果后,已将人类带入了无知和贪婪的尘世中。在基督教神学观看来,上帝是永恒的、神圣的和完美的,而人却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是有限的、堕落的、世俗的和贪婪的。人之有限性成为了一切罪恶的根源。人注定要在满足自己生理需求的过程中耗尽其体能,但在满足欲求时,已冒犯了上帝。“由于人把对自己的爱放在对惟一能满足人之需求的上帝面前,人成了自己需求的奴隶。终归,上帝是仁慈的,他为我们提供了经济学这门知识。”②[美]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9、10、24、26页。而这门学科的要旨,正在于研究人类为满足私欲而进行理性选择的策略,在于探明人如何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回报。萨林斯指出:“正是基督教宇宙观中的那种不幸状态观,为自由意志向理性选择的提升设下了想象的空间。”③[美]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9、10、24、26页。如果说西方工业社会将经济人从基督教伦理的禁锢中解救出来,并允许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遮掩地标榜自己,那么,迄今为止,西方的人性观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人永远是一个不完美的生命体,其需求总是要超过他的能力,现代社会中的经济人依然是亚当,“这个有需求并由稀缺性予以驱动力的造物,并没有因时间推移而消亡,反而存活至今并成为一切人文学科的主要敌手”④[美]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9、10、24、26页。。
基督教神学对人性的认知与现代资本主义人性观之间存在悖论。西方人对自身欲望的极度关注,对教父来说是一种束缚,而在现代社会中却成为了个人实现自由的前提。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个人的需求与贪婪是社会美德的力量源泉与社会发展的基础⑤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者斯密在对人性及人的经济行为动机进行阐述时,曾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情感基础,强调同情心、良知和正义对于限定个体的贪婪与私欲的重要性。不过,他的这一观点并未在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引起共鸣,反而被后者所摒弃。萨林斯所批判的,正是建立在经济理性和功利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斯密关于经济行为道德基础的论述,可参见[英]斯密《道德情操论》,赵康英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人们聚集成群并发展社会关系,要么是出于有利可图,要么是将彼此视为满足自身目标的工具。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没有任何神圣存在于世间,人丧失了人格化特性,缺失了神人同形的主体性。
在基督教神学看来,人一半是神一半是兽,他不仅是一种双重的、分化了的生命,还被诅咒着拥有永恒冲突的精神和肉体。由于人本体上充斥着肉体和非理性力量,使他经不起贪欲的考验,从而出现“肉体因渴求贪欲而与精神冲突,精神也同肉体相冲突”⑥[美]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9、10、24、26页。。这种身体与心灵间紧张的二元关系乃是基督教神学的原罪。依照这种神学逻辑,似乎只有死亡才能医治一个人身体的堕落。因为只要是出于肉欲,肉体就总是精神难以对付的敌手。与精神的不确定性相比,肉体具有确定性,其质量、重量、体型和各种物质欲求均可计量。这种将人视为追求物欲的功利主义人性观,从根本上歪曲了人性的本质和人之所以为人的多重属性。
总之,在萨林斯看来,犹太教——基督教的神学观念,在造物主与造物、圣神与世俗之间形成了一条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在西方宇宙观中,上帝是绝对超验的,而自然则是纯物质性的。作为神和自然之中介的人类,唯有通过主观的苦乐体验方能理解生命的意义。基督教所起的作用,恰恰是在反对古典唯意志论当中继续扩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分离,这正是追随原罪而蔑视物质世界的必然结果。依照个人的苦乐体验来理解经验实在,用效用来协调客观性,是功利主义者处理社会经验现象的一贯逻辑。西方本土知识长期将客观性等同于理性:“物体的客观性由身体的健康代为经验。它是针对我们而言的客观性,是我们幸福的客观性。”①[美]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3、67页。而堕落的亚当成为了解读功利主义思想的道德前提,他通过对身体的感知来认识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人们趋利避害时,一切都降为简单而又悲哀的生活观。那些将生活界定为追求所谓幸福的人实际上是不幸的,因为“耶稣,从未笑过”②[美]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3、67页。,基督教神学观早已在西方每个人的心灵中种下了不幸的种子。
四、嵌入在象征理性中的部落民族经济社会关系
萨林斯对实践理性及其功利主义道德根基的质疑,其目的在于彻底摆脱政治经济学阴影,使人类经济社会生活回归并重新嵌入到象征秩序之中。他拒绝从经济理性逻辑出发来理解部落民族的经济生活。在他看来,部落民族在物质生产实践和经济社会交往中并没有明确的生产目的和物质欲求,经济关系呈现的是社会的物质生命过程,是“社会本身,是上天的智慧之神决定着经济学的观念。”③[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45页。因此,“社会是弥漫而无所不在的实在,它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包围我们,向我们渗透,指导我们的全部生活。”④[法]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交换》(第二卷),顾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99页。让人类学重返经验世界,关注和体悟部落民族真实的经济社会关系实践,是对实践理性最好的回击。
他基于丰富的田野民族志资料进行考察后指出,部落社会是一个富足的丰裕社会。狩猎采集民族的物质需求很容易满足,成功适应了其所处的环境。他们对自然的索求不多,满足需求的方式很多。人们量力而行,对食物和生计的追求是间歇性的,食物摄入是丰富的。因此,对部落民族经济的认识,不应想当然地将物质环境和经济结构联系起来,由此错误地推导出他们经济生活的艰辛。生活的闲暇是部落民族经济生活的重要特征。这些民族劳动的特点就是断断续续、干一天歇一天。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受环境影响,的确保持在较低的生活水平。但他们所掌握的生产手段,已足以满足其物质需要。与之相反,当今人类社会中,还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处于饥饿和贫困中。在技术力量发展到顶峰的今天,饥饿却仍然司空见惯。世界上最原始的人们拥有极少的财产,但他们一点都不贫穷。因此,“贫穷不是东西少,也不仅是无法实现目标;首先这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贫穷是一种社会地位。它恰是文明的产物。”⑤[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45页。现代人由于追逐无限的欲望,才使自己陷入了短缺和贫困的宿命。
部落民族经济往往维持在低度生产水平,这种低度生产主要表现在资源低度利用、劳动力低度使用等层面。低度生产与原初丰裕是一致的,亦即既然可以很轻易地满足自己的需求,也就没有必要过度使用劳动力和过度开发资源了。部落民族刀耕火种的农业耕作方式是资源低度利用的典型形式。这种耕作方式极其简单,土地耕作一到两季后,便被抛荒多年,直至恢复植被,重新积聚肥力。然后,这块土地重新开辟,进行新一轮耕作和休耕。刀耕火种低于其技术能力所能达到的水平,处于低度开发状态。劳动力低度使用是部落民族经济低度生产的重要特征。在这些社会中,人们承担的经济义务和他们的身体能力相比较而言严重失衡,青壮年不事生产,反而将工作的重担留给了年老力衰之人。他们工作的动力难以持久,工作时间很不规律,大量劳动力被闲置,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仪式、娱乐、社交及休息的需求,是经济活动的重要补充,也是社会结构对经济活动的动态适应。部落经济追求具体而有限的目标,是一种为使用而生产的经济形态。
这是一种典型的家户经济,它强调以生存为本①萨林斯明确表示,他关于部落民族家户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源于俄国著名的农民学家恰亚诺夫。恰亚诺夫是农户经济分析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从农民的文化心理和农业组织形态层面探究农户经济行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农户经济的组织理论,形成了著名的“恰亚诺夫定理”。关于恰亚诺夫农户经济理论的更多讨论见[俄]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其首要目标是满足家庭的生计需求。家户经济追求的是生活的路径,遵循着反剩余原则,它的生产模式专为生计所设,只要略有剩余,便会终止劳作。在由家户生产群体组成的社会群体中,家户相对生产能力越强,其成员工作时间越短。在部落经济中,生计的标准往往以大部分家户所能达到的程度为依据。这意味着,家户经济不存在生产剩余品的动力。那些生产能力较强的家庭,不会为了穷人的利益而扩大自身的生产。
从社会组织层面看,部落民族的经济行为受制于亲属关系,呈现出权力关系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亲属关系与制度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更是家户经济的决定力量:“这些力量依托家庭之上的社会结构,以及生产过程之外的文化结构,控制着社会经济的张弛。”②[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6、215页。同时,部落民族的家户经济受到政治体制和政治组织的强烈影响。家户经济受到部落政治力量的干预,生产的动力是由政治权力传送出来的。头人、酋长本身是集体命运的化身,他们激发集体的经济动力,做到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因此,政治制度是约束家户经济及其生产模式的重要机制。酋长和头人慷慨赠予是一种强加的义务。这种赠予体现了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政治关系。酋长因控制财富,而具有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权力。他通过赞助公共福利、组织公共活动而为集体创造了巨大利益。
与现代社会一样,部落经济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它会在部落内部、部落与部落之间发生交换和互惠。不同的是,部落民族往往将经济交换视为社会互动和社会链接的一部分,交换活动与社会制度、亲属制度和亲属关系相嵌合。在这些社会中,“物品的流动是社会规范的一部分,并受到社会规范的限制。”③[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6、215页。在家户与家户、部落与部落之间,人们主要通过互惠方式进行经济交往,将物品流动与社会关系链接起来,物品的流动开启了社会关系。而以礼物交换为基础形成的互惠经济是部落社会经济社会交往的典型形式。这些民族将礼物交换视为个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之间基于互为主体性基础上的社会互动过程。人们正是通过礼物流动,建立社会联系,增进社会团结。因此,礼物经济成为了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的基本纽带,成为了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④马良灿:《论“莫斯精神”在当代社会学中的遭遇》,《青年研究》2011年第1期。。
依照初民社会经济社会关系的性质,萨林斯将互惠分为“慷慨互惠”、“等价互惠”和“消极互惠”三种类型⑤萨林斯一方面承认他关于初民社会经济交往的认识受益于波兰尼的启发。但他指出,初民社会中,互惠和再分配是一回事,两者可以合二为一。再分配是一种互惠的组织和系统。以此为基础,萨林斯建立了部落民族互惠关系与社会融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模型。波兰尼关于市场、互惠、再分配和家计经济等经济社会整合机制的讨论,详见Polanyi,Karl.1992.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Granovetter,M.& R.Swedberg(eds.).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Boulder:Westview Press:pp.29-51;[匈]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8页。。慷慨互惠是一种利他的交换过程,在这种交往模式中,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不计回报,交换的物质方面被社会性所压制,对互惠的期求可有可无。而等价互惠指的是直接交换,参与互惠交往的群体以更为明确的经济和社会目的面对彼此,交换的物质和社会动机并置,给予的物品必须在短期内回报,社会关系随物品流动的变化而变化。在部落社会交往中,等价互惠往往是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契约而存在的,它是和平与结盟活动首选的媒介,是群体间从自我封闭走向联合的方式。人们通过等价互惠,建立了很多契约关系。消极互惠是一种只进不出的企图,集中了对报偿和利益的贪求,物质交换中充满着欺诈和投机,其交换动机是为了赚取实际利益。因此,消极互惠是个人间的交换,通过不断讨价还价,最终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萨林斯明确指出,互惠的形成与社会距离、社会的结构性位置、财富密切相关,初民社会中的亲属关系距离和亲属关系等级决定了他们所采用的互惠模式。首先,亲属关系距离决定了互惠的模式。一般而言,近亲之间近于分享,乐于利他和奉献,契合慷慨互惠,而对陌生人与非亲属则是对等交换或诈欺。其次,与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相关的重要因素是道德。初民社会的经济社会关系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原则之上,部落民族将依据交往对象的差异而采用不同的道德原则。第三,亲属关系等级对人们之间的互惠关系和交换模式也具有一定的作用。等级意味着特权,特权意味着义务。上等人只有通过将财物进行赠送和分配才能获得权威。互惠成为了启动机制,它参与了社会等级的建构。第四,社会团体之间财富差异和社会地位也会影响人们的互惠模式。在亲属共同体中,富人会给予自己的族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人们总会关心自己的近亲而非远亲。初民社会中,慷慨互惠不仅是一种交换活动,它使所有人特别是穷人在灾难面前增加了幸存机会。
总之,在部落社会中,人们之间进行经济交往的价值受制于“交换区域”的限制。交换区域依照不同的等级秩序标准,规定了物品的不同价格。物品的不同价值取决于它们在交换过程中所处的社会区域。同样的物品在不同的交易过程中,会表现出不同的交换比例。现代社会中盛行的市场原则无从解释原始交换关系。在部落社会中,亲属和友好群体会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商业中的竞争关系。部落民族的经济交换关系遵循着严格的道德规范,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人可以为了利益不顾一切,是“社会关系而非价格将‘买方’与‘卖方’联系在一起”,“交换过程应该被理解为社会整合的类型,而不仅是 (简单的)交换类型”①[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39、347页。。原始社会的贸易活动体现的是一种伙伴关系,其本质是交易过程中的交换比率由社会交换的经验所决定。通过物质交换同外族建立社会关系,对交易本身而言是最有意义的。
五、结语及讨论
萨林斯从学术思想的源头与现实的经济社会场景、从功利主义的道德与哲学根源、从部落民族经济社会关系的真实经验出发,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功利主义经济思想展开了全面论战。从他关于物质实践由文化构成、社会距离、亲属制度和交换区域决定部落民族的经济交往关系、关于生计经济、伙伴关系重于经济利益的论述中,能体悟到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物质实践与社会制度的相互契合与连动。在萨林斯笔下,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塑造的理性人将人视为追求私欲的贪婪动物、把人们之间的关系表述为受自由竞争的市场法则支配的观念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受家庭伦理、文化制度、生计原则和社会习俗制约的社会人。
萨林斯在思考初民社会中人们的经济社会关系时,其理论的立足点是人群,是集体,是部落民族中的家庭、亲属、社区和伙伴关系等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体。在他看来,部落社会的人们在进行经济社会交往时,若离开了其所居住的社群,他们的行为是难以理解和想象的。在这些社会中,人们的经济行为必然受制于生存伦理、亲属关系、社会距离和群体关系的制约,是一种被象征理性支配下的社会行为。即便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经济社会交往也不可能完全脱嵌于价值伦理关系的约束而任凭经济理性的摆布。正是在同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论战中,萨林斯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即人类的经济行为首先是一种文化行为,受到文化制度的规约和限定;经济交换首先是一种社会交换,是社会整合的一种形式;经济理性首先是一种象征理性,是被象征理性所限定的行为。萨林斯赋予了人类经济社会行为坚实的文化与道德基础,直接延续了波兰尼所开创的实质分析传统。
不过,生存理性、道义伦理、亲属关系、社会距离等文化与社会要素不仅仅是初民社会中特有的现象,也远非仅在初民社会中才制约人们的经济社会行动。萨林斯以部落民族的经济社会关系为基本理论素材,来挑战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体系和经济学说。这种以卵击石的勇气一方面令人钦佩,但其力量十分微弱。在世界体系范围内,从生存空间和人口数量分布看,部落民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现今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民族所剩无几了。以一个即将消失或已经成为历史的民族为基础来同形式经济学说进行论战,其理论的说服力的确太有限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萨林斯陷入了传统经济人类学的狭隘视野中,他并未认真对待其他学科关于多元社会中人类经济行为逻辑的研究成果。萨林斯更喜欢将部落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作为相互对立的两极来看待,将前者视为文化伦理型经济,而将后者视为以经济理性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经济类型。部落经济强调特殊性、差异性、多样性和非营利性;资本主义经济强调普遍性、一般性和功利性。将弱小的部落民族经济与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相并置,将两者置于同一理论平台上对话,显然不太具有可比性。特别是,萨林斯对遍布世界各国的农业经济和似乎能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平分天下的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转型经济缺乏系统认识,导致了其经验素材的缺失和理论力量的单薄。更应指出的是,象征理性并不是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的唯一制约因素,除象征理性外,社会形态、制度环境、政治权力结构、制度变迁因素等均可能制约人类的经济社会行为。或者说,人类的经济社会关系本身是被多重因素、多种力量合力推动的结果,是一种被多元嵌套逻辑所限定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萨林斯关于人类经济社会关系的象征理性分析,从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