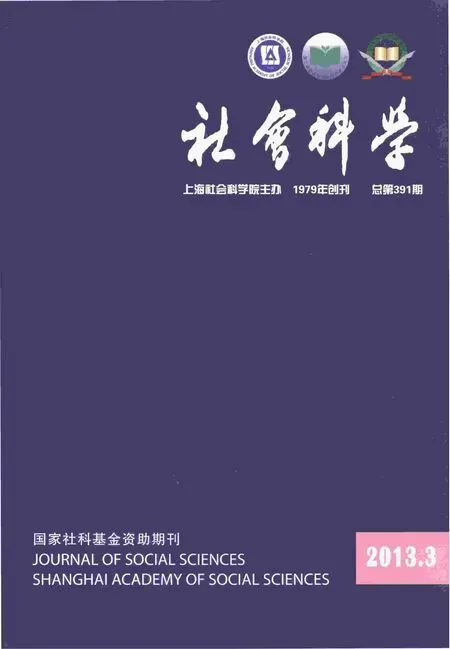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国民幸福*——幸福经济学研究的经验启示
郝身永 韩 君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发现了所谓的“幸福—收入悖论”,是指虽然一国之内高收入者的幸福感更高,但随着一国人均真实收入的不断上升,人们的平均幸福感并没有明显的趋势性。幸福—收入悖论的发现重新引发了经济学家对于幸福问题的研究兴趣,同时也因为幸福相对于收入至少是一个更高层级和更终极的目标。
显而易见,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是与居民幸福感紧密相关的两个因素。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社会呈现出两个最明显的特征,其一是经济持续而快速的增长,人们的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二,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收入差距在整体上呈不断拉大趋势,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以及城乡内部。因此,今后政策的着力点要以实现国民幸福为目标,协调兼顾促进经济较快增长、缩小收入差距和实现公正分配而不能顾此失彼。
一、促进经济增长与提升居民幸福感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幸福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兴趣。相对于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幸福与绝对收入、参照收入、预期收入、需要收入、失业、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等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试图探究背后的影响机制①在此有必要对“相对收入”概念作一个说明,大多数学者在参照收入 (reference income)——个体进行比较的群体的收入——的含义上使用“相对收入”(relative income)概念,也有学者将“相对收入”界定为个体自身收入与参照收入之差。为了作区分以避免混淆,如无特殊说明,后文中我们在后一种含义上使用“相对收入”概念,将前一种意义上的“相对收入”统称为“参照收入”。,就幸福与绝对收入的关系而言,研究发现:
其一,就一国内部特定时点居民个体而言,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有正向相关。这种正向关联不仅在发达国家发现,例如Blanchflower和Oswald对美英两国的研究发现“金钱可以买来幸福”,即高收入与高幸福感相关②Blanchflower D.,Oswald A.,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88(7-8),pp.1359-1386.;而且对发展中国家也发现了类似关系,例如Graham和Pettinato对拉丁美洲的研究③Graham C.,Pettinato S.Happiness,Markets,and Democracy: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01,2(3),pp.237 – 268.。罗楚亮利用2002年中国城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否控制相对收入效应,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④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财经研究》2009年第11期。。
其二,就穷国与富国居民幸福感的比较来看,许多文献发现富国的居民确实比穷国的居民更幸福。Diener和Biswas-Diener回顾前人的研究发现,各国平均收入 (通常以人均GDP或购买力平价衡量)与各国平均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度都很高,各不同研究的平均相关系数约为0.60⑤Ed Diener,Biswas-Diener R.,Will Money Increase Subjective Well-Being?A Literature Review and Guide to Needed Research,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2,57(2),pp.119-169.。但对此结论必须持谨慎态度,因为富国通常在政治上更民主,民众更自由,社会保障更健全,而这些因素也会对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并且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自评的主观幸福感可能缺乏严格的横向可比性。
目前幸福经济学关于幸福与收入的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利用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分析。第一,通过面板数据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异质性。当然,这种方法的局限在于,一些国家或地区缺乏大规模的个体跟踪调查数据,没有现成的面板数据可用。并且,这种方法仍然无法控制依时间变化却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而Li等应用2002年中国五城市的双胞胎数据尝试同时解决可能的变量遗漏、测量误差和反向因果带来的估计偏误,结果发现收入对幸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⑥Li H.,et al.,Does Money Buy Happiness?Evidence from Twins in Urban China,Working Paper.2011.。第二,利用自然实验。Frijters等利用柏林墙倒塌和两德统一这个“自然事件”研究东德的生活满意度,发现因为统一所导致的外生的人均实际收入提高使生活满意度有相当大的提高⑦Frijters P.,et al.,Money Does Matter!Evidence from Increasing Real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East Germany Following Reunification,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2008,94(3),pp.730-740.。Gardner和Oswald利用中彩票或继承遗产这种外生事件研究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状况改善确实会带来主观幸福感的上升。第三,工具变量法。Knight等采用了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系数从0.17上升到了0.58⑧Knight J.,et al.,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2009,20(4),pp.635-649.。Powdthavee采用工具变量法后也发现之前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被低估了⑨Powdthavee N.,How Much Does Money Really Matter?Estimating the Causal Effects of Income on Happiness,Empirical Economics,2010,39(1),pp.77-92.。
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不是最重要,但收入确实是影响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收入越低,单位收入增量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越强,而这也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就我国现实国情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是,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还比较低。按汇率法计算,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在215个国家中排在第121位,刚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10]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和作者据以计算而得,下文数据若无特别注明出处相同。。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从2010年各省份居民消费水平看,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西藏的7.15倍。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按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1274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仍有2688万人。因此,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稳定发展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许多问题也需要在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得到解决。
一些研究发现,就一国人均收入与平均幸福感的跨时比较来看,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居民的平均幸福感变化并不大。伊斯特林基于对美国的研究,发现高收入与更高幸福感相关,但跨时比较发现随着人均实际收入的提高,平均幸福感基本没有变化,此即所谓的“幸福——收入悖论”①Easterlin R.,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Some Empirical Evidence,In:David P.,Reder M.: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witz,New York & London:Academic Press,1974,pp.89 –125.。但人追求的是一生幸福总值的最大化,而不是一时的快乐最大化。经济的发展通常也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医疗条件的改善,预期寿命的提高,健康状况的改善,这有助于提升生命周期的幸福总值。经济的发展通常与社会文明的进步、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公民权利的维护等相互促进,而后者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变量。因此,即便平均幸福感跨时变化不大,但从提升生命周期幸福感的目标出发,也需要坚持不懈地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平稳健康地发展。
二、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公正分配与提升居民幸福感
标准经济学通常假定,经济个体完全受自利动机驱使。纯粹自利模型假定人们试图最大化的效用函数不受其他人效用的影响,仅包含自身的收入或消费。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标准经济学所秉持的工具主义和个人主义方法论。但这种假定与人们的常识相悖,马克思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杜森贝里③Duesenberry J.,Income,Savings,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亚当·斯密、阿尔弗莱德·马歇尔、阿瑟·庇古等都表述过人际比较影响效用的思想④Akay A.,Martinsson P.,Positional Concerns through the Life Cycle:Evidence from Subjective Well-Being Data and Survey Experiments,IZA Discussion Paper,2012,No.6342.。
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实验发现,人们具有公平偏好和不均等厌恶,而“公平”的评判必然包含有人际横向的比较。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揭示,如果提议者给自己的分出额过小,回应者通常会拒绝,尽管拒绝提议会一无所得从而损失一个正的收益额。在实验中,大部分提议者都会提议40%-50%的分出额,回应者一般会拒绝低于总额30%的分出额⑤Camerer C.,Thaler R.Ultimatums ,Dictators,and Manner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9(2),pp.209-219.。Forsythe等所进行的独裁者博弈实验发现,有80%的提议者不会独吞所有的钱,且有20%的提议者提议的分出比例50%⑥Forsythe R.,et al.Fairness in Simple Bargaining Experiments,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1994,6(3),pp.347-369.。另外,囚徒困境博弈、公共品博弈、信任博弈、礼物交换博弈、第三方惩罚博弈等实验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人类具有公平偏好,关注相对收益和相对地位。另外,Fliessbach等在《自然》杂志上刊发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证明这种偏好具有来自脑神经科学的证据⑦Fliessbach K.,et al.Social Comparison Affects Reward-Related Brain Activity in the Human Ventral Striatum,Science,2007,318(5854),pp.1305-1308.。这充分地说明公平偏好是一种内生偏好,具有生物学基础。
与行为经济学对人的内在公平偏好的揭示相呼应,幸福经济学对幸福与参照收入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综合来看,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考察幸福与参照收入或相对收入之间的关系。其具体做法是将参照收入或相对收入引入个体幸福函数。Clark和Oswald利用1991年BHPS数据发现比较收入的系数为负,与个体收入的系数符号相反,大小相等⑧Clark A.,Oswald A.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61(3),pp.359-381.。McBride利用1994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 (GSS)数据研究了个体满意度如何依赖于与他年龄相差在5岁以内个体的收入。研究发现,在控制自身收入等变量的情况下,个体满意度随参照收入的增大而下降,并且个体收入越高相对剥夺效应就越强①McBride M.Relative Income Effect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e Cross-section,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Organization,2001,45(3),pp.251 – 278.。Clark利用BHPS前11次调查的数据也发现主观幸福感随着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增加而下降②Clark A.,Inequality-aversion and Income Mobility:A Direct Test,PSE and IZA Working Paper,2006.。
其二是,考察幸福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其具体做法是,将反映国家或地区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指标 (如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引入个体的幸福函数中并考察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Schwarze和Härpfer对德国的研究发现基尼系数有一个负的且显著的系数,说明德国人存在不均等厌恶③Schwarze J.,Härpfer M.Are People Inequality Averse,and Do They Prefer Redistribution by the State?Evidence from German Longitudinal Data on Life Satisfaction,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7,36(2),pp.233-249.。并且 (根据总收入五等分)无论他们在国家或地区收入分布中的位置如何,也无论相对于国家收入的平均水平如何,上述结论都成立。王鹏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考察了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该影响呈倒U型关系:当基尼系数超过0.4时,主观幸福感随收入差距的增大而下降④王鹏:《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3期。。
结合我国的现实看,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较改革开放之初已极大提高,但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利益分配机制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陈建东等对我国1978-2006年基尼系数的估计,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国收入分配比较平均,基尼系数均在0.3左右;1985年之后,收入差距开始逐渐扩大,2006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⑤Chen J.,et al.The trend of the Gini coefficient of China,BWPI Working Paper,2010,No.109.。从地区收入差距看,不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2010年全国31个省市区中,上海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为13977.96元,而最低的甘肃仅为3424.65元,二者相差10553.31元,前者是后者的近4.1倍。根据调查数据,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23倍,而1978年这一倍数约为2.57。按收入等级分,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户收入最高的10%的人均全年总收入和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分别是最低的10%的8.42和8.65倍。按收入五等分,农村居民家庭高收入户的人均纯收入是低收入户的7.51倍。这说明无论是城镇居民内部还是农村居民内部,均表现出巨大的收入差距,而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看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差距,则差距会更大。而从行业收入差距看,1990—2008年间,以基尼系数计算的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由0.067窜升至0.181,扩大了近两倍,年增6.5%,而同期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年均增幅只有1.5%。若不考虑从业人员比重,仅以行业特征计,则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将进一步上升至0.257,这一水平即使在国际比较中也是很高的⑥武鹏:《行业垄断对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10期。。
由以上数据我们看到,我国的总体、城乡、城乡内部、地区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都比较大。结合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公平是人的内在偏好,而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揭示,不管是整体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还是个体所参照和比较的群体的收入会对人们的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正基于此,我们需要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问题,抑止并缩小收入差距。
另外,标准经济学的效用是结果导向的,但Frey等人指出,人们对过程的偏好产生过程效用⑦Frey B.,Benz M.and Stutzer A.Introducing Procedural Utility:Not Only What,But Also How Matters,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2004,160(3),pp.377-401.。在我国现阶段,不仅仅是收入差距过大这一结果使人们产生分配不公平感,收入差距产生的过程和原因也挫伤了居民的分配公平感。因为,虽然分配公平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产出或回报的分配一定是以某种投入特征为基础的。如果不是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所得,而是通过非法牟利、官商勾结、腐败受贿、侵吞国有资产或者是凭借垄断牟取暴利等途径获得高收入,则会加剧收入差距对人们分配公平感和幸福感的挫伤,更容易强化人们的相对剥夺感。现实中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公的抱怨,不是单纯指向收入差距本身,更是收入差距形成与拉大背后的不公正。王小鲁对我国灰色收入规模进行了估算,根据初步的分析结果,考虑灰色收入,2005年城镇最高与最低10%收入组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大约是31倍,而不是现在统计的9倍①王小鲁:《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31辑,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0页。。由此说明,由于制度漏洞等原因,灰色收入问题严重,这会加剧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不公问题。基于此,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分配过程公正,也是提升国民幸福感的题中之义。
三、提高收入流动性与提升居民幸福感
关于幸福与参照收入的研究中,大多数文献发现参照收入对个体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但Hirschman和Rothschild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和不平等背景下,参照群体的收入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渠道影响个人幸福感:比较渠道 (comparison channel)和认知渠道 (cognitive channel)②Hirschman A.,Rothsechild M.The Changing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3,87(4),pp.544-566.。比较渠道使人们产生相对剥夺感,对幸福感产生直接负效应;而认识渠道发挥“隧道效应”(the tunnel effect),对幸福感产生间接正效应,这是指以一种认知的方式,参照收入作为个体形成自身未来收入预期的有用信息来源。比如,当参照群体收入提高时,个体便对自身未来的收入形成好的预期,而这种好的预期会提升个体幸福感。
Senik利用俄罗斯1994-200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验证,她发现参照收入对个人满意度有正的影响,并且这一结果对不同的统计模型都是稳健的③Senik C.When Information Dominates Comparison:Learning from Russian Subjective Panel Dat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88(9-10),pp.2099-2123.。作者指出,这一不同寻常的结果必然与此一时期俄罗斯转制的不确定性这一背景有关。在经济转轨的背景下,收入快速流动,人们的相对位置快速转变,其他人收入的认知效应有理由会压倒收入比较效应。Ferrer-i-Carbonell分东德和西德分别考察了参照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对西德,参照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东德,参照群体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④Ferrer-i-Carbonell A.Income and Wellbeing:An Empirical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5-6),pp.997-1019.。作者的解释是,东德的经济确实更不稳定,失业率比西德高,此种情境下参照收入的两种效应互相抵消,可能就变得不显著了。另外,Caporale等的研究发现,对西欧,参照收入影响为负;而对东欧,参照收入影响为正,也证实了隧道效应的存在⑤Caporale G.,et al.Income and Happiness across Europe:Do Reference Values Matter?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009,30(1),pp.42-51.。
个体存在不均等厌恶,但经验研究的发现启示我们,人们对不均等的容忍以及不平等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与收入的流动性密切相关。通常以年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只能反映人群中收入的静态分布。在收入发生了流动的情况下,基尼系数仍可能维持不变或者增大,而个体福利实际上依赖于生命周期内的总收入。因此,收入的流动性本身带有平等主义的本质。0sberg和Smeeding曾指出,流动率高的社会的民众比流动率低的社会的民众更能够接受社会不平等⑥Osberg L.,Smeeding T.‘Fair’Inequality?Attitudes toward Pay Differentials: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6,71(3),pp.450-473.。Alesina等发现,不平等程度越高,个体报告幸福的倾向越低。有趣的是,相对于美国的贫困者群体,欧洲的贫困者群体更不能接受不平等⑦Alesina A.Inequality and Happiness: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88(9 – 10),pp.2009-2042.。作者认为这与美国人认为美国更具流动性的信念 (并不必然是事实)相关,而欧洲人认为他们的社会更缺乏流动性。佐证的事实是,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71%的美国人相信穷人有机会走出贫困,欧洲只有40%;70%的西德人相信贫困是由社会而不是懒惰所致,而60%的美国人认为人穷是因为懒惰①Senik C.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What Can We Learn from Subjective Data?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2005,19(1),pp.43-63.。在更具流动性的社会里,个人有机会通过努力向社会的上层流动,即存在向上流动的可能。Alesina和Ferrara利用美国数据的研究还发现,再分配倾向 (表征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不仅受个人的收入地位影响,而且确实受各州社会流动性程度的影响②Alesina A.and Ferrara E.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in the Land of Opportuniti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5-6),pp.897-931.。
要提高收入的流动性,机会公平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何立新和潘春阳指出,参照收入要想发挥对幸福感的“正向隧道效应”,前提条件是机会均等③何立新、潘春阳:《破解中国的“Easterlin悖论”:收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管理世界》2011年第8期。。如果在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不能保证机会均等的实现,则必然导致收入流动性的降低,参照收入作为自身未来收入预期信息源的机制便不能成立。因此,为了弱化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感的负效应,确保机会均等以提高社会和收入的流动性是重要的途径。
结 语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分配,合理适度地拉开收入差距,是经济良序健康运转的必要前提和必然结果。但是,有失公正的利益分配过程和贫富悬殊的分配结果,却都是使相对剥夺感发酵的酵母。因此,既要确保分配过程的公正,也要力避收入差距过大乃至贫富分化,否则容易导致低收入群体的心理失衡,激化社会矛盾,带来社会关系的紧张,影响社会的和谐。因此,为了提升国民幸福感,一方面要继续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地增长,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避免收入差距过大,使其维持在人们可以承受的心理范围内。弱化收入差距对人们幸福感负效应的重要途径就是提高收入的流动性。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流动性,社会底层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渠道堵塞,社会结构就会板结和结晶化,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贫富分化。所以说,政府要负担起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公共品供给,为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保障其基本生存权利,缩小起点差距,而从更深层次讲,需要健全制度,促进机会均等,因为机会均等对于结果不平等的缓解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公正性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