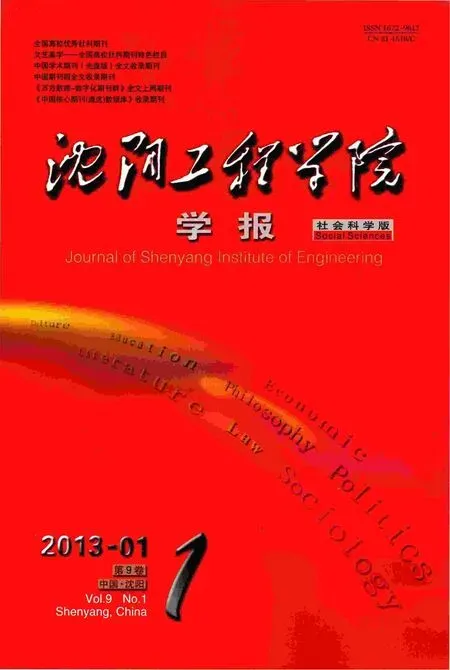对沈从文、孙犁作品中传统水文化的解读
童 敏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从地理学的角度而言,中国的地形结构相当复杂,同时亦丰富,不仅多山而且多湖泊河流。相对于山而言,水因为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人们对它的依赖感与认同感则较强。从原始社会人们“逐水草而居”开始,“水”就在中国古代社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人们对水的崇拜、依赖并由此而产生的对水的神秘主义想象影响到了古代文化乃至文学。从古代的神话传说开始,如大禹治水、祭祀河伯等,到文学创作中的流水意象,都不难看出水与华夏子孙的情感世界有着很深的渊源。而沈从文、孙犁这两位作家虽然属于现当代作家范畴,但是他们的作品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继承传统水文化内涵。
一、忧郁的气质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水代表着孤独、忧郁。这与西水东流、一去不还的自然现象有关。人们长时间生活在水边,水的这一自然属性也影响到了人们的情感体验。孔子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就是对年华老去、时光飞逝的感叹。同时水在爱情中也有象征。四大民间传奇之一的《牛郎织女》中因天河阻隔,牛郎与织女被迫分割两岸,倍受想见不能见的煎熬。在这里水象征了孤独。而“登临送别”中水又是另一番姿态。古人非常重视友情,“登临送别”就是说的友人之间依依不舍的分别。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南浦”是水边送别的地方,屈原《九歌·河伯》:“与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由此不难看出,传统水文化内涵的一个层面就是,它代表着忧郁与孤独。人们正是借助于对“流水的观照和对流水意象的认真品味,中国古人的生命意识、人生悲剧感与历史宇宙观念互为整合,共同得到了动态性的真实呈露。”[1]165
沈从文一直很重视水与他作品的关系,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这篇文章中,他说:“……我学会用小小脑子思考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的深一点,也亏得是水。”[2]42同时,“水”也是沈从文笔下不可缺少的东西,说它是载体也好,说它是意象也行,总之,“水”在沈从文笔下获得了与众不同的生命。“我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2]44一条汤汤不停的沅水给沈从文带来了无限的创作源泉与灵感,同时也给他的创作带上了一点孤独的气息。沈从文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寂寞的人,他说:“海边是那么寂寞,它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2]44,在与妻子张兆和的通信中,他也提到因为看久了水,便“觉得惆怅的很”。《边城》是沈从文最富盛名的一部作品。女主人公翠翠表面上是一个快乐的孩子,实则却是一个忧郁的少女。她的爱情、爷爷的去世、天保的意外以及傩送的出走,都让这部作品在表达至善至美的人情时打上了忧郁的色调。在作品的结尾,沈从文是这样说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这种没有结局的结局,以及对人生无法做出确定把握的感叹,使得《边城》这部作品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部爱情悲剧。《长河》(未完)中的忧郁气质就不再限于男女情感世界了,而是沈从文理想中的“湘西文明”的忧郁。因为“新生活运动”,原本平静的乡村生活有了波澜,作者开始意识到湘西世界古朴美好的人性和宁静的乡村文明不可避免的就要受到冲击了,代之而来的是“近二十年世纪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2]56沈从文用了清朗的调子却唱出了内心的忧郁。
作为一位解放区作家,孙犁一直是以热情积极的态度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但是细读他的作品却不难发现,孙犁也是一位极具忧郁气质的作家。这与他生在滹沱河岸边不无关系。滹沱河并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因为它不仅哺育了沿河两岸的居民,而且在当时也是重要的抗日据点,“孙犁和其他表现作家抗日战争的小说、诗歌、戏剧等,多次写到过它。”[3]9孙犁在《风云初记》《滹沱河上的梦》等小说中不止一次谈到了它,从他的文章不难看出滹沱河两岸的风俗人情以及发生在滹沱河岸边的抗日事迹都深深地影响了孙犁的创作。因为战争,滹沱河变得沧桑而沉重,虽然它哺育了沿岸居民,但是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它却无法抹平。在孙犁的眼中,故乡以及滹沱河正变得面目全非。后来他到了白洋淀,并且创作了很多关于白洋淀的名篇,如《荷花淀》《芦花荡》《采蒲台的苇》等作品。白洋淀在北方非常有特色,草肥水美就如江南水乡一样美好,孙犁还曾写过《白洋淀之曲》来赞美这个地方。但是战争却破坏了原本的宁静,平静的水面、茂盛的芦苇掩盖不住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痛。孙犁的作品赞美劳动人民,歌颂抗战英雄,但是冷静叙述的背后也有对生存在战争之下的普通群众流露出的痛惜之情。孙犁自己曾说:“我自幼年,体弱多病。表现在性格方面,优柔寡断。多年从事文字生活,对现实环境,对人事关系,既缺乏应有的知识,更没有应付的能力。在各方面都是失败多,成绩少。声音将与形体同时消失,没有什么可以遗留于后人或后世的。”[4]553孙犁说自己“优柔寡断”,其实这就是他的忧郁气质。
二、水与女子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贾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水女儿便觉得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正如曹雪芹所言,在传统文化中,水象征女子。水的自然本性乃柔弱、纯净,这与传统女子所表现出来的柔和婉约的阴柔之美有相通之处。《白虎通·五行》中说:“水为阴者。”“由于具有相同的审美特征,女性与水产生了美学上的直觉联系,用水象征女人也极为贴切。”[5]101中国传统文化中“水文化”的这一内涵影响了包括了神话在内的各种文学创作。巫山女神就是与水有关的女神之一,《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所说的女子也是生活在水边。民间传说《牛郎织女》的牛郎与织女因触犯天规,而被分隔在天河两岸,《白蛇传》中许仙与白素贞也是在西湖边的断桥相遇的。再如上文所述贾宝玉认为女子是水做的等等,诸如此类,都证明了女子与水的相通性。
沈从文的作品讲的大多数都是发生在“水边的故事”,故事的女主角也都有水一样的天性。《边城》中的翠翠脱俗如水般清纯,“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长养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麑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6]75如此具有灵性的女子就如水一样灵动。《长河》直接以“河”为题,女主人公夭夭同样具有水的阴柔之美,柔和、宁静。此外,像只把心事告诉水的三三(《三三》),以及那些生活在水边却与当地水手保持着纯洁的、无功利的爱情的妓女们,她们不仅生活在水边,而且获得了水的灵性。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几乎每一个女子都被他刻画得如水般飘逸灵动柔情似水。沈从文把自己对水的热爱与他笔下的女子交织在一起,合为一体。
孙犁的作品中女性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与沈从文作品中的女性一样,孙犁笔下的女性也如水一般。《荷花淀》中的水生嫂这“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7]31从这幅画面来看,完全看不出是一篇描写抗战的作品,诗情画意的情节,宁静而又美好,水生嫂就像月光下的荷花淀一样,清澈、忠节,荷香四溢。再如《铁木前传》中受人非议的小满儿,被人认为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这里需要提下传统“水文化”的一种偏见。虽然水的美好象征女子的美好,但是“红颜祸水”“水性杨花”等词语又是用水来说明女子的不忠。在《铁木前传》这部小说中,小满儿是一个个性复杂的女子,其实她并不是“水性杨花”,而是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只是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与自由罢了。在孙犁的笔下,小满儿不是水生嫂那样的宁静清澈的荷花淀,而是一条欢快的小溪,那么招人喜爱。
三、“上善若水”的人格与文品
老子曾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哲学”可以称得上是老子学说体系的核心与灵魂了。水是至善、至真、至纯的物体,在老子看来它滋润万物却与世无争,最后停留在众人都不想去的地方,故而最接近“道”。老子在这里以水论道,其实也是在以水论人。“上善若水”的人生哲学就是教导人们要有水一样的美德,即谦卑、与世无争。这也是老子“无为”思想的体现。老子“上善若水”的哲学思想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并补充了儒士的内圣外王、自强不息的价值的追求。”[1]171“水文化”在道家哲学体系内的这一层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且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封建知识分子。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的生活方式,洒脱超然,“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更是一种与世无争的体现。这就是老子所谓“上善若水”的人生哲学的写照。
沈从文与孙犁这两位作家的人格修养与他们的文学理想都与“上善若水”的传统文化内涵密切相关。沈从文来自湘西农村,对古朴原始的湘西文明有着深深的眷恋,他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并且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打量着一切。即使后来到了都市,他也不愿意和“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妥协,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讴歌健康合理的人性。在沈从文看来,文学应当独立于政治和商业之外,保持自身的品格。因此他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被承认,处于主流文学的边缘,而作为一个“落后的”“反动的”作家的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没有在文学史中获得他应有的“一席之地”。沈从文恋水,写水,他的生命是与水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作品如一股细流轻轻流淌在读者的心中。与世无争的人格与文学品格成就了沈从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上善若水”的文化内涵与沈从文的内心是相通的,他自己曾说:“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并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8]206沈从文的人格修养与他所坚持的文学理想就像水一样“善利”“处下”“不争”。著名画家黄永玉教授评价沈从文时说:“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9]1
同样来自乡下的孙犁也有“上善若水”的品格。滹沱河和白洋淀不仅让孙犁养成了忧郁的气质,也教会了他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品格。晚年的孙犁写下:“淡薄晚年,无竞无争;惟对于书,不能忘情”两句话,这成为他晚年的处世原则,也是他一生经历的写照。1945年《荷花淀》一经发表使得孙犁一下成为文坛上瞩目的焦点,但是他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骄傲。建国后的他,作为文坛前辈享受高官厚禄本是无可厚非,但是对名誉没有多少奢求的他却以《天津日报》副刊科副科长的行政职务走完了一生。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的孙犁正体现了传统“上善若水”的人生哲学,同时他的文学理想也打上了这一品质。孙犁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在大唱赞歌的政治背景之下,他也用笔热情地歌颂过。在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他并不否认“党及八路军总部提出的文艺方针可以大大促进我们的工作”[10]335,但是孙犁并没有因此放弃文学创作的主体性。他的作品总是以小见大,从平常普通劳动人民的身上发掘创作的闪光点,执着地描写劳动人民的善良美好,刻画自己心中“真善美的极致”。他并没有像其他一些作家那样盲目地唱赞歌而忘记了眼前的历史。通观孙犁一生的创作,是坚守自己内心文学理想的表现,没有随波逐流。这样的文学理想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相比,正是“上善若水”哲学的写照。
中国传统的水文化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在沈从文、孙犁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中传统水文化的一些内涵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他们笔下的水或者与水有关的东西都与传统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当然,沈从文与孙犁的水情结也是乡土意识的体现。沈从文对沅水念念不忘,没有沅水沈从文怎么会创作出如此丰硕的作品。孙犁在滹沱河岸边长大,最后去了白洋淀,对这两个地方都有很深的感情,他的部分作品都是发生在水边。只不过沈从文的水带一点楚地文化特有的婉约气质,而孙犁笔下的水都是在北方,多了一丝清新壮丽。
[1]王 立.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流水意象[J].中国社会科学,1994(4).
[2]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C]// 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3]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4]连云飞,潘陆阳.孙梨散文(上)[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5]晏杰雄,刘又华.水的原型意义分析[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6]沈从文.边城[M]//沈从文文集: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7]孙 犁.荷花淀[M]//孙犁全集: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8]沈从文.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M]//沈从文全集:十三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9]黄永玉.平常的沈从文﹒[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10]孙 犁.论战时的英雄文学——在冀中《前线报》文艺小组座谈会上的发言[M]//孙犁文集:四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