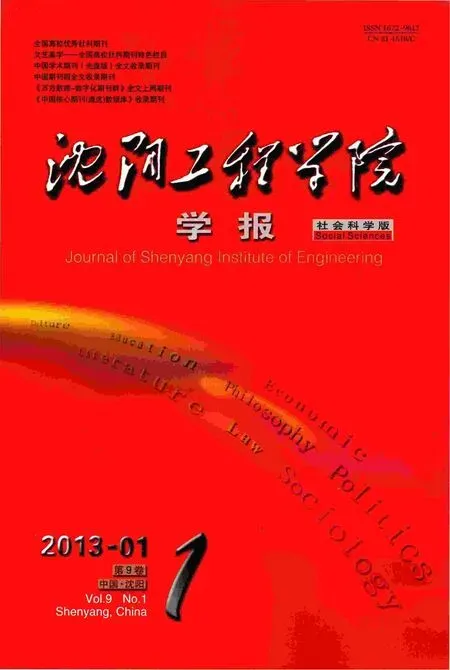《倾城之恋》解构主义色彩中意义消解的研究
林亚芬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州 350007)
解构主义理论在20 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它以反结构主义的姿态问世,随着几十年时间的推移以及人们的广泛关注,它已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指引人们的思想不断深化和发展。“任何统一性、整体性、权威性都是解构对象”,他们旨在“瓦解原意的向心性,打破作品形式的束缚,超越一切逻辑链条的桎梏,以一种全新的视界、一种自由创新的形式,使文本语言活泼起来”,“真正禀有‘文化相异性’和‘多音谐调’的后现代性”。解构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终极不变的意义[1]。德里达通过“分延”与“播撒”,对意义进行消解,使其不再具有中心性和稳定性。而《倾城之恋》则通过对文本意义和形象意义的消解,否定这些意义的原有中心与确定旨意,对它们进行不同程度的解构。
一、文本意义的消解
“理解文本的意义就是认清文本表述所遵从的逻辑规则和整个意义表述系统的特性,确定意义成分在表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从结构系统的整体上把握文本的意义内涵”[2]。即文本意义主要包含文章表述逻辑和文本既定意义两个部分,而《倾城之恋》正是通过反高潮的表现手法对小说叙事逻辑以及关于“倾城之恋”这个词语进行意义上的消解。
(一)叙事逻辑意义的消解
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是一般小说文本的叙事顺序,这种既定的顺序有其稳定的地位,对故事有序发展有既定的意义。而张爱玲运用反高潮的叙事顺序对传统文本叙事顺序进行了创新,从而对文本意义进行解构。一场战争促成了范柳原和白流苏走到一起,当范柳原向白流苏郑重求婚时,白流苏掩盖不住内心的欣喜,“一句话也没有,只低下了头,落下泪来”,“嗤的笑了出来,往后顺势一倒,靠在他身上”,哭与笑是白流苏革命胜利的喜悦。当所有读者沉浸在他们婚姻结局的美满时,张爱玲迅速将二人婚后的情况娓娓道来,“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婚后的不稳定因素太多,白流苏“还是有点怅惘”,读者的阅读情绪也立马低落,回到现实。按照文本的逻辑规则,或许在范白二人结成连理便可收笔,以呼应“倾城之恋”四字,而张爱玲偏偏反高潮,打破既有规则,给人强烈的情感起伏,实现对结局意义的消解。
(二)“倾城之恋”既定意义的消解
初看“倾城之恋”这一小说题目,读者便会有这是一部关于爱情罗曼史小说的预设,这是“倾城之恋”的文本既定意义,而当细读文本后会发现,其与传统的“倾城之恋”有着截然不同之处。首先,“倾城”很容易让人想起《汉书·外戚传》中“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3]的语句,即形容女子美色,而小说标题所指的“倾城”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城市的倾覆,使人出乎意料;另外,“恋”即标题隐喻下的爱情,“倾城”与“恋”的结合,让人联想才子佳人美好恋情,可小说呈现的范白二人的情感是赤裸裸的交易,给人不小的冲击力。对“倾城之恋”这一词语的反高潮是张爱玲对“倾城”与“恋”的解构,她消除了世人对二者关系的二元统一,淡化了词与词之间的既定关系,重新对词语进行再创造,赋予其全新的解释。
二、形象意义的消解
形象意义包含人物形象、景物形象、意象形象以及意境形象四部分。而人物形象是指“典型形象的特征是贯穿于他的全部活动,融化于他的血液,深入到他的每个毛孔,成了他的灵魂和中枢神经,成了统摄其整个生命的东西”[4],即人物形象具有同一性和确定性。意象是指“能独立表现情感的形象结构”[5],是对物象本身的特殊表现形式。
(一)白流苏形象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具有女性革命形象的特征,但她又不完全具备,因为她的革命并不彻底。在这里,张爱玲通过塑造一个具有矛盾性的女性革命者形象,来消解女性革命者形象意义的同一性,她以分延的意义不定取代人们所理解的女性革命形象的意义确定性,以唤醒读者的审美思考,同时强化白流苏悲剧命运的不可避免。
1.白流苏具有女性革命者形象特征
其一是面对压迫的抵抗。在父权文化笼罩下,“夫为妻纲”是当时婚姻观念的核心,妻子理应顺从丈夫,不得反抗。然而,面对前夫的花天酒地、吃喝玩乐,甚至接二连三的毒打,白流苏毅然以离婚来反抗,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幸福。白流苏面对压迫的抵抗,具有女性革命者敢于人先的勇气。其二是主体意识的觉醒。白流苏自我意识的觉醒始于她的面对镜子审视自己,她从光亮的外表下看出自我生命的价值。她意识到自己不老,自己依旧年轻,于是,一切还来得及,“她忽然笑了”,虽是“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但这背后是她清醒的自我觉醒以及对自己价值的明确把握。其三是幸福权利的争取。当白流苏意识到独自争取幸福已刻不容缓时,她以革命者的姿态宣告革命的开始和结束。她踏上香港之旅,顾不上家人的轻视,顾不上范柳原是否对自己有感情,她凭着一股冲劲给自己下了赌。在与范柳原的周旋中,她费尽心机地讨好范柳原,又做得滴水不露,她为了自己到达目标想方设法。虽然,她没有真正凭自己与范柳原结婚,但她革命历程的奋斗与努力,正是女性革命者所具有的。
2.白流苏对女性革命者形象意义的消解
传统的女性革命者是指那些主动地对周遭的不公平提出抗议,凭借自己的信念与力量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女性同胞,它具有同一性和确定性。而白流苏对女性革命者形象意义进行了消解,表现在:
(1)时间意义的不确定。白流苏无法自始至终都贯穿女性革命者的形象。首先是引发革命的被动性。“这是一个懦怯的女儿,给家人逼急了才干出来的一件冒险的爱情故事”[6],掀开白流苏革命动机的是来自家人的压力——三哥的势力、母亲的冷漠、四奶奶的刻薄,她并不是主动地想逃离封建秩序束缚,不是自觉地寻找自己的幸福。事实上,她离婚七八年都在白公馆呆着,“每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这都显示出其革命本身的被动性。其次是革命过程的妥协性。她无法把握自己被人主宰的命运,在她不得不成为范柳原的情妇时,她既不能在感情上深爱范柳原,也不能在现实中离开范柳原,于是她安于现状地、无可奈何地在大房子里独自寂寞,她的革命终究以失败告终。
(2)空间意义的不确定。这个女性革命者总是活在“空城”之中,不管她在哪里抗争,她都没法找到心灵的寄托之处。首先是上海的白公馆。这里是白流苏革命抗争的第一站,却是她真正的家。家对她来说却是冷漠无情、充满利益斗争的空房子。其次是在香港范柳原为她租下的房子。房子大而静,是“清空的世界”。在这无人之境中,白流苏的革命斗志完全被消磨,清净的日子里,在一间又一间屋子里呼喊空虚。最后是白流苏革命胜利的果实——家。有着婚姻保障,白流苏“笑吟吟”的,但底色依旧苍凉。这个“家”始终是不确定,流苏“还是有点怅惘”。
(二)男子形象力量的弱化
在父权文化体系中,男子应具有英雄气概,具有人格力量。张爱玲试图以小说男子形象的不健全对传统封建男子形象进行意义的消解,这与解构主义理论“替补”的解构策略刚好不谋而合。“替补因存在的虚空而起,是存在不完善的证明,它的根本指向是彻底否定存在的根源和形而上学绝对真理的神话”[1]。在《倾城之恋》中,出现的男子形象不多,主要有范柳原、四爷、三爷和没有现身的白流苏的父亲、前夫。
作为小说的男主人公范柳原,他的男子力量弱化的体现十分明显。
(1)男子人格魅力的丧失。范柳原作为小说中女人们的宠爱对象,并不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而是他的金钱。与其说这些女人愿意嫁给范柳原,不如说她们愿意嫁给金钱。而范柳原不过是金钱的替代品。他没法用自己的人格吸引女性,只能用老爸的遗产去诱惑女性,这是他人格的悲哀。
(2)男子伟岸豁达性格的流失。小说多次提到范柳原性格的怪异,徐太太评价“他脾气本来就有点怪癖”,白流苏认为“他脾气向来就古怪”,两个“怪”显然有所不同。徐太太认为的“怪”是范柳原的浮华与轻飘,白流苏认为的“怪”是范柳原的善变和小心翼翼。这些都让人觉得这个男子实在不够稳重与豪爽,男子的力量在范柳原的性格中被弱化了。
(3)自我命运的不能自主。这是范柳原男子力量弱化的最大体现。小说中他经常对流苏感慨命运的无法控制:爱情上,他无法得到白流苏的真情切意,范柳原在爱情上不过是白流苏的猎物。亲情上,他有父母却无法感觉到爱,他有姐姐却与她们为敌,亲情是他年轻时遭受的最大刺激,他在意亲情却无法得到,于是“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喝,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一个男人因遭打击而走入歧途,是软弱无能的。物质生命上,他依旧无法掌握,战争毁灭了无数生命,范柳原叹道“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战争使他意识到自己对生命的不能自主,他反问流苏,“你打算替我守节么”,两人无缘无故地齐声大笑,笑完了浑身打颤。他意识到了,假使他死了,他不能给生者留恋什么,那他的生命似乎就无意义了。范柳原对自我命运的无法掌握,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张爱玲对男子力量弱化的深刻阐释。
此外,小说中出现的三爷、四爷以及未现身的流苏的父亲、前夫,都是无能软弱的男子,在他们身上依旧无法窥探男子的真正力量。三爷将自己股票投资的“一败涂地”归咎在用了流苏的钱,沾了晦气,这是他的无能;用光了白流苏的钱,趁机会就想把她赶出家门,这是他的无情;用“三纲五常”来劝流苏回到夫家,这是他的虚伪。而四爷,成天在家拉胡琴,“狂嫖滥赌,玩出一身病来不算”还“挪用公帐上的钱”;流苏的父亲,“一个有名的赌徒,为了赌而倾家荡产”;流苏的前夫,“不成材”,吃喝嫖赌,外加家暴。他们都是软弱无能的男人,在事业上,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在家庭上,无心打理,婚姻惨淡。
三、《倾城之恋》解构主义色彩背后的价值
通过以上论述,《倾城之恋》是极富解构主义色彩的。但也必须认清,《倾城之恋》并不是以解构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它只是具有解构主义的某些特点,而且张爱玲在写这部小说时解构主义也还未真正兴起。张爱玲的解构意图与解构主义理论有着巨大的差别。张爱玲的解构意图,是对存在的具体的某种意义和秩序进行消解与颠覆,她的消解与颠覆过程中带有极强的主观评价,而在否定那些意义与秩序后,她自然而然地提出和建立自己的意义与秩序。因此,构建独特的秩序是张爱玲解构的终极目的,而这也是《倾城之恋》解构主义色彩背后的价值所在。这种独特的秩序主要在艺术张力和思想内涵上有所体现。
(一)独特的艺术张力
张爱玲说,“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7]。《倾城之恋》呈现的艺术张力正是由这种“参差对照”中产生的。它不是大红配大绿的激烈冲突,而是葱绿配桃红的参差对照,使得读者能不断玩味着其中悠长的韵味。在这种独特的艺术张力下,是张爱玲在建立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反高潮对文本意义的消解,在这过程中,人们能体会到其“参差对照”所带来的艺术张力。张爱玲刻意制造的反高潮,在抵制明亮戏剧效果背后,是其经久不衰的艺术感染力。首先,它起到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令读者摸不清作者的写作笔法,标题与结局的出乎意料,让人感叹张爱玲独特的创作天赋;其次,它将起伏归于平静,控制读者的阅读情绪,让人在大喜之后是由浅入深的悲哀,比如标题先让人眼前一亮,随着对文本解读后,又会恍然大悟,使读者的阅读情绪起伏不定;再次,它引人深思,标题中所谓的“恋”在文中是这么的卑微和脆弱,结局的不定让人感到人世间的苍凉,而究竟为何,张爱玲说了,“不问也罢”!
(二)深刻的思想内涵
《倾城之恋》消解了白流苏女性革命者的形象意义,弱化了父系文明下的男子力量,并颠覆了封建道德秩序与父系文明下的社会秩序。可见,其目的在于否定与批判庞大的父系文明,并试图抵制与推翻它,从而希望建立一个独立于父系文明之外的女性神话。张爱玲说,“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支,屈服在男性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的妻妾之道”。正是基于这种妻妾之道,白流苏的女性奴性意识始终没有改变,她的人生基调是苍凉的。张爱玲否定白流苏的这种劣根性,也认为“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男子的力量在《倾城之恋》中被弱化,男子的主体性完全被肢解被碎片化了。这样,父系文明下的男子和女子都被张爱玲否决了。在这基础上,张爱玲继续否定封建伦理秩序,而父系文明下的社会秩序在战争面前、在白范二人面前也毫无价值。父系文明的弊端被一一揭露,父系文明显得苍白无力。
张爱玲解构父系文明的意图在于建立独立的女性神话。她“打破了传统的男女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模式”[8],试图用女性话语将女性心灵、女性意识表现出来,用小说的形式表达自己对独立女性自主的期望。而女性神话的建立,首先是要摆脱可恶的父系文化。就拿白流苏来说,她独立自主的梦想不可能在父系文化桎梏下实现,她只有脱离封建道德秩序的轨道,不顾所谓的社会秩序,远离父系文明才有可能实现。只有这样,她才能获得女性真正的优美自在。小说中,当战争摧毁了父系文明,在那一瞬间,白流苏与范柳原才真正动情,才有人性美的最高体现。“铃一响,流苏自己去开门,见是柳原,她捉住他的手,紧紧的搂住他的手臂,像阿栗搂住孩子似的。人向前一扑,把头磕在门洞子里的水泥墙上。柳原用另外的一只手托住她的头,急促地道:‘受了惊吓罢?别着急,别着急……’”。可见通篇全文只有这处最真挚,范白二人仿佛一对老夫妻,对彼此十分的体贴依靠与信赖。此时的流苏没有父系文明的束缚,自由自在,还原了真实人性的美好。
[1]胡经之.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71-411.
[2]凌晨光.文学交流的构成与文本意义的揭示[J].文史哲,2001(5):36.
[3]颜帥古.汉书:第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2:45.
[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07.
[5]余正彬.形象、意象、意境析[J].西部科教论坛,2009(6).
[6]李 桦.婚姻叙事中的性别视角[J].作家杂志,2007(12):44.
[7]张爱玲.张看[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373.
[8]王 超.女性话语霸权下的男性形象透视[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07(1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