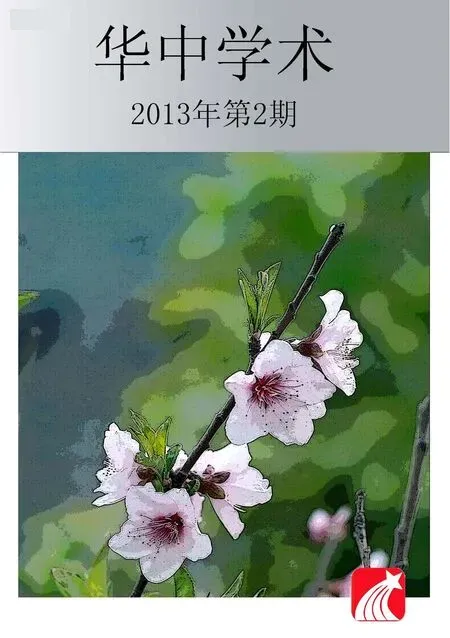无以承载爱的灵魂的悲剧
——《伤逝》主题的另一种解读
陈天天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在面对全部文学现象时,高尔基道出了一句真理,即文学是人学。五四新小说引进“摩罗诗力”,一方面瓦解了历史,另一方面,也瓦解了人的统一性幻象。它穿过人的外在言语、行动及其矛盾,捕捉在人面背后的一颗颗卑微、颤动的灵魂,人性成为新小说的人学主题。鲁迅的《伤逝》就是这样一部审视人卑微而颤动灵魂的作品。
诚然,《伤逝》的悲剧有其社会悲剧,也有子君自身的悲剧,可无疑的是,在我们深入其中时,却能深切地感觉到,最深刻的悲剧并不是社会的,也不是子君的,却是涓生灵魂的悲剧。
五四时期,“科学”和“民主”之风吹入中国,知识分子们经历了周作人所说的“科学的洗礼”[1],每一种有关个人、爱情、自由、“主义”等的主张,仿佛都在为人们扯掉那重遮挡着这个世界的屏障,都在为人们指示着一种新的可能——向实在靠近,世界在他们眼前越来越清晰起来。于是,逐渐觉醒的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去追寻“人身”与自由,然而,现实的世界并没有为人们在内心深处准备好巢穴。鲁迅就说道:“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是分明的看见了周围无涯际的黑暗。”[2]在光明和黑暗的边际,知识青年们在一路追逐的过程中,随处撒下来的却是支离破碎的人心的各种碎片,“低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明言的断肠之曲”[3]。拾取起这些“断肠之曲”,收集起那些心的碎片,作家们完整地提出人的问题,这也成为新小说的另一种“呐喊”。1925年10月,鲁迅写下小说《伤逝》。这是鲁迅唯一正面描写爱情的小说,然而,爱情并不是小说的主要叙事。鲁迅借助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深入地探索以涓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灵魂深处的问题,在面对现实世界中启蒙之风的盛行,知识分子们灵魂所受的洗礼与洗礼后所受的迷茫的折磨。小说的副题是“涓生的手记”,这也代表着鲁迅是从涓生方面来对爱情与个人关系进行深刻地思考,更深入确切地说,这就是把爱情与个人同时放到立人的意义上,是对人本身的思考。而对人“本身”的思考,并不是在表层面上来探讨,那样的话,是没有多大的价值,若是关乎人“本身”的思考,就必须上升到人的灵魂。
一、无以承载爱的灵魂——脆弱与不确定的涓生
涓生——一个具有坚定理性的知识青年,灵魂里的脆弱和不确定性,在与子君同居前已经开始显现。“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寞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4]这虽然不是涓生爱子君的全部的原因,但可也构成他爱情原因的一部分,而这个爱的理由从一开始就让人如此心寒。仗着子君来暂时逃出内心寂寞和空虚的折磨。而即使是在一年前,常常含有期待的破屋里也逃不出内心的寂寞和空虚,“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5]。在涓生的悔恨自省中重复的字眼总是“空虚”和“虚空”,这无疑就是涓生内心灵魂深处的真实写照。
涓生从一开始就是以子君的精神导师自居,“默默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6]。作为恋人的关系,他们之间并没有所谓的甜言蜜语,涓生并不是从爱情的视角来对子君说话,他没有对子君许诺所谓的未来的生活,他们之间并没有正常恋人之间对以后生活的幻想。从一开始,涓生就以一个“战士”的形象站在子君的面前,他对子君说的话,无疑大部分都是在以一个“战士”的逻辑去引导她。无疑的是涓生是有着清醒的个性意识,自觉地对社会现实进行抗争,在与子君的恋爱过程中,他沉静而自信地以自己的觉醒来唤起子君的觉醒。“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7],这是那个时代里发出的最强音。在涓生听到子君这声呐喊的时候,确实也震动了他的灵魂,可是,他随之想到的不是他和子君不远的美好未来,却是全中国的女性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这无疑就是一种“战士”的姿态。这个“战士”灵魂的不确定性在以后的求婚与同居时已经显露无遗。
按正常的恋人之间,求婚的过程应该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可是对于涓生来说,他已经记不清那时是怎样地对子君表示纯真热烈的爱,“岂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糊,夜间回想,早只剩下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个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8]。对于这些所谓“爱”的印记,他选择了忘却,不仅如此,在子君温习这些时,涓生感觉到的不是甜蜜却是可笑,甚而至于可鄙的。这该是一种怎样的不确定灵魂,才会让涓生在面对爱时是如此的软弱与不堪,他慢慢发现自己,在内心的深处已经无法去承载爱。与之相比的子君,却勇敢而坚决许多。
在中国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束缚下的子君,不顾家庭亲人的反对,不在意旁边人的鄙夷和讪笑,勇敢而坚决地与涓生从相爱到同居,勇敢地追求了自己的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为了筹备他们自己的小家,她不顾涓生的拦阻,执意卖掉自己的金戒指和金耳环。而相比之下,涓生这个思想和精神上的战士却要懦弱得多,面对会馆中那“老东西”和涂着雪花膏的“小东西”的窥视和鄙夷,子君是“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9]。在寻住所的时候,“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和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10]。这里,涓生在子君的衬托之下,显得如此的懦弱。所以说,同居前,涓生就是一个灵魂脆弱的理性“战士”,内心不够强大以及不确定的他总会在意旁人的看法和猜测,同时推想着别人的讥笑和鄙夷。涓生虽然是子君精神上的“启蒙者”,但另一方面,子君却成了涓生在空虚寂寞人生中借此前行的动力和勇气。
王尔德曾说到悲剧:“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另一种是得到了。”[11]在王尔德看来,求而不得和求而得之都是一种悲剧。就子君与涓生的爱情而言,社会无疑是他们爱情的大敌,在爱情发生时如此,在爱情结束时亦如此。但是,若是把他们爱情的结束简单归为单纯的社会问题,显然是被涓生的自我欺骗所欺骗。在涓生求而得之的短暂爱情里,“那个满怀希望的小小家庭”[12]正是在这个与爱情为敌的社会里开辟出来的,撑开它的力量来自子君和涓生那极为坚定的个人意志。而到最后,真正让他们爱情结束的,只能是来自那家庭的内部,来自他们自己。
可以说,在小说中,涓生对子君的失望从一同居就开始了:“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个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了许多先前原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确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13]接着,由于经济拮据,子君不得不整日忙于家务。涓生也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14],为生活而忙碌着。他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谈易卜生和雪莱,也不一块读书了。“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15]涓生爱子君,不过是仗着子君逃避寂寞和空虚,不过是这个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借此从子君身上汲取动力和勇气,而此时的子君再也没有时间与涓生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再也无法满足涓生的这种要求。最后,涓生的失业对于他们原本僵化的爱情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失业导致了他们的经济陷入困境,引发了生存危机。而此时的涓生并不是积极地寻找解决的办法,而是消极地等待。面临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困境,涓生选择躲在通俗图书馆里幻想着在他面前豁然开朗的种种生路:“我看见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上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昏夜的运动者和深夜的偷儿。子君——不在近旁。”[16]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涓生以后生活的幻想中是没有子君的存在的。
经济的压力渗透进家庭小事中,加深了涓生对子君的不满。为了涓生的生存,吃了油鸡,赶走了阿随,下一个为了涓生生存而被舍弃的只能是子君了。在面临这些生存危机时,涓生想到的却若是一个人远走高飞,生路会宽广的很。他把如今忍受的生活压迫的苦痛的原因大半归于子君。所以生存危机到来时,他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于他们的分离,他认为子君应该决然舍去,更令人心寒的是他甚至想到了子君的死,而这样的念头却不止一次。爱此时在涓生的心里已经消失殆尽,此刻的他认为子君就是自己的包袱,所以他决定要甩开这个包袱,要对子君说出那个“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的“真实”[17]。《伤逝》的爱情,也结束在涓生的这句话上,即涓生的所谓的“真实”。“你已经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对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牵挂地做事”[18]。爱情到了这一步,我们可以看出,爱与不爱,其实不过是涓生有用与无用的托词。如今,在涓生的心里已经没有了爱情的位置,子君于他已经没有任何用处,当初的子君是他前行的动力和勇气,如今的子君只是一个只知道捶着一个人衣角的人,一个可能会让涓生这个“战士”难于战斗的人。
“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极冷的早晨,这是从未见过的,但也许是从我看来的怨色。我那时冷冷地气愤和暗笑了;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若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19]
爱情到来时,似乎不需要去解释,然而不爱了,却需要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在这些理由里,涓生没有爱情的视角,只有作为“战士”的逻辑。
在涓生看来,在子君失去“战士”的品质之后,剩下的只有“空虚”。不仅如此,子君在同居后生活和精神的“空虚”,把她相爱时“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也变成空虚浮泛的东西。子君的“空虚”,使涓生理直气壮地放弃了这个人,然而,使涓生备受折磨、无以自赎的,是他在子君死后醒悟的,真正的“真实”不在自己手上,而在子君那里,真正的空虚,不是子君,却是自己!
“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忌,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但这恐怕是我错误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20]
从头到尾真正“真实”的东西是“因为爱”。真实的无爱的责任并不都是子君的,子君的爱,一日不曾失去,所以子君不曾“空虚”过一日。即使是离开,她也收拾好两人“生活材料的全副”,“郑重地将这留给我一个人,在不言中,教我借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21]。她还是那么爱着涓生。子君最终为了她的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涓生发现子君“空虚”的时候,实质上,他所发现的是自己的空虚。在涓生这个“战士”的逻辑里,他看不到爱的存在,看不到子君的爱,也看不到自己的爱。按照这个逻辑,涓生向子君说出的那个“不爱”的“真实”,就有了充足的勇气,在“战士”的逻辑上,没有爱的位置,这是多么贫乏、苍白的灵魂!
当西方理性传入中国的时候,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礼教、传统的人伦秩序、传统的精神价值,无法去支持理性生活,另一方面,与西方理性共生的基督教信仰并没有随之而来,这却使中国人在一种空前无根的状态中体验着理性生活。上帝救赎的理念,与上帝同在的虔诚信念又与中国的灵魂格格不入,灵魂的归宿由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进一步说,涓生的空虚,并不是涓生个人的空虚,而是“五四”一代人在整体上灵魂无根的写照[22]。生活着的“涓生”们,突然发现,他自己甚至无法把爱包容在自己的灵魂中。面对人生中的难题,脆弱而不确定的灵魂让他一次又一次地选择逃避,他仗着子君逃出寂静和空虚,不久之后,又靠摆脱子君逃离新至的空虚,到最后,用遗忘和说谎做指导,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向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
二、通常之解脱——悲剧价值之显现
王国维曾认为:悲剧价值之显现,乃在伦理学之解脱论上。他说:“通常之解脱,存于自己之苦痛,彼之生活之欲,因不得其满足而愈烈,又因愈烈而愈得不得其满足,如此循环,而陷于失望之境遇……举昔之所执著者,一旦而舍之。彼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彼以疲于生活之欲故,故其生活之欲不能复起而为之幻影。此通常之人解脱之状态也。”[23]涓生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他们的分离,子君应该决然舍去……找到新的道路的开辟,便在这一遭。在面临生活的压力和情感的空虚困境中,痛苦的涓生认为最好的解脱就应该是和子君的分开,或者更残忍的想法的是——“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24]。让读者感到悲哀的是,涓生是在一种理直气壮的心志中披露出内心这一并不光明的思想的。他在寻求的解脱之路,却是以牺牲子君为代价的。
涓生在与子君同居后,爱消失殆尽,看到的尽是爱情背后的空虚。而从文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知到两人开始同居时这种空虚感便开始慢慢遍布涓生的周身了。文中多次出现“空虚”和“虚无”两词。它们出现的频率之高,足以显现出涓生灵魂的深处的脆弱与不确定性。只有在一种极其不确定的状态下,人们才会感到一种虚无。子君死后,本以为能从那爱情的空虚中解脱出来的涓生却陷入另一种虚空——“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的存在”[25]。
当初是理性让涓生和子君能大胆地走到一起,爱情自由、个性自由充斥着当时的社会,而这也是涓生所追求的。也可以这样说,涓生同子君从相爱到同居,他关注的并不是两人之间的两情相悦,而是逸出爱本身,更着意于“个性解放”“个性自由”“我是我自己的”诸多个人价值观念的实践。这些理性的追求,在当时的涓生这类知识分子看来是无比坚硬的,它响彻在当时的社会中,振奋着每个知识分子的灵魂。然而当理性并非像涓生所想象的那样坚固和无所不能时,在他所不可认识的“内心灵魂”面前,理性暴露出他的脆弱和不确定性。帕斯卡尔曾证明,理性之渊薮在人心,人心才是理性所从出的精神中心。他说:“我们认识真理,不仅仅是由于理智而且还由于内心;正是由于这后一种方式我们才认识到最初原理,而在其中根本就没有地位的推理虽然也在努力奋斗,但仍是枉然……理智所依侍的就必须是这种根据内心与本能的知识,并且它的全部论证也要以此为基础。”[26]于是,对理性的追问就激起了对人自身的深入思考。面对理性的脆弱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苦痛与空虚,涓生选择舍弃子君,他认为只有舍弃子君,才能得以解脱。而最后,当他开始在子君死后反思自己时才发现,自己所遭遇的悲剧却是自己在为了爱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之后,却没有负担爱的勇气和力量的悲剧。这才是真正深刻的灵魂的悲剧。鲁迅在这里以爱情为镜子,折射出涓生——一个具有坚定理性的人的灵魂的脆弱和不确定性。
“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地重担卸给她了。她爱我之后,就负了这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
我看见我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摈于强有力的人们,无论是真实者,虚伪者。”[27]
鲁迅曾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8]20世纪社会转型以来,理性权威确立之后,觉醒的知识青年在走出传统之后,立于理性的世界中,回头发现的“人”的问题必须放在理性的背景上来思考,生活在这个“无爱的人间”,所谓的启蒙却存在于一个“虚无”的环境中。在这里,鲁迅再次正视了人心的困难和痛苦,将人生的有价值的爱情自由和个性自由建立后再摧毁,启蒙者的理想在现实中遭遇隐退,而痛苦本身就是寻找出路的痛苦,悲剧的价值在这里也显现出来。
三、起步之后如何向前走?
在爱情的前前后后,逃不掉的空虚,可见涓生的“觉醒”,也只有觉醒的意识,才会有主体性的虚无感。鲁迅曾在《野草》的题辞中就表现出这样一种矛盾——“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29]。这该是一种怎样的分裂灵魂?我们该怎样去理解这样的一种“空虚”?人思想世界,也思想人自身,他是脆弱的,但他也知道自己的脆弱,而世界对此却一无所知,于是,从这里便有了人的尊严。在一个以理性为特征的“五四”时代里,觉醒的知识青年从理性开始的追问,然后“还原”出人的形象,最后找寻灵魂与内心如何安顿的出路。不像西方的世界有其灵魂安顿的地方——上帝,中国没有基督教传统,在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是没有来自外界世界的救赎者,人心的安顿、道德的善不是由上帝予以保证,人唯一能够确信的,不是上帝的存在,而是人自己生命的存在,人的一切问题,仍然必须由这个生命存在自己承担起来。这就决定了中国在“五四”时期对人学上的坚守,新小说以其在转变期所特有的敏锐和诚实,把人的问题,尤其是人的灵魂的中国形态真切地描写出来。最后,涓生把人的空虚同时转变成人没有退路地承担空虚的力量。
“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30]
涓生的力量从何而来?涓生的灵魂又将走向何处?内省后的虚无和紧张,灵魂对于忧患的无条件的担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31]鲁迅《伤逝》的深刻与不可代替,不在于他是否提出问题的答案,而在于彻底、无条件地把握着这个问题,担当起这个问题——一个关乎人的问题和灵魂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小说《伤逝》可以认为是鲁迅的“人学沉思录”[32]。思考方向上的曲折、阻碍和执著的纠结,使《伤逝》布满了人学的谜团。
注释:
[1]周作人:《再论“黑幕”》,芮和师、范伯群、郑学弢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28页。
[2]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4]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5]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6]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
[7]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8]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9]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10]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
[11][英]奥斯卡·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王尔德作品集》,黄源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
[12]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13]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
[14]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9页。
[15]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8页。
[16]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17]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
[18]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
[19]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
[20]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0页。
[21]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