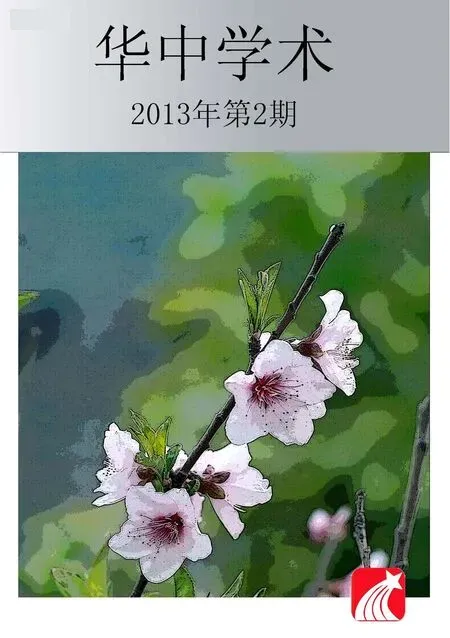有意味的人名——重读鲁迅小说《故乡》
许祖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有意味的人名——重读鲁迅小说《故乡》
许祖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鲁迅小说《故乡》中有一个人物,她的名字叫“豆腐西施”。鲁迅为什么给这个人物取这样一个名字呢?是亦有故。这个人名不仅对塑造人物形象有重要意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人名既以显然的存在含纳了鲁迅故乡绍兴的历史掌故,使小说《故乡》的地方色彩得到了显现,又从一个特殊的方面显示了鲁迅的艺术创新,同时,还显示了鲁迅对故乡、对人的复杂情感以及相应的理性判断。
《故乡》 豆腐西施 有意味 人名
一、 问题的提出
为研究鲁迅的小说,我不止一次读他的《故乡》,每次读完,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个问题:故乡究竟是什么?答案似乎不言自明,而又似乎一下难以说清。故乡是一个空间?因为她保留着一个地方的种种有形的文化,以及与这些有形的文化密切相关的无形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故乡是记忆?因为她总会在人的灵魂中镌刻下种种美好的或不怎么美好,甚至是很不美好的印象,以及与这些印象如影随形的复杂的情绪;故乡是关系?因为说到故乡,就不能不说到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过去的关系,人与现实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构成的人曾经生活或还在其中生活的环境;故乡是历史?因为没有历史也就无以为“故”,在时间的链条上形成不了称谓;故乡就是人?因为没有人也就不能成“乡”,在事实上也就没有了依据……
我的脑海里之所以会总盘旋着关于故乡的这样一些想法,是因为每次读《故乡》,我发现鲁迅对故乡的书写涉及的就是这样一些关于故乡的问题,鲁迅对这些问题的形象书写所表露出来的对故乡复杂的情感,我一下又无法用抽象的语言来概括。有时候即使绞尽脑汁,调动自己的知识积累进行概括,也总觉得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说服不了自己,无法达到“自圆其说”、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境地,而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的概括就更不要说去说服别人了。所以,这些问题像一个结,而且像一个死结,长时间地盘踞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欲罢不能,也让我欲说难写。而要解开这个结,我又始终找不到头绪。直到今年四月,为完成一篇关于鲁迅与越文化关系的论文,我又一次读《故乡》,读到中间,我突然眼前一亮,似乎找到了多少能解开这个结的途径。不过,这个途径并不神秘,也不具有任何隐蔽性,相反,它十分显然,显然得让我无法相信,也当然让其他人难以相信,从这里可以解开这个结,这就是《故乡》中的一个人物——“豆腐西施”。
说到这个人物,想来读过鲁迅《故乡》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有印象。对于学界同仁来说,这个人物因鲁迅在小说中言简意赅的卓越描绘,使之成为除闰土之外的又一个典型人物,所以,学界同仁不仅对这个人物有印象,而且有关这个人物的典型性及其意义,历来的研究成果虽不能说已经达到了汗牛充栋的地步,但也还是很可观的。不过,既往的研究,无论从什么角度展开,也不管基于什么价值目的,其所关注的往往都是这一典型人物的属性和性格等内容和问题,鲜有人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鲁迅为什么给这一人物取这样一个名字?更没有人对鲁迅为这一人物取名的匠心以及这一人名修辞的功能和意义等艺术性问题展开研究,我自己也不例外。事实上,“豆腐西施”这一人物的言语行为所表现出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属性的代表性与深刻性固然值得探讨,但这一人物别具一格的名字也同样值得探讨,因为,从这一人名的艺术功能来看,它不仅具有标示这一人物的职业并进而反映这一人物性格规定性的功能,而且凝聚了浓厚的绍兴文化色彩;它不仅具有表现鲁迅对故乡的历史、现实以及故乡人的复杂情感倾向和同样复杂的理性判断的功能,而且以小见大地体现了鲁迅运用反讽修辞的非凡能力。从这里展开相应的研究,虽然我不敢说能解决我上面提到的与故乡有关的所有疑问,也不一定能较为全面地揭示鲁迅对故乡书写中所包含的所有丰富的情感内容、文化心理、社会意识等,但却总可以部分地实现“以一斑而窥全豹”的目的,起码能实现这样一个研究意图:从一个特殊的层面,而且是一个并不开阔的层面,揭示鲁迅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就以及这篇小说浓厚的地方色彩。
二、 从“豆腐西施”人名的构成看鲁迅的艺术匠心
如果结合小说所写之事对“豆腐西施”这一人名细细品味,并将这种从艺术审美感受的角度进行的品味逐步沉淀为一种理性的分析,那么,我要说,这一人名的确很有意味,也很值得分析。“豆腐西施”这一人名,从词语的形态来看,是一个组合式的人名,即,是由两个词语组成的人名,这两个词语分别指称人物的两个方面:“豆腐”是人物职业的代名词,其意是指“卖豆腐的人”;而“西施”则是人物外在与某种内在特征的修辞性指称。前者的指称,具有较为明显的写实性,它标示的是人物在现实社会中的谋生手段和社会职业;后者,则具有借代的修辞性,意指人物“像什么”。前者具有直接反映人物性格特征的艺术功能和反映越地民风民俗的文化功能;后者则在反映鲁迅的情感倾向和娴熟运用反讽修辞技巧能力的同时,也反映了越地掌故文化的魅力。两者合一,则综合地体现了鲁迅为人物命名的艺术匠心。
“豆腐西施”这一人物的性格特点概括起来说是精明而势利,这种性格特征正是一般小商人共有的特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当然,作为一个卖豆腐的小商人,“豆腐西施”的精明和势利又是充分个性化的,这一点在作品中鲁迅以简洁的笔墨给予了形象的刻画,如,为了达到从“我”这里得到好处的目的,她一进门就主动而热情地与“我”套近乎,正显示了她特有的精明和事故;但当她发现我竟然完全忘却了她后又马上“显出鄙夷的神色”等,正是这一人物十分个性化的势利性格的表现。所以说,鲁迅在小说中用“豆腐”(即卖豆腐的人)来称谓人物,不仅使这一人名具有表明人物职业身份的作用,也具有揭示与人物的职业相关的性格的规定性的功能。同时,豆腐作为绍兴人喜爱的一种食物,是绍兴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油豆腐”就是绍兴的一道最普通和常见的地方菜,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有相应的提及。如在小说《在酒楼上》中鲁迅就有如是的叙述:“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所以,吃豆腐是绍兴的一种饮食文化,这种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昔日的绍兴人爱吃油豆腐,今天的绍兴人也爱吃;不仅绍兴人爱吃,到绍兴的外地人也爱吃。按照市场经济学的原理:有消费和需求,就自然有生产和销售。正因为绍兴人爱吃油豆腐,所以,从事豆腐的生产和销售,也就当然地成为绍兴人的一种职业,不仅成为一种职业,而且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还逐步地成为具有绍兴地区特色的物质生产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鲁迅用“豆腐”来为人物命名,指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有个性特征的典型人物,也直接地反映了绍兴地区的生产与生活内容以及与这些内容相关的绍兴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特色,从而使小说的“故乡”色彩在这样一个似乎不太起眼的方面机智地得到了体现。
西施作为越地历史上的美女,不仅因其倾城羞花之貌为人艳羡,更因其“柔肩担道义”的行为而受人敬爱,她的事迹广为流传所形成的知名度,不仅使她的故事家喻户晓,而且也使她的名字成为具有修辞功能的名词,在人们的日常交流和文学作品中,这一“名词”常常用来指称那些与西施一样,不仅有姣好、美丽的外貌,而且有善良、义勇品性的女子,其价值取向多为赞美。如《红楼梦》中曹雪芹在描写林黛玉时就曾有这样的形容:“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1]这里的“西子”就是西施,曹雪芹用西施之态来比喻林黛玉之相,其意就是赞美林黛玉,所用的比喻也十分恰当,很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林黛玉第一次在小说中出现时给人的印象。
但是,与曹雪芹相反,也与我们日常交流中用西施来称谓美女的习惯相左,鲁迅在《故乡》中用这一人名来称谓自己所创造的这个人物,却恰恰没有按照这一“名词”应有的修辞规范和所指来使用,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地刻画了一个样子像“圆规”(外貌不美),德性充满小市民习气(内心也不善)的人物。鲁迅如此使用“西施”这一人名的修辞性功能,我们当然不能,也无法从“西施”这一人名应有的修辞性来解读,而应该从更为复杂的内容和目的来解读。不错,无论从其外貌,还是从其言行来看,《故乡》中的这一人物都与越地掌故中的西施完全搭不上边。尽管鲁迅在小说中没有细致地交代,这个“我”已经二十余年未见的五十岁上下的女人,当初是否也有越地美女西施的容貌,其在“卖豆腐”的过程中,是否具有职业道德,是否受人赞赏等,但也无碍于我们对“豆腐西施”这一人名的解读。从这一人名构成的艺术手法来看,如果说,“豆腐”采用的是写实的手法的话,那么,“西施”则完全没有写实性,也没有一般修辞格所包含的象征、借代、比喻所应有的指示性,而是一种语言艺术变异的产物,所采用的修辞手法是反讽。从功能的角度看,如果说,“豆腐”的写实性具有标明人物的职业及其性格特征的功能的话,那么,“西施”的反讽性,则具有表达鲁迅的情感倾向的功能,它们功能不同,各司其职,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显示了鲁迅塑造这一人物的艺术意图和思想、情感倾向。
当然,说这一人名中的两个词语各司其职,并不意味着这两个词语所指的内容和发挥的功能没有关系,恰恰相反,两个词语的各司其职仅仅只是表象,密切联系才是“豆腐西施”这一人名的本质。不过,这种联系不是两个名词相加所构成的一般性词组的关系,即,两个词语之间的关系,既不是语言学上的“偏正关系”、“平行关系”,也不是修辞学上的一般比喻、借代关系,而是两个因素之间“张力”的关系。这种张力,既表现在两种手法的相互对立与联系方面,也表现在鲁迅对故乡文化的复杂情感方面。
写实与反讽作为两种规范、功能都不相同的艺术手法,它们是既对立又有联系的,不过,对立是相对的,而联系则是绝对的,就“豆腐西施”这一人名的“名”与“实”的关系来看,“豆腐”如实地表明了人物的职业和性格特征,具有名与实对应的一致性;而用反讽的手法描写的“西施”的外在特征与内在心理却与具有修辞功能的“西施”的应有之意相反,完全是“名不符实”,这正是两种修辞手法不同的规范所导致的名与实的不同与对立性。就联系来看,“西施”所指的落空与反讽形成的基础,则恰恰正是建立在关于“豆腐”的言语行为的如实描写之上的,正是有了关于“豆腐”像个圆规的外在特征和小商人、小市民习气浓厚的言语行为的精细描写,才为反讽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文本内部的语境,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文本内部的语境作为坚实的基础,也才使“西施”所指的“名不符实”具有了艺术逻辑的依据,鲁迅对这一人物否定的思想倾向与艺术意图也才有了按图索骥的线索,也才最终形成了反讽性的艺术效果。这正是“豆腐西施”这一人名中两个词语及其所指的联系性之所在,这种联系性所凸显出来的正是鲁迅对故乡文化的复杂情感和态度。
三、 从人名的构造看鲁迅对故乡文化的复杂情感与态度
毫无疑问,鲁迅对民众身上沾染的故乡的劣性文化气是深恶痛绝的。他在《故乡》中对豆腐西施这个人物身上的“豆腐”气的刻画就已经表明了他的这种情感和理智的倾向,但对故乡的优良文化传统,鲁迅却是赞赏的,也是常常引以为自豪的。他在《女吊》一文中曾说:“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句话。”[2]对优良文化的代表人物,鲁迅也是赞赏的,如辛劳治水的大禹,卧薪尝胆而完成复仇大业的越王勾践等,但对同为越地美好人物且与“报仇雪恨”的优良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人物西施,鲁迅的态度却是复杂的。在《阿金》一文中鲁迅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3]鲁迅这里说的“西施沼吴”,就是“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掌故。这里的“沼吴”语出《左传》,其内容为,哀公元年,当越王勾践战败向吴王求和时,吴王的幕僚伍员向吴王夫差谏言拒绝越王勾践的求和,但吴王夫差不听,于是,伍员“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结果也真如伍员所预料的一样,二十年后,越王勾践灭了吴国。而在二十年的休养生息中,为了迷惑吴王,越王勾践将越国的美女西施送给吴王,西施也以她的美貌和能歌善舞等获得了吴王的宠信,完全消除了吴王对越王勾践的警惕,使越王勾践顺利地完成了向吴国复仇的各项准备。这个掌故不仅在绍兴地区家喻户晓,而且在全国其他地方也可谓妇孺皆知,在这个掌故中西施不仅被当作一切美丽女性的代名词,而且也似乎成为越王勾践报仇雪耻的功臣。而鲁迅却说他“不相信”,他不仅不相信西施有这样的力量和伟业,而且也完全否定了“西施沼吴”这一掌故中对西施忍辱负重行为的赞美。从这方面看,鲁迅对西施的态度的确复杂,其价值取向具有鲜明而坚定的“反潮流”倾向,但,这种复杂不是无缘无故的,其“反潮流”也并非意气用事。
鲁迅之所以“不相信”“西施”能够帮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是因为他认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4],也就是说,在理智的层面,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了故乡掌故中对西施帮助越王勾践向吴国雪耻的赞美甚至拔高的“反历史”的性质。按鲁迅的历史观来看,中国的社会是男权社会,女子只是附庸,作为统治者的男人是绝对不会给予女子权力的,历史的事实也的确如此。而绍兴的掌故中对西施的赞美甚至拔高,不仅无视历史的事实,而且也与鲁迅所保有的历史观相乖,所以,鲁迅“不相信”“西施沼吴”的态度,不仅体现了鲁迅一贯的特立独行的思想本性,而且体现了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洞悉。但另一方面,在情感的层面,鲁迅对像西施一样的女子们又是同情的,甚至为她们常常被男子当作推卸责任的对象而愤愤不平,他曾断然地说:“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5]其实,早在写作《我之节烈观》一文时,鲁迅就已经发出过这样的质疑:“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老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阁在阴类肩上。”[6]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鲁迅借用“西施”来给一个市民习气很重的人物命名,不仅表现了他对故乡文化,包括对掌故中所包含的文化的复杂情感,而且也表明了他对现实中女人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不相信在男权社会里像“西施”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大的力量;但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这个“西施”的精明、势利特点和行为及显示的“力量”,又以无法回避的事实,彻底颠覆了鲁迅“一向不相信”的“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力量的”的观念,而现实中这个“西施”为自己得到“好处”所显示的力量及产生的能量,又并不是什么积极的力量和什么“正能量”,而恰恰是小市民气漫溢的消极力量和“负能量”,是让鲁迅深恶痛绝的消极力量和“负能量”,这又在现实性上消解了鲁迅对像西施一样的女人曾经葆有的同情心,至少是使鲁迅对像西施一样的女人的同情心的浓度大大地降低了。所以,对现实中的这个“西施”,除了用文字进行讽刺批判之外,似乎别无他法。于是,小说改造国民性的题旨也就这样地被导引出来了。
“豆腐西施”这一人名的魅力就在这里,鲁迅为这一人物如此取名的艺术匠心也在这里,鲁迅对故乡复杂的思想与情感倾向也从这里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注释:
[1]曹雪芹:《红楼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2]鲁迅:《女吊》,《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37页。
[3]鲁迅:《女吊》,《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
[4]鲁迅:《阿金》,《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
[5]鲁迅:《阿金》,《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
[6]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