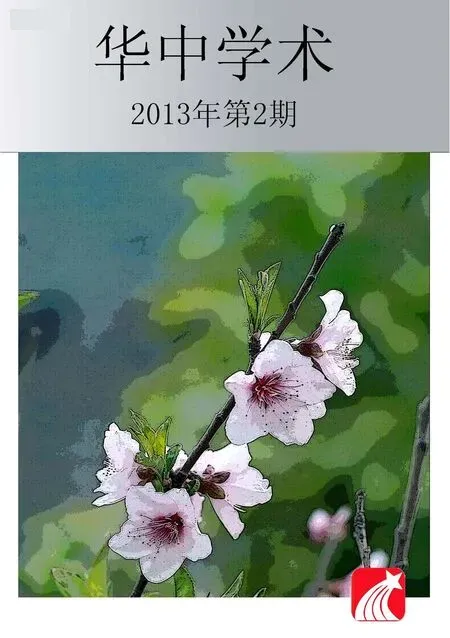“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中国近现代思潮中的荀学话语
周志煌
(铭传大学应用中文系,副教授,333)
一、引 言
清末民初引进西学,对于自然名物与社会群己观念着墨诠释甚多,其中由先秦学术思想援之以为西学之对比参照,亦常见于相关学者的论述当中。在这些诠释先秦学术思想的见解之中,荀学之“推类”与“辨异”观念尤其值得注意。荀子《正名》曾说道:
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说之用也。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1]
这种对于名物及伦理关系的推类观念与知识,在清末民初有关自然与社会范畴的“科学性话语”解说中,常被援引以作讨论。例如高元在民初所写的《辨学古遗(三续)》曾言及:“辨异者,于同类各物之中,辨其各个之差实,以分之为各异也。推类者于各异物之中,推其互相同之点,以为公实,而统之为一类也。类异之系统分明则位定,位定则名之被物也无越位乱次之虞。名之被物各就其位,则各之外延清矣。”[2]换言之,不论是辨其差异之“分”;或者在推类中求其相同之“公实”。“推类”与“辨异”两组观念,不是纯粹的逻辑知识而已,其涉及的是如何看待、思考人生存的历史情境及生活世界的各种复杂关系网络,并就此思考秩序安顿的可能。就晚清介绍“社会学”的概念,多以荀子所言“群”学名之。严复就曾指出:
所谓小己,即个人也。大抵万物莫不有总有分,总曰“拓都”,译言“全体”;分曰“么匿”,译言“单位”。笔,拓都也,毫,么匿也。饭,拓都也;粒,么匿也。国,拓都也,民,么匿也。社会之变相无穷,而一一基于小己之品质。是故群学谨于其分,所谓名之必可言也。[3]
从总分的概念运用到政治、社会,乃至事物之对象上,严复要说明的是全体与部分并非相对立的概念,而是一种“含摄”关系,部分构成全体,全体包含部分。正如“理一分殊”的观念一样,也与荀子谈“类”(伦类、物类)之概念相通,用之于政治社会关系,既呼应了荀子“明分使群”之说,也反映了晚清群学意识底下对于个人与社群关系的讨论。
清末民初关于推类、辨名的言说,其中涉及自然名物及社会群己关系的探究颇众。荀子言“类”与“名”本就相关于政治及道德伦理课题,晚清民初学者如何在传统知识中,运用相关思维与观念藉以融通诠释西学,这些学者所运用的荀学话语,又如何成为清末民初学者观看世界思潮的方式与途径?凡此相关问题,本文皆欲透过晚清民初学者的专著、报刊文献,以及翻译著述等材料加以爬梳厘清。就“观念”本身而言,往往源自于对于经验世界的存在作抽象的归纳,以一些“字”或“词”来表达对于繁复的现象界的统摄解释。透过这些观念字或词的厘清,可以了解一个思想家是怎样看待以及如何解释这个生活世界(life world),其对这个经验世界的意义掌握究竟为何?西方对于“观念史”概念著名的阐释者诺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1873—1962),曾列举了属于观念史研究的五种基本类型,第一项即是:
有一些含蓄的或不完全清楚的设定,或者在个体或一代人的思想中起作用的或多或少未意识到的思想习惯。正是这些如此理所当然的信念,它们宁可心照不宣地被假定,也不要正式地被表述和加以论证,这些看似如此自然和不可避免的思想方法,不被逻辑的自我意识所细察,而常常对于哲学家的学说的特征具有最为决定性的作用,更为经常地决定一个时代的理智的倾向。[4]
本文希冀能将荀学放在清末民初的学术思潮之中,揭示其作为诸多学者的重要观念及其话语,虽“不被逻辑的自我意识所细察,而常常对于哲学家的学说的特征具有最为决定性的作用”,并呈现这些“决定性的作用”其背后所能彰显的学术思想意义。
二、必也正名乎?——荀学“名”、“辩”观念的伦理意涵
先秦时代讨论“名”、“辩”两个观念的意见颇多,如孔子《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里主要谈“正名”的作用,礼以安上,乐以移风。在百事之名的确立上,才能带来人我沟通及维系和善秩序的建立;《墨子·耕柱》也说道:“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从百工分业的角度来说,“辩”作为一门专业知识,是可以学习的。
当代学者谈先秦时代的名学与辩学,最常举证的就是战国时期惠施、公孙龙等辩者之学(“名家”为汉人统称辩者之用词),以及墨、荀两家讨论名实问题,尤其墨辩当中的三物论式[5],被认为等同于西方形式逻辑的三段论。而荀子《正名》篇也常被当代学者引用,以资作为讨论中国先秦时代“逻辑学”的材料。如文中提到的:“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这里提到的“名”、“辞”、“辨说”等观念,即使许多学者指出相近于现今逻辑学当中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但如果还原于先秦时代的历史条件,显然荀子着意并不在此。即使荀子曾针对墨子、惠施、公孙龙等人的“乱名改作”,而要破除“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用名以乱实”等“三惑”,然而荀子论述“正名”观念,阐释“推类”言明“辨异”,以及与这两个意义底下,其他相关的观念群组,其背后的意向归趋仍在于现实经验世界的“治世”,旨趣是在道德及政治方面。而不像战国时期的辩者或墨辩部分,在思辨的名、实问题方面,走向形而上学及逻辑方面的课题。
清末民初时期重视“逻辑学”,与追寻现代化的科学理性精神息息相关。当日人用汉译词汇“论理学”来翻译西方“逻辑学”时,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序》中就曾有感于“论理之学,彰于大秦。而中邦名学,历久失传,亦可慨矣”[6],特别提倡先秦的正名之道,从孔子“首倡正名”讲到荀子“有循乎旧名,有造乎新名”。刘氏还注意到“倡明名学”,介绍其归纳派和演绎派,又以荀子思想与之比较,认为“归纳者即荀子所谓大共也……演绎者,即荀子所谓大别也”[7]。相较于刘师培举《荀子》为例,梁启超则特别推崇《墨子》书中的逻辑观念,其不仅以《墨子之论理学》(《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七》)专文介绍《墨子》书中的逻辑观念,同时也曾感慨说道:
欧洲之逻辑,创自阿里士多德,后墨子可百岁,然代有增损改作,日益光大,至今治百学者咸利赖之。《墨经》则秦汉以降,漫漫长夜,兹学既绝,则学者徒以空疏玄渺肤廓模棱破碎之说相高,而智识界之榛塞穷饿,乃极于今日。吁,可悲已。[8]
事实上,自明代李之藻(1569—1630)、葡国傅泛际(Franciso Furtad,1587—1653)合译《名理探》(原名《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一书于1631年初刻,其中把名学当成名理,并用来翻译西方逻辑概念,在这第一本西方逻辑著作引入中国的译述之后,有清一代相关逻辑学著作的译述也迭出不绝,如1824年乐学溪堂刊行佚名译的《名学通类》;1903年晚清严复译《穆勒名学》和1908年翻译的《名学浅说》;1903年杨荫杭著的《名学教科书》;1925年屠孝实著的《名学纲要》;乃至胡适著的《先秦名学史》于1922年出版,均把名学当成逻辑学。对此,徐复观在《先秦名学与名家》中就曾指出,“先秦名学”或“我国名学”,不同于逻辑学,他说道:
自从严复以“名学”一词作为西方逻辑的译名以后,便容易引起许多的附会,实则两者的性格并不相同。逻辑是要抽掉经验的具体事实,以发现纯思惟的推理形式;而我国名学则是要扣紧经验的具体事实,或扣紧意指的价值要求,以求人的言行一致……两者在起步的地方有其关连,例如语言表达的正确,及在经验事实的认定中必须有若干推理的作用,但发展下去,便各人走各人的路了。[9]
因此,从这个分野来说,荀子固有批判先秦诸子(如《非十二子》)需借用到一些名、辩思维方法及说明,尤其对当时的辩者惠施、公孙龙(即汉代所称“名家”),抑或宋牼、墨家之徒“墨辩”部分,均注力于散名之一点,荀子自然需扣紧在对方言“散名”之失而进行所“辩”。然而另一方面,荀子把刑名、爵名、文名等属于政治及伦理范围的问题,都放在“礼”的方面去讨论,因此考察荀子所关切的名、辩,其真正依归之处仍是政治、社会等伦理秩序的安顿,“隆礼”之意义也即在此。
三、“推类”与“辨异”:借传统以阐发现代性
晚清民初学者直接以荀学当中的名、辨、辩等观念来接榫西方逻辑之学,从荀子原意旨趣来看,其故多不相应于荀子欲回复天下秩序的政治、伦理课题;然而另一方面,从一些散见的报刊材料当中的言论,在因应世变、王朝秩序崩解的救亡启蒙话语中,反而可以看出在时代感受中,知识分子如何援引传统观念、知识,来思考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历程中,该有的新方法及新观念,并以此作为会通西学的进路。
“推类”与“辨异”这两组观念,与荀子对于“类”的知识建构息息相关,荀子重视万事万物之分类判别,借由“类”的清楚掌握与分析,能将各种事物之类属作一妥善之归纳与安顿,并连结成一缜密而又有序的关系网络(relationships networks)。因此,《荀子》一书言“类”之处相当多,从最基本的物类之别,到圣人、大儒如何“统类”,皆有完善的说明。以物类的观察认识来说,荀子说道:“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劝学》)这里强调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察,了解各种物类的属性,并加以“推类”,就能建立各种“类属”关系的链接,并建立经验知识的法则。
除了认识物类建立知识以外,在人所属的群居社会里,荀子也重视“知类”所能建立起来的社会伦理秩序(“伦类”),以及圣人如何“知通统类”,建立一个儒家理想的圣王之治。就“伦类”而言,荀子说道:“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劝学》)“忠信以为质,端悫以为统,礼义以为文,伦类以为理。”(《臣道》)“伦类”之道理必须在群体关系中来加以思考,若未能知晓通达,势必随时会面临人我关系失序之可能。也因此,荀子特别重视圣人“大清明心”所具有的知通统类的功能发挥,来为瞬息万变的社会找到理序。荀子面对的是周文的崩解,尤其到了战国后期,整个天下是:“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荀子·尧问》)这种政治、社会、伦常秩序的崩解,在晚清民初时代,即使成因不同,但就如何振衰起弊,安定生活世界的秩序而言,两者时代氛围尤有相类近之处。
就荀子的“法后王”思想而言,对晚清民初学者来说,不仅涵括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现况,也同时纳入了对于西方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降,现代化理性思潮的反省,就“后王”的概念而言,历代诠解颇多,众说纷纭。梁启雄《荀子柬释》曾云:“《荀子》以久晦之故,杨倞已谓‘编简烂脱’,后世传钞转刻者,又多沿讹袭谬;更以奥谊艰辞,多难索解。”[10]也因此,关于“后王”之说,唐代杨倞(?—?)认为:“后王,近时之王也。”清代王念孙(1744—1832)、刘台拱(1751—1805)不认同杨倞的说法,刘台拱认为:“后王,谓文武也。”王念孙以为:“后王,指文武而言,杨注皆误。”而王先谦的看法又与杨倞为近,认为:“后王,近时之王也。……言近世明王之法,则是圣王之迹也。”[11]如果我们将“后王”的观念对照于荀子所云:“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天论》)显然荀子认为有一种可以用来作为政治原则的常规惯例(道),可以应付各种历史社会的兴衰变化。天下之治乱,也决定于圣王是否能掌握这种常规原则。换言之,后王之政是可以因时因地制宜而有所变革,但“道”却是恒常不变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可以名之为“知通统类”。
荀子说道:“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儒效》)“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性恶》)这样的圣人、大儒形象,若考察荀子所说:“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异理而相守也。庆赏刑罚,通类而后应。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大略》)其实荀子对人事生活秩序的安顿,并未采取绝对的以“法”来决定一切,尤其当社会进展,旧法无法跟上时代进步所产生的新问题,由日常生活“知类”、“通类”所形成的判断,往往也能对于安定社会秩序有所发挥,并据此来进行赏罚。《儒效》说道:“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荀子认为大儒必须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即重视礼法不可拘泥而不懂通变,大儒或圣人知类、通类的前提,必须时时对身处的环境有所省察、有所顺应变化才行,也因此礼法并非一套泥守之成规。荀子曾经说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礼”的存在是可以用来安定社会秩序的,先王的礼是创制法度的原则,也是推知各种人事之理(伦类)的准绳。一切人群社会的复杂“类”属只有“知、通、统”,人伦关系才能有效地运作。
换言之,如同本文开头所引《正名》篇的一段话:“道也者,治之经理也。……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这里不仅直接指出“道”是政治的永恒法则,而且认为能够辨别不同的事物而不失误,依类推度而不违背其类之共理,正是掌握道之法则所使然。“推类”、“辨异”这两组概念,我们可以连结到先王、后王这两个概念上。“推类”之所以能够操持进行,连结各种自然物类,析辨其关系网络,依荀子思想而言,正在于“道贯”的原则。这是超越历史、地域的界线的普遍原则,然而“辨异”部分,正是区隔历史条件、地域风俗民情之不同,而该有的务实性做法。就晚清民初的知识界而言,“中体西用”的概念运作,也大抵可以相应于“推类”、“辨异”这两组概念,“推类”是会通中西、体用结合的思维可能;“辨异”则因时制宜,在近现代中国法政制度、科学器物、思想文化的变革上,采取有效益的作为,为全体人民之“善”作该有的因应。
四、“推类”的观念群组与近现代思潮
荀子“类”的意涵,既含括自然层面,也涵盖社会层面。既言其“分”(殊相),也论其“合”(共相)。分殊各“类”之理,再通统共理者为一类,由此以族类来辨物统类,开展其“天生人成”的生活世界之安顿。荀子所言“类”所涵括的知识论及存有学意义,在晚清民初,也常常在当时知识分子的诠释底下,带出各种自然名物、法政制度等物类、伦类相关知识探索,并展现其会通西学的可能思维。
以“推”的概念而言,本身即涉及一种“连类”的过程。在《荀子》一书中,与“推类”意义相关的观念群组,还可以包括以类相从、以类行杂等,以下即援引几个观念群组,以见晚清民初知识分子的思维当中,如何运用荀子“类”的观念知识以因应时代思潮。
(一)推类
晚清对于自然界的动植物知识,得力于西学翻译颇多,而此类翻译作品,有些往往是从日译作品再辗转介绍到中国境内。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在1880年的《日本国新订草木图说·序》中就提及:
至挽近发明草木有雌雄两蕊交感生生无穷之理,而众议大定林娜氏,由之以建纲目属种之条……唯能以我已精详者,照彼精详之书,推类比例,寻纲逐目,覃思精核,则辨知亦非难,而得美玉于荆棘之中,亦未可必无也。[12]
生物学的知识,在当时流行着达尔文相关的演化观念,而对于自然生物的分类知识,正是科学理性的展现。相同的推类观念也见之于严复译《名学浅说》所说:“大地北溟。其间冰界。冬长夏消。人所亲见。是故火星白趺。所以消长之故。依外籀术。有可言者。独至推类而极。必谓火星如地。亦有生物。”[13]推类是建立对事物认识的一个重要门径。“现代性”往往代表的是一种理性化及秩序性的追求。自然名物之认识如此,在社会群我关系的探究上亦复如是。例如对于孔教运动的诸多言论中,就有学者言及:“且国人中有一部分。方以奉耶稣而正其身心。则若全国而悉奉耶稣。其政俗之清明。当远逾于今日。亦为逻辑推类之所宜然。虽不必尽当。愚爱言论自由。愚则爱推寻至此。”[14]另外关于清末革命与立宪派之争,双方对于西学关于政治体制、人民自由都各有主张与阐释。代表革命派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就曾刊出汪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一文,其中说道:“其言曰:‘英人自诩其享自由。然其自由。第选举国会议员之片时而已。选举已终。则彼曹皆奴隶也。’其言可谓推类至尽矣。然其民约论第三编第四章。则云‘真正之民主政治。终不可睹。盖欲人民常相集合。以处理国家之事务。’”[15]这种报刊上的论辩,对于“推类”得当与否,往往是论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尤其《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对阵,“推类”一词常常出现在讨论国家政体、经济赋税、人民权利等现代性的公共话语之中。例如《民报》第十七号刊出《斥新民丛报驳土地国有之谬》一文,作者太邱就曾批评梁启超说道:
若使于从来租税全额外,别有所增加,甚至其赋病民,民不堪其苦,则行单税制足以召乱者,行复税制庸讵不可以召乱乎?吾故谓梁氏好为推类至尽之言以此,吾复有一言忠告梁氏曰:大凡言学,有须分析言者,有须综合言者,有互相关联者,有不容牵涉者,非若文辞,故为抑扬顿挫,推波助澜,以耸人观听为能事也,以如是方法而言学,失之远矣,梁氏识之。[16]
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然而如何不增加人民过分的负担,涉及经济政策制定的良善与否。在《荀子》观念中,“养民”观念却至为切要。《荀子·大略》说道:“不富无以养民情……。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可以看出“养民”与“富国”之间是息息相关的。此外《天论》篇有云:“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利用自然界的物类供给人类生活所需,让人生命得以延续,在荀子看来,既是社会生存之道,也是自然界的法则秩序。
荀子认为圣者要能“称王”于天下,必须善于拔擢晋用“圣臣”,而圣明的臣子其特色之一,即在于能“推类接誉,以待无方”,《臣道》篇说道:
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
政治事务的多变性,以及百姓需求的多样性,要有推论类似的事物、综合对照同类事物的能力,才能成为圣臣,其举措也才足以作为准则榜样。晚清政事多云“推类”,其作意大抵也即在于此。
(二)以类相从
在讨论治乱赏罚之举时,荀子特别提到行为与刑罚之间的“对称性”,而用“以类相从”来说明,荀子《正论》说道:
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
在荀子看来,爵位、官职、奖赏、刑罚都是回报,与行为的类别相应。一件事情赏罚失当,那就是祸乱的开端。德行和地位不相称,能力和官职不相称,奖赏和功劳不相当,刑罚和罪过不相当,都是会给国家及人民带来祸害的。此外,国家施政如何“以简驭繁”,也跟是否能善用“以类相从”之思维,以作相当的分类归属有关。晚清相关政治档案文献,也提及:“一事而有两奏者,则以后奏为准。由各部及各衙门分任编纂,各就主管事务,酌量分类,每件例案,以类相从,均冠以各项法令名称。无论从前通行例案,或历年奏咨成案,概将所定办法列为条文。”[17]现代性当中的理性化及官僚化特征,在科层架构之中,所要建立的即是有效率的管理。在治国上,“以类相从”不止用在赏罚方面,荀子也说到爵列、官职的安排,亦需与行为能力相应,这是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要。清末立宪改革的相关档案中,亦提到:
离而仍严守官等之限制,则不特有裨于职任之确定,亦庶几无戾于久任之观成矣。若夫与本职而摄他职时,亦必宜以类相从,仍不得越二职之限。至凡在监督机关之下而任有职事者,仍不得摄被监督机关之职事,所以杜舞文弄法之弊。[18]
从政治层面上看,现代化首先意味着政治权威的理性化;对国家的管理是政治职能的分工、制衡抑或协同。这段奏折之语不仅谈及派任官职需考虑能力,即使职务有所兼摄,也仍须“以类相从”,注意专业性的问题。另外,在职官权责划分上,在两个机关任事,需注意避免“监督”与“被监督”的角色上的混淆,这种思维亦颇符合学习西方民主政治制度,需考虑的“制衡”关系。
此外,在中央政府机构改造上,李鸿章曾上奏折提到:“臣等窃惟裁并官职,诚为今日当务之急。然各衙门承办多年,另改旧规,非取其素有交涉者,以类相从,不足以臻妥善。谨案会典内载,詹事府掌文学侍从,拟请归并翰林院;通政司掌纳各省题本,拟请归并内阁。”[19]这里“素有交涉者”能够“以类相从”,用荀子的概念,即为大儒。
在国家财政上,预算、决算事项繁琐,中央、地方收支划分,亦需“以类相从”加以分门别类,使其各有归属。度支部的奏折就提到:“议决预算、决算事项,不出地方用款之范围,此为宪政编查馆咨明之权限,臣部综核各款,研究性质,分别名目,以类相从,是以现拟章程有各省预算、决算册,画分国家行政经费、地方行政经费之议。”[20]在另一位大臣载泽的奏折中也提到:“国家岁出表册,皆分别事项,造送主管预算各衙门核定编制,而仍以臣部总其成。此外在京各衙门亦仿各省之例,以类相从,造送主管预算各衙门核编。其关于皇室事务各衙门预算分册,仍暂送臣部汇编,俟皇室经费确定后,即专归内务。”[21]这里所涉及朝廷、地方财政划分及预算编列问题,亦强调需透过“以类相从”的思维来统筹分配。另外,在晚清政权对待有功之满族人士,如何学习汉人功臣赐姓之举,也认为可用“以类相从”的思维方式来运作:“况功臣赐姓,史册维多,满洲本有老姓,可拟照汉军有姓之例,各冠之于名字上,与汉人无或异,则以类相从,自可泯猜嫌之渐矣。”[22]在此“以类相从”的推类知识,不只是引古例为今所用,且超越族类之局限,名字背后所反映的宗族血缘关系,在朝廷皇恩“赐姓”底下,也不得不臣服于其下。
(三)以类行杂
《荀子·王制》曾云:“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这里一样强调运用各类事物的法则去治理各种纷繁复杂的事物,用统括一切的法则去治理万事万物。就一国而言,外交事务较之于内政,其间所涉及的语言、风俗、国情之差异,可能更需要此一“以简驭繁”的思维及能力。晚清大臣周传梓在《湘学报》[23]所刊载的《交涉之学》一文中,就申发阐述“以类行杂”之理。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奉行“公法”,关乎国家之强弱,其说道:
我中国四万万人之众,神州三百五十方万里之大,而受哃喝,若此,其故何也,盖西人视我为公法外之国,不能举公法以与之争,即与之争,诸国皆漠视之,不肯发一公论也,……交涉之案,层见迭出,任情蔑理,藉端滋事,而皆非彼所谓公法者,与西人交涉,既不伸直理驳谲觚,又不能援据彼所谓公法者,然则公法果可恃乎,其不可恃乎,其不可恃也,则必往复辩论,焦唇敝舌,毁已成之约,如曾惠敏而后可也,其可恃也,遇有参差,则必中西法律,参用而后可也。[24]
荀子在先秦,本就主张“隆礼重法”,其目的在于建立社会国家秩序。如前所述,荀子谈“名”言“辩”,皆以礼义为核心,其施用于“公”,本来就兼具道德及伦理内涵。周传梓引晚清外交名臣曾纪泽(谥号惠敏,1839—1890)为例,说明他在会通中西法律之余,能据理(公法)力“辩”,为公众利益交涉。周氏接着说道:
问公法之行,以彼此交接之道,推之一国,由一国推之,万国权则伟矣,其利安在,曰,公法本性法义法,推其所出,仍本于天,即中庸所谓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也,其利有三,有公同约定而遵守者,有未经约定而遵行者,有未行而中心信服者,盖性法酌理准情,不偏不倚,人之好恶,本于天性,性无不善,至善之法,遵行者固皆信服,即不行者,其心未尝不服也,是无它故焉,曰能群也,国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疆,强则胜物。政虽杂而类焉,国虽万而一焉,荀子所谓以类行杂,以一齐万也,所谓以一行万者,君主之国也,以类行杂者,民主之国也(得其统类则不患于杂也),君民共主之国,则以杂为类,以万为一者也。[25]
这里完全借用荀子“群而能分”的观念来谈求竞生存之道,虽然将“以一行万、以类行杂”两个观念,解说成“君主之国”与“民主之国”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这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但在强权环伺之下,“以类行杂”、“统类”等观念,能促成国家之强大,也正是荀学观念在近现代思潮中,能展现其与时俱进的一种表征。
五、荀学“辨异”的观念
(一)“辨”与“辩”:公心与礼义
《荀子·正名》曾说道:“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能以“公心”辨之,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基础,犹如“群”是人之贵于禽兽的重要基础。《荀子·非相》提到:“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由“辨”连结于“分”,“分”所涉及的是“礼”的秩序及政治、社会中的“名分”。钱穆曾经比较荀子以前的社会是“依阶级而制礼”,荀子则反其道而是“本礼以制阶级”:
古人本阶级而制礼,先有贵贱而为之分也。当荀子世,则阶级之制殆于全毁,乃欲本礼以制阶级,则为之分以别其贵贱也。荀子之分阶级之贵贱者,则一视其人之志行知能以为判。曰“大儒”,为天子三公。曰“小儒”,为诸侯、大夫、士。曰“众人”,为工、农、商、贾。[26]
此一阶级之分,着眼于“志行知能”,可以说是道德与能力的整体考虑,而非以世袭爵位作为阶级贵贱之分。因此,在“群”的概念意义之中,圣人所制之礼如能透过能(辨)之“公心”来(明)“分”、(反)“正”,则能去世袭之弊,存阶级之善,个人与群体关系之中,完善秩序的追求亦不远矣。
关于“名”的起源,《荀子·正名》篇特别指出:
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
这里涉及“辨异”之所以能够进行,关乎是否能够“知类”。因为不同的人有其不同的意念,不同的事物的名称和实际也有所不同,如果不能知类而作辨异区分,则混乱地缠结在一起,影响所及,不止事物的同异无法区别,会产生对于事物的错误见解及判断;同时社会地位的高贵和卑贱也不能彰明。对于治国者而言,其纷乱是显而易见的。1916年高元在《辨学古遗(三续)》一文中就特别说道:
然则推类与辨异宜何守。曰不悖不过。辨异不过者。谓必其为类而后从而分析之。非是者谓之过。如分一树为根干枝叶是也。推类不悖者。谓必从物之常实而推其相类之点。苟惑于其寓类而同之。则悖矣。如以鲸为鱼是也。[27]
其举例证虽以近现代生物学知识为例,但就先秦荀子言圣王能知类、统类、义而能辨的角度来说,其所涵摄的观念不仅仅是物类知识,同时也包含治理社会群体的伦类意涵。因此圣王给万事万物分别制定名称来指明实际事物,既可彰明高贵和卑贱之别,也可用来分辨相同和相异。《荀子·正名》另外也提到:“所为有名,所缘以同异,制名之枢要。”换言之,圣王需要“制名以指实”,来区别事物的同与异,其不仅在背后凸显对于自然秩序的认识与掌握,同时在社会秩序当中,也能让社会地位的贵贱有所彰明。
“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虽然会带来对于事物同异关系的认识局限以及名实关系的紊乱,然而在对其他物类的区分上,当人类运用感官接触外在事物时,因人“类”的共同身份,故能“同情”运作而对事物掌握,使用概括的名称来作为彼此对事物的了解及进行交流互动。荀子所谓“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荀子·正名》),即着意在此。
与“辨”相关的,还有“辩”之一字,前述提及清末民初学者,多以名学与辩学来等同于西方逻辑之学。例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严复在翻译英国哲学家John Stuart Mill于1843年出版的“ASystemofLogic,RatiocinativeandInductive”时,所使用译名为《穆勒名学》,并称名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28]。光绪三十四年(1908),王国维在翻译英国逻辑学家 William Stanley Jevons出版的“ElementaryLessoninLogic:DeductiveandInductive”时,将之译为《辩学》。胡适用英文写成的《先秦名学史》,也是此一思路底下的产物。“名”、“辩”这两个先秦典籍当中的文字之所以被青睐,如同有学者指出的:“这是因为西方逻辑缘起论辩,研究思维,兼渉语言。先秦时期对名、辩的讨论则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中较为侧重智与言的一个方面,二者被认为有某些相同之处。”[29]不过王国维在1905年发表的《论新学语的输入》一文中,也曾经分疏中国、西方思维特质之差异,他说道:
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除迫于实际的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夫战国议论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学派及希腊诡辩学派之时代。然在印度,则足目出,而从数论声论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学,陈那继之,其学遂定。希腊则有雅里大德勒自哀利亚派诡辩学派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名学。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30]
王国维所谓“名学”就是指逻辑学。然而王氏指出“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辩”之一字在荀子,不是只有辩论的意义而已,其必须连结“辨”、“类”、“公”、“义”等观念来说。也就是说,荀子言“辩”,必须放在道德及伦理意义方面来思考。就此,《荀子》文献当中,多次提及“礼义”优先于“辩”,其重视“礼义”作为个人修为及价值归趋的意义,超过“辩”作为一种专业技能的训练。《劝学》:“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非相》:“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大略》:“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非十二子》:“故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这里所言君子或圣人之道,并非反对“辩说譬谕”,而是顾虑缺乏“礼义”为导的“辩说”,一方面如战国惠施、邓析等辩者,成为无益世道人心的“诡辞为辩”、“苛察缴绕”之谈[31];另一方面则成为纵横家之流,存为私心一己之利着眼。因此《非相》篇还特别区分:“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其中“圣人之辩”是“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圣人礼义之于内心,发而皆能中节,其辩说既富有文采,又合乎礼法,措辞和改换话题,都能随机应变而不会穷于应答。可以说,“公心”、“统类”是圣人治理天下,“义而能辨”、“礼义之辩”的重要基础。
(二)“辨异”:“类”的差等性
《荀子》一书,谈“辨异”之观念,曾以资作为批评墨翟、宋钘“节俭寡欲”之说的用语。《非十二子》提到:“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墨家学说有别于儒家差等之爱,主张“兼以易别”,来作为挽救周文疲弊的失序情形。而墨翟、宋钘“节俭寡欲”之说,显然也有违荀子对于人欲存在事实的看重。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一文中曾指出:
(荀子)反对墨子的兼爱,说他“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说他看见人类平等的方面,忘却他不平等的方面,确能中墨子之病。但荀子自己,却是“有见于畸无见于齐”。他认“容辨异县(同悬)君臣”是社会组织唯一要件,全是为阶级观念所束缚,见地实远在墨子下了。[32]
荀子言“人生而有欲”,此正是社会群而能分的基础,也是荀子“隆礼”以作为“化性起伪”的思想依据。其阶级观念的存在,是建立群而能分,进一步带动政治、社会秩序建立的重要凭借。若依寡欲之说,既不能承认社会群体人欲需求差异的存在事实,也无法重视“礼”、“乐”对于人性的调节作用。就荀子来说,圣王的“天养”、“天政”是必须注意群体之内各个组成“分子”的差异性。也因此《君道》特别指出:
圣王财衍,以明辨异,上以饰贤良而明贵贱,下以饰长幼而明亲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晓然皆知其非以为异也,将以明分达治而保万世也。故天子诸侯无靡费之用,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其能以称义遍矣。故曰“治则衍及百姓,乱则不足及王公”,此之谓也。
圣王能制天、用天,以控制分配富饶有余之物来满足人欲的不同层次需求。并由此彰明社会人群的等级差别。自然、社会关系中的各个“分子”,可以用“类”称之,《荀子·天论》提到:“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天地万物中,人类与其他物类的存在,若能利用其他物类以为人类生活所资者,即能增进人类生活福祉;若否,则会让人类“欲穷于物”而不得,生活因而带来祸殃。因此,对“类”的清楚认识,可以说是建立在人与人,以及人与天地万物复杂关系网络的构成基础之中。只有认识“类”的存在性,以及掌握“类”的属性、关系网络等相关知识,才能使得“天养”以及“天政”得以展现在社会和谐的运作中。从这个角度而言,“明辨异”并不是要来制造等级差别,而是要用它来确定名分、达到治理的目的。
六、结 论
荀学作为“群”体社会“伦”的积极意义的开拓者,事物之“道”、生命存有之“道”,都必须在社会群、己关系,自然物、我关系的相互含摄中,得到安顿与体会。因此,“类”可以说是人与人,以及人与天地万物复杂关系网络的构成基础,认识“类”的存在性,以及掌握类的属性、关系网络等相关知识,是“天养”以及“天政”所能展现的意义。而这样的意义在晚清亟欲改革政治、社会的思想氛围中,荀学提供了相关的思维型态及知识内涵。荀子对于“类”的划分及所建立的自然与社会意义,包含了对于天地自然的观物分类知识,以及经验世界中的推类感通形式。荀子在《正名》中曾经说道:“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荀子要通过分类和以名指类的方式,以达到辨同异、定名实,以及志通道行的目的。晚清严复曾经说道:
是故欲治群学,且必先有事于诸学焉。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力学者,所谓格致七“之”学是也。炙“质”学者,所谓化学是也。名数力炙“质”四者已治矣,然其心之用,犹审于寡而荧于纷,察于近而迷于远也,故非为天地人三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而三者之中,则人学为尤急切,何则?所谓群者,固积人而成者也。不精于其分,则末由见于其全。且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大小虽殊,而官治相准。故人学者,群学入徳之门也。[33]
在此群学是与西学重要学门相接榫,掌握数学、名学、力学、质学等,有助于人对于生活世界建立正确的认识与掌握,也由此提升由个别之人所组合而成的群体社会之进步。严复将生物个体与社会关系加以模拟,并运用“全”与“分”、“体”与“用”的概念来分析“群”之意义,并模拟于“生物之一体”。换言之,“群”的概念虽然含括了分化的关系,但这种分化关系只有建立在一种全体的理解方式之上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据此,群学所建立的知识及伦理各种面向的关系网络,也使得荀学所能连结的意义群也随之多矣。
注释:
[1]王先谦:《荀子集解·正名》,台北:华正书局,1988年,第280、281页。以下引《荀子》原文,俱依此版,兹不再作注赘述。
[2]高元:《辨学古遗(三续)》,《大中华》,第2卷第10期,1916年。
[3]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群学肄言·译余赘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6页。
[4][美]诺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著,张传有、高秉江译:《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页。
类似的看法还有美国哲学家博蓝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所提到的“支持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他认为影响一个人研究或创造能力最重要的来源不是表面上可以明说的“焦点意识”(focal awareness),而是来自于每个人心中不可予以形式界定、无法表面化的“支持意识”,这是从大家过去所接触的文化或教育背景中,经由潜移默化而获取的。相对于其注意力集中在可以明显意识到的对象或问题时的“焦点意识”,隐含而丰富的“支持意识”往往可以成为转化、解决、创造等能力的重要来源与依据。关于此一概念,可参照博蓝尼著、彭淮栋译:《意义》,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博蓝尼讲演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
[5]“墨辩”包含《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文献。
[6]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论理学史序(即名学)》,《刘师培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页。
[7]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论理学史序(即名学)》,《刘师培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9、40页。
[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8·专集之三十八·墨经校释·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9]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上海:上海书店,2004年,第212页。
[10]梁启雄:《荀子柬释·自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页。
[11]王先谦:《荀子集解·非相》,第51页。
[12]傅兰雅:《日本国新订草木图说·序》,《格致汇编》,第2册。
[13]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著,严复译:《名学浅说》(第一百六十六节),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25页。
[14]张尔田:《孔教五首(致甲寅杂志记者)》。章士钊(秋桐)主编:《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三号,1914年7月10日,第24页。又见娄子匡编著:《景印中国期刊五十种》(第二十二种)(台北:东方文化书局复刻,1972年)。
[15]汪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七号,1906年7月25日,第54页。又见黄季陆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第二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
[16]太邱:《斥新民丛报驳土地国有之谬》,《民报》第十七号,1907年10月25日,第276页。又见黄季陆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第三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
[17]奕劻等:《内阁总理大奕劻等奏请饬各衙门编纂现行法规及具奏办法折 附清单》,宣统3年闰6月29日,收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汇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08页。
[18]增韫:《浙江巡抚增韫代奏在籍编修邵章条陈厘定官等事宜折》,宣统二年3月初2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42页。
[19]李鸿章:《大学士李鸿章等折》,光绪二十四年7月20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75页。
[20]度支部:《度支部奏拟清理财政章程折》,光绪三十四年12月1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1020页。
[21]载泽等:《度支部尚书载泽等奏试办全国预算拟暂行章程并主管预算各衙门事项折(附列表三)》,宣统三年正月14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1044页。
[22]贵秀:《御史贵秀奏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六条折》,光绪三十三年7月初10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921页。
[23]《湘学报》原名《湘学新报》,为清末维新派在华中地区的重要报刊,1897年4月22日在湖南长沙创刊,为旬刊。由湖南学政江标、盐法道兼署按察使黄遵宪、继任学政徐仁铸等先后任督办,唐才常、陈为镒等主笔,撰稿者还有杨毓麟、易鼐、李固松、李钧鼐、杨概、周传梓、胡兆鸾、邹代钧等人。以长沙校经书院名义发行。线装书形式,每期约30页,将近2万字。同年11月5日第21期起,改名为《湘学报》。此处征引自邱沛篁等主编:《新闻传播百科全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24]周传梓:《交涉之学》,1898年3月22日,《湘学新报》(四),《清末民初报刊丛编之一》,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6年,第2759—2762页。
[25]周传梓:《交涉之学》,1898年3月22日,《湘学新报》(四),《清末民初报刊丛编之一》,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6年,第2759—2762页。
[26]钱穆:《国学概论·第二章先秦诸子》,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甲编》,第64页。
[27]高元:《辨学古遗(三续)》,《大中华》,第2卷第10期,1916年。
[28]穆勒(John Stuart Mill)著,严复译:《穆勒名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页。
[29]崔清田主编:《名学与辩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页。
[30]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6页。
[31]《非十二子》篇批评战国时期辩者惠施、邓析说道:“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
[3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8·专集之三十九·墨子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1页。
[33]严复:《原强》,《严复集》第一册,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