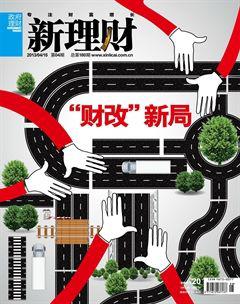财政供养难“裁员”
武彬
财政供养人员是政府行政工作的基础,其规模大小直接影响政府效能。上世纪末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有效地抑制了财政供养规模的膨胀,而在过去的十年中,“精简”改革似乎陷入瓶颈。此外,在优化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与功能方面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财政供养问题其实是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政治体制的很多深层次问题都会在财政供养问题中得到集中反映,而财政供养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也只有通过政府体制改革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可以看出中央此次行政改革的决心。
结构性过剩
财政供养人员,包括两部分:一是在职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二是离退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由此推断教师、科研人员、离退休人员等等都是财政供养人员。这就有了疑问,比如在不少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教师的编制还有不足,科研人员亦是如此,而退休人员也不可能人为减少,可见总理的话不是针对这一块。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财政学系主任曾康华教授认为,目前所谓的财政供养人口只减不增的范围,可能侧重点更多的还是在公务员这一块。而对于为何现在的说法还比较模糊,可能是为了在随后留下一定的操作空间。至于其他的,涉及“吃财政饭”的人员,这个要纳入其中恐怕有些难度。
我们知道,在任何国家,政府要想有效地治理国家,并向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都必须用自身的财政资金供养相当数量的公务员、军队、警察等人员。因此,财政供养人员堪称是政府提供服务的基础。
而问题正是在于,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究竟应维持在何种水平才是合理的和适度的,这一直是困扰各国政府的一个理论和现实难题。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时期,又在经历着经济体制转型的重大转变,同样需要供养大量人员来履行政府的管理、监管和服务职能。同样,我国当前的财政供养规模是否合理,与我国的国力是否相称?这个问题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广泛关注。此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就曾表示,政府党政公务以及行政事业和养人的支出,占政府全部支出的44%,主要是工资、社保、办公费用,还有公招、公出、公车等等一系列的费用。44%在全世界也是比较高的,日本的行政公务开支只占2.4%,可以说是最便宜最廉价的政府。比较昂贵的政府可能是意大利,大概是19%,也只是我国的一小半。
据了解,目前财政供养问题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一些人士对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进行了古今比较,认为中国当前的财政供养率同历史各个时期相比都显得过高,并由此得出“当前中国的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已到了极限”“急需下大力气精简人员和机构”等结论。也有一些学者借助“财政供养率”等指标,将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财政供养规模不是偏大而是偏小,认为中国财政供养问题中,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公务员的比例和结构不合理,从而导致“结构性过剩”和“运行性过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白智立教授认为,现在从纵向来比较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比如在唐宋时期政府的公务人员其实是很少的,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很少,基本只有治安和审判而已。而现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多,小规模的公务人员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需求。
“巧妙”加减法
减员增效一直是这些年政府转型的主旋律,而具体效果如何,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
“人,这个问题,在中国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曾康华说,“很多改革,一涉及到人,就困难重重。我觉得这次的改革从现在来看力度可能还不如朱基任总理时期的力度大一些,那时还是裁减了不少人员,好多部门裁员达到50%左右,当然最后的效果也不是很好,中央部委不少人员要么就是去了事业单位和企业,要么就是通过各种途径又回来。而且现在最头疼的问题是,市场本身也有自己的容量,可能也已经饱和,这些被精简的人员很难推向市场,更难以为市场所吸收。”
据某部委人士回忆,在那个时期,有很多人都“被裁员”。他的一位熟人也在此列,据说当年走出原工作单位就去了奥委会,几经转折又回到了该局,此间在国外拿了学位,还保留几年的工资,解决一套福利性质的分房。他说,这些政策无疑都是安抚,也有一部分人在经过培训之后就去了企业或是其他机构,不过他始终认为这样的改革,成本依然是很高的。白智立认为,也只有中央机构才有如此的“容量”来安排这么些人,省级可能还好点,地方要大量“减员”压力就会更大,这也是当年机构精简为什么在基层难以推行的原因了。
就精简问题,记者还采访了某市财政局的一位干部李某。他认为现在的精简工作其实还是名义上的改革,在工作量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减员会催生出一些不良的反应。就拿这些年的派遣员工,频繁的借调来说,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说现在很多局里的公务员,看上去人数变少了,其实去办公室一看,人都还在,而区别在于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是事业编制,从编制上来看确实是减员了。而且这些人员的工资也是由下面的单位来发,机关的负担减少了,不过随之就是下面单位的负担变大了。而且现在更普遍的是派遣员工,人事关系在外包公司,工资也在这些公司领。再比较“流行”的就是借调,下属单位或事业单位都有。他回忆说,以前碰到一个其他分局的干部跟他吐苦水:“上面老是来借人,我们招的人都快不够借了。”他认为还是越到基层越混乱,举个例子,市政府要是借1个,那下面局里就要借3个。李某在机关工作也已经快10年,他回忆在若干年前60个编制里,上面占的编制就有20个左右,几年前精简过一次,现在大概90个里有4、5人。不过随即他向记者表示,这几年下属单位的数量也在增加,总人数不见得有多大的变化。而当问及编制不够怎么办时,他很轻松的说,首先是名义,这个问题一般机关都有借口,再到具体的编制,如果实在不够,由局长出面向人事局协调几个名额即可。对于借调的“盈亏”之说,他认为上级机关往往也会给政策、给资金或者项目,总之是有利因素向下级单位倾斜,结果是双方往往都有“动力”。
效率优先
白智立认为要想预防此类情况的发生还是要加强立法,他说,中国公务员现在存在着义务与身份的分离问题。在日本,中央公务员到地方工作,或者地方公务员到中央工作,身份就必须发生实质性的转换。而且还存在临时公务员管理办法,比如某企业的员工去区政府工作一个月,在这一个月时间他就是公务员,必须遵守公务员的法规,财政也必须负担其工资。白智立指出,目前某些基层的“临时”执法人员违规执法,而且还不受公务员法的管理,单位也没责任,甚至“一开了之”,就是因为身份与义务发生分离。
“中国的公务员比例实际上并不比国外高,相反还要低很多。”白智立说,“比如日本400万,中国700万,而日本的人口只有1.3亿。国外政府提供的服务很多,所以需要的人也很多。比如在日本的400万公务员中,还包括了负责收垃圾和处理垃圾的人员。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国外的政府人多、提供的服务也多,然而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却远远不及“小政府”的中国。可见公务员规模大小之争,对于目前的放权、搞活市场似乎意义不大。白智立表示,现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受到的制约不足,他更“愿意”伸向利益之处,食品安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还是没有做好。所以我国政府的改革还是应该转变政府的职能,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服务上面。”
曾康华认为:“从新一届政府上台发表的声音来看,本届政府改革目标更多的应该是效率这方面的,而反观以前,我们政府在市场功能上替代的太多,财政更是各个方面都要管。我觉得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应该把更多的机会交给市场,人员改革也是,应该把精力放在放权和搞活市场上来,而不是大包大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