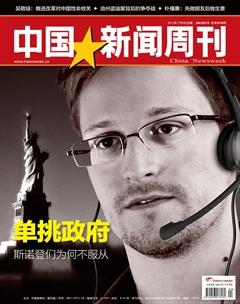被误读的“大调解”
申欣旺
随着中共中央提出的六十项司法改革任务陆续收官,于2009年启动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也进入最后的验收阶段。
这项俗称“大调解”的改革中,改革推动者希望使诉讼与其他矛盾纠纷解决方法衔接起来,在社会矛盾多发期,“更大程度化解矛盾”。
尽管改革试点在事实上显示出化解矛盾、节约司法资源的优势,但改革本身却一直伴随着质疑和不信任,令改革者始料未及的是,“来自法学界的质疑更多。”
在一次有最高法院领导参加的会议上,法学界一位知名学者甚至调侃说,最高人民法院干脆改名“最高人民调解院”得了。言下之意,最高法院是在放弃司法功能,把自己降低到与人民调解一样的位置。
改革的推手之一,最高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多位法官直言,“很多人包括法学界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个改革,甚至法院系统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
多元纠纷解决成“替罪羊”
司法实践上对调解原则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调解逐渐被“加强”的信号。
1982年,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民事诉讼法》(试行)中规定“着重调解原则”,到1991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法院调解的原则被修正为“自愿、合法调解原则”。调、判关系也相应调整为“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 2008年,这一方针转变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

调解率的变化也证明了调解得到加强的过程。据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浩研究,“在1989年之后的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由于法官们认为判决比调解更能彰显法官的司法能力,调解率曾节节下降,全国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的调解率在1989年时曾高达63.9%,判决率只有16.5%,而到了2001年,民事案件的调解率只有36.7%,判决率则达到41%。”
李浩认为,随着中央高层开始重视调解,尤其是“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的提出,调解在司法实践中的比例越来越大,2009年,调解率首次超过判决率。而2010年,全国一审法院的调解率为38.80%,判决率为30.99%,调解率超出判决率近8 个百分点。”
这种改变是“调解优先”原则的具体体现,背后则是依靠法院系统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李浩说,“许多地方采取用调解率考核法院和法官的方法,把调解率的高低作为衡量法院工作是否先进的指标,把调解率同法官的个人利益挂起钩来。”
另外,在中国“调审合一”的审判模式中,法官事实上往往具有选择的决定权。当拥有裁判权的法官一心要调解时,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很难拒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强迫调解。
研究者认为,由于在实践中出现了“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率、未能遵循自愿原则、弱化了对民事权利的保护、软化了法律规则、忽视了对事实的查明”等诸多问题,使公众和学术界对调解质疑不断,甚至认为这是对法院司法属性的自我放弃。
质疑中,很典型的观点是,最高法院是不是要放弃司法功能,把自己降低到与人民调解一样的位置,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似乎正好是在做这个事。
2011年4月,在中央十六部门共同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调解优先”亦被置于显著位置,在此方针指导上,“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作用。”
最高法院司改办副主任蒋惠岭介绍,中央推进的大调解,落实到司法改革任务中,实际上就是司改办承担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改革。
在公众看来,人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法院内部推行的诉讼调解还是大调解,其方式方法目标都是一样的。
蒋惠岭私下只能笑称,“诉讼调解的确存在一些问题,相关的改革方案也正在论证之中,但千万不要让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成了诉讼调解问题的替罪羊。”
社会力量在哪里
虽然质疑不断,但法院系统内的这项改革仍在推进。最高法院司改办指导处副处长龙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改革能使纠纷解决更加便捷高效,成本降低,法院案件数量增长得到有效的遏制,也极大缓解了法院和法官办案压力。”
在改革推动者看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提出,最大的背景正是社会转型期中,矛盾纠纷多发,诉讼案件数量激增,申诉缠访数量不断增多,而司法资源是有限的。而且有些纠纷用其他方式解决,其效果会更好。
其实没有哪个国家依靠司法可以解决所有纠纷。龙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法治发达的国家真正起诉到法院的案件一般只是在所有纠纷数量的20%上下。”
但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龙飞说,“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有纠纷打官司的观念,很多人不信任且不愿意接受法院之外的调解,对非诉讼机制认可度较低。”
在国外则是相反,“有纠纷首先想到的是行业组织,通过这些渠道解决成本低、速度还快,比如美国,打一个官司要花很多钱,而且旷日持久,这时候非诉讼的机制就发挥作用了。”
差别在于,西方国家有了一个立体的纠纷解决机制,而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司法在发挥作用。
2002年以后,随着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调解被认为是更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实现社会和谐的一种解决纠纷方式而重新得到重视,最高法院也不断强调应当注重用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纠纷。
此后,《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正式提出,“加强和完善诉讼调解制度,重视对人民调解的指导工作,依法支持和监督仲裁活动。与其他部门和组织共同探索新的纠纷解决方法,促进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为此,最高法院确定了上海浦东新区法院、甘肃定西中院、福建莆田法院等九家试点。
蒋惠岭说,“随着案件数量增长,法院处理的效果也不是很好,当时想促进仲裁的发展,和包括医疗、劳动人事等矛盾多发的部门建立了处理纠纷的机制,但最重要的一点,法院在中间应该怎样运用这些机制做的还不够。”
2008年,中共中央确定60项司法改革任务,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被列入其中。
2009年,最高法院提出,完善诉讼与仲裁、行政调处、人民调解、商事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机制,为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繁荣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这种改革要求之下,2012年,最高法院将试点法院扩大到42家,区域范围上从东部中部和西部全覆盖,而法院层级则涵括高院、中院和基层法院。
改革需要“整体保障”
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改变把法院作为解决纠纷唯一渠道的固有观念,调动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积极性,并且建立良好的诉调对接关系。
按照龙飞的说法,“真正成熟的法治社会,不仅依靠司法来解决纠纷,还要通过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规制来自我消化矛盾。”
最高法院试图通过平台建设、工作机制和保障机制来推进这个过程。
以平台建设为例,改革要求试点法院应当建立诉调对接中心,并与仲裁、行政调处等外部调节力量建立对接关系。
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在所有的试点法院中走得最远。2009年,该院成立诉调对接中心,到2013年3月进一步成立了单独建制的民七庭(也称为诉调对接中心),人员包括1名主任,6名诉调法官,35名诉前调解员以及30名其他工作人员,并设有15间调解室、4个派出点和4个工作站。
蒋惠岭认为,在各级法院设立专职的调解员,与法官分开,在调解过程中能够避免“审调合一”, “推进诉讼调解本身没有错,但在有些法院在具体做法上有偏差。调解和审判应当是分离的,裁判的法官不调解,调解的法官(或专职调解员)不裁判,这应当成为法院诉讼调解未来的改革方向。
改革者认为,单独设立的诉调中心还节约了大量审判资源,以浦东新区法院为例,2010年8月至2012年期间,该院诉调中心用全院不足4%的审判资源,共处理案件58227件,其中非诉调解协议司法确认58件;诉调成功案件37291件,速裁案件5312件,分流了全院30.6%的民商事纠纷。
但设立机构并不容易,因为涉及到编制、经费等,如无地方政府支持,很难做到。在42个试点法院中,仅有上海浦东、上海普陀、四川眉山、江西南康、北京朝阳等八个试点法院争取到了单独编制的诉调对接中心。
除了编制、经费等现实困难,法院内部和外部对价值上的误读也使改革面临难题。
蒋惠岭说,“法院系统内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诉讼外调解室调解组织的职责,法院过多地参与诉前调解超出了法院审判职责范围,影响了法院自身的审判工作。”
更具体的影响是,因为这些纠纷未进入诉讼程序,无法进行司法统计,一方面无法体现法院审判工作中化解大量社会矛盾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不能纳入对法官办案数量、调解率等考核指标中,进而影响到法院开展工作的积极性。
对外部而言,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多元纠纷解决理念尚未普及,包括调解员的素质不高,调解的认同感不强,违背调解原则造成的负面影响等,整个社会对非诉讼机制的认可度仍然处于低位。
作为改革的组织者,最高法院司改办向有关部门提出的改革建议指出, “为了促进这个改革的长远发展,必须从国家层面上通盘考虑,整体规划化解纠纷的经费保障问题,为各类社会调解组织的行业发展提供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