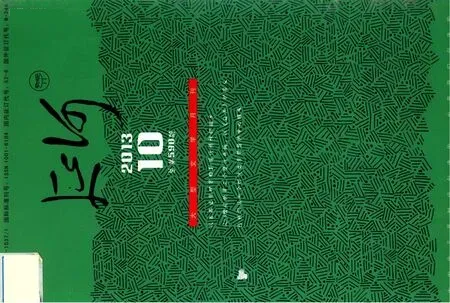舌尖上的故乡
野 水

水盆羊肉
水盆羊肉,有别于清真的羊肉泡馍。既是水盆,当然汤多。正宗的水盆羊肉,应该是选用黑山羊的肉,其肉质细密绵厚,往往是沉在碗底的,约莫三四片,常常煮得飞花稀烂,入口嫩酥。汤是清亮的最好,这与厨师的手艺密切相关。好厨师做的水盆羊肉,不但肉烂汤清,鲜嫩爽适,而且味道悠长。做得不好,汤色发混,调料咬合不均,色香味就欠佳,倒食客胃口。吃一次,下次人可能就不来了。

据说水盆羊肉的调料多达几十种。除了常用的花椒、桂皮、生姜等,还有丁香、草果、白芷等中药材。具体配方,那属于商业秘密,外人是不能知道的。羊肉性温味甘,入脾胃,达心肾,补血精,助元阳,生肌健力,御抵风寒,自然应为冬令大补。然三秦大地,炎炎夏日里,随处可见“水盆羊肉”的牌子,或堂皇地高挂于一些闹市大街;或歪歪扭扭四个大字写在一块门板上,伫立于尘土飞扬的乡间路边;或干脆什么牌子也没有,门前支一口大锅,锅里吱吱冒着热气,一大锅的羊肉,远远地便飘过一股羊膻味。吃的人汗流浃背,从背后看去,一个一个的头埋在大碗里,只见后脖颈上闪着汗光的肉在蠕动,一片吸吸溜溜喝汤声。蒜皮在风扇下乱飞,满地便飞花片片,蔚为壮观。
这种反季节的吃法,我想可能和四川的火锅大致吧。大热的夏天,川人对火锅也是情有独钟。脚下的地板上,到处是油腻的,走来令人战战兢兢。他们不用什么油碗,直接从锅里捞出来,放在面前的吃碟里,就开始吞咽了,与我们这的火锅有区别,区别就是吃法简单,大概是源于重庆的朝天门码头,那个挑着担儿的火锅鼻祖的简单设施吧。秦人的水盆羊肉,吃法也是简单,一老碗汤水带几小片肉,两个烧饼。一碗水盆端上来,食客先拿起黑而粗的筷子,“哗啦”一声翻江倒海,肉汤在碗里打旋儿,肉片就在漩涡里浮上来。肉少了,嘴里就嘟嘟囔囔;肉多,则喜眉笑眼,连说不错不错。馍也不需要像清真羊肉泡那样掰得很碎,直接大块泡进碗里,一会儿就膨胀飘浮起来。想吃辣,剜一勺油泼辣子,再大刀阔斧一搅,立刻汤红油亮,筷子也就沾满泡沫了,半截子是油水,就将筷子紧紧地夹在两片厚嘴唇中间,“吱”一声如拉响锯,便光洁了;又在桌子上“当”的一声蹾齐,就着生蒜便吃。蒜是不提前剥皮的,倘若撕一小片餐纸,将剥得赤条条的蒜瓣一字儿摆在上面,就显得小资了,那往往是少数的穿白衬衣打领带的人的优雅动作。大多数的人,一手执筷,一手拇指与食指捏了蒜瓣的尾巴,先豪迈地一口咬掉蒜头上的棱角,舌头只一卷一舒,便将蒜瓣咬成一朵盛开的莲花,蒜皮也自然张开一圈。偶有些许小皮儿粘在嘴唇上,“噗”一声吹气,蒜皮便尽飞远处。也许粘在别人的腿上了,管它哩!嘴唇一呡,兀自便光洁了去。如羊吃枣刺,一树的叶子全吞下去,竟无一刺扎了嘴舌。
记忆里,第一次吃水盆羊肉,是跟着父亲去十几里外的公社粮站缴公购粮。前一天的晚上,父亲说明天跟他一块去,顺便吃一回羊肉。我兴奋地一夜未睡,一直凝心那羊肉。第二天,我不用父亲叫,早早就起来了。十五岁的我,仗着不小的块头和亢奋的心情,一个人将装满麦子的大口袋挨个扛出门,放倒在架子车里,一路昂扬地拉到粮站。到粮站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在门口排队等候,直到天大亮,粮站的门才开。交完麦子,已是中午,在烈日的烘烤中,我们疲惫地走进街道的老食堂。
那一碗水盆羊肉,三毛五分钱,肉三毛,馍五分,父亲要了一份,分成两碗。他只吃了一片肉,我却吃得酣畅淋漓,风生水起,如过年一般。那碗羊肉的清香,通过我的嘴,在学校里飘扬了好长一段时间。
后来上高中,学校就在老食堂不远处。每每放学,经过老食堂的门口,我都要奋力地张大两个鼻孔,美美地吸气,期望更多的羊肉味被一丝不剩地吸进鼻子,然后闭了眼,感受肉的芬芳与清香。有好几次,我甚至张大了嘴巴,不由自主地空嚼,猛地就又羞愧起来,四下看看是否有人笑话我。然令我吃惊的是,我看见好几个人,也如我一般,呆呆地立在门口,突出的眼球死死盯着提瓢舀汤的人。他们嶙峋突兀的喉结,在细长的脖子上上下蠕动,又都张大了嘴,眼睛似闭似睁,只听得牙齿在响——古人所谓“屠门大嚼”,真的不余欺也!
最近的几年里,在西安,我也吃过好多家的水盆羊肉,有蒲城的,有澄城的。虽然加了好多的调料,总觉得味道不是很地道。东门外的老孙家,也带上了水盆,但供应的是糖蒜和辣子酱,没有生蒜和油泼辣子的生猛和倔劲;发现了方新村的一家,后来搬到了文景路,又撵到文景路去吃。肉少,刚刚温热了牙,没了。便常常怀念起老食堂的水盆羊肉来。
前段时间,回老家,去了老同的电器商场,老同问,想吃啥,我说回来了,肯定是老家的水盆么,老同说没麻达,不过咱街道的水盆不行,难吃得很,干脆去蒲城吧,比咱门口这美得多,一碗能顶你西安三碗的肉。我说太远了,就在这凑合吧,又耽误你挣钱呢。
老同说,挣锤子钱哩!门一锁,走!“日”地一声,车屁股冒出一股黑烟,冲出了街道。
面的诱惑
我一直是爱吃面的。妻子说,一天不吃面,能把你饿死么!我说,饿不死,但哪天没吃面,总觉得好像没有吃饭。
小时候,面对我的诱惑,始终不能抵御。这也源于当时的物质匮乏。山里人的饭碗,总是稀汤寡水。一年到头,农业社分的那点麦子,是极少有白面吃的。磨面的时候,总是要等到有人先磨,好填塞了磨面机的大肚子;磨完了,又要将磨面机肚子里的旮旯犄角打扫得干干净净。中午一顿饭,不是黑面擀的短节节,就是玉米面片儿。少量的白面粉,是留下来蒸年馍用的。偶尔吃一两顿白面条,那一定是家里来了重要的亲戚,不是母亲娘家的侄子,就是姨家的儿女们,也是等人家吃完了,剩了一点,我才有吃的机会。若是姑家来人,母亲是不擀白面的。
于是,对于白面的渴望,与对那些客人的反感交织在一起。我想吃面,却不想见到那些说话居高而临下的人;而没有那些人来,平日里,是不可能有白面吃的,这样就很是难受。但我能将心里的渴望藏起很深,任何人也看不出来。每当他们吃白面的时候,我就出了门去玩,没有人叫我,我不回去。也许,我本来就是吃黑面的命。

有那么一天,是午饭时间,我起先是坐在门口的槐树下的,眼睛呆呆地望着被槐叶割碎的那些亮光发瓷。但随风飘来的一股葱花的味道,顽强地窜入我的鼻子。它像一个被堵在地洞内的老鼠,在我的心里撕咬碰撞,冲击着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那点脆弱的心理防线,身子便不由自主了,随着那葱花的油香,在巷子里荡来荡去,像一匹逐肉而奔的饿狼。终于,在巷子东头,我看到了二爷。二爷家的劳力多,每年夏收后能分好多麦子,所以二爷吃白面的时候要多一些。现在,二爷正高高地端着一个耀州烧的青瓷老碗,边走边吃。他用一双筷子,将面条高高地挑起,一张嘴努力地向前鼓出,宛如一个小小的圆洞。那圆洞正对着挑在空中的面条嘶嘶地吹气,舌头也不时地伸出来,擦抹着嘴角的辣子,如蛇吐信子。面条里的辣子调得红如鸡血,如一面小而艳红的旗帜,随着他晃动的身体,在筷子上摇摇摆摆。他在巷子里转悠,却并不立即去吃,而是左右搜寻着可能射来的羡慕的眼光。我瞪了他一眼,咽了一口唾沫,转身走开了。
巷子的西头,六爷坐在一棵皂角树下,头埋在一个大碗里。我老远就听见他大声地吸溜。走近了,六爷抬起头来,笑呵呵的问我吃了没有,我没有吭声。六爷的碗里,是一堆黑面条。黑面没有筋丝,擀不成细长的面条,便都是些短节节,但六爷依旧吃得轰轰烈烈。他拿起筷子,在碗里当当当地刨着,将碗的四周,刮擦得一干二净,最后都收拢在碗底,再拿筷子有力地夹起来,像在麦场里用木杈挑起一捆麦子,对着那口訇然中开的大嘴,全部塞了进去,两腮便鼓如青蛙。又“吱”的一声,将碗底的辣子水水吸得光净,碗竟如洗过一般。
六爷将空碗放在一旁的碌碡上,抹一把沾满辣子的嘴,说,如果天天都能吃上一碗白面,就受活死了。
如今,大街小巷的饭馆,多如繁星。在一张张铁皮包裹的案板上,一团面被捶打揉捏,声震屋檐。在手撕刀削中,竟变出万千花样来,相对我闻香逐走在村中巷道的当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一碗面里的佐料,岂是当年二爷碗里仅有的辣子葱花醋水可比!西红柿鸡蛋、木耳红油、大块牛肉。即使最简单的一碗棍棍面,也有半碗的青菜豆芽青辣椒。面条也可以先捞出来,用水透过,再小瓢爆炒。可以肉炒之,也可以蛋炒之。做面的师傅,将一盆的面,盘若卧蛇,在头顶绕匝,于空中划弧。宽者如裤带,言“杨凌蘸水”;细者如发丝,是“兰州拉面”。据说拿一苗针来,可以其为线,自针屁眼穿过。面条凌空跳跃,锅下火星四溅;落入火锅中,似白龙翻腾;盛于瓷盘里,更油香喷鼻。看门口“闻香止步,知味停车”的牌子,诚如斯言也。
面馆多,缘于三秦大地,自古便是天下粮仓,麦子遍地,秦人便以面食为主。在“以食为天”的岁月里,更是积累了繁多的面食做法。耀州的咸汤面,户县的摆汤面,陕北的羊肉面,岐山的哨子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尤以岐山哨子面名气多多。走州过县,在这西京城里,已成连锁,遍布大街。其面薄、筋、光;其汤煎、稀、汪,辣得人吸吸溜溜,吃的人热汗涔涔,却不舍不弃,手握两根筷子,如扫一片秋叶。我每每路过那些面馆,总要探头张望,逡巡不前,鼻翕而口张,若咀嚼状。肚子饥了,就去吃;若是不饥,也记下店名和方位,以便下次来这里办什么事情,也好有个吃面的地方。
不管是哪一种面,不管什么高汤,也不管佐料如何的丰富,总是手工擀的面好吃。冰凉的机器,始终代替不了温热的手工,那其中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东西在里面。黄的土,产出白的面,这是一种怎样的质变?无人能说得清楚。厚重无言的泥土,被柔水抚摸,以温馨的爱意,产出这白生生苗条可人的尤物,分明是大地给予人的恩赐啊。所以,我永远不能忘记,婆在吃过的面碗里,舀半碗的面汤,一边慢慢地转着碗,一边用筷子将碗壁附着的葱花辣子刮刷得净光,然后一滴不剩地喝完那半碗的面汤,锅里剩下的面汤,再用来和面蒸馍;父亲拣起掉在地上的面条,在清水里涮干净,再送入口中。与其说他们怜惜自己劳作的艰辛,不如说有一颗虔诚的对于土地的感恩之心。

大的街道,那些高档的饭店,也有面吃,却不是贵,就是机器压的细面,没有嚼头,我吃不起,也不爱吃。于是便常常走进那些背街小巷的面馆。门前一口大锅,小伙子手托面团,手起刀落,片片如叶,直跌入滚锅中。或者两手如纺线一般,将连绵盘桓的一根面条,拉成白色的细线,飞流直下入沸水,疑是螣蛇乘雾来。须臾捞出,或佐以炸酱,或以油泼之。满桌大蒜,随取即食。吃饭的多是下苦人,粗瓷大碗,面量充足,喝汤就蒜,煞是满足。我吃一口面,喝一口汤,置身其中,恍然如坐在村口的皂角树下,再也不用仰望二爷那面迎风飘摆的“旗帜”了。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前几日,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他把母亲从老家接来了,捎了两袋面。还有老人家自己酿的一桶粮食醋,一捆屋前擁的大葱,中午,母亲要给他擀面吃,问我来不,顺便给我拿一袋,我说一定去咥一顿。当年我经常去他家,他的父亲在煤矿下井,不常回来。隔三差五,我就去他家,和他一起,不是出羊圈,就是给家里拉土。自然没少吃过他母亲擀的面条。面白味香,入口滑筋,如老人家当年织布机上的白线一般。那一碗面,我吃得豪情奔放,滋润了好几天。妻说,大热的天,跑那么远吃一碗面,能有多香?我说,你不懂。
五豆粥
五豆粥是今天中午才熬的。要吃饭的时候,才想起来,今天已经是腊月初五了。
两个人的饭,我竟熬了一大锅,看来要喝上一天了。花生豆、黑豆、红小豆、豇豆、黑米、糯米、小米,家里所有的能熬粥的东西,都被我倒进了锅里,期望在这阴冷的天气里,熬出一团温暖来。

蓝色的火苗嘶嘶地舔舐着锅底。我手捧着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自选集,点起一支烟。窗外一片灰蒙蒙的天空。没有鸟儿在飞。
要不停地搅锅,阅读便被打断。干脆合上书,望着窗外。
婆总是在腊月初五的前一天里淘好玉米的。泡涨了,滤去水分,倒在门前擦干净的碓窝里,坐个小木凳子,手里提着沉重的礓锤,一声接一声地砸进碓窝。那些脱去皮壳的玉米粒,便不时地从碓窝里飞溅出来,落在旁边的柴草堆里,婆就摸索着去捡拾,在围裙上蹭去浮土,放进去,礓锤沉闷的声音便又响起来。
有一两只鸟儿飞过来,围在碓窝旁边。婆看着它们小小的嘴,在地上不停地啄着溅出的玉米粒,婆就停手,静静地看着它们欢快地啄食。
每年的腊月初五,婆都会送来砸好的五豆。婆将那些砸好的颗粒裹在围裙里,藏在衣服下面悄悄送来。她总是说,多煮些时辰,煮烂,娃吃了好克化(消化)。
我再一次向窗外望去,却看不清外面。我走向窗户,擦干净玻璃上的水汽,依旧看不清——我的眼睛模糊了。
回过头来的时候,锅里的粥已经糊了。
搅团
现在的我,不需要吃搅团了,一来煤气灶上架个小锅,两个人,一个搅翻,一个死死按住小锅,终是做不出一锅满意的搅团来,不像早年农村的大锅镶在锅台里那样稳固,一个人手持擀面杖搅得翻江倒海,锅却稳如泰山;二来我从来不觉得搅团有多好吃,那个年月里,我吃了太多的搅团,所谓“吃伤了”。
总有一些饭局,一旦菜单上有搅团,点菜者连呼“搅团,搅团”,就来一碗。但我很少将筷子伸进搅团里,不管是“水围城”,还是凉拌,我都没有多少胃口。童年吃过的那些玉米面还少么。
但那时的搅团,却也时时就映入脑海了。
每年的秋后,玉米收了,除了碾苞谷糁,也磨成面粉。秋后到年上的那段时间,天天中午饭吃玉米面搅团。放学回家的路上,一想到搅团,心里就堵。想吃白面条,可我知道那是奢望。没有多少白面,那要留着过年蒸白馍,或者重要亲戚来家擀面。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打搅团之后锅底粘的一层硬壳,类似现在的锅巴,我们称作“锅渣炸”。母亲铲将下来,我用手掰碎了,装在口袋里边走边吃,嘴里嘎嘣嘎嘣地响一路,直到学校。


上初中,路远,一天不回来,需要背馍,早上鸡叫起床,摸黑到厨房,揭开厚重的瓦盆盖子,取几个玉米面花卷装在书包就走了。晚上摸黑回到家里,母亲已在大杜梨木案上晾好了搅团,不用问,那是中午做好的,已经凝固成一片了。我自己爬上大案,取下菜刀,将搅团犁成长条,再切成小块,浇上辣子和醋水,我们叫辣子水水,那就是“凉调搅团”了。哪一天母亲高兴了,会自己亲自切成小块,再切些山韭菜,绿辣子,萝卜叶子放在锅里,烧火煎热,这种吃法,叫“煎搅团”。星期天的中午,我会参与到打搅团的工作中。先用大火烧开一锅水,母亲一手向锅里撒玉米面,一手拿着擀面杖搅,感觉面粉撒得差不多了,就放下碗,两手握着擀面杖搅。我坐在灶台前的石墩上向灶膛里填麦秸,麦秸是不能集中在中心的,需要用小小的炭锨拨开,分散在灶膛四周,便于锅底均匀受热,不至于搅团粘在锅底。黄亮的火苗升起来,又分散向锅底的周围舔舐锅底,锅上升腾起浓厚的雾气,母亲贴着锅台,肥胖的身子不断抖动。长时间搅拌后,她会提起擀面杖,看淌下来的面水是否合适。她很有经验,会根据擀面杖上淌下的面水的稀稠判断搅团的软硬和生熟程度。
做一次搅团,能吃三天,凉调,热煎,就是不油炸。母亲先舀出一部分晾在案上,摊平,案上又会升起大团的热气。剩下的,一人一碗,辣子水水是早已和好的,只是辣,红,没油水,上面飘几片菜叶。辣子水水浸满了老碗,一疙瘩一疙瘩用筷子夹开,蘸了水水吃。端碗出门,墙根下满是血红的嘴,吸吸溜溜呵气。看着不冒热气,似乎凉了,咽下去,烧得眼冒金星,却无法吐出来,搅团已经滑进喉咙了,烧心也没办法,硬忍,一会就没事了。

大约觉得我们都厌烦了搅团,母亲和几个邻里合资,花三块钱买了一个“漏鱼锣”,谁家要打搅团,就相互借用。将打好的搅团舀进漏鱼锣,用筷子搅拌挤压,形似小鱼的搅团就从那些窟窿里流出来,滑进冷水里,用笊篱捞起,泼洒上辣子水水,搅匀了吃。不管变换多少花样,我始终对这种“哄上坡”的饭食缺乏热情,也许,与搅团里缺少现在的芝麻、香油、酱油等调料有关?
文豪杂粮食府,桃花源休闲山庄,东晋桃源,都有玉米面搅团,满足了好多人吃搅团的愿望,一盘子几十块钱,有那时半碗的量,却都说好得很,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现在人们把搅团归到小吃里,可在那时,却是“大吃”。天天吃,能不是大吃?好多餐馆里,都在造一个食物的文化概念,贴在墙上,画在纸上。羊肉泡有,过桥米线有,却没见过搅团的。据说搅团是诸葛亮西岐屯兵时发明的吃法,我就恨他了,为什么不发明好吃的呢。害得我吃了那么多。
也许,现在加入很多调料的搅团,比起那时只有辣子醋水的搅团,要好吃很多。我抄起筷子,也夹过几块,掉在地上,竟摔不破,滑溜筋道,说是里面有食用胶。
荞面饸饹
饸饹,古称“河漏”。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其《农书•荞麦》里说:“北方山后,诸郡多种,去皮壳,磨而成面或作汤饼(即汤面)”。李时珍《本草纲目》载:“荞麦降气宽肠,故能炼肠胃滓滞,而治泄痢、腹痛、上气之疾”。可怜的山民不识王桢和本草,只是觉得荞面饸饹吃了抵饥,长气力,好干农活而已。
在故乡,荞面饸饹主要是在夏天吃,多以凉调为主,麦面仍然少,玉米面和荞面饸饹多些。后山不长麦子的薄地,长荞麦。夏秋交接,紫红的荞麦花盛开,煞是热烈。荞麦开花的那几天,父亲很是担心,荞麦的花儿,既怕雨淋,又怕暴晒,最好是阴沉天气,但这样的日子是很少的,所以荞麦有“十料九不收”的说法。父亲却年年种,大约也是因了荞麦适于生长在贫瘠之地。
那个年月里,荞面饸饹是我最爱吃的主食。
村上有一台饸饹床子,是村里的王木匠做的。两根粗长的木头,下面的一根横在锅台上,中间挖一个窟窿,嵌进铁制的圆筒,下底是一个一个的小眼眼。两根粗长的木头一张一合,细长的饸饹便从那些密密的眼里流落下来。床子上坐两个人压,嘎吱嘎吱地响,梢头已被磨得油光铮亮。饸饹落在滚开的锅里,像柳树的须根在水里漂游。一家压饸饹,几家来搭手合作。端一盆自己在家和好醒匀了的面,一群妇女叽叽喳喳地说笑,饸饹一疙瘩一疙瘩晾在竹筛子里沥水。热闹的场面散尽之后,每人端着自己的饸饹回家,嗷嗷待哺的孩子和扛着镢头回家的男人,早坐在门口树下的青石板上等待一顿饕餮大餐。他们将喉咙里涌上来的唾沫都咽下去了,连树上的鸟儿也听见了嘴的咂吧声。
靠山吃山。山里人的菜,在山上。野地里有小蒜,山坡的蓑草底下有山韭菜,其味皆辣而悠长。挖了、摘了炒“葱花”,拌在饸饹里,佐以芥末(父亲在一片坡地种的),香辣无比。嘴里噙住几条饸饹,用力吸吮,细长柔滑的饸饹便如蛇的尾巴在空中乱摆,“哧溜”一声就打在脸上,酸醋溅进眼里,眼就睁不开了,索性闭住眼吃。吃完一碗,唇如血狼,红辣子、芥末渣子、韭菜叶子挂在脸上。缺水,不洗,用手一抹了事。六爷吃饸饹,不挑起来,他用筷子一圈一圈地在碗里打转转,直到在筷子上绾起一疙瘩,高举起来,张开破窑洞般的大嘴,就送进去了。他舍不得咽下去,藏在嘴里体验,嘴又微张,将两只染得血红的筷子夹在双唇中间,“吱”一声,筷子上的油水呡得干干净净,然后和我一样闭了眼睛,深深地吸一口气,从鼻孔里慢慢慢慢吐出来,这时的嘴,才开始砸吧。

因为荞面的“十料九不收”,玉米面也做饸饹。冬天压一大堆,放干了,像一圈一圈黄亮的钢丝。好几年的过年待客,竟没有了麦面,只是玉米面饸饹,不柔滑,扎喉咙,并不好吃。在水里泡软了,煎一锅汤,白菜叶子萝卜缨子,能有的菜都放进了。海吃,竟也吃得大汗淋漓。
这许多年里,所谓的荞面饸饹也总是在眼前晃悠,我知道那是色素染的,并无什么荞面,却也忍不住买过几回,极为难吃,从此不再吃了。
人高马大,虎背熊腰的我,一定是吃了很多荞面饸饹的缘故。而我也一直将那根饸饹含在嘴里,默默地咀嚼至今。
那是一根长长的扯不断的饸饹。
皂角芽
吃皂角芽,记不清是那一年的春天了,很早。婆从门后取出一个长长的木杆,木杆的手把磨得黑光,顶上安着一个铁挠钩,挠钩是用绳子绑得死死的。婆举了木杆,站在皂角树下。开春的阳光,温暖中有些许刺眼。婆咪了眼睛,颤悠悠地将木杆伸进高大的皂角树枝间。婆转动手里的杆子,皂角的嫩芽就被挠钩拧折下来。雨后的皂角树身,青灰的树皮闪着亮光,那些才发上来的皂角嫩芽,很像香椿的芽子,老远却闻到一股苦味。
婆不让我上树,怕皂角树上的陈年老刺扎了我。我和一群孩子围着高大的皂角树玩。
婆站在门口的粪堆上,那样她才能够着。婆的身子索索地抖。皂角的嫩芽像小小的降落伞,随着风忽忽悠悠地落在粪堆上。我捡起一个,塞在嘴里嚼,苦得我赶快吐出来。

婆将落在地上的皂角芽子拾起来,裹在围裙里进了低矮的厨房。那些皂角芽被泡在水里。婆说要泡一夜,才好吃。
第二天的清早,低桌上有了一道菜:皂芽。切得细碎的皂芽,已看不出嫩叶的模样了。婆给皂芽里滴了几滴菜籽油,调了柿子醋和辣椒。厨房里弥漫了酸味和一丝淡淡的苦味。我吃了很多。
吃完饭,婆给笼里放了我的脏衣服,从屋子里取出几根去年摘的老皂荚,提了棒槌,去河里洗衣服。
村里再也见不到一棵皂角树了。老的老了,砍了;小一些的,被城里来的人收走了。
在高层小区的院子里,大门口,我又见到了好几个皂角树,不很高大,似乎有几十年树龄的样子,身上还缠着草绳,树身上吊着塑料袋。皂角树在打点滴。
皂角树的叶子也很繁盛,叶子上有一层灰土,但没有结皂荚。是雄株,是老村里雌株皂角树的儿子么?但树下却没有了和我当年一样围着叫喊的声音。星期天里,有几个孩子从树下匆匆走过,他们的妈妈一手提着书包,一手紧紧地攥着孩子的手。
一个孩子指着皂荚树问她的妈妈,那是什么树,年轻的妈妈说,是槐树。
苜蓿卷卷
那一年开春,婆提了笼,厮跟了几个老太,去西梁的那片坡地。那是村上的苜蓿地。苜蓿是给饲养室的牛种的。苜蓿地有人看守,婆见到看守的人回家吃饭了,婆要给全家人吃苜蓿。家里已经没有一颗麦子了。
婆的腿疼,她跪在坡地上。那几个老人,我也应该叫做婆的,都跪在地上。她们穿着黑粗布衫子,像落在地上的黑老鸹。笼已经满了,婆压瓷实,又撅。婆觉得额颅上冷冰冰的,有水流下,婆觉得天下雨了。她用沾满土的手抹一把脸,抬起头来。一个大灰狼蹲在她面前,长长的尾巴在地上扫来扫去,舌头上向下滴水——那是狼的涎水——涎水流在婆的额颅上。婆喊一声狼,提了笼,踮起小脚跑回来。
笼里的苜蓿一根都没少。
那一笼苜蓿蒸了麦饭,全家人吃了两顿。

婆坟头的麻黄,黄了绿,绿了黄,几十年过去了。
我想吃苜蓿卷卷,总是吃不上。没有多余的白面做。
寒食节,我和哥在县城街道的一家饭馆里吃苜蓿卷卷。一笼六个,十块钱。嫩绿的苜蓿散发着香气和热气,苜蓿卷卷散漫而可爱地躺在小小的蒸笼里。苜蓿的叶子从卷卷的边上露出来,露出来的还有粉条和零星的虾皮。我蘸了火红的辣子水水——辣子水水上飘着一层芝麻。我夹起一节苜蓿卷卷,就着大蒜,将整个卷卷凶恶地塞进嘴里。烫面的苜蓿卷卷松软可口,苜蓿的清香透过薄得发亮的面皮散发出来,我要不停地嘘气,才能避免烫嘴。
店里没多少人。一个服务员呆呆地看着我吃。我低下头,一嘴一个,狠狠地吃。我吃了三笼,添了两次辣子水水。
哥说,这家的苜蓿卷卷远近有名,他经常来吃。
我带走一笼。清明,我和哥去了婆的坟地。哥和侄子扛了五棵小柏树,给婆栽在坟地边上。天阴沉地厉害,远近的山梁黑沉沉一片。侄子点了鞭炮,我将坟炊上的疙瘩掐下来扔进火纸堆里。钱是几亿元的面额,烧了好些时间。我将带来的苜蓿卷卷扔进火里,苜蓿卷卷烤得焦黄,发出哔哔啵啵的声音,后来变成了黑色,和那些纸灰一样了。
那晚的雨很大。哥兴奋地说,柏树能活了。
我在心里骂了一句:狗日的苜蓿卷卷!
大颗糁子
门口皂角树上的子规发出叫声的时候,我的眼睛慢慢地睁开。父亲踢踢踏踏的脚步,已经在院子里响成一片。随后,我听见镰刀在磨石上发出沙沙的声音。父亲开始喊我起床,而窗外的天空,依旧是灰蒙蒙的一片。他怕我误了割麦子。我却赖在炕上不起来。
尽管我知道第二天要早起,却并不想早睡。他们睡下了,我重新点起煤油灯,看那些厚墩墩的“闲书”,一晚上能看完一本。在停下来的风箱声之后,母亲开始吼叫。我懒散地起来,就闻到了一股玉米糁子的味道。风箱呼呼的声音彻底停歇下来,一股呛人的烟气从厨房门窗里窜出来;母亲给灶膛里塞进一棵大树根,用慢火煮熬一锅的大颗玉米糁子。树根是湿的,那些潮湿的水分,会在热火的蒸腾中慢慢散去。延伸在灶膛外边的,长长的树根,会被一节一节地推进去,直至燃烧完毕,大约需要半天的时间。而那一大锅稀稀的玉米糁子,会变成全家人一天的饮水——母亲将熬好的汤水刮进瓦盆——谁渴了,随手拿起飘在上面的铁瓢,舀进瓷碗,咕咕地喝下去。
小而细碎的玉米糁子,是在冬天熬的。依旧是文火,熬成糊糊的粘稠的一锅,每人端起一碗,上面漂浮一堆腌在瓮缸里的萝卜叶子。我会坐在门口,就着阳光吃下去;耳边听着鸟叫,眼睛瞅着远处山外的公路,想象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精彩,看汽车扬起的灰土一点点消失在天际。

大颗糁子,只在石磨上碾碎,一遍就行。那是一颗颗完整的玉米被碾成的小块,用来熬汤止渴,是在夏天喝的。从割第一镰麦子,直到秋天,几乎天天的早晚饭,就是大颗的糁子汤。每天天不亮,风箱就呼呼地响起来,那是母亲烧的武火,夹杂她高声大气的呼叫。随后停歇,一棵树根被塞进灶膛。这锅汤水,当下是不能喝的,需到干完地里活回来。一棵树根烧完了,它就熟了。
那是我们一天的饭。
我一直厌倦那每天的大颗糁子汤,但我从来没有说出来。父亲做不了主,母亲脾气暴戾,我也不能改变什么,就只有默默地喝下去。又能吃什么呢。也许,世界上所有的乡村,那一口锅的下面,都在燃烧着一棵永远都烧不尽的树根。每当跟上父亲去挖树根的时候,我都在消极怠工。那一次,我抡起的镢头渐渐缓慢下来,后来,我说上个厕所,父亲说,就在自己地里拉吧,我不愿意。周围的地里,都有人在干活。父亲叹口气,抱怨我将肥水流进了外人的田地。
我扔了老镢头,钻在别人家的玉米地里,半天不出来。
父亲是以门口皂角树上子规的叫声来判断起床时间的。我摸到了这个规律。我悄悄掮了一根长长的杆子,试图将树上那一窝子规赶走,但我够不着,那窝实在是太高了。我用石头子打,石头落在邻家的屋瓦上,兵兵乓乓地响,我在慌乱中逃回家里。子规依然每天叫起,父亲准时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多年以后,我突然又想喝大颗糁子了。我的锅里重新煮了大颗糁子,是在超市买的。没有树根,没有呛人的烟雾,糁子在煤气蓝焰的煎熬里翻滚。没有出现我所期盼的味道。
老屋已破败不堪,铁锁锈迹斑斑。门口的皂角树不是我家的,树已不知去向。在这个即将收割麦子的夏天,我独步残破的乡道,只看到远处上辈人的坟茔。
大颗糁子是需要树根来慢炖的,但我已经找不到根了。

- 延河的其它文章
- 自然的寓言化:一个人的绘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