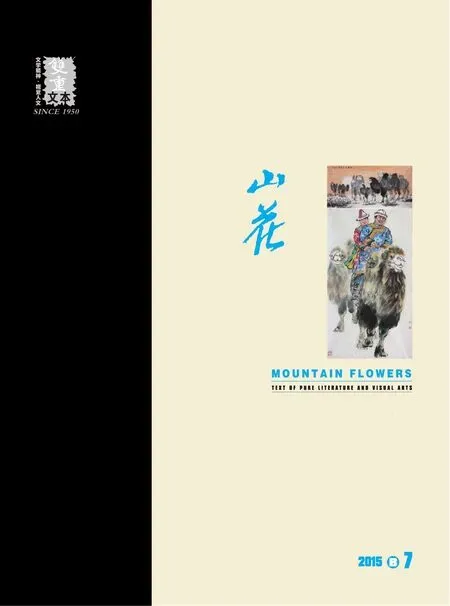传统伦理与现代理性的双重博弈——从《傩赐》看王华小说创作
向贵云
一
王华,贵州仡佬族作家,主要创作小说,目前已发表4篇长篇和一系列优秀中短篇。在贵州作家群中,王华有很多个第一:第一个在《当代》杂志上发表长篇小说,第一个以长篇小说获少数民族“骏马奖”,第一个被茅盾文学奖(第八届)提名等[1]。《傩赐》发表在2006年《当代》第三期上,这是目前王华在《当代》发表的三个长篇小说之一[2],小说讲述了一个荒唐的共妻故事。
故事的女主人公秋秋,嫁三弟兄:雾冬、蓝桐和岩影。雾冬负责去跟秋秋提亲、打结婚证、拜堂入新房,新婚第一个月秋秋跟雾冬过。第二个月头一天早晨,公公直截了当对秋秋说,“从今天起,你就搬到蓝桐这边来。”“你嫁到我们家里来,不光是雾冬的媳妇,还是蓝桐的媳妇。你跟雾冬的一个月新婚已经满日子了,从今天开始,你要和蓝桐过一个月新婚。”[3]同样,第三个月的第一天早晨,秋秋哭啊闹啊踢啊打啊地被她的第三个男人岩影扛回了家。这一切,秋秋婚前完全被蒙在鼓里,傩赐式的谜底就这样诡异地一层一层揭开。
共妻曾是部分少数民族的民俗现象(如现存的摩梭人的“走婚”制),是与自由和美好的爱情联系在一起的。曾经,傩赐人也是这样。“我们的祖先是看上了这个完全被大山封闭起来的地方,他们对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生活寄予美好的愿望,起名傩赐。他们在这儿自由耕作,自由生息繁衍,……我们庄上两三个男人共娶一个女人的婚俗,就是从那一段自由日子里产生出来的。”[4]但是后来那些美好的东西遗失了。
据说后来,山外有人进了傩赐,告诉他们傩赐属于谁,傩赐人又属于谁,又给他们定下一些规矩,……这之间,山外来的人不让傩赐人延用他们几个男人共娶一个女人的传统婚俗,傩赐人也就照着别处的模样过起了日子。但是据说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变革,……到傩赐来说话的人越来越多,叫傩赐人上交的款项越来越多,傩赐人在地里埋着头从春天刨到冬天,到头来连过年都捞不上一顿干的。才发现傩赐这地方到底跟别处不同,日子自然也不能效仿别处的,就重新把丢弃了的东西捡了回来,重新把它当宝贝。
比如婚俗。[5]
秋秋的故事就发生在后来。
傩赐人共妻完全是因为经济问题,几兄弟才能凑足彩礼钱。岩影已经三十五岁,为了凑钱娶媳妇,不得已去挖煤,被煤块削掉左耳和左手。蓝桐十八岁,父亲强硬地把他高三的学费拿来凑份子娶秋秋。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初衷,王华说,“我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在遵义下去正安县的一个很偏僻的村庄,当时我是记者,我下去采访的时候,……那个乡的乡长告诉我,他们那儿有个村因为很贫穷,所以那个地方,留下了几百个光棍儿,当时这几百个光棍儿这个概念让我很震惊,后来回来我就想写个东西……”[6]
钱和权,是王华作品中的两个黑洞,其创作所揭示出的底层民众生活的贫穷和苦难程度令人震撼。2006年《傩赐》在《当代》发表之后,责任编辑周昌义接受采访时说,“在《当代》发表东西其实是很难的,同一个作家在《当代》发一两个中短篇,也是比较忌讳的,而连续发两个长篇更是大大的犯忌。我们之所以连续发王华的作品,是因为感到她的作品值得发表。”“她的文字中充满了忧国忧民四个字。”“她的作品关心的是民众,关心的是苦难,这也正是《当代》的宗旨。”[7]王华笔下的苦难不是畅快淋漓、疾风暴雨式的。《天上没有云朵》、《母亲》等作品中的苦难是一种幽咽、一种上齿咬下唇的压抑式的泪流满面,一种想呐喊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这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是被现代文明完全遮蔽的死角,这里的人物除了被动承受苦难外没有拓展延伸的空间。而《傩赐》,同样是令人窒息的苦难感,但人物生存的空间已经呈现半开放状态,有了可左可右选择的可能性,也因此有了裂缝,有了被分裂的撕扯感。这种被撕扯的张力感来自来于文本中传统伦理观念和现代理性意识之间的不和谐,来自二者的博弈。这两者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即小说人物层面和作家层面。
二
先从小说人物层面谈起。
傩赐庄大山环绕,终年浓雾弥漫,一年能见到太阳的时间不到两个月。而且,这里的太阳是“白太阳”,这“变态”的太阳呼应了傩赐诡异的人文环境。傩赐人靠天靠地吃饭,然而这里土地贫瘠,阳光不足。所以,傩赐人穷,娶不起媳妇,养不起牛。自古以来,傩赐的男人就是牛:耕地得赶季节,白天,傩赐的男人们在田地里累死累活;女人是几兄弟共有,夜晚,傩赐男人便在女人身子上累活累死。傩赐庄,是如此躁动不安,又如此亘古安然。因为亘古如是,他们倒也并不怎么感到痛苦和悲哀。但蓝桐和秋秋不一样,他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傩赐人。秋秋出生成长在山外,成年后才嫁进傩赐,蓝桐是傩赐人,但上过学,走出过傩赐庄。他们接受过现代文明的洗礼,傩赐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现代社会的理性意识在他们内心掀起滔天巨浪也便是势所必然。他们使傩赐这个封闭自足的世界出现了裂缝。
秋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作为共妻嫁到傩赐,对这种违背“一夫一妻制”家庭伦理的傩赐式婚姻,她的直觉反应便是反抗。新婚第二个月,当秋秋必须跟第二个丈夫生活时,她坚决不从,跑回娘家向大哥求助。但大哥还不起彩礼钱,秋秋被“绑架”回傩赐,并遭遇到一系列伦理陷阱。首先,雾冬用朴素的知恩图报方式诱逼秋秋,“蓝桐替你挡过牛呢,为了你他命都差点儿送了,你不跟他就是欠下他了。”接着,妈妈“长久地看着秋秋”,“像长江决堤一样”哭着说,“娃啊,你就依了吧,妈也是从这条路过来的,不也走过来了吗?”,“没有过不了的路,咬咬牙就过去了。”然后,爸爸“扑通跪在了秋秋的面前”,“不光跪下,还咚咚地给秋秋磕头”。[8]传统的女性伦理观念、忠孝观念、父权等级制度等等不断地变换面孔,轮番轰炸,秋秋的反抗土崩瓦解。秋秋屈服了,跟蓝桐做了夫妻。新婚第三个月,岩影以秋秋第三个丈夫的面貌出现,激起了秋秋的第二轮反抗。秋秋向整个傩赐庄发起进攻,她去乡政府告傩赐人的状。但傩赐整个儿就是一个组织严密、包装完备的封建小皇朝,从村长到乡民,众口一词,否认共妻事实,秋秋和乡政府的干部在这里完全找不到裂缝。事情闹大不好,任凭岩影拼着命喊 “我不要钱,我要女人”,村长陈风水果断决定,秋秋只嫁雾冬和蓝桐两个,岩影凑的彩礼分子由雾冬和蓝桐负责还。陈风水是傩赐的土皇帝,主宰着整个傩赐的生杀大权,他说过的话就是铁板上钉钉的事情,其他人都遵从了,只有秋秋不同意,她一定要跟雾冬离婚,坚决只嫁一个男人。
看到这里读者不免疑惑:在此之前,秋秋已经跟雾冬和蓝桐分别过了一个月新婚生活,嫁两个男人已成既定事实,为什么这时候又坚决要跟雾冬离婚呢?大家不要忽略了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当秋秋作第一轮反抗,蓝桐表示自己愿意退出这种多角婚姻关系时,他惊异地发现秋秋“眼神里感伤比感激多”[9]。因此,前边讲到的秋秋的屈服在这里可以做进一步解读:即,从感情上讲秋秋是喜欢蓝桐的,因此从雾冬那儿搬到蓝桐这儿时,秋秋的内心是复杂的,这时候,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理性的婚姻观念达成短暂合谋,对秋秋产生一种合力:表面上,秋秋在传统伦理道德的攻势下屈服了;而实际上,秋秋是在现代的婚恋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为自己的幸福婚姻争取到了某种可能性。所以,走到蓝桐这儿,秋秋不愿意再走了。但当与雾冬离婚不成,蓝桐决定和秋秋逃走时,秋秋发现自己怀上了雾冬的孩子,痛苦矛盾之后决定跟孩子的父亲过一辈子,放弃了跟蓝桐出走。与逆来顺受、认命式的传统女性相比,秋秋有很大进步,她敢于反抗不道德的旧伦理,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她的反抗不彻底,止步于生育伦理。秋秋的悲剧,是文化的悲剧。蓝桐的徘徊不定是导致孩子出现,导致秋秋悲剧的又一个因素,所以,秋秋的悲剧,又是爱情的悲剧。
蓝桐是小说的另一重要人物,他是傩赐唯一一个上过学的人,相对傩赐人的封闭性而言,蓝桐是开放的。也因此,蓝桐之于傩赐庄始终是一个漫不经心的游魂,徘徊在“走还是不走,我始终是要走的,什么时候走”的臆想中。这一人物的突出特点是徘徊不定:他“喜欢上学”,但没有违抗父亲将其高三学费用来娶秋秋的决定;他不愿意参与共妻的婚姻关系,又与秋秋过起了夫妻生活;他喜欢秋秋,却不支持秋秋与雾冬离婚,导致秋秋怀上雾冬的孩子;他鄙视陈风水的装腔作势,又主动去请他来主持自己的家庭会议;他不想长期待在傩赐,然而又与之纠缠不清,不能果断出走……,直到小说结尾,他也未能作出选择。但同时,蓝桐这个人物对于傩赐庄来说又是重要的,秋秋被俘虏后,蓝桐是沟通傩赐与外界的唯一桥梁,作者在这一人物身上寄予了厚望。我们看到,作者给了这个人物反对父权、族权及男女平等等现代意识。小说中只有蓝桐敢于挑战父亲的“权威”,敢于蔑视村长的威风,在傩赐他第一个真正把妇女当作独立的人的个体来看待,懂得跟秋秋说“对不起”。但蓝桐这一人物的不彻底性,又导致他对于传统伦理道德虽具有审视和判断的眼力,却没有决策和行动的勇气。
除《傩赐》外,《后坡是片柏树林》、《紫色泥偶》、《家园》等小说中都写到传统伦理与现代文明的冲撞。《后坡是片柏树林》中的石板上村,村子后面曾经是一大片柏树林,随着村里人口由十几户剧增到七十几户,后坡的柏树林被开荒成庄稼地,这几年,村民中但凡有点力气的都外出打工挣钱,后坡荒芜了,随之后坡上所有水井都干涸,只剩坡下一口井还细细地流着,村民白天黑夜地等水喝。大自然以生生不息的资源孕育着人类的生息繁衍,但人类社会不买账,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关系难以为继了。并且这种潜在危机没有引起人类关注,比如石板上村的人,他们,包括村长都忙于外出赚钱,没有把退耕还林当回事。只有泉子不顾妻子反对,不管村民阻挠,毅然要把后坡还原成柏树林。小说这样描写泉子跟屋后那口老井的关系,“泉子跟我家屋后那井亲如母子,听他说,我奶生下他以后就死了,我爷是用屋后井里的水把他奶大的。所以泉子看不得这井干涸,那简直就像亲眼看见老娘枯死一样难过。”显然,井就是井,不是泉子母亲,光是井里的水也奶不大泉子,这是一种隐喻。泉子跟老井的“亲如母子”,隐含的是人类跟大自然的关系。种完树后泉子拗不过妻子而终于走入现代工业文明并被其吞噬,但泉子的英雄行径感化了妻子柳风,柳风执着地坚持着他退耕还林的未竟事业。《紫色泥偶》中,铜鼓心疼月亮湾的那一坝好田被抛荒,他喜欢“田底下发出来的那种味道”,“见不得田给荒着”[10],自家买了牛不要工钱也要去犁了那坝田。在妻子反对、乡亲们不理解、乡长以及乡长背后一整套现代商业运行法则不允许的情况下,铜鼓孤注一掷,成为明知不可为而强力为之的殉道式的悲剧英雄。如果说在《后坡是片柏树林》中泉子的事业还后继有人,那么铜鼓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孤独者,除了行将老朽的顺儿爷,周围所有人都把铜鼓看成疯子。“作者在通过铜鼓悲壮的仪式性活动中,对农耕文化在现代性操作中的沦丧做了一次精神上的凭吊。”[11]《家园》里的陈卫国也一直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人情人性的对立和冲突之中,他“潜伏”到安沙这一人间化境以摆脱现代工业文明的噩梦,但安沙被连根拔起,他甚至至死也无法摆脱,这一噩梦在他死后又转嫁到儿子的身上。
三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着深刻变化,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人们在现代性和民族文化的双重焦虑中开始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种政治经济背景和文化语境也影响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文化处境在全球化和汉化的双重影响下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态。王华出生成长在黔北仡佬族聚居区,黔北在中国版图上偏安西南一隅,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处于边缘位置,但王华同时又接受过中国现代汉文化的教育,这就使她能够获得本民族文化和汉文化的双重在场意识[12],并具备一种跳出本民族文化局限反观和审视这一文化的眼光与能力。
深入王华的创作可以发现,对全球化背景下仡佬族民族文化的遭遇和我国传统汉文化现代转型问题的思考贯穿于她的整个创作。王华的小说大多写家乡黔北的风物人情,这些作品中出现一个相似的人物系列:彭人初(《老师彭人初》、《香水》)、泉子(《后坡是片柏树林》)、铜鼓(《紫色泥偶》)、爱墨(《旗》)、安沙的老人们(《家园》)、管粮爹(《回家》)、王红旗(《在天上种玉米》)、伍佰(《伍佰的鹅卵石》)……他们极端自尊,又相当固执地坚守。彭人初是一位教了几十年书的代课教师,正直,善良,真心爱护学生,然而无论他如何努力,也改变不了被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教师取代的命运,从教主科被排挤到副科,再到守门的老头,然而他不死心,极尽心力地挣扎。《旗》中的爱墨老师把教书当作一项事业,几十年如一日,在乡村小学奉献着自己的生命,但中心学校校舍好,师资好,学生们跑那儿去了,留下的越来越少,爱墨不管,照样兢兢业业升旗,备课,一个学生也没有了,爱墨就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对着课桌板凳讲。《回家》中,管粮爹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认定“自家有块地在那儿,就是不生庄稼,想想心里也辽阔,一点儿地都没有了,你不光脚下逼仄了,心里也逼仄了,做农民没有地,还活啥活法啊!”[13]所以,他以死胁迫儿孙们去买回政府征用的土地,导致儿子有家不能归,孙子被逼进关押所。《在天上种玉米》则讲王红旗被儿子接到北京享福,心里却念念不忘家乡的田地、庄稼和乡亲们,于是他幻想着在北京再建一个家乡三桥,甚至尝试在北京的房顶上种起玉米来。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表现来完成对现代文明的思考与反省在王华的创作中很突出,人类在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和索取中制造着现代文明,同时又在颠覆和摧毁这个文明赖以存在的根基。小说《家园》描绘的安沙是现代社会的世外桃园,这里人和自然和谐共处,人们快乐地生,安然地死,后来政府要在这儿修水电站,安沙被整体搬迁到山外,安沙人被迫接受完全不一样的语言、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年轻人尝试接纳、改变,但老人们不行,他们甚至采取集体自杀的方式来捍卫自己民族的丧葬仪式……王华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的车轮必将滚滚向前,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我国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流、碰撞、吸纳、再生是必然的,无论如何固守、封存都将无法阻止这一进程。
但不同文化在相遇初期,边缘文化潜意识的自卑、疑虑甚至恐惧是一个必经阶段。面对现代工业文明:长篇小说《桥溪庄》揭示生态伦理遭到严重破坏将给人类带来断根灭种的毁灭性打击;《天上没有云朵》中李大国为逃离黑溪门天旱争水的野蛮格斗,带领家人外出打工,为此失去了胳膊、腿,还带回一个傻呆儿子;《傩赐》中岩影和雾冬都因挖煤残废,秋秋和蓝桐也差点儿为此送命;《后坡是片柏树林》中泉子被摔死……作者看到了现代文明的负面因素,所以2006年写作《傩赐》时,作家将蓝桐的出走处理得如此艰难。但出走是必然的。《回家》里边,管社会“不再怕这怕那了”,可以无牵扯地闯社会了,《在天上种玉米》中的王飘飘可以说是管社会形象的延续,他已经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将妻儿和老人接到北京享福了,当然,从他的生活状况我们不难看出其融入现代社会的艰难历程。
另外,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也将同时伴随着传统汉文化或民族文化中某些优质成分的流失和熟悉的生存方式的改变,身处其中的生命个体,必将感受到被割裂的文化阵痛,作家王华也是这样。《一只叫耷耳的狗》作者通过一条狗为恩人守灵时的庄严肃穆,反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感叹传统美好人伦关系的日渐消逝。《傩赐》中仡佬人的油茶和桐花节也将随着时代的发展慢慢消逝。《家园》里人与动物与大自然亲密无间的相处将成为人们美好的记忆。这种优质文化因子的流失激发出一种不顾一切、歇斯底里的坚守,比如铜鼓、伍佰、爱墨等人物,这无疑反映出作家王华对传统文化中优质成分执拗的坚守姿态。传统女性伦理的现代转型,也是王华一直都在思考的。《天上没有云朵》中李大国的女人勤劳,善良,长期服侍残疾丈夫和痴呆儿子,坚决抵制村长的调戏和霸占,自尊自爱,这样一个柔顺的女人却为了给村里人争到灌溉旱田的救命水自愿被邻村五个男人蹂躏,最后在丈夫维护男子汉尊严的殴打和村人的唾弃中绝望自杀。小说《母亲》中那位年迈的母亲为儿子、孙子含辛茹苦,那种度日子的难让人不忍卒读,“你们听到我的骨头唱歌了吗?”[14]这是王华的神来之笔,令人震撼。《傩赐》中的女人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秋秋的婆婆就是一个例子,到秋秋已经出现了现代女性的迹象,但传统女性伦理显然具有强大的同化作用,婆婆简直就是秋秋的精神导师,诱导着、引领着秋秋一步步朝传统妇道的路上走。2009年王华发表《在天上种玉米》,小说中的妇女变化就非常大,这些妇女跟随丈夫生活在现代化的大都市,已经敢于跟丈夫对峙、跟公公叫板,甚至因为玩麻将忽视了接送孩子上学,但同时,她们也失落了传统中国女性的坚忍、包容和担当。传统与现代,边缘与中心,民族性与世界性……这种文化的“两难”处境促使王华做进一步思索,在依那、小同(《家园》)、王格式(《静静的夜晚》)等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边缘少数民族文化中优秀文化因子强大的反辐射力和文化建构能力。
仡佬族是贵州的一个古老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在世代延续中形成了自己独立于汉文化之外的,有着自身承传体系和历史命运的族别文化。其实,在其与汉文化及周边少数民族文化漫长的共存发展过程中,文化入侵、文化碰撞、文化交流与再生是其长期面临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它生存发展中的常态。我们可以也应该对此抱平和理性的态度。而仡佬族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处境和当前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处境具有内在的同质同构性。因此,王华的这种文化思考就具有双重的意义。
注释:
[1]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参赛作品178部,第一轮投票选出81部作品,王华的《家园》排在第56位。
[2]《桥溪庄》发表于2005年《当代》第一期,《花河》发表于2013年《当代》第二期发表。
[3][4][5][8][9]王华:《傩赐》,载《当代》2006年第01期,第152、110、110、158、158页。
[6]陈敏、王华:《新锐女作家王华——陈敏 王华访谈录》,贵州电视台科教健康频道《倾听女人心》栏目,2008年11月24日。
[7]罗晓燕:《她写苦难,写得有张有弛——与周昌义谈王华作品》,载《文艺报》2006年6月17日第 4 版。
[10]王华:《紫色泥偶》,载《民族文学》2008年第10期。
[11]刘大先:《2008年〈民族文学〉阅读报告》,载《民族文学》2009年第01期。
[12]因为作家这种文化的双重在场,所以本文中的“传统伦理”和“现代理性”也具有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文化双重内涵。
[13]王华:《回家》,载《当代》2009年第5期,第178页。
[14]王华:《天上没有云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