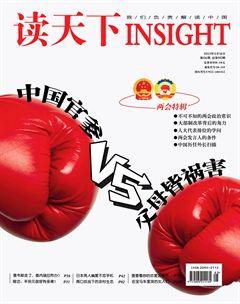建一座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库
简单
《汉声》创办人黄永松40年的坚持:
“电子有很多不知道的伤害,等知道时这一代就伤害了。”科技当道,电子工具是非常好的,但是孩子需要的是什么?
40年意味着什么?坚持?
“不是坚持,坚持意味着有痛苦的存在,我们没有坚持,只是觉得这条路我要走,就好好地走,我们还蛮高兴的。”台湾《汉声》杂志创办人黄永松说。
创办《汉声》杂志,定义“中国结”,启发《舌尖上的中国》,主编《最美最美的中国童话》,守护无数濒临消失的中国传统民间文化,这些是他的“使命”,也是梦想。黄永松用40年时间去实践自己的“文化大梦”,并将继续走下去——2013年春节假期结束,70岁高龄的黄永松就带着汉声的北京团队展开一系列实地调研,他们称之为“魔鬼训练营”,2月25日,汉声团队的行程是钧天坊琴馆(出品传世名琴的摇篮)。
开启“文化大梦”
1971年,台湾,黄永松27岁,从“国立”艺专(今“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科毕业,在一个电影公司美术组工作。一天,一位电影制片的好朋友跟他说,有一位叫吴美云的朋友,要办报纸,找他帮忙,于是他就约了吴美云在一个餐厅见面,谁知道却因为手上的另一个报社工作耽误了时间,当黄永松赶到餐厅时,已经迟到了一个半小时。
没想到正是这次迟到的见面,黄永松和吴美云的合作持续了40年,而黄永松的“文化大梦”也在此开启。
吴美云任总编辑,黄永松任美术编辑和摄影,《汉声》杂志就这样创刊了。《汉声》初期是一本英文杂志——《ECHO》。其第一期选题是介绍台湾的妈祖祭祀,之后几年,《汉声》每月出一期,从祭典到手工艺、到饮食、到风俗,他们将台湾跑了个透。
曾经有人问黄永松,有想过这份工作会一千40年吗?黄永松回答,没有。
《汉声》的创刊资金是吴美云向父母借来的,后来黄永松也从家里借钱入了股,那时工作条件艰苦,为了把有限的资金都花在印刷、制作上,吴美云将家里辟出一角作为办公室,厕所当作暗房。但是杯水车薪,杂志资金紧缺,一度举步维艰,甚至曾经因为付不起印刷费,而被印刷厂威胁要把稿子锁起来。而最初的《汉声》,吴美云还是聚集了一些资深出版人和编辑的,黄永松加入时只是一个小朋友。但是慢慢的,三三两两的,人几乎走光了,最后只剩下吴美云和黄永松。于是黄永松开始一人多用,即是美术编辑、摄影,也是文字编辑、记者。
也许不进入传统民间文化的世界很难理解其魅力所在,黄永松显然被吸引了,“我们做的是民间文化,就会了解到祖先的生活方式,不是历史课本上的,而是一个可以想象的、活生生的历史。我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沉醉其中。”
1978年,《ECHO》中文版创刊,名为《汉声》,取“大汉天声”之意。此前,英文版的准备工作,为中文版的推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8年,两岸通道开启,黄永松更是立即飞往大陆,台湾已是隔靴搔痒,有机会回到文化母体自然要回来。二十几年来,黄永松台湾大陆两边跑,早已踏遍大陆各处。
很多的无能为力
40年来,黄永松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带着抢救的心态记录濒临灭绝的传统民间文化。他去浙江山区,寻找失传已久的唐代夹缬蓝印花布;他找到默默传承技艺的风筝老师傅,把营雪芹扎燕风筝谱变成实物;他盘坐在西北的土炕上,看窑洞里的大娘剪纸;他为福建土楼留下完整记录……而他的最终梦想是,建一座“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库”。
很难想象40年的坚持,但是黄永松说,他不是坚持。他说,“坚持意味着痛苦的存在,我们没有坚持,只是觉得这条路我要走,就好好地走,我们还蛮高兴的。”
带着这样的信念,至今四百多期《汉声》杂志,每一期一个选题,每一期也都成为了一件艺术品。《读库》张立宪说,“《汉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儿子侍奉母亲的态度”。黄永松说,“我们不像一般的杂志,赶时间,一星期或者一周要完成,我们是一步一步地做出来,我们有一个条件,一定要做深入。”
《曹雪芹风筝谱》整个制作过程耗时9年,黄永松说还不是最长的,在他设定的五种十类五十六项“基因库”中一定还有更多的9年。
当然,理想与现实的碰撞,黄永松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而且很多。对“资金”的无能为力。无论是创刊初,还是直到现在仍有很多人质疑,这样一本专业的小众化的杂志出路在哪?选题制作的精良,消耗的不只是时间,更多的是金钱。说到这个问题,黄永松显露出一份淡然,“我们做一些力之所及的部分吧”。而他对另一个现实则更无能为力——时间,不是他的时间,而是采访对象、民间老艺人的时间。黄永松说,他一直在与时间拔河。“《黄土高原母亲的艺术》那期,陕北,里面有19位老大娘的剪纸高手,15年前工作的成果,不久前跟朋友询问这几位老大娘的情况,走掉了15个,只剩下4位,不珍惜怎么行。”
他想拯救这些濒临消失的民间文化,这些无能为力是黄永松最大的困难吗?他说,不是困难,是动力,“知道时不我与,知道世界那么丰富,那就赶紧做”。
连接传统和现代的肚腹
黄永松拯救的是历史,但是其意义却远不是历史的回顾。黄永松曾经就保存传统文化的意义向“文艺青年之父”俞大纲请教。俞大纲说,“你要做一个肚腹。传统就像头颅,现代就是双脚,现在的情形是传统被抛在后面,双脚往前跑,是一个缺少肚腹的断裂状态,你要做一个肚腹,把它们连接起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黄永松去做“水八仙”,了解关于它“吃”的部分,更从它的植物学特征开始,研究它的构造、栽种、收集过程。因为黄永松认为,当下出现严重的“食物污染”问题,原因出在人们“不认识食物”。
黄永松在做一个连接传统和现在的肚腹,不遗余力。但是单靠黄永松一个人,显然是不够力量的。每次有媒体采访黄永松或者有读者向黄永松提问,他总是很风趣的予以回答,他乐于借助其他形式让更多人知道这项事业的重要性,“把有限变成无限的情况”。
而这个“无限”最近更是伸向了小朋友。1982年,黄永松主编了《中国童话》,原本这本儿童读物是《汉声》为了缓解资金不足问题开发的“副业”,想不到,这本童话书畅销台湾30年。2013年,《中国童话》在大陆发行,更名《最美最美的中国童话》。如果说《汉声》是成年人世界的民间文化“科普书”,那《中国童话》则是以同样的民间文化、故事深入小朋友的内心。
说起这本童话书,黄永松不是带着对“文化大梦”的执著,而是对中国下一代的宠爱。当越来越多的孩子拿着iPhone、iPad点来点去、滑来滑去时,黄永松表现出担忧,“电子有很多不知道的伤害,等知道时这一代就伤害了。”科技当道,电子工具是非常好的,但是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是在妈妈怀里,在爸爸膝盖上坐着,感受妈妈的体温,爸爸的心跳。讲故事给孩子听,孩子可以反问,可以交流。孩子要面对的应该是一个真的人,而不是将来被那些高明的工具操纵。”黄永松用“网囚”来形容这些被工具操纵的孩子以及成人。
也许这样来看,《中国童话》30年后在大陆出版,其意义已等同于《汉声》拯救传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