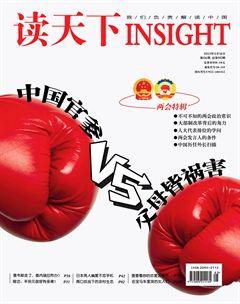黑暗时代里的光照
严杰夫
汉娜·阿伦特曾说:“即使时代黑暗,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照明,这种照明未必来自理论和观念,而多是源于明暗不定、常常很微弱的光。这光照来自那些男男女女,来自他们的生活和著作,无论境况如何,这光始终亮着,光芒散布。”阿伦特的这句话落到中国当代史上,显然是为顾准“量身定做”。
对于当下的大多数人,甚至读书人来说,很难给顾准明确定一个身份。他曾经是一个会计学家,也是一位革命者,建国初一度是上海的财政局长,随后却被打为右派,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今天我们再度回顾顾准一生的贡献时,往往会说他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只是对于了解及期待了解顾准的人来说,这一历史评断显然远远不够。
诚然,了解一个学者,最直接的方法便是阅读他的文字。然而由于时代的关系,顾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字和著述留下的并不太多,那本《顾准文集》也是直到1994年才最终付梓发行。那本文集,对于理解顾准和他的思想,虽然恐怕只起到了管窥的作用,但无疑还是让大众第一次能去直面这位“燃灯者”的心路历程。在仅四百页的并不算厚实的文集中,《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应算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个篇章不仅最直接地触及顾准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对顾准一生经历最准确的概括。所以,今次光明日报社将这个部分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无疑是给了我们一次重读顾准的绝佳机会。
回顾顾准的一生,他年少在会计界成名后即投身革命,跟随了那个革命年代里狂飙的理想主义潮流,他借着会计学家的身份,实则是在用红色革命理论来救国图存,这段革命经历不仅让顾准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而且也让他在实践中体会到了革命理论的力量。建国后,顾准由于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令自己在仕途和生活上遭遇了巨大挫折,直到最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惨痛的经历并未使他消沉,反而让他冷静下来开始反思大家对革命理论的认识误区,这种反思让他最终从一位“理想主义者”彻底转变为一位“经验主义者”。于是,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我们读到了作者那个惊世骇人的发问:“某种远大的理想,以及由这种理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都需要从理想主义转到经验主义吗……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正是在这样发人深省的提问下,顾准在那个黎明前尚最黑暗的时代(1973~1974)里,还冷静地指出,现在我们最为需要的是“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是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是的,“实事求是”,正是这四个朴实的汉字,却在顾准提了五年后,最终被真正落实到了治国理念中。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尽管在文体上只是一些读书笔记和随想,却并不容易读懂。一方面,作者的旁征博引和恣意挥洒包含了庞大的信息量,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恐怕很难理解其中表达的意思;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的叙述思维常常在不同的时代间跳跃,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红色革命,从古典哲学到马克思经典,他的叙述时空常常一跨数千年,其中蕴藏的说理和感情交杂在一起,仿佛是一曲节奏迅疾激昂的进行曲,读者稍不专心就很难跟上作者的叙述节奏。事实上,从希腊城邦到十月革命,从黑格尔辩证法再到马恩列思想,作者在恣意的书写中实则是在慢慢梳理并重新认识那些革命经典理论。所以,无论是希腊文明还是俄国革命,无非都是作者在借他国历史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在《辩证法和神学》一文中,作者写道:“马克思、恩格斯的眼镜,从人类历史来说,不过是无数种眼镜中的一种,是百花中的一花。”读到这里,我们终于意识到,作者那庞杂的信息和宏大的叙事下,归根结底就是要表达这样一个简单却在那个年代很少人能意识到的“常识”。
顾准离开我们已经将要三十年了。三十年间,中国社会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作者那些振聋发聩的文字大多已被现实证明了,只是“娜拉出走以后怎样”这个问题依旧在当下叩问着我们,直到现在,我们依旧未能对这个问题提交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所以,我想,那些拿起《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重读的思考者们,依旧会在脑海中盘旋着这个经典的提问,依旧会被顾准那些激扬的文字而感动得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