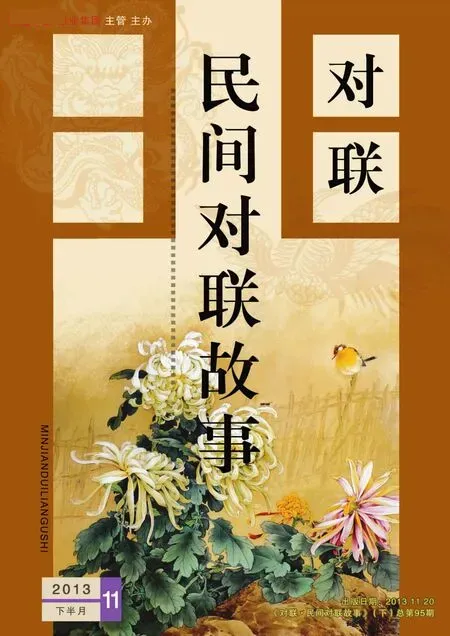古今对课谈(一)
□万吉利
一、对课的简介
对课是明清以来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精华,其内容就是学习怎样对对子。主要以“属对”方式开展,属对是由老师出上联,学生对下联,字数由少到多,内容由简到繁。
张志公先生可谓当代语文教育大家中对“属对”这一传统语文教育方式最为关注,并且研究最为透彻之人。他的《传统语文教学之得失》一文中说:“传统语文教学采用了一种符合汉语文特点的、有一定科学性的、综合的语文基础训练——属对。属对,俗称对对子。比如,先生说‘天’,学生说‘地’,与‘天’相对。从一字对开始,然后二字对,三字对,一直练到七字对,八字对,十字对,甚至更多。这是一种高度综合的语言基础训练。它是把词类、词组、声调、逻辑几种因素综合在一起的一种训练。三字对以上,就复杂了。然而,只要用之得当,这种练习非常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既训练他们的头脑要清楚,能够辨别词性、结构、声调、概念的异同,又训练他们的思维要敏捷。属对,古已有之,到了近体诗(律诗、绝句)时期,成了一种格律,诗里的某两句必须成对。属对这种语文教学方法的形成,显然和近体诗有渊源关系,然而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作诗的范围,发展成一种教学手段。明朝以后出现了一批专为教学用的属对教材。”(《张志公语文教育论集》)。
可见对课是一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鲁迅先生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就曾学习过对课,这成了他在枯燥私塾生活中的一抹亮色,许多年后他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现在仍选作初中语文课文。)
一天,鲁迅先生的一位姓寿的老师出了一个上联“独角兽”,让学生们对下联。一位学生对“四眼狗”,被寿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还有学生对“九头鸟”、“八脚虫”、“六耳猴”……寿老师都不满意。这时鲁迅站起来说:“老师,我对‘比目鱼’。”寿老师听了非常高兴,翘起大拇指对他说:“好!对得好!你真是个才子!”这就是寿老师的一堂对课。
“比目鱼”对“独角兽”好在哪里呢?
“独角兽”的“独”字,不是数字,但是有“单独”的意思。比目鱼的“比”字也不是数字,但是有“成双”的意思。“比”对“独”,比用“四”、“九”、“八”、“六”来对“独”要巧妙!
长沙岳麓书院大门的对联即是对课教育的结晶。清嘉庆十七至二十二年(1812年——1817年),袁名曜任岳麓书院山长,门人请其撰题一副书院大门对联,袁以“惟楚有材”让诸位学生应对。有一位学生叫张应声的以“于斯为盛”对上,这副名联就此撰成。
郭沫若幼年时在一所私塾读书,有一次与同学们偷吃了庙里的桃子。和尚找先生告状,先生追责学生,没人承认。先生说,我出个对子,谁能对上免罚。先生曰: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郭沫若思索了片刻,对道: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先生惊其才华,极为高兴,全体学生都免予处罚。
这也是一堂对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