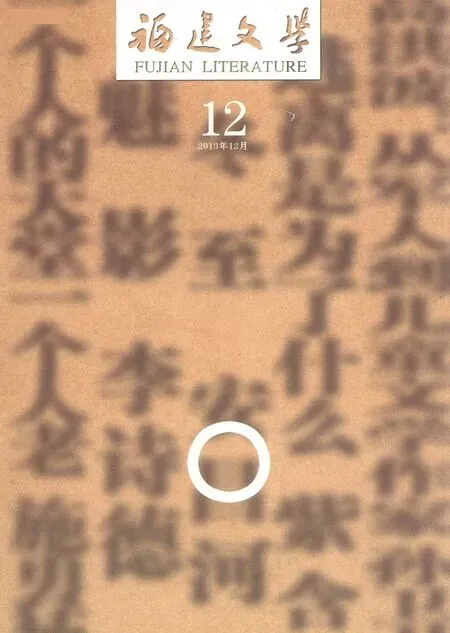撕 裂
□秦彩明
一
师傅杨东建的电话,就像一把双刃剑,一面切开了李庭良内心深处的快乐,另一面却切开了他的愁绪。八年不见的恩人来京,能尽地主之谊,感谢师傅当年的大恩,顺便弥补一下上次未解师傅燃眉之急的内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期盼。可老婆佟艳梅这一关太难过,在这个并不殷实的家,招待客人只是偶然事件,而且,师傅是老婆心中的一根刺,老婆已经下过通牒,如果他再为师傅花钱,就离婚。他的嘴巴是扁的,三年前犟着借给师傅两万元,至今没还。今年初师傅又借,他只能狠心婉拒了,他不想离婚,只能对不起师傅了。他以为师傅会尴尬或是失望而不理他了,没想到师傅不计前嫌,到北京来还是找他了。
比照那些从农村跋涉到城市的“凤凰男”,李庭良给自己取了个“麻雀男”的雅号,虽然没有“凤凰男”那么光鲜,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大山移栽到北京,好歹也在首都买了房安了家,只是不可避免沦为“房奴”,不富裕罢了。没办法,他就是一普通“北漂”,收入有限,幸亏同是“北漂”的老婆也挣工资,而且很会过日子,否则,房将不房,家将难家。
为了有限的收入能勉强灌溉家的良田,重感情的李庭良狠心截断了友情的毛细血管,老家的亲人同学朋友,到北京来找他时,他一般都会“在外地出差”,他们自是无从核实真假,因为不会有人将他的手机定位,至于家里的座机,对这些直系和拐弯亲友来说,永远都是没有安装。他对他们如此有意避而不见,实属无奈,只为省掉一笔作为临时驻京办的招待费用,即使单笔费用微小如沙子,但财力有限的他,针眼一般地被众人穿来穿去,也会聚沙成塔。
但师傅杨东建例外,因为杨东建有恩于李庭良,而且是危难之时的大恩,李庭良曾发誓要好好报答师傅。所以,当师傅电话里说他下午到北京时,李庭良连想都没想,就海口说,您就住我家吧,我到车站接您。
老婆佟艳梅系着围裙,佝着瘦小的身子在水池边收拾带鱼。李庭良低头琢磨该如何与老婆说,这才发现难度系数极大,悔不该刚才不过脑子就向师傅海了口,却又觉得这根本就不需要想。下意识地搓着手,没着没落地在客厅里转圈,最后,深吸一口气,豁出去似的移向厨房,却突然犹豫起来,顿住脚,将瘦长的身子斜在门上,看着农妇般勤劳的老婆镶在红色橱柜前,心里一阵内疚感动,这个善良贤惠的女人,跟着他可真是受苦了,却是对他万般的好。老婆和师傅,爱人与恩人,两个看似矛盾的人,两个他都不想伤害的人,在情感的天空里,在缺钱的背景下,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与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相遇,一阵无声的闪电雷鸣在内心深处激烈上演。李庭良犹豫感慨一会,怀着复杂的感情,从后面包抄过去,搂住老婆细软的腰。“老夫老妻”之间这破天荒的一抱,成分很复杂,有爱,有感激,有内疚,也有讨好,立刻激起被抱者的综合反应,意外,温暖,欣慰,还有满足的小幸福。
“干吗呢?没看我用刀呀!”
“喜欢我‘媳妃’嘛。”
“去去去,今儿嘴巴抹蜜了?还‘媳妃’呢,都成‘非佣’了,有事求我呢吧?”
“‘媳妃’大人英明,是有件事要请求‘媳妃’恩准。”
“准不是什么好事儿!该不是想去见初恋情人吧?嘻嘻,可别重色轻友哦,晚上可是你生日宴呢,你那三个哥们儿可都要来的耶。”
小女人嗔怪玩笑的阳光,并没有照亮理科男心底的温情,师傅这一重大课题,山一样压在心头,急待愚公搬移。
“怎么会?净瞎想!是——是我师傅来北京,送他女儿上大学,我想让他住我们家。”
小女人温馨灿烂的心情,立刻被乌云笼罩,大雨欲来风满楼。
“没可能!就那借钱不还的主?我伺候他?嘁,有病呐我!你还想把他当爹养怎么着?我可没那义务!”
“就这一回,最后一回,我保证,求你了!人家毕竟在我最难的时候帮过我,别让我良心不安好不好?他也就来这一回,也就住个一晚两晚的,对了,没准儿——没准儿他顺便来还钱呢。”
“还钱?可能吗?醒醒吧你,都三年了,要还早还了,银行邮局遍地都是,要还还不简单,犯得上亲自背着现金上门?”
“万一有可能呢?也许来看看我,顺便还钱嘛!”
“万一没可能呢?是想揩你的油,给他女儿找个落脚点吧!”
虽然,两个“万一”的后缀部分意思截然相反,但话缝里的意思有一点是相同的,两个人都殷切地希望,欠钱者这次来能把钱还了,这个并不殷实的家,太需要尽快把应收账款清零了,两万元,是一个让他们非常心痛的数字。
二
车子都疯了,扎堆挤到回家的路上,载着李庭良的公共汽车,像个耄耋老人,挪两步,便要停下来喘一会。李庭良楔子一般插在过道里,透过人头间残缺的缝隙,茫然地望着窗外一片红色的刹车灯,说不清是急还是烦,只觉得心中有团毛刺刺的东西扫来扫去,弄得疼不是疼痒不是痒,想躲又躲不开,想抓还抓不住。颠簸摇晃中,脑海里不断晃过师傅杨东建的脸,师傅清晰又模糊的脸,就像一只奇特的开关,又像一条神奇的纽带,让厂里那段被他封存在心底的日子,瞬间开启接通。
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光鲜,却痛心。
李庭良本科毕业后,分到一家效益不佳的国营工厂,唯一吸引他的是,工厂在省城。为着这一抹诱人的光亮,也因为没有别的路子,他认命了。
他分到表面处理车间见习,跟在班长杨东建后面搞电镀。站在脏污不堪的电镀槽边,他的心顿时跌入冰谷,好歹也是一重点大学优秀毕业生,干部身份,居然做一工人的徒弟!他不服气,不甘心,甚至觉得是一种耻辱,憋着劲,发誓要尽快脱离工人岗位。当他发现铝制零件上镀的黑色膜容易掉时,立刻请求搞电镀液配方改进试验,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当工人了,没想到喜欢创新的车间主任批准了。李庭良利用表面处理的专业知识,整天琢磨,后来,经他调整的配方镀出来的零件又黑又亮,而且膜不容易脱落,这可给厂里解决了大难题。他一夜成名,厂里很多人都佩服地称呼他才子“黑又亮”,风光无限。
好事接踵而来,他的爱情之花也突然盛开了,厂花周兰兰居然离开她的厂子弟男友,主动向他这位全厂公认的才子示好。这可是另一种莫大的成功,他这个农家穷小子的虚荣心顿时爆了棚,每天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凯旋般带着厂花“压马路”,引来无数羡慕嫉妒恨的眼球。
那个炎热的南方夏夜,十一点钟的风,依旧高烧不退。李庭良把女友送回家后,独自回单身楼。路上行人稀少,银色的月光,从法国梧桐茂密宽大的枝叶间筛下来,一路的斑驳月影,镀了他一身银斑。远处的蛙句一串又一串,偶尔一声碎啤酒瓶的爆响,撕破夜空的寂寥旷远。他浑身燥热兴奋,心中的爽劲绷得浑身饱满,一把将T恤脱了,捏在手里,又在空中挥舞击打一下,哼起了快乐的歌。
就在他乐颠颠地一路走一路哼歌时,厂里的两个混混横在了他面前。外号叫韩老大的那个,把刀架到他肩膀上,将他逼到暗处。韩老大叨着一根烟,从嘴角熏出一缕雾,喷到李庭良的脸上,又“嘶嘶”吸两口,便“啪”地把烟吐了。半截烟在空中划了一道示威的弧线,猛然栽倒在地上,闪着一点红光。李庭良背顶一根粗壮的树干,斑驳粗糙的树皮扎着他的背,可他丝毫感觉不到,他只觉得冰冷的刀锋压着他的肩,是那样的寒彻骨髓。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危险,他傻愣着,身子突然被抽空风干,轻飘飘如一张纸,被一柄尖刀牢牢钉在树上,任人摆布。深深的恐惧蛇一样缠住了他,不知所措中,脑子一片空白,只知道不能动弹丝毫,免得那不长眼的刀刃划破了肉。这时,外号叫宋老虎的混混停止了晃腿,上前一步,把提在手上的三尺铁棍横过来,轻轻敲打自己的手掌,一下,又一下。斑驳的月影下,宋老虎胳膊上的长刀疤依稀可辨,一口白牙闪着寒光。
“你们认错人了,我们没来往的。”李庭良努力镇静下来。
“你不是才子‘黑又亮’吗?哼哼哼……”韩老大低声冷笑。
“少废话!你太不识相了,知道不?今儿老子就让你长点记性!”宋老虎停止了敲打自己的手掌。
李庭良正要试图与他们理论,只听得“呼”的一声,宋老虎手中的三尺铁棒猛地抡过来,李庭良的头挨了重重的一击,顿时金花四溅,本能地将头埋进两只并不宽大的手掌,混沌良久,渐渐愣过神来,从指缝间向外窥探,两个混混已经扬长离去,阴森寂寥的路上,滚着一句狠狠的话:“再不识相,小心做了你!”
李庭良顶着一头雾水,捂着满头的血,独自到职工医院,缝了四针。
消息在一夜之间传遍全厂,却没有一个人来看李庭良,就连周兰兰也没来。谁都不想因为同情一个势单力薄的“穷学生”而得罪两个混混,这两个厂里有名的混混,在父母关系网的保护下,到处滋事,连命都不要。李庭良躺在冰冷的病床上,望着疗伤的药水一滴一滴流进自己的身体,觉得委屈,觉得窝囊至极,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黑的了。他想不出招谁惹谁了,想不出为何挨打,内心是那样地恐惧,是那样地伤心,是那样地无望,想躲回家再也不来厂里了。两滴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很久,却转成了一声强硬的命令,必须坚强,绝不能躲回家!
只有师傅杨东建来看了李庭良,师傅带来了奶粉、水果和二百元钱,也带来了一份危难之时的温暖关爱和一种不怕报复的仗义,真是莫大的安慰和力量。当杨东建提着东西走进病房时,从不掉泪的李庭良眼睛立刻就湿了。这个与他只有一年名誉师徒的人,这个与他非亲非故的人,这个他从心底里瞧不起甚至反感的工人,居然冒着遭报复的危险,来看他了!
“师傅,谢谢您!”
“谢什么?应该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
“对,终身为父。”
李庭良出院那天,师傅杨东建接他到家里吃了顿饭,后来,还常到单身楼去看他,有事没事地聊几句,有时干脆什么也不说,就是陪他坐一会儿。师傅的关心和陪伴,让诚惶诚恐的李庭良觉得宽慰多了,也安全多了。
李庭良被打的事,在厂里传得百花齐放,什么说法都有,机器旁马路上,当班时下班后,全厂的人都议论纷纷。他走在路上,总有异样的目光射向他,总有指指点点的手指戳向他,好像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熟悉和不熟悉的人都远离了他,就连周兰兰也离开他了。这种当头的棒击,可比宋老虎那一棒重多了,他痛心、委屈,觉得窝囊至极,气不打一处来,却又无可奈何,而且害怕得很,总觉得那两个混混随时会再来找他的麻烦。
他在第一时间向厂保卫处报了案,可保卫处哼哼哈哈,迟迟没有处理意见,最后不了了之。还是师傅杨东建动用关系网,查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厂花周兰兰和李庭良好上以后,周兰兰的前男友气不过,找了两个混混教训抢他女朋友的人,好在,师傅杨东建用好烟好酒搞定了宋老虎和韩老大,他们答应不再找李庭良的麻烦。
三
李庭良觉得,人生只剩下一个安全出口了,那就是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如此“声名狼藉”又势单力薄的一个人,在势利眼如尘埃般遍布的厂里,真是没法混了。一张二十天的探亲假条,帮他上演了一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好戏,借着回家探亲的名义,他独自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开始了艰辛的“北漂”生活。
临走的头一天晚上,他还是决定将此事告诉师傅杨东建,师傅是他在厂里唯一感激和信赖的人。
“我都帮你摆平了,走啥呀?”
“谢谢师傅,可我已经决定了。”
“再想想吧,在厂里成个家就好了,一个人到北京吃得消吗?”
“反正在厂里也一样难混。”
“北漂”的日子艰辛无比,李庭良忙于生计,一直没与师傅联系,因为境况不佳无颜见江东父老,也因为不想与那块伤心之地再有任何联系。一直到三年前,结了婚买了房,生活安定下来,才突然发现,经过时间的慢慢冲洗,居然对逼他来京的挨打事件有了感恩之情,觉得真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要是没有当初的挨打事件,现在他绝不会在北京扎下根来。开始真切地怀念师傅杨东建的好,以及厂里辛酸却奇特的经历,觉得现在也算得风光体面了,可以任厂里人评说甚至羡慕了,就莫名地想让厂里人知道他的消息,知道他不是任人宰割的窝囊废,知道他是有能耐有出息的人,便想办法和师傅联系上了。
“可算有你的消息了!师傅可是一直记挂着你呀!唉!”
师傅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如释重负的一声叹息,让李庭良突然觉得自己真他妈是个犬子,师傅对自己那么好,怎该和师傅断了联系?
也就是在那一年,师傅被疾病捉进了医院,胃要切除三分之一。李庭良接到师傅的电话时,雪正下得疯狂,师傅大概是病得很重,而且急坏了,声音有气无力的,充满着一种深深的绝望,李庭良调动满脑子的劝慰之语,却只汇成了一句话。
“师傅,您别急!”
“能不急吗?厂里都几年没发工资了,手术钱还不知在哪儿,你帮帮师傅吧。”
“应该的,没——没问题!呃,您需要多少?”
“两万就行。”
李庭良在客厅里徘徊,师傅气若游丝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回响,如果他还没结婚,而他的银行卡上又有大于等于两万的数字,那么他连眼都不会眨一下,就立刻给师傅汇过去了,而且不要师傅还。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师傅命悬一线?可问题是,他已经结婚了,而且严重缺钱。卡上的两万元,是他和老婆精打细算攒下来买家具的,新房马上就装修好,就等着把新家具搬回家。老婆佟艳梅正撅着屁股拖地,看着老婆认真努力的样子,李庭良心里泛起一股暖意,紧接着就成了愧意,觉得不该海口借钱给师傅,应该先和老婆商量一下,可一会儿又觉得根本没必要商量,恩人正命悬一线,应该义无反顾地帮一把。犹豫斗争中,他走到窗边,树桩一样立着,茫然地看外面,一个又一个鞋印子,柘到湿气未干的地上,老婆的埋怨声就砸过来了。
“成心是吧?地上都是你的脚印哎,你不拖就算了,还让我重复劳动,什么人呐,真是的!”
就是老婆佟艳梅这一埋怨,没来由地帮李庭良做了决定,应该帮师傅渡过难关!因为,新家具可以等,师傅的病可等不起!
李庭良突然转过身来,不由分说地夺过老婆手中的拖把,狠命地擦起地上的鞋印来,似乎一个知错的孩子,要努力弥补自己的过失,或者赌气折磨伤害自己,以抗议父母的管教。老婆佟艳梅呆在那儿,惊诧地看着李庭良笨拙而努力地拖地,悔不该那么埋怨他,踩几个鞋印,划拉两下就行了,何必说得跟个怨妇似的?佟艳梅怀着内疚的心情,跑过去夺李庭良手里的拖把,但李庭良固执地不撒手,而且使劲拖了好几个来回,佟艳梅就觉得不对劲了,老公心里肯定有事。这时,李庭良说话了,他的话,让佟艳梅立刻就气不打一处来了。
“我厂里那个师傅,帮过我的那个,还有印象吧?”
“怎么了?”
“他病了,胃病,要部分切除。”
“哟,这么严重,不是恶性的吧?”
“谁知道?他的手术费还没着落,我们那两万,借给他吧?”
“借给他?家具不买了?他家没人了吗?你是他儿子还是什么?知恩图报没错,可不能为了报恩连日子都不过了吧?”
李庭良没法容忍自己躺在舒适的新床上,眼睁睁地看着病入膏肓的师傅,因为无钱手术而一点一点地死去。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只是给恩人借点钱?他鬼迷心窍一般,孤注一掷地将买家具的两万元汇给了师傅。
争吵不可避免,内疚也不可避免,但比起师傅的命,就算不得什么了。老婆佟艳梅哭过,闹过,却无力将舟还原成木头,就说了狠话下了通牒,如果李庭良再给师傅借钱,就离婚。
李庭良自知做错了事,但挨了老婆一顿臭骂,心里反倒舒坦多了,而真正让他舒坦的,是救了恩人的急,债一样压在心头多年的恩情,终于有机会还了。
可让李庭良没想到的是,三年了,师傅杨东建一直没还钱,人情话说了一堆又一堆,可就是不还一分钱。李庭良知道师傅日子难,还不上,每次都劝师傅别着急,可当他看到老婆守着清贫的家哭和怨的时候,心里又特别内疚特别痛苦,觉得太不应该太对不起老婆了。老婆总催他讨账,可他哪能开口问师傅要钱?所以,每逢老婆催问,他都理亏得抬不起头,却还得小心敷衍,安慰老婆说,我问过了,快了,快了。敷衍得久了,老婆就发现了问题,并断定这钱是要不回来了,说人家压根儿就没打算还。李庭良怪老婆把人想得恶毒,可慢慢地,也隐隐地担心起来,对师傅居然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似乎是怀疑,又似乎是担心,或者两者都是,或者两者都不是。
而今年初,师傅居然再次开口向李庭良借两万元,说厂里开不出支来,生活没着落,想借点本钱做点生意糊口,还说等下半年赚了钱,就把以前借的两万也一并还他。李庭良却狠心地回绝了,这对严重缺钱的夫妻,再也经不住因钱生隙了。心里却内疚着,觉得对师傅见死不救,很对不起师傅,似乎和恩将仇报差不多。
四
钥匙在锁孔里“咔嚓”转一下,门就开了,麻雀窝一般的家,向李庭良敞开了袖珍却温暖的怀抱,三位好友的调侃大笑扑面而来,原来他们早已经来了。
李庭良随意地“嗨”一声,举手招呼沙发上的三位好友,同时弯腰给师傅父女找拖鞋,见餐桌上放着个大生日蛋糕,知道是三位好友的心意,一股暖意油然而生。漂泊在京,有这三位好友,大家相互温暖,真是挺好的。三位好友也“嗨”一声,其中一人还招了一下手。三个人见李庭良身后跟着个年长者和一个女孩,都愣一下,又都笑一下,突然就都站了起来。沙发跟前长出的三根粗粗细细的树,被拘谨弄得有点僵硬地弯着。三位好友,不约而同地认为,年长者是李庭良的父亲,却都疑心这父亲为何如此年轻,而且脸也没晒黑,根本不像农民。老婆佟艳梅正关着门在厨房里忙饭,没出来迎客。李庭良心里紧一下,默默求着老婆网开一面,给他点面子,对师傅热情一点,却是莫名其妙地回头看师傅。师傅杨东建站在后边,一脸的沧桑卑微。
李庭良领着师傅杨东建走向沙发,向三位好友介绍说,这是我师傅杨叔,又指着师傅的女儿介绍说,这是杨叔的女儿杨岭,交大的新生呢。三位好友会心一笑,错落有致地叫着杨叔好,师傅杨叔局促地点头笑笑,就周正地坐下了,努力把自己调整到长辈那种谦卑庄重的状态,赶紧教不知所措的女儿,说这三位都是你李哥的朋友,也是哥呢,女儿杨岭就尴尬地依次叫了三声哥,才局促地坐下。李庭良把脸笑成一盘向日葵,给师傅父女泡茶,给朋友续水。老婆佟艳梅系着围裙急颠颠地跑出来,一脸热情地笑着,向杨东建表示歉意说,抱歉抱歉,刚才炒个菜占着手了,这才出来,怠慢了杨叔,随即又把自己关进忙碌的厨房。李庭良一块石头落了地,突然心生感激,就差发誓要一辈子对老婆好了。
四人餐桌挤了七人,很有点亲密无间的味道,师傅杨东建一边是李庭良,一边是女儿杨岭。推杯换盏中,大家对师傅的尊重显而易见,纷纷给他敬酒,就连不喝酒的佟艳梅也以水代酒,敬了师傅一杯。寿星李庭良反倒成了次要角色,三位好友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划拳痛饮的初衷,自觉做了李庭良招待师傅的陪客。师傅的礼数也很周到,先是举杯祝贺李庭良的生日,然后举杯感谢佟艳梅做了一桌好菜招待他,还一一回敬李庭良的三位好友,说出门靠朋友,庭良在北京,感谢你们对他的关照,其诚恳之态,绝不亚于一个父亲。
酒过三巡,师傅的脸慢慢红了,亮堂堂的像镀了一层膜,眼睛定定地盯着身边的李庭良,散发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慈爱的情感。
“庭良啊,你在北京混得真不错呀,幸亏当初没听师傅的,离开厂了。”
“惭愧,惭愧,还在努力中,努力中。”
“你要是当初听我的,在厂里成个家,那我可就真把你害惨了,幸亏你有远见呀!”
“师傅,您对我的好,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当初要不是您帮我,我不知道会……”
“嗨,别提了,都过去的事了,还扯它做什么?看到你现在混得这么好,我不知道有多高兴。”
李庭良心头沁出一股暖意,又起身举杯敬身边的师傅。此时,杨岭已经吃完饭,见又有人让父亲喝酒,急得什么似的,祈求一般地看着父亲,欲言又止,赶紧在桌子底下扯父亲的衣服,示意他别喝了,可杨东建根本不听,豁出去一般,爽快地一口干了,又执意让女儿到客厅看电视,女儿虽不放心父亲,却也只好听话地下了桌子。接着,杨东建向李庭良讲起厂里的人和事。三位好友插不进话,就相互用酒杯碰桌子“打电话”喝酒,佟艳梅闷头细细地吃饭。李庭良恭敬地听师傅说着,心情很复杂。师傅说,厂里好多人都出去打工了,技术处的一个技术员最划得来,把厂里的一套产品加工图纸带到广东,卖了十万元。还有不少人在工厂边上开小厂,用厂里的人厂里的技术干厂里的活,却挣自己的钱,好多都发大财了。有人给这些个小厂取了个形象的名字,叫“围墙工厂”,厂里当官的都忙着往自己腰包里捞钱,也没人管没人问,效益一塌糊涂,连工资都开不出来了,好几年了,员工每月只能领五百元的生活费,那还是大家聚众堵高速公路冒着生命危险闹来的。
李庭良心中莫名地生出几分感慨来,对那个生活了两年的厂子,对那个人生职业生涯的第一站,他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忍不住向师傅打听一些熟人的现状,师傅都数家珍一般地相告,当李庭良问到师傅的另一个徒弟小谭时,师傅的情绪突然有点低落了。
“他弄了个‘围墙工厂’,搞电镀,也就拉两个人弄个槽子,生意好得很呢,听说赚不少钱了。”
李庭良觉得师傅的情绪不对,似乎是有点嫉妒小谭,也似乎是有点遗憾,而师傅对徒弟小谭也非常好,如今小谭出息了,师傅应该高兴才对,莫非师傅是伤感自己老了或是觉得徒弟超过自己了没面子?于是安慰起来。
“哎呀,师傅您是电镀大拿,要是您开这么个厂子,那绝对比小谭强多了。”
师傅的情绪就更低落了,闷了一会,还是吞吞吐吐地说话了。
“唉,本来是我拉他一起做的,可我,唉,实在没找到本钱,后来,后来他就和他亲戚一起做了。”
李庭良的心突然被刺了一下,觉得师傅现在的拮据窘况,他有不可饶恕的责任,年初师傅向他借钱时,他要是借了,师傅现在的日子就好过了,而他当时的存款是够两万的,那是他们攒下准备要孩子的钱。他简直恨死自己了,觉得自己没法饶恕,简直跟个凶手一样,害得师傅惨兮兮的。又觉得自己也是无可奈何,也是实在没办法,要是动那笔准备要孩子的钱,老婆佟艳梅是绝对不会同意的,真跟他离婚也未可知。又觉得老婆不通情达理,为了不让他再给师傅借钱,居然拿离婚来威胁,真是太过分了,就有点恨老婆了。可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没良心,老婆对自己那么好,她对钱算得细密,也是为了这个缺钱的家。又恨自己了,没本事挣大钱,让老婆跟着自己受苦,却怪老婆把钱算得紧,还叫人吗?
李庭良沉在心事里,一时无话,气氛就有点尴尬了,坐在旁边的佟艳梅赶紧拿膝盖碰了碰李庭良,李庭良愣过神来,抬头看师傅一脸尴尬黯然,对师傅的歉意就压倒了一切。
“对不起,师傅,上次,我……我没能帮您……”
“庭良,你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命,要说对不起,是师傅我对不起你啊,真的对不起,当初借你们的钱,到现在还没办法还,唉,真是对不住你们呀……”
佟艳梅惊着一双明亮的眼睛,瞟一眼李庭良,手悄悄在他腰上意味深长地掐一下,站起身来,说是去做个汤,便把自己关进了厨房。李庭良就把头低下了,做了亏心事一般,饭桌上的气氛又莫名地尴尬起来,李庭良闷了片刻,把头抬起来,努力笑笑,开始转移话题。
“师傅,您家杨岭考上交大了,好学校呀,您真该高兴呢,来,我敬您一杯,恭喜恭喜!”
三位好朋友突然有了共同的目标,也纷纷举杯敬杨东建表示祝贺,杨东健一一谢过,笑笑地把酒都喝了,末了,才感慨闲聊起来。
“杨岭考上大学,我是真高兴呢,只是,要不少钱呢,不过也还好,我和你婶儿把厂里分的房子租出去了,在外边租个小点儿的住着,差价差不多也够她开销了。”
杨东健说完,见李庭良一脸惊异和担心,赶紧补充道:“厂里好多人都是这么弄的,这叫靠山吃山,靠房吃房,厂里给大家伙儿分的福利房,这下真管大用了呢。”
李庭良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师傅想的这个办法,虽然让他觉得于心不忍,但很实用,好歹能帮师傅渡过难关,突然又想起师傅的身体,就关心起来。
“师傅,您的胃没事了吧?复查过了没有?”
师傅脸上掠过一丝愁意,无奈地笑了笑,回头看女儿在离餐桌很远的角落里看电视,这才转过身来说道:“我的胃,没事了,好得很呀!”说罢突然将声音调到很小,接着说道:“唉,我那破零件儿,凑合着使吧,前一阵儿疼得厉害,去查了一下,复发了,医生建议我赶紧做手术,可我哪有那么多钱做手术?上次做手术借你们的钱都还没还呢,管他呢,不做了,都这个年龄了,吃点药控制也是一样的。”
李庭良突然心里一阵绞痛,师傅放弃手术,靠吃药控制,无异于选择了死亡,只是因为缺钱!他似乎觉得师傅很快就要死了,真想再给师傅借点钱,让师傅去做手术,可只是一念,就无奈地偃旗息鼓了,老婆那一关,他实在过不去,突然后悔自己结了婚,如果没结婚就简单了,他一定会义无反顾地帮师傅。可他已经结婚了,而且老婆的离婚通牒就摆在他面前。他没办法了,左右不是,无力至极。如果不帮师傅,师傅会深陷不幸甚至死,那是他极不愿意的;而帮师傅,又会不可避免地伤害老婆,老婆一气之下真跟他离婚也不一定,那是他更不愿意的。师傅和老婆,恩人和爱人,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人,这两个因为他而矛盾的人,这两个他都不想失去的人,又在情感的天空里遭遇,一阵风起云涌,巨浪翻滚。冲突纠结中,他试图在师傅和老婆之间找一个勉强平衡的点,以求不被恩情和现实撕裂,突然灵光一闪,就下定了决心。
“师傅,我借给您的那两万,您就别还了,忘了它吧,您对我那么好,就算我一点小小的谢意吧,以后别再提它了!”
这当儿,一直躲在厨房门后偷听的佟艳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生咽一口粗气,端起新做的西红柿鸡蛋汤,木着脸走出来,努力地笑笑,说道:
“李庭良,你胡说什么呢?喝多了?来来,大家都喝口汤吧,醒醒酒!”
佟艳梅一边说着,一边挤歪李庭良的身子,把一钵汤放到桌子上,突然狠跺李庭良一脚,李庭良疼得憋着气咬牙,脸上努力装得无事发生,一口气还没匀出来,腰又被老婆狠劲掐了一把,他疼得缩了一下身子。
两口子的暗语,没有逃过三位好友的眼睛,三位好友尴尬着,面面相觑,起身要走,却被佟艳梅拉住了。
李庭良自然明白老婆的意思,她是要他改口管师傅要钱,但他已经下定决心为师傅免单,也算是实实在在地帮师傅一把报一下师傅的恩,他觉得家里也不是非缺那两万元不可,那种潜意识里的大男子主义就钻了出来,生出一股一不做二不休的气概,坚定地说道:
“谁说我喝多了?我没多!我清醒得很!”
佟艳梅气不打一处来,愣一下,知道老公李庭良是不会讨账了,眼看着这笔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血汗巨款就要打水漂,情急之下,只能豁出去了,于是转向杨东建说道:“杨叔,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辛辛苦苦一点儿一点儿挣来的,两万不是个小数,我们也不宽余,到处都要用钱,每个月要还那么多房贷,还得要孩子,我们都三十多了呀,等着这笔钱要孩子的,您是个大好人,不会借了我们的钱不还吧?”
师傅杨东建一脸尴尬,还没来得及回答,李庭良就一把抓住佟艳梅的胳膊,掷地有声地说道:“你说什么呢?今儿我就做主了,师傅借的钱不用还了!师傅对我有恩,我得知恩图报,知道不?孩子我们晚几年再要吧,啊?”
佟艳梅见李庭良心意已决,执意不顾她的意见,把要孩子的事都不当回事,把她的离婚通牒都不当回事,非要把那两万元给师傅,是铁了心不顾她不顾这个家了。心里就极不平衡了,她这么努力地和他过日子,可在他心里,她居然还比不上那个不沾亲不带故的人,脑子里又翻涌着当初他瞒着她借钱给师傅的事,再想想如今他居然得寸进尺由暗转明,明着不顾一切地对师傅好,真是太猖狂太不把她当人了!新气旧恨一股脑儿往心头涌,情绪立刻山洪一般爆发,突然就发了疯,一甩胳膊出了门,砸过来一句气愤而又绝望的话:
“李庭良,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