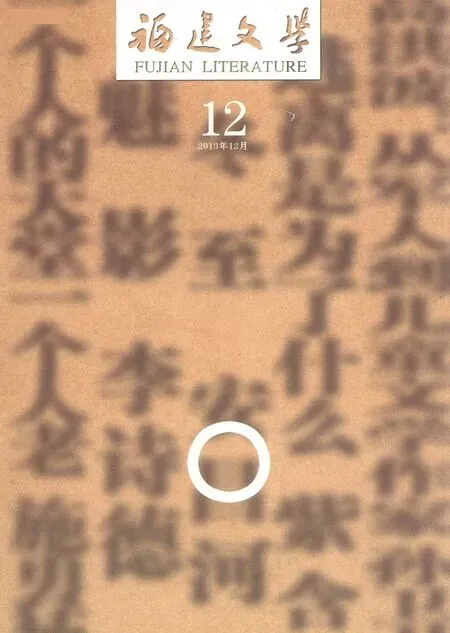冬 至
□安昌河
1
北县的旧县城最起初叫响石驿,后来被做为县治就叫城关,一直叫到2008年5月12日午后,地震发生了,城关被埋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在为新县城落在哪里着急。本来是准备落在鼓镇的,勘探说鼓镇地基不稳,还是在断裂带上。又说准备落在安镇,结果安镇三面环山,还是在地震带上。最后,新城落在了土镇上头的坝子里。
土镇不大,一直想搞发展,结果弄了很多项目都没怎么搞起来,还老样,一条十字路,南北长,东西短,横竖都难看。
北县新城建得很漂亮,被称为“中国羌城”,远近的人都来看,看新城,看北县人怎么从悲壮走向豪迈,跟着这些人来的还有很多投资。
北县新城落在土镇上头,对土镇来说这是个机遇。为了接受一个现代城市的辐射,土镇城镇建设开始向北县新城靠拢,要跟新城做“无缝对接”。效果当然明显,人们游完了北县新城总不忘到土镇耍上一盘,还有那些搁在北县新城不合适的项目也就顺理成章地摆到了土镇。
——于是土镇从原来横街那个地方一分为二就变成了两重天:横街上头靠近北县新城的地方高楼林立,繁华热闹,他们把这里叫新区。横街下头先是一片低矮的安置小区,过了安置小区就是一片废墟。那片废墟曾经是土镇最热闹的地方,土镇最好吃最好玩的都摆在那儿,饭铺子、烧腊摊子、供销社、庙子……陈厨子的家也在那里,陈厨子在那里度过了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如今他们把那里叫老区。
陈厨子每天吃过早饭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新区出来,跨过那条现今叫“幸福大道”的横街,穿过安置小区,去那片废墟上看望秦三老汉。
秦三老汉住在永福寺门口的一棵柏树下。永福寺垮了,大门口只剩两根柱子,还半截,像戳出地面的指头。好多信徒想要恢复重建,被阻止了,说要重新规划。柏树是棵老树,有很久远的传说,还挂了保护的牌子,可能是因为太老了,现今已经半死不活的。秦三老汉用捡来的彩条布和破铁皮倚靠着柏树搭了个窝棚,住里头已经快一年了。
“秦三老汉,秦三老汉……”
蜷缩在一堆破棉絮里的秦三老汉蠕动着,探出脑壳来,黯淡无光的眼珠子翻了翻,摆摆脑壳,缩回到棉絮里。
棚子里堆满了秦三老汉从外头捡来的饮料瓶、烂台灯、塑料袋子、破布烂纸……昨天晚上送来的饭菜还原封不动地搁在一边的纸箱子上。
“你得吃东西啊,老伙计!”陈厨子将一盒牛奶和两个鸡蛋搁在纸箱上,“鸡蛋是热的,牛奶也还是热的,你起来吃点喝点吧。”陈厨子推推那堆破棉絮。
秦三老汉没动弹。
“老伙计,今天冬至呢,只怕往下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啰。”陈厨子叹口气。
远处传来一阵轰鸣声,地面都在颤动。秦三老汉哆嗦着挣扎起身子,恐慌地看着陈厨子。
“莫怕,不是地震,是铲车,他们要把这个地方都清理了,说过阵子有个工厂要进来……”陈厨子拿起牛奶,递给秦三老汉。
秦三老汉摆摆脑壳,重新钻回到棉絮里。
“中午吃萝卜炖羊肉,今天冬至呢!”
一台挖机在扒一座破楼。一台铲车把扒下来的砖头水泥块往一个坑里填。要不了两天,它们就会碾到这里来。
陈厨子没有回家,直接往菜市场去。
有人在吵架,是卖灯具的赵光头和他的买主。赵光头凶神恶煞的样子,好像要把他的买主撕碎蘸酱吃啰。那个买主也不是个胆小的主儿,脖子抻得老长,往赵光头怀里钻,不住地叫嚷:“有本事你开我的瓢啊!你开啊,你要不下手你是孙子养的!”
围观的人很多。街道阻断了。
“咳,都奔钱去啰,都撂脑壳后头去啰,丢啰,忘啰……”陈厨子一边叹息一边摇头,折身拐进一条小巷子,从这里去菜市场虽然远点,可是清静。
结果遇到施工,巷子中间被挖了一条深沟,泥巴堆在两边像小山。陈厨子本想折回去,又一想已经走这么远了。刚硬着头皮没走几步,就栽进了沟里,膀子先着地,蹭了一脑门的泥,当时还觉得没啥,起身就疼了,肩膀疼,刺骨钻心地疼。上了年纪的人,疼痛都会跑路,那刺骨钻心的疼很快就弥漫到了胸口和手臂。陈厨子站立不稳,靠在沟壁上,短短长长地呼吸了几口气,似乎要好点儿了。
沟齐头深,陈厨子试着往上爬,根本不可能爬得上去。陈厨子吆喝了两声,哪里有人应答。“未必然就陷在这里了?”陈厨子望望天,两边楼都很高,天窄窄的一条像大路。再看看脚下,因为前两天一直下雨,沟里全是稀泥和积水。再揉揉肩膀、胸口,动动胳膊,似乎比刚才又要好点儿了,不咋疼了。“咋不往前走呢?走到头再说!”陈厨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开了步,几步下来鞋子就被稀泥糊得没鼻子没眼了,里头也灌了水。
走到头,居然是个缓坡。陈厨子小心爬上去,终于回到大街上,回到人群里。陈厨子跺跺脚上的泥巴,觉得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疲倦像温吞吞的水泥浆灌满了身子,很想找个地方躺下。
冬至到,羊肉俏。菜市场的人很多,车铃铛敲得人心焦,羊肉摊子跟前更是挤满了人,见了陈厨子,一个个都趔开身子往旁边躲,不光怕沾上臭泥巴,还怕被讹上。
“你要吃哪里?”肉贩子问。
“这个,来两斤吧。”陈厨子指着一扇羊排。
肉贩子麻利地下刀,飞快地剁了,一秤,两斤三两——
“二十七一斤,两斤三两,合计六十二块一……六十二好啦。”肉贩子说。
陈厨子伸手往口袋里一摸,心头一凉,口袋咋空落落的呢?钱呢?陈厨子把身上几个口袋掏干净了,啥都没有。“未必然是落那个深沟里去了?”
见陈厨子没钱,肉贩子问另外一个顾客要多少肉,然后顺手将那袋肉递给人家——
“那是我的肉呢。”陈厨子说。
“钱呢?没钱就吃不成肉的,晓得不?老大爷——”肉贩子说。
“我等一下给你拿钱来行不行?”陈厨子低声说。
“我这里不赊账,再说我也不认识你啊。”肉贩子懒得再理他,大声招徕客人——
“冬至吃羊肉,暖和一个冬啊,快点来啊,正儿八经的平武羊子哦,吃野草长大的哎……”
“我姓陈,都叫我陈厨子,这个土镇哪个认不到我?”陈厨子看着身前身后的人。哪个认得他呢?都是生面孔。他低着脑袋出了菜市场。
“去哪里呢?去那个深沟找钱?找到了再来买菜?”陈厨子往前走了一截,停住脚步,他实在没那个勇气下到那个深沟里去了。他的一双脚冷得生疼,木头一样。
2
陈厨子原来并不是厨子,他老婆才是,绰号宽面条,在饮食店上班。陈厨子是怎么成为厨子的呢?这在土镇还是个故事。那还是三十多年前,陈厨子在土镇坛罐窑上班,坛罐窑垮杆后,他的工作没了着落,三个娃娃又要念书,咋办呢?宽面条说,我们的饮食店也要垮杆了,干脆我们整个铺面,你来跟我学炒菜,我们开个饭铺子。
陈厨子人聪明,还爱钻研,没两年工夫,手艺就盖过了宽面条。那阵生意好得不得了,每到逢场天,前来吃饭的就差没把门槛踩断了。生意好,钱自然是不少挣的,只是这些钱都用在了儿女身上:老大陈建东大学毕业,教了几年书,下海去了广东,娶老婆的时候给他拿了五万。老二陈建西高中毕业,当了几年兵,复员的时候给他拿了七万。老幺陈建南是陈厨子两口子的心头肉,没舍得让她跑多远,嫁到了绵城,成家的时候给她拿了八万,买房的时候又给她拿了八万。
儿女们都安顿好了,宽面条的眼睛也被油烟熏瞎了,而陈厨子也累成了个驼子。因为店面破旧,而陈厨子又不肯招帮手,铺子里的生意慢慢也就冷淡了,就算逢场天也没几个食客。
宽面条是大地震那年早春死去的。宽面条得病有些年头了,一直对子女隐瞒着病情。直到头年腊月,宽面条要陈厨子给子女打电话,催他们早点回来过年。过完年,宽面条还不肯让他们走,要他们再呆些日子,说自己可能会很快死去。建东不相信,建西不相信,就连跟宽面条最亲的建南也认为妈妈在开玩笑。陈厨子把他们叫到一边,严肃地说他们的妈妈不是在开玩笑。但是他们还是当成玩笑话,耐下性子住了两天后,一个个找着借口离开了。结果刚过完正月十五没两天,宽面条就在一个深夜死去了。
陈厨子没有把宽面条去世的消息告诉子女,他给她放完落气炮,烧了倒头纸,用竹竿将房顶捅个窟窿,让宽面条的魂魄进入天堂。但是宽面条的肉体呢,陈厨子却把她留在了床上。
此后的日子里,陈厨子和往常一样大早起来开门,只是再不见他牵着宽面条去买菜了,也不见宽面条坐在角落里给他洗碗了。
“宽面条呢?”丁酒罐问。
大茶壶问,“咋不见瞎子呢?”
“老宽呢?”胖婆问……
面对大家的关心,陈厨子只说宽面条有点不舒服,睡床上了。
等到夜里关了门,陈厨子会打开炉子,按照宽面条喜欢的口味做几个菜,然后端到床边的几子上,靠床那头搁个空碗,摆双筷子,就当她还在,给她夹菜,给她说些街头上的见闻。他抿着小酒,没人劝阻,不经意就多了两杯,就脑壳疼,就悲上心来,就忍不住唤起宽面条来,唤着唤着就落起了眼泪。
过了一阵,胖婆带着几个女人家拎了些东西想要看看宽面条,说都想她,想跟她说说话。结果被陈厨子挡住门口,说莫打搅她睡瞌睡。这时候大家才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头。再问,陈厨子就不理会大家了。
又过了一阵,有人闻出了味不对——
“陈厨子,你老龟儿子在卖臭肉哇?”大茶壶抽着鼻子叫嚷。
“是啥子臭哦?”几个食客也跟着问,“这么臭,你叫我们咋个吃得下东西呢?”
陈厨子不吱声。大家见他神色不对,意识到出问题了。也不顾陈厨子的阻拦,大茶壶和胖婆钻进里屋……
子女们先是怀疑陈厨子的脑壳有问题,软磨硬缠把他送进医院,等到各项检查出来,发现他是正常的之后,责难就开始了。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不打电话告诉他们?考没考虑他们做子女的感受……陈厨子始终沉默。那阵子好多人都在责难陈厨子,尤其是那些在他那里吃过饭菜的人,说陈厨子这么做不光是在糟蹋死人,也在糟蹋活人,因为一想起那场景来,就忍不住发呕。
饭铺子是不可能继续再开了,谁还敢来吃呢?他想给儿女们做顿饭,都劝他歇着,陈厨子晓得,他们不是心疼他,而是嫌弃他。几个孙儿孙女听说了那事后,都不肯往他身边去,说他身上有味儿,没呆几天,就哭着喊着离开了。
“你当时咋想呢?”有时候儿女们冷不丁就会问这么一句。
“你们懂啥?”陈厨子气呼呼地瞪着他们。
还是街坊邻居们懂他,胖婆送来新做的茵陈蒿儿粑粑,他一口气吃了五个。丁酒罐邀约他喝酒,他一杯接一杯。大茶壶搞坐唱的时候喊他打堂鼓,他就跟着小鼓的点儿认真敲……子女们又要走了,邻居们看着他们,说你们咋个不再陪陪你们爹呢?建东说我说了接他去上海,他不肯,多半是舍不得你们。建西说我倒是非常想接他去东北,他哪里适应那里气候呢?再说我妈在这里呢。建南眼泪汪汪地说,有你们呢,过阵子我再回来看他。
转眼就是三月了。三月过了四月。农历四月初八,地震发生了。地震发生时陈厨子坐正在厨案前发呆。等到他从案子底下钻出来,等到尘烟散尽,土镇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残砖破瓦堆子。
这条街的房子是清朝修的,夯土墙,鱼鳞瓦,为了显示大门大户,房子都建得高高的,由于年久失修,打个炸雷房子都在哆嗦着掉渣子,哪里经得住那么大的地震呢?胖婆当时就被砸死了,嘴巴里还有一口干饼子。丁酒罐是第二天死的,他被打烂了脑壳。大茶壶是半年后被车子撞死的,那个开车的说是他故意撞上来的,现在两家子都还在打官司……老邻居们死了很多,没死的大都跟儿女们搬出去了。住在土镇的也都成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肯出来,出来干啥呢?见啥都会惹出泪花子来。
建南是地震后第三天回来的。建东是第五天回来的。建西回来得晚,半个月后。起先他们还争执,究竟把老父亲安置在哪里呢?是接到上海?东北?还是接到绵城呢?
“我的意思还是先住在这里。”有一天建南突然这么说,她看着两个哥哥,眼睛里有亮光在闪,像是心里头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了。“我们为什么不都留在这里……做点啥呢?”
建南很快就做起来了,她办了个砖厂,原来才两三毛一块的砖,现在给一块也买不到手。建东也眼热了,找了几个同事,成立了个建筑公司。建西哪里肯示弱,也成立了个公司,专门经营建材。
3
陈厨子想要回家。太冷,腿脚硬邦邦的不听使唤,不是往别人身上蹭,就是往街边上栽。眼睛也迷糊了,看哪里都眼生,而且感觉是进入了个绝望的地盘,越走越深,越走越远。难不成在生活了一辈子的土镇还迷路了?陈厨子站在街头,正东张西望,听见有人喊“爸爸”。
“声音咋这么熟呢?”
是建南,建南站在对面,正把他打量,好像认不得他了。陈厨子腿一软,就要往地上瘫。建南上前一把扶住他:“你咋个搞成了这样?你跑哪里去了?你咋样?”
“莫得啥子事……”陈厨子故作轻松地笑着,“只是不小心滚了一下,滚了一下……”
建南叫了辆车子,一边往家里去,一边给两个哥哥打电话——
“老爷子也不晓得钻哪里去了,摔了一身泥,我就把情况说给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出租车司机不时拿眼睛瞟陈厨子,关心地问:“老大爷,你是被抢了吧?最近乱啊,昨天我就碰着个抢包的,骑着摩托车,把一个女娃子拽了个筋斗……”
“爸,你不是真的被抢了吧?你咋会这样呢?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不舒服我们就往医院去。”建南正说着,电话响了,是建西的,他不跟建南说,要建南把电话给爸爸。
陈厨子拿过电话,却举不到耳朵边,只好弓着身子去听。
“我没啥,就是滚沟里去了,没啥……你忙你的,我好好的,正跟老三回家呢。好啦,好啦,我会注意的,会注意的……不说啦。”
就这么短短几句话,让建南不高兴了,她叹口气,自言自语似的说道:“我问你,你半天不开腔,你跟他们倒是不缺话说呢……”也不晓得她底下还要说什么,好在又来电话了,是建东的。建东还是要爸爸接,建南把电话给陈厨子,陈厨子不肯接,要建南跟建东说一句就是了,他没啥。
“你喊爸爸接电话!”建东的嗓门很大。
“爸爸说他不想接!”建南的嗓门也大,“假惺惺地打个电话就行啦?是死是活你们自己回来看!我看你们是钻钱眼子里出不来了!”
建南气咻咻地刚挂了电话,车子就到了楼下。
“我说爸,你究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不舒服我们就坐车子,去医院一趟,你别在乎钱,给你吃药的钱我还拿得出来,不消他们管!”建南说。
“没啥。”陈厨子艰难地下了车,扶着车门跺跺脚,觉得有点知觉了,这才敢开步。
陈厨子住在一楼。这房子是土镇第一栋震后设计、震后重建的,全框架结构,据说可以抗住八点五级大地震。房子钱是三个子女凑的,空间很大,一百五十多个平方米。才开始的时候三个子女都跟他住在一起,每天都有很多人进进出出。可是没过多久就陆续离开了。先是建西,他最后一个办公司,赚钱最多,他搬到了北县新城。第二个搬出去的是建东,他搬到了爱城,下一步还准备把老婆孩子都安顿过来。最后一个是建南,两个月前才搬出去。
建南把陈厨子送到浴室里,给他打开热水,关上门。陈厨子艰难地脱着衣服,使不上力,动作大点儿胸口就疼,就憋闷,就出不来气。脱裤子更难,弯不下腰,只好解开裤带,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蜕皮一样……等到终于脱光,已经没力气往水底下站了。
建南在外头催:“爸爸你洗好没有?我有点事要跟你说,说了还要走,我那头忙……”
“给我拿个凳子来。”陈厨子说。
“冲一冲就是了,还要坐下来洗?”建南嘟囔道。
原来老房子的卫生间里是有个凳子的,是陈厨子专门给老伴买来洗澡用的。那时候他们总是一起洗澡,说这样节省水,也便于相互照顾。老伴比他高,要给她洗澡就得踮脚。后来他就去买了个凳子,防止凳面上积水,他还钻了几个小眼。每次洗澡,老伴就坐在凳子上,他给她洗头,给她搓背。有时候老伴也要他坐着,她来给他洗头、搓背……
4
建南要陈厨子明天不要出门,就在家呆着,她要搬东西过来,而且屋子也要重新布置一下,因为还有两个人也要住进来。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过几天就去办证。”建南扫了她爸爸一眼,“我给你说的意思,是想叫你给他们两个打打招呼,莫要总是跟我找别扭。”
陈厨子没表态。
“爸,你听见没有吗?”建南走到陈厨子身后,把着他的肩膀轻轻晃晃。见陈厨子点头了,建南很高兴,转到陈厨子跟前,蹲下,仰脸看着他:“爸,还有个事……我听说老街那片土地已经出让给一家公司了,说要建什么工业园,你听说了么?”
“我晓得这个事。”陈厨子说。
“他们找你了吗?”建南问。
“找了。我已经答应把土地给他们了,过两天就签协议……”陈厨子说。
“钱呢?补偿款呢?”建南把着陈厨子的膝盖,轻轻摇晃,如同小时候撒娇,“爸,你把钱给我吧,我会付你利息的,我想再搞个啥……我还年轻,你得给我机会让我重整旗鼓啊,爸。”
陈厨子将女儿额前的一缕头发轻轻拨绕到耳后。从这个细微的动作建南已经明白,爸爸虽然没有马上答应她,等于是已经同意了她的请求。
“这些衣裳先放在这里,明天我来抽时间洗。过阵子就专门有人帮忙打整了,我们准备把他妈妈接过来,让他妈妈专门给我们煮饭洗衣打扫清洁……”建南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已经快中午了,她也没问一下我的中午饭咋个吃……”听着建南轻快的脚步声远去,陈厨子心头很不是个滋味。
建南原本生活得很幸福,丈夫是一所中学的副校长,女儿成绩优秀,她自己呢,在绵城经营了个服装铺子。就是那场地震——不,是那个砖厂毁了她。她把那么多年的积蓄全部投进砖厂,还叫丈夫去外头借贷。砖烧出来了,虽然没撵上一块多钱的高价,但是六毛钱一块的火砖已经算是天价了。那时候的建南简直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以为自己打开了金库大门。没过多久,火砖跌价,从六毛跌到两毛七。人工费那么贵,煤炭根本抢不到手,而且还滞销,供大于求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这个节骨眼上头,火砖质量出了问题,上了电视报纸,陈建南一下子变成了坑害灾区人民的黑心老板。有人说可以帮建南摆平这一切,没想到那人是个混蛋,骗了建南一大笔钱,还祸害了她的清白。接下来就是砖厂倒闭、离婚、躲债……
外头有人吆喝卖菜。陈厨子去买了点蒜苗,然后切了截腊肉,做了一盘腊肉炒蒜苗。闻起来很香,陈厨子却没食欲。勉强扒拉几口,陈厨子将饭盒洗干净,舀了些干饭,把一盘腊肉炒蒜苗倒里头,又找了个保温杯,倒了半杯热水。
秦三老汉已经好些天没在外头走动了。
秦三老汉是秦村人,曾经是有名的吆鸭子的竿儿匠。每年一过芒种,秦三老汉就会从孵房里逮上五百小鸭儿,担着他的鸭儿棚子,带着他老婆一块儿,赶着鸭群出了村。鸭子在闲田里自由觅食,他就跟他老婆手持长竹竿站在高处,一个这头,一个那头,不时相互吆喝一声,通报鸭子的去向。到了夜间,两口子就搁下鸭儿棚子,一个烧火做饭,一个圈鸭子。等到天亮,继续赶着鸭群走,走过土镇、走过爱城、走过竹城……一路上走走停停,等走到成都已是中秋,鸭子也肥了。
卖了鸭子,揣着钱,秦三老汉回到土镇总会和他老婆在陈厨子的饭铺子里气气派派地吃一顿。
那年夏至,秦三老汉带着他老婆,赶了一大群鸭儿夜宿土镇,没想到半夜碰上涨贼娃子水,不光鸭子被大水冲走了,他婆娘也被带走了。秦三老汉拄着长竹竿站在河堤上,裤腿挽得高高的,每一个走近他身边的人都听到了他的嘟囔:“到哪里去了呢?到哪里去了呢?”
从那以后,陈厨子再没看见过秦三老汉,有时候突然想到他,也以为他早死了。秦三老汉还活着。今年开春,陈厨子在一个垃圾堆边见到了他,他嘴上叼着半个饼子,趴在垃圾桶里翻腾。
“秦三老汉!”陈厨子喊了他一声。秦三老汉没理他。陈厨子继续喊,“秦三老汉,秦三老汉……”等到他终于扭过头来,陈厨子心头一紧,晓得这个人坏了,因为他那眼神是呆板的,是傻子才有的。
秦三老汉是坏了,得了老年痴呆病,成了个老傻子。三天后,他的儿女们撵到土镇,把他带回家。没过两天,他又出现在土镇,继续在那些垃圾桶里翻腾东西吃,不翻东西吃的时候就站在河堤上,树桩一样戳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不了几天,他又被带回秦村……结果他总是会再次出现在土镇……他的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干脆也就懒得管了。
5
陈厨子从外头回来,刚到门口,就碰着建东和建西了。陈厨子开了门,把他们让进屋里,然后打开手上的塑料袋子,从里头端出秦三老汉没吃的剩饭和鸡蛋、牛奶。
“看样子确实没啥问题嘛。”建西看看建东,呵呵笑着说,“你还担心他,他现在都在照顾别人呢。”
“你们给建南打个电话,喊她晚上回来吃羊肉,今天冬至节呢。”陈厨子说完进了睡屋,他要躺一会儿,他觉得有些不舒服。
“我要回广州,看你没事我就准备走了。”建东跟着进了睡屋,摘下手套,摸出一叠钱放在桌子上。
“把钱拿走,我不要钱。”陈厨子慢慢脱着衣服。
“不要?建南跟你伸手,你拿啥给她啊?”建西站在门口,笑嘻嘻地问。
陈厨子脱了衣裳和鞋子,蜷上床。建东上前扯了被子给他盖上。
“建南是不是又在开始打拆迁款的主意啦?”建西还在嘻嘻笑。
“她是你们的妹妹,就算再咋个丢你们的颜面,她也是你们的妹妹啊。”陈厨子扫了两个儿子一眼,叹口气,闭上眼睛:“你们也莫要以为你们多成功,这一辈子的路长着呢!”
建东和建西都怔住了,两个人相视一眼,决定离开。
“晚上叫上你们妹妹,早点回来,冬至,我炖羊肉给你们吃。”说这话的时候,陈厨子没有睁眼。
“他们还等我回家吃晚饭呢。”建东说。
“你跟他们说,我哪一天没死,这里就是你的家!”陈厨子语气很重。
建西本来也是要说晚上没空的,听了陈厨子的话,赶紧住嘴。
“好吧。”建东叹口气,“你晚上也不用做了,我们带你出去吃,建西,你早点定个桌。”
“还是打包带回来吃吧。”建西看见陈厨子的眼角有亮晶晶的东西流出来,戳了建东一下,示意给他看。建东看见了,欲言又止,摆摆头,轻叹一声,扯着建西出了门。
陈厨子并没睡着,他只是想躺着,觉得躺着可能舒服点儿。在去给秦三老汉送饭的路上,他觉得胸口一阵刺疼,都疼出冷汗了,只好靠在一堵烂墙上喘,正喘着,有东西涌上来,随口一吐,满嘴血腥。低头一看,自己刚才吐的是血,黑色的疙瘩血。
饭菜还原样摆在那里,鸡蛋牛奶也没动。秦三老汉还蜷缩在破棉絮里头。挖机和铲车的响声越来越近,地皮子颤得所有东西都跟着一起跳。
陈厨子喊了秦三老汉几声,没应,推了两把,他蠕动了几下,并没像早上那样钻出脑壳来,只哼唧了几声。陈厨子把手钻进棉絮里,摸出秦三老汉的胳膊。秦三老汉的脉象很虚很弱,像垂挂在檐口的蛛丝一样捉摸不住。
“老伙计啊,今天冬至啊,是应该来碗羊肉汤的啊……”陈厨子搬了个砖头过来,在棚子门口坐下,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跟秦三老汉扯闲条——
“以往我开饭铺子的时候,冬至这一天,羊肉汤起码要卖一百碗,遇着逢场天三百碗也不止呢!熬羊肉汤呢,就是清水、羊骨头、羊杂,先大火,后小火,羊肉要最后才放,汤熬成奶白色了,这才搁点儿花椒,搁点姜,有点凉惙感冒的也不怕,给他搁点胡椒面子。要是有贪图味道大的呢,再给他搁点芫荽末子,辣椒面子搁那儿随他加,要是他想下酒呢,就给他搁半把炒黄豆,那香哟……”
秦三老汉像是没受住诱惑,他从棉絮里钻出脑壳,像只缺氧的老龟。
“这个吆喝,‘嗨,陈厨子,给我来一碗,’那个吆喝,‘嗨,宽面条,收钱哦……’喊收钱的肯定是第一次来喝羊肉汤的,哪个收钱啊?墙边上搁了个箩篼,自己把钱往里丢,吃多少丢多少,要找零呢,也自己动手,我们哪里得空嘛,是不是……”陈厨子嘿嘿笑两声,揩了鼻涕和眼泪,“只有那个大茶壶不老实,只给一碗的钱,他肚皮大,又爱喝酒,没个三碗四碗,哪里填得满他那个狗肚子呢?”
秦三老汉满是眼屎的眼睛睁开一条缝,咧咧嘴,笑了。
“今天冬至呢,不光羊肉汤,酒这东西——咱们晚上是不是也该来点儿?老伙计。”陈厨子看着秦三老汉。
秦三老汉点点头,闭上眼睛,老龟一样,慢慢缩回到破棉絮里。
陈厨子睁开眼,他躺不下去了。也不晓得这个时候市场上还有没有羊肉。起床很折磨人,胸口憋闷,浑身乏力。在床沿上坐了一阵,一阵寒意袭来,他哆哆嗦嗦穿上衣裳,揣好钱。在出门的时候,顺手抓了根拐杖拄着。
6
每个餐馆都挤满了吃羊肉的人。建南去了家新开张的“羊歪歪”,叫了个大锅打包,还另外买了两斤熟羊肉。建南的男朋友小心地端着锅跟在身后,她一手拎羊肉,一手牵着个小男娃,男娃是男朋友的,七岁,路上一直低垂着脑袋。
陈厨子没有在家。锅里炖了一锅羊肉,汤色雪白,案子上摆了黄瓜条、莴笋尖、豌豆尖、茼蒿、芫荽末子、白萝卜丁儿、葱花儿、豆腐乳、腌菜粒儿和炒黄豆。
“老爷子整得齐备啊,到底是开饭馆的。”建南的男朋友拿勺子舀着尝了一口,啧啧称赞,“‘羊歪歪’哪里敢跟这味道比啊,这才是美味呢!”
“我要跟你说个事情,你肯定会后悔的。”建南说。
“啥事?你说。”男朋友往建南身边凑。
“你离我远点儿。”建南搡开男朋友,“我说真的……”
外头传来一阵脚步声,是建东和建西回来了,身后跟着个送外卖的,端着一口大锅子。
建东进屋一看就笑起来:“今天晚上开羊肉大会啊?爸爸炖了一锅,建南端了一锅,这里又是一锅,吃哪一锅啊?”突然一眼瞥见站在一旁的那个小娃娃,“哎,这是谁家的娃娃啊?”
“过来。”建南向那个男娃招招手,又向她的男朋友招招手。等两个人都站到了身边,建南给建东和建西做起了介绍,“这是我……我老公,明天我们就去办证,姓张,叫柏霖。这是柏霖的娃娃,来,娃儿,叫舅舅,这是你大舅陈建东,这是你二舅陈建西……”
那个男娃也听话,就按照建南的吩咐怯生生地叫,晓得自己叫得小声了,又赶忙大声重复了一遍。
“张柏霖,嘿,跟张柏芝家有关系么?不是香港过来的吧……”建西笑呵呵地问。
建南恨恨地瞪了建西一眼,正要回嘴,建东摆摆手:“爸呢?爸去哪里了?”
“我回来就不见他,可能是出门买东西去了吧。”建南说。
“是给那个疯癫老头送吃的去了吧。”建西说。
“你们倒是去看看啊。”建南说。
建东和建西出了门。兄弟俩在门口站了一阵,想要就建南的事情交谈点看法,却又觉得不好说什么,各自叹了口气,走过幸福大道,穿过安置小区,来到那片废墟上。正四处瞅呢,突然听见废墟当中炸起一阵火光,响起一阵劈里啪啦的鞭炮声,没过一会儿,燃起一团火来,像是在焚烧什么。又过了一会儿,一个黑影从废墟里走出来,走到微弱的路灯下。
“那是爸吗?”建东眼睛近视。
“是爸。”建西说。
陈厨子手里拎着个酒瓶,像是喝醉了般晃晃荡荡走过来,走到建东和建西跟前——
“你咋喝酒了?”建西问,“你不是有高血压不能喝嘛!”
“今天是冬至嘛,喝点也没啥。”建东说,“只是你咋跑这里来喝酒啊?我们都在家等你呢。”
陈厨子穿了套崭新的衣裳,脖子里还围了条围巾,头发也是新理的,还梳了个大背头。他看都没看建东和建西一眼,径直走了,走得越来越快,晃晃荡荡的样子活像一只飘起来的葫芦。建东和建西跟在身后,都快小跑起来了。这情形叫他们心头发毛,却又不敢吱声,生怕惊动了他,使他噩梦惊醒般坠落地上。
到了家里,建南正拿着两个小瓶纳闷呢,也被她爸爸的样子吓了一跳——
陈厨子面带微笑,他看看桌子中间的两大盆羊肉汤锅,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火炮和一叠纸钱,又摸出个打火机搁在上头。接着,他仰脖儿一口将酒瓶里的残酒喝掉,顺势一抹嘴,酒瓶往边上一撂,快步进了睡屋,坐在床沿上脱掉鞋子,小心躺下,捋捋衣领和下摆,双手抱在胸前,闭上眼睛。
建东和建西从建南手里拿过两个小瓶,嗅嗅,问:“哪来的?”
“我在他床头上看见的。”建南说。
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桌子上,看着那盒火炮,看着那叠纸钱,看着那个打火机,都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