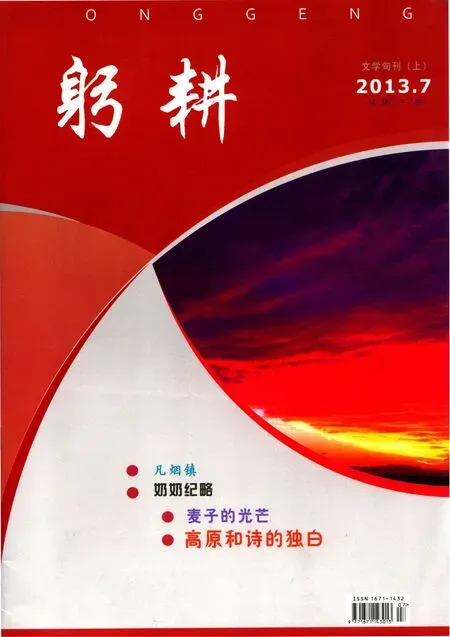悠悠祠堂情
◆ 肖华文
常言道,亲情抵万金。
那尘封的亲情,宛若神奇的魔方,对我这位身处异乡他地的游子来说,像春之百花,飘溢着浓郁的清香;像夏之繁星,闪烁着耀眼的光环;像秋之蝉鸣,撩拨着美妙的心弦;像冬之飞雪,舞动着敏感的神经。
心路遥遥,情思迢迢。往往在那静谧之夜,独望天穹空轮月,任凭云朵缭绕,飘飘洒洒,朦朦胧胧,陡增几多思绪,倍添几多情怀;常常独伫小桥旁,一缕缕清风,一曲曲蛙鸣,一叶叶纸船,一只只风筝,淡淡的情丝,漫漫的眷念,浓浓的追忆,无不浸透着沉沉的感伤,一番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情别意袭上心头。是啊,祠堂院里那如丝如线的一脉血缘,那如火如焰的一腔亲情,那如醉如痴的一帘幽梦,虽穿越久远而浩淼的时空,总是久久挥之不去。
情之所钟
祠堂院对我来说,可谓雨离不开云,云之所生,雨之所成。
祠堂院萧氏宗祠,可谓祖祖辈辈魂牵梦萦的心灵圣殿。大概始建于明清年间,如今显得陈旧破落不堪的宗祠,不仅供奉着先祖牌位,也曾是行使家族仪式和宗族议事的中心。虽仅存大殿和东西廊房,孤独地坐落于村之“心脏”,但昔日的繁华魅力依稀可窥。纷至沓来的缅怀与崇拜者,凝视那结构、布局和工艺,虽处处显露斑驳陆离之状,却无不凸显着祖先的智慧与眼光。大殿木梁斗拱之处,清晰地镌刻着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木雕工艺,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精美绘画,两者错落有致,交相辉映,折射先辈的崇高修养与情操。尤其被人称道的清代怪才庞振坤手书牌匾,曾高高悬挂在祠内,后来不翼而飞,着实令人哀叹惋惜。而那些惟妙惟肖的石雕、泥塑等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随着年远日久早已灰飞烟灭。两棵参天古树,其中最高大的一棵搭置的木梯可直插树冠,我年仅七八岁时,穿着短裤衩小背心,曾一个人胆战心惊地爬上过,那毛骨悚然的滋味至今记忆犹新;只见光秃秃的顶端有几片稀疏的枝叶,枯黄的枝桠间安装的高音喇叭震耳欲聋,高昂的声音覆盖整个村庄,远及田间地头,大队广播员一声通知开会,社员们便三三两两云集到大队部,听村支书慷慨激昂地训话。后来,这两棵古树因干枯而死,被人拿着钢锯和斧头给伐倒了,连留下的树根亦已荡然无存。惟独矗立的两块碑刻,历尽风雨剥蚀独显沧桑,不过上面书写的方块汉字依稀可辨。说一千道一万,宗祠那一砖一瓦,一花一石,一草一木,无不诉说历史沿变,记录时代变迁,品读血脉相传,感受枝干蔓延,见证辉煌荣耀。
时光飞逝,岁月如歌。如今,记忆中的父老乡亲有的已驾鹤西去,那些童年时玩耍的伙伴已朱颜先悴、两鬓染霜。惟独孩提时大人们讲的诸子百家、笑话谜语、神灵传说、妖魔鬼怪、灵禽异兽和创世神话,仍蕴藏在心灵的感光片上。如烟往事,宛若经典电影回放,令人目不暇接,忍不住咚咚地心跳。
是啊,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我们族人历尽磨难修炼路,演绎了无数悲喜剧。无论有多少故事发生,不管有多少传说流传,大都成为过眼烟云。追溯起来,那些与族人世代朝夕相依相伴的家什,总在我心灵的回音壁上激起悠远的震颤,依然如缕不绝。那些族人日常使用的祖传工具,有的大浪淘沙成为历史的记忆,有的熠熠闪光历久弥新,足以见证一代代萧氏庄户人家的历史。从东倒西歪的土坯墙到黑咕隆咚的土坯房,从轱辘轱辘的辘轳到盘卷弯曲的井绳,从吱扭吱扭的石磙子到咕噜咕噜的石碾盘,从黑糊糊的土灶到咯嗒咯嗒响的风箱,从吱吱拗拗的纺花车到啪哒啪哒的织布机,从冒着黑烟的煤油灯到遇上刮风下雨中手提的马灯,从耕犁耢耙铡刀到木轮车独轮车劳车;从碾道上被蒙着双眼满圈子转的毛驴,到那些田间地头被鞭子打得震天响的老忙牛;从房前屋后被赶得圆圈乱转的猪狗,到扇动着翅膀满院子扑腾腾乱飞的鸡鸭……以及男人们说不尽的明代镂空青花瓷碗、清代纯手工龙凤银酒杯和民国老铜水烟袋,女人们道不完的明代蝴蝶簪子、清代银鎏金手镯和民国翡翠胸花,这些祠堂院里的“宝贝疙瘩”,无不印证岁月梦想,镌刻永恒时光。每每想起,仿佛时间凝固,似乎时光倒流。
祠堂院,是我族人的生命之根,是吾辈人的血脉之源。无论是祖辈世系,还是祖训家规,以及子孙繁衍,宛若一条条无形的丝带牵系着,不管山高水长,不管天南海北,使族人们总有一种莫名的没完没了的感激,总有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原来,这是一份留恋,这是一份牵挂,这是一份难舍难断的情缘,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在这片生我养我的热土上,那个曾经从歪歪扭扭爬行,到咿咿学语;从挂着书包上学堂,到放学后拾柴割草放羊;从萧氏祠堂院这个圆圆的零点起步,到毅然投笔从戎,几经砥砺,几经磨练,终成正果,变身为堂堂正正的胸前挂着两枚军功章的军官,再次变身为衣食无忧受人尊重的国家公务人员。曾几何时,那个赤巴脚、穿着土布开裆裤、光着腚、被大人拧了小脸蛋也不吭声的憨娃子,那个剃了个瓦片头、平顶头、光光头、偏分头后光知道龇牙咧嘴嘿嘿笑的傻瓜蛋,那个嘴上无毛、乳臭未干、不知屎香尿臭的楞头青,那个在小学出黑板报、写作文总被老师褒扬、起五更爬半夜在煤油灯下苦读的穷书生,竟不知天高地厚走进了繁荣喧哗的大都市,住进风不刮雨不淋日不晒的高楼大厦,但在心灵的深处似乎总有一条无形之网,网住我对祠堂院萧氏宗祠这个根的绵绵思念!
归根到底,最好听的莫过祠堂院的土话,最好喝的莫过祠堂院的井水,最好吃的莫过祠堂院的干饭,最好客的莫过祠堂院的主人。祠堂院,这里有我最真的浓浓亲情,有我最纯的绵绵友情,也有我最深的拳拳乡情。这些情感像一张巨大而无形的网,交织在一起,如丝如发,千丝万缕,捋不出个头绪来,往往牵四挂五,历历宛如昨,似乎触手可及,网住我永永远远的心海。毕竟亲情无价,什么都比不上我认同的血缘和根脉,一抹认同感和一种归属感,每每触及那道泪腺,便汩汩如泉,晶莹剔透。
情之所至
这个纯朴的村落,成为萧氏族人理想的居宿地,成为萧氏族人完美的居善地。这里不仅具有独天笃厚的地理优势,而且具备山水相宜的风水格局,不愧为风水宝地。萧氏族人世世代代望山而居,依水而生。望东北一眼看到安然无恙的土谷山,瞧西北瞅见那心驰神往的灵山,西傍蜿蜒奔腾的七里河,东依邓州当年巨大引水工程湍惠渠。这里土地肥沃,草木茂盛,承载着世世代代的延绵,天灵水秀养育着一代又一代勤劳、淳朴、善良、热情的吾辈族人。
一到春天,杏花、梨花和槐花粉白粉白的,一簇连一簇,一串接一串,开满枝头,清馨扑鼻。这些花灿烂地笑着,蜜蜂成群结队,嗡嗡来嗡嗡去,在每朵花蕊上尽情吟唱着吮吸着;各种鸟儿成群结队也来凑热闹,叽叽喳喳,从这枝跳到那枝上,一展婉转动听的歌喉。而在田野的沟沟壑壑间,长着倔强的酸枣花和灿烂的野菊花,还有许多无名花花草草,有紫色的、有粉红的、有橘红的、有紫色的,在沟沟边边沿沿竞相开放。记得小时候,同伴们放学后,背着书包,撒欢似地跑到土坡上,躲进一人多深的草丛,左藏右躲,藏老猫,捉蝴蝶,扔稀泥巴,比赛跳高,享受童年的乐趣。有的为摘一朵鲜艳的花朵,有的为捉一只漂亮的花蝴蝶,你争我抢推推搡搡,甚至嗷嗷狂叫打起群架;有的玩疯了,躺在草丛里打滚儿翻跟头,也不管弄脏衣服会不会被家人挨骂,那笑声笑得多开心多灿烂啊!直到玩耍到日头落山月挂树梢,小伙伴们才扫兴而归,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每个人手里攥着、书包里放着一把把野花,有的女孩还将几朵花插在头上,一蹦一跳地像小燕子似地飞走了。
一到秋天,枣儿缀满枝头,红艳艳的,煞是一番美景。有的枣儿一片片密密麻麻地压弯到房顶上了,有的一串串沉甸甸的枣儿延伸到猪圈里和茅屎缸中。尤其家家院落内堆满了晾晒的包谷棒子,有的被编成辫子盘在树干上挂在树杈上,一眼望去金灿灿黄橙橙香喷喷。还有的沿着用树杆订的梯子,攀爬到自家房屋上面,在日头底下细细翻晒棉花,薄薄地摊开来,远远地看去,像天上的朵朵白云飘落。在这收获的季节里,小伙伴们到田间地头抛红薯,拔野菜,摘芝麻叶,掐野韭菜,剜圾圾菜,刨刚子姜,挖茅草根。不管劳动成果怎样,收获的是一筐筐一篮篮的满足和喜悦。几百年来,族人们世世代代生于斯,祖祖辈辈长于斯,几乎每天都在重复上演着周而复始的生活故事。在曦微的晨光中,伴着雄鸡引颈高歌,窗外小鸟清脆地鸣唱,族人们赖以生存和生活的村庄苏醒了。此时,有人用扁担挑水,有人用斧头劈柴,有人忙着推碾子,有人用条帚扫院子,一缕缕炊烟袅袅飘荡,各家各户奏起锅碗瓢盆交响曲。于是,狗吠鸡鸣鸭叫,哼哼叽叽的猪在圈里抢吞食物,夹杂着牛群哞哞、羊群咩咩的叫声,而被晒得黑黝黝的族人们,开始了一天崭新而又忙碌的劳作。就这样,一代代传承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有滋有味地过日子。
萧氏族人,得先祖的遗传基因之力,造就了朴实、憨厚和善良,也造就了勤快和忍辱负重。因此,子子孙孙永保佑,世世代代传香火,不管世界怎么改变,时间怎么变迁,始终坚守“养气忘言守,降心为无为,动静知宗祖,无事更寻谁”的道理。不论喜怒哀乐,还是悲欢离合,我们的族人,从迁徒定居后便以农耕为主,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繁衍不息;族人还抱着“重耕稼、鄙商贾”的老主见,认为民以食为天,对经商做买卖不屑一顾。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造就了古朴厚道的民风和自然亲切的乡情,但也养成了小富即安和墨守成规的意识和观念。随着改革的春风和开放的浪潮,这种古旧的小农意识正被逐渐淡化,族人们不再满足于“一家人几分地一头牛,老婆娃子热床头”的家庭生活,开始这山望着那山高,将眼光投向更高更远的地方。
情之所达
萧氏家族的人向来将做人做事看重的是过程与结果。族人觉得,要想先做事,必须先做人;做好了人,才能做成事。做人要低调谦虚,做事要高调自信。
族人们好字当头,快在其中。常常好热情,好排场,好攀比,有时喜欢吹牛,喜欢给自己脸上贴金,难免爱显摆,爱面子的结果是吃了哑巴亏,嘴边却说“上当如领教,吃亏买回能。吃亏是福!”实际上心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在哪个特殊的岁月里,尽管家里穷得叮当响,有的瘦成皮包骨,有的饿得眼睛凹陷,有的脸色腊黄,有的腿脚浮肿,要什么没什么还穷大方,遇到门口来要饭吃的,还打肿脸充胖子,从家里抓几把红薯干、捞几把箩卜秧、丢几个包谷馍,打发人家走开;碰到揭不开锅盖的邻居和亲戚,不加思考地拿出一条破裤子撕扯开来,将裤脚用麻绳扎死,再从破烂堆里扒拉来扒拉去,噙着热泪盛好用瓢子将缸底中刮了又刮的白面、红薯面、包谷粉之类能吃的东西,亲自送上门来手把手交过去,嘴角上仍挂着笑意,“土帮土成墙,穷帮穷成王!穷不失义,穷不失志,这有啥窝囊的。”
族人能喝酒,从青晌(早晨)喝,喝到晌活(中午),喝到夜黑(晚上),连续喝个三四场不成问题。天天如此,从前隔(前天)到夜隔(昨天),从今隔(今天)到明隔(明天)或到过明隔(后天),可以连续喝几天是小意思,不胜酒力的被称为老鳖一,能喝的被视为英雄好汉。自恃酒量过人,滴溜着酒瓶,边走边对着瓶口往嘴里吹。有的沾点酒就不知自己是老几了,故意借酒兴找茬闹事打老婆孩子;有的喝得烂醉如泥,连天王老子地王爷也敢乱骂,甚至动手动脚乱打人乱踢人。第二天大家不再迷瞪,再次碰头时,喝酒时说什么讲什么骂什么,全都丢到后脑勺了。这就是我们的族人,有时候既出洋相又闹笑话。
族人的作派常常不拘小节,好像什么都满不在乎,说话不讲究,大大咧咧,习惯大嗓门大腔调,离老远都能听见谁在拍话拍什么话,听得一清二楚;拍话不讲场合,有时拍话带把儿,夹杂着不少难听的脏字,一点也不顾是否有妇女儿童在场,往往让人面红耳赤下不来台;也有时候,拍话不注意别人的眼色,不管三七二十一,拍完了讲完了拍屁股走人,根本不理会别人是否能够承受。但族人有话直说,水过地皮湿说完拉倒,从不往心里撂。
族人憨态可掬,平时穿衣戴帽不讲究,衣冠不整,有时歪戴帽子,有时挽袖子,有时及着裤腿,上身光嘟嘟的,坦胸露肤,拉拉踏踏。一到夏天,日头晒得地上发烫,皮肤晒得黝黑的族人们赤巴脚,挥舞着锄头在田地里挥汗如雨,汗津到眼里蛰得睁不开眼,汗流到嘴里咸得不是滋味,便用背心或黑糊糊的毛巾胡乱抹一把了事。在茶余饭后,族人们离离拉拉走到一起,坐在土疙瘩鹅乱石堆上,不自觉就用手指夹摆置角莫指头(脚指头),或站起来将头皮屑抓得纷纷掉雪花儿,那玩挠痒痒的感觉像神仙般过足了瘾。一旦逢年过节,走亲串友,族人如果出门,总是把头发洗上几遍,对着镜子不停地摆弄头型,穿上支支楞楞的衣服,人模人样的,见人彬彬有礼,说话客客气气,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族人有时爱耍个小聪明耍个滑头失弄人,说你看看谁长得像露骨鼻,讲你瞅瞅谁是一副瓦刀脸,背后指桑骂槐好像别人是聋子是瞎子;族人有时站没站像坐没做像,见到长得漂亮的女人会主动凑到眼前,没事找事没话找话,花搅(调戏)人家半天,尽管让人白了眼吐了唾沫星儿骂了个狗血喷头,心里倒是喜滋滋的别提有多得劲。族人的表现给人的感觉反复无常,时而顽世不恭,时而磨磨蹭蹭,时而拖拖拉拉,脸皮似乎特别厚,被人开玩笑说成一城墙拐弯。族人有点傲气,富有霸气,对瞧不起的人就既打面鼓也敲背后锣,说谁谁是圣人蛋,论谁谁是铁公鸡,讲谁谁是白眼狼,道谁谁是喂不熟的狗,议谁谁是披着人皮的狼。这样的闲话,族人能说出一大堆,能装一大箩筐。有时候,族人好胜心极强,一点也不服输,假若姜拧儿(刚才)自尊心遭受打击,独自一人默不作声生闷气,从不斜货(叫喊),也不会将暴怒的情绪转化为暴力伤害,而是将自尊心转化为自信、自爱和自强。
族人遇到刮大风下连荫雨,或到了割罢麦收完秋,或到过冬农闲时,或在下着稀稀拉拉的毛毛雨,大家觉得闲着无聊,就掰掰手腕,学学狗叫。除此之外,或偷偷摸摸躲在鸡不下蛋的僻静处,或躲在兔子不拉屎的旯旮地,或猫在屎尿味熏人的牛棚子,或藏在烟叶味扑鼻从不蹙眉的炕烟炉中,神不知鬼不觉,一边吸着旱烟袋,一边摸着纸牌,明眼人一看就估摸个八九不离十,这帮人的赌瘾上来了。起初之赌,小打小闹不算啥,一毛二毛不算多,后来零打碎敲都不屑一眼,时间一长,有的赢上了瘾,有的输红了眼,有的想见好就收。此时,赢者双眼珠子滴溜溜乱转,渴能(狡猾)劲来了,输者心明镜似的,双眼瞪的比电灯泡还大,赢者想喝水借故离开没门,想借尿泡说急得尿到裤裆也休想脱身,只有大眼瞪小眼干耗时间,或像小孩子撒尿走到哪尿到哪。当然,也有例外,赢的主动说请客下馆子,将赢来的钱花光喝个底朝天,输的人心里也就觉得不憋屈了。
有道是,十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更何况对食人间烟火的萧氏家族人呢!对此,我们既不要鸡蛋中挑骨头,更不过于苛求挑剔,平平淡淡才是真啊!
情之所系
萧氏家族民风纯朴,比较讲究礼仪,日常相见、迎送、借还、庆吊、生育、成年、婚嫁、寿诞、丧葬等,不仅真诚待人,正直善良,而且知书达礼,睿智贤德。
族人见面,通常用手打个招呼,点点头,就算是问候了,常说的口头禅是“吃了木有”“喝没喝”。小辈见长辈,首先要让路,让长辈先走,或上前扶一把;每逢大年初一晚辈着一身新衣,鬼撅(臭美)极了,约上兄弟一起给长辈磕头,长辈给一两毛压岁钱,高兴得合不拢嘴。平辈相见,比较随意,但要称兄道弟,对聪明者称为伶俐鬼、机灵鬼,或叫狗娃、虎子、石头蛋的小名;如果喊姐叫妹,对漂亮者赞不绝口,什么天女下凡啊,什么美如天仙啊!平常叫得最多的是梅啊、芬啊、花啊、琴啊,这样叫得女孩子心花怒放!长辈对小辈,或直呼其大名或小名,或按兄弟排行叫,老大老二老三。长辈对孙辈,可相互开个玩笑,也可骂着玩,笑骂之时没有大小之分。男女之间,相互不来住,见面时打个称呼,但不握手,不单独相处。也有例外,逢接亲娶媳妇,一方面讲究选黄道吉日,不仅选时辰,还讲礼节,图个大吉大利和喜上加喜,另一方面闹新房逗新媳妇,三天不论大小。这在当年可是一个巨大的娱乐节目,比看电影耍大戏热闹多了。
族人无论年龄大小,无论职务高低,无论贫富贵浅,都知道老祖宗定下的铁规,人人走得直,行得正,走得端,从不做损人事,不做不主贵事,更不做亏心事。就拿族人的豪爽义气来说,如果一家有难,左邻右舍不用说,主动伸手相帮,帮完后扭头就走,连句话也不说,连个烟都不抽,连顿饭都不肯吃。萧氏家族的人不坑人,不蒙人,不拐人,不骗人,堂堂正正,规规矩矩。族人常说,人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子歪,那些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低三下四、随声附和的话,即使烂在心里,也不愿说出口,就是说出来脸也会红的。在萧氏家族,知书达理者受人尊敬,有“礼多人不怪”的谚语常挂在嘴边。待人知礼,谓之“懂事”、“明理”、“懂规矩”,反之,则遭人白眼,被人贬斥。
我们的族人有的性格粗放,有的质朴爽快,有的真诚善良,有的圆滑老道,有的精明洒脱,有的包容宽厚,有的实诚可靠,有的吃苦耐劳,这些已成为祖传的本色。另一方面,我们的族人非常抱团,个个义气,人人豪爽,不乏侠义忠胆,重情重义,有时为人两肋插刀,如果一人受欺负,族人们闻讯后跑来,一边说咋了,招谁惹谁了,一边捋胳膊挽袖子一起,吼叫道“弄他个缺胳膊少腿”“整他个半死不活”,只是吓唬吓唬人,不到万不得已不出手;一旦遇到外村人打听个路,寻找个什么人的事,一大片热心肠的人会围拢过来,指指点点,有的担心走错路还充当带路人,大老远地送,一点报酬也不讲。
萧氏家族的人真诚热情厚道,有情有义有信,不贪不嫌弃人,知人间冷暖,知屎香尿臭,知亏欠,知恩图报,常讲坷拉蛋也是有用处的,何况是人。族人在村里村外有口皆碑,人人称道。听说客人要来,总是提前上街赶集,割肉买菜,放在橱房舍不得吃干等着;将院子里里外外扫得干干净净,屋里收拾得整整洁洁,将不分男女的又脏又臭的茅坑冲洗得一点气味都没有。客人一般都是晌午来,主人见面总是笑脸相迎,打热水洗脸,端上热腾腾的荷包蛋,拉着手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亲热极了。遇到贵宾,一定会请来村里最好的厨师,准备七个盘子八个碗,喝酒吃饭时,不停地用筷子给客人夹菜,自己却舍不得吃。客人离开时,不管客人是否愿意,把家里好吃好喝的硬往客人篮子里撂。但对自己家人,节俭得近乎吝啬,抠抠掐掐,恨不得一分钱能掰成两半花。
族人在饮食上从不眼气谁,看不惯吃香里喝辣里的城里人,不奢望山珍海味,也不企求鱼翅捞饭,一日三餐吃五谷杂粮觉得有劲,喝粗茶淡饭感到美气,讲究“细粮俭用,粗粮细吃”。早上煮稀粥啃馒头,晌午饭吃手擀面条,夜黑吃炒菜烙馍喝汤。一日三餐,族人们端着大黑碗,一边走一边吃,总能听到嘴边胡胡喽喽,口中稀稀流流的交响曲。有的族人,或一屁股坐在砖头瓦块上,或双脚圪蹴在橙子上,唠唠叨叨,喋喋不休,漫无边际,闲情逸致地说些家长里短的话;即使在村里穷得掉渣儿时,族人粗粮细做,做成了红薯和绿豆面条,逢年过节包扁食蒸发酵馍,下锅炸油馍,想着法子变着花样去吃,生怕肚子饿偏了。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萧氏族人的生活开始嬗变,衣食住行不再犯愁,那些布票、油票、粮票和肉票已成为收藏品,可以说穿越穿越讲究,吃越吃越精致,住越住越舒适。如今,族人的新屋老房,交相辉映,使村里充满了特有的风韵和宁静。我离开家时,家乡那凹凸不平的泥巴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如今,族人们的日子越过越富裕,越过越火红,越过越喜庆。尤其可圈可点的,全国政协前主席李瑞环挥毫为萧氏宗祠题词,使总感到天高皇帝远的族人们,每每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喜悦;朱德元帅之女朱敏教授亲笔为萧营学校题词,据说后来周围村庄的学校一个个被关停并转,而萧营学校荣幸被保留完全沾了她老人家的光。全国著名书法家何耀军、张才、朱继国先后为萧氏宗祠题词,也成为族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由于我身居首都皇城根边上,站在天子脚下,有天时地利之便,能成就族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名人名家墨宝,也算给先祖先贤及族人点滴的报答。
不过可惜的是,原来高大的寨墙早已面目全非,留下一堆堆残缺的黄土被乱七八糟的垃圾和杂草埋没了,过去蓄满深水的寨沟几乎被夷为平地,很难再寻到当年的景象,实在令人扼腕。更令族人痛心的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堆在门前屋后的垃圾多了,蚊子、绳子满天飞,灰雾天气增多,空气不再新鲜,七里河水和村里池塘成了污泥浊水。夏天之时,孩子们再也没有跳下去的冲动和勇气,小鱼小虾在水里游来游去的情景一去不复返了。这给族人增添了新的忧虑与无奈!
说一千道一万,祠堂院对我来说,不管走得多高离得多远,宗族这一壶壶酽酽的茶,族人那一杯杯醇醇的酒,时时品尝,足以令人怦然心动,足以让人肝肠寸断,一如绿叶对根的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