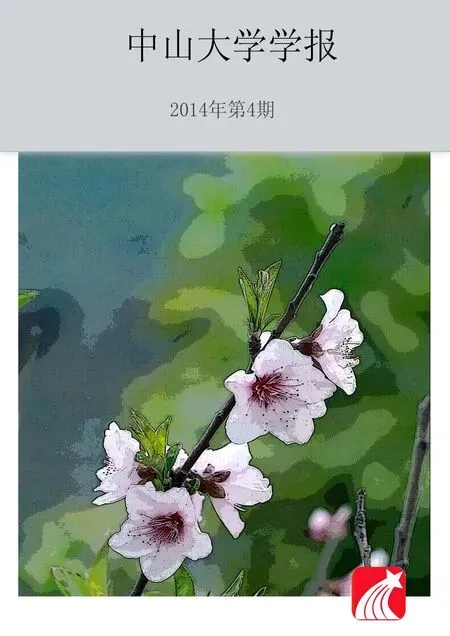解构批判:八股文的另一类历史意见*
陈 志 扬
八股文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而殆成刍狗,刘绍棠一段话颇具代表: “在我的印象里,八股文是和缠足、辫子、鸦片烟枪归于一类的,想起来就令人恶心。”①刘绍棠:《八股文概说·序》,见王凯符:《八股文槪说》卷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二十世纪以后,八股文处一片咒骂声中,时代意见不断寻找历史意见中与之相吻合的消极面,因此现代学术主要集中于对古代八股文批判材料的梳理。《儒林外史》更以其通俗文体方式而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批判材料,彰显二十世纪对八股文的批判所来有自。这种一边倒的现象造成对另一种声音的严重遮蔽:古代不乏真诚维护八股文者。倘若我们对辩护意见一概视而不见,就有违“了解之同情”的真义。
一、路德与八股文政治功能的思考
作为得益于时文并培养过不少掇青拾紫弟子的路德,其时文理论的重要内容是解决攻击者提出时文无法选拔真才的责难。路德认为八股文本身并无用处,却是一种最佳的手段:八股文以其题之万变,最能督促实学。
八股文设计者们认为:圣贤之言是治国理家良方,经典文本传载其言,示来者以轨则,现世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但是此种说法难以经受实践的检验,早被人道破。康熙年间,索尼、鳌拜辅政时曾公开诏称“八股文章实与政事无涉”②王逋:《蚓菴琐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9册,第578页。,乾隆间力主八股文的鄂尔泰事后也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用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③陆保璿辑:《满清稗史》之《满清兴亡史》第三十一节,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2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67页。。嘉道时期,盛世后的社会危机已经显现,应经世思潮之需,研究史学、考证掌故蔚然成风。经世史学的兴起表明,先知先觉者已不再从经书里寻找治世方法,若再沿用“圣贤之言乃治国理家良方”来为取士制度辩护,明显是游谈欺人。另有一种递相祖述的说法是:八股取士制度可迫使士子研习经典,培育士子与圣贤心灵遥契,并归之于躬行践履。嘉庆帝曾谕示考官周系英云:“命题必正,当录文必雅厚。言为心声,其文醇者,其人必端重,异日出身加民可以为好官。”*参见包世臣:《戊辰江南试录后序》,《小倦游阁集》卷24,《续修四库全书》第150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90页。文品与人品一致的事例固然可以举出很多,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文品与人品不一致的事例亦不胜枚举。雍正朝李元直曾言:“夫八股时文能为端人正士之言,未必无卑污苟贱之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91页。连康熙皇帝也曾指出韩菼作时文甚佳,但为人不称其学,有学问而无人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9,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月条下,《清实录》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85页。。因此从道德社风层面肯定八股取士制度同样苍白无力。
修身、治国始终是八股文的主题,然“圣贤之言,外可治国、内可修身”既已为易于攻破之陈言,道光年间的路德故不得不对此作出修正。路德认为八股文内无益于己,外无济于人,考察的重心不是什么道德之心,而应是实干精神。他的理念是:为文与为政本一心,若以求实之心为八股文,日后亦必以实学之心治国,其言云:“士当未遇时,无民社之责,无簿书符牒之劳;不商不贾,匪农匪工,其日夜所业者不过案头数事耳。于此而卤莽灭裂,何事不卤莽灭裂乎?于此而因陋就简,何事不因陋就简乎?于此而务苟得,何事不务苟得乎?于此而贪逸获,何事不贪逸获乎?今日之士,即异日之官,即不尽为官,亦乡闾之所矜式,子弟之所则效也,不务实学而惟剽窃之是务,是亦大可忧也。”*路德:《柽华馆全集》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09册,第341,337,327,337,337,338—339,318页。在路德看来,实心为文与实心为吏是同构一致关系。“文人之文,文人之心也;作文此心,作吏亦此心,心顾可以转移乎哉?”⑤路德:《柽华馆全集》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09册,第341,337,327,337,337,338—339,318页。路德认为文士登仕籍者或竟不达于政的现象,乃是“文士操术之误,亦鉴裁者未得其真”⑥路德:《柽华馆全集》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09册,第341,337,327,337,337,338—339,318页。。乾隆三年(1738)的八股文兴废论争是一次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视角的大碰撞。以鄂尔泰、张廷玉等为意志的礼部在复奏舒赫德废除八股文取士提议时,就搬出“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议覆制科取士疏》)的论调,认为倘若司文衡职课士者,循名责实,力除积弊,杜绝侥幸,就会文风日盛,人才自出。概而言之,八股文之弊不在取士内容、方式,而在于执行者未能有效落实措施。这一托词在当时颇为官场所沿用,甚至连普通下层知识分子也怀此看法,如科举沦落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更多的是将矛头集中于科场上的不公,把责任归结于考官的无能、贪赃,或时运不佳。英雄失路的蒲氏无意击垮维系读书人身家性命的科举制度,而是期盼有所改良。路德的解答在思路上完全借用这种套语,并未提供新的内容。
路德坚信“神不可伪”,真伪作八股文者一定能够鉴别。他在《求益斋时艺序》中用李惠击羊皮而负薪者屈、张举验猪口灰而作奸者伏罪、传令破鸡得粟而争鸡者无辞三个典故说明一个道理:人事机隐,躁人视之不可见,惟静者审查而得之,时文与此同理。“惟静者审查而得之”未免过于玄乎而难于操作,为此路德又提供了一条简单易行的途经:他认为倘若士人一入宦途便束书高阁,不谈八股,此人便是伪作八股文者。“彼所涉者,藩篱耳;所学者,土梗耳。其入之也浅,故其出之也速;其得之也易,故其弃之也不惜。”⑦路德:《柽华馆全集》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09册,第341,337,327,337,337,338—339,318页。路德承认辨于应试非具眼不能,转而寄希望“辨于通籍后,凡作伪者可立谈而破”⑧路德:《柽华馆全集》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09册,第341,337,327,337,337,338—339,318页。,这不是事后诸葛于取士环节无补于事吗?
路德讲席关中三十余年,以时文授徒,扬名西北,他为八股取士制度辩护最重要的策略是区分真伪作八股文者。路德认为只有研精理法的有志之士才算是真作八股文者。他鼓励士子读书研理,敢于不蹈袭旧说,取士若“羌无故实者录,引经据典者黜,是禁人读书也;蹈常袭故者录,自出心裁者黜,是禁人立志也;不著痛痒者录,务为警闢者黜,是禁人研理也”⑨路德:《柽华馆全集》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09册,第341,337,327,337,337,338—339,318页。。他在《周勉斋先生文集序》中阐述其经典阐释观:“汉唐诸儒言之而未确者,宋人言之;宋人言之而未尽者,元明人言之;元明人言之而犹未尽,国朝诸家言之……儒者宗程、朱,是已。岂谓程朱而外,概从废置哉。”⑩路德:《柽华馆全集》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09册,第341,337,327,337,337,338—339,318页。基于这种阐释无止境的观念,他高度评价明末刘凤翔《四书鞭影》不泥古徇时,义多创获。该书被时人指责“牴牾程朱,喜为异论”,而路德则赞同重刻此书。路德在教学中始终坚持“以读书为本,以研理为宗,以法律为门,上溯古文以增其笔力,旁及诗赋以发其才思”*路德:《仁在堂时艺辨序》,《柽华馆全集》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09册,第340,341页。,诸生虽来去无常,然其秉持该理念坚如磐石。
八股文重在考察“实学之心”既已辨明,路德第二步是回应考察“实学之心”何以必用八股以及现实中“积学之士数十年不中有司程式而终老场屋”该如何作解?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他在《仁在堂时艺辨序》中给出了回答。对于前者,路德的观点是:学人之病莫甚于喜剽而惮实学,实学不废则真才自多,国家取士不能变更八股文在于它可拔真才而斥剽窃。他阐述云:“惟时艺限之以题,绳之以法,一部四子书离之合之,参伍而错综之,其为题也不知几万亿,虽有怀挟,弗能该也;虽有宿构,未必遇也。非学焉而有心得者,不能游其彀中也。取士以此,可以储官材;训士以此,可以端士习。”②路德:《仁在堂时艺辨序》,《柽华馆全集》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09册,第340,341页。路德认为前代或以策论,或以表判试士,命题有限,难以杜绝剽窃宿构,唯独“四书”离之合之为题不知几万亿,这种“题之万变”法可最大限度杜绝怀挟宿构,有效端正士习,督促实学。对于后者,路德的观点是:才人恃其才学之过人,往往不循绳尺不趋风气,故而反不如辁才浅学之士用其所短仰而掇之。以八股文特征而言,古今之文随时而变,时艺之变尤甚。昔之文不可用于今,今之文不可用于后,匪世运使然,乃人事为之也,所以才人学人之阸虽曰风气阸之,亦是其人自阸之也。从应试者角度而言,应当出其才学以趋风气,如此则中试视他人当更不难。路德这种辩护实存重大漏洞。任何一种考试都存在预拟抄袭的可能,尤其是八股取士制度延续几百年,“题之万变”空间已非常有限,钱大昕就曾指出:“四书文行之四百余年,场屋可出之题士子早已预拟,每一榜出,钞录旧作幸而得隽者盖不少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8“科场”条,《续修四库全书》第1151册,第327页。当时考官往往割裂经文截搭为题,实属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截搭题的出现表明“题之万变”窘境的显露,预拟抄袭之风顺势而生,督促实学已变得不可能。同时,路德要求士子“出其才学以趋风气”,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他已默认八股取士对人才的压制,其回应已呈捉襟见肘之态。
二、姚鼐与文体无尊卑论
姚鼐是乾嘉朝推尊时文不遗余力的巨擘,他的“文体无尊卑论”是当时最具学理的辩护理论。言圣贤之道、以古文为时文是流行的推尊制举文论调,姚鼐“文体无尊卑论”在具体运用时整合上述两种论调,因此实际上又落入大众化辩护套路。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他推尊八股文观点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姚鼐自退出四库馆修书后,先后受聘于江南多地书院,教书授徒是他后半生的主要生活内容,于是时文写作成为他不得不面对的话题。姚鼐不仅自己平生不敢轻视经义之文,甚至尝欲率天下为之。为开塞后学,使知举措取舍之宜适,姚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钦定四书文》为蓝本,选隆、万、天、崇及清人四书文251篇,并增益后来之名家及小题文,授敬敷书院诸生课读。姚鼐对该选本十分满意,写信向后学门人推荐,甚至直接邮寄。此外,在《与陈硕士》书信中他还有“时文除石士所刻六十篇之外,又得百廿余篇,其中佳者似可与荆川鹿门抗行”*姚鼐:《与陈硕士》,《惜抱先生尺牍》卷6,陆国强等编:《丛书集成续编》第130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944页。之言,透露出他热衷编撰时文选集似乎不止一次的信息。清代八股文水平整体而言难以与明代相提并论,顺康雍乾尚差强人意,自乾隆中叶后则渐趋巧薄而就衰。姚鼐对清八股文衰败现状痛心疾首,他以为困境缘于人们对八股文认识之不足:“今世时文之道殆成绝学矣,由诸君子视之太卑也。”*姚鼐:《与鲍双五》,《惜抱先生尺牍》卷4,陆国强等编:《丛书集成续编》第130册,第924页。张帜八股文,首要在端正人们的认识,为此他提出了文体无尊卑的观点:“论文之高卑以才也,而不以其体。昔东汉人始作碑志之文,唐人始为赠送之序,其为体皆卑俗也;而韩退之为之,遂卓然为古文之盛。古之为诗者,长短以尽意,非有定也;而唐人为排偶,限以句之多寡。是其体使昔未有而创于今世,岂非甚可嗤笑者哉!而杜子美为之,乃通乎《风》、《雅》,为诗人冠者,其才高也。明时定以经义取士,而为八股之体。今世学古之士,谓其体卑而不足为,吾则以谓此其才卑而见之谬也。”*姚鼐:《陶山四书义序》,《惜抱轩文集·后集》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453册,第138,138页。姚鼐指出文体本身无雅俗高卑之分,关键在于作者能否驾驭。足以驾驭,俗可成雅,卑可变尊;反之,则雅亦成俗,尊亦转卑。姚鼐以“文之高卑不以其体”的大命题为前提,推论落足于八股文应持之态度上,很显然,他的文体无尊卑观似专为八股文而设。此观点又见于其《与管异之》、《与陈硕士》两封写给门人的书信中,可见文体无尊卑论并非姚鼐应人作序的临场敷衍之辞。
在《与鲍双五》、《复秦小岘书》两封书信中,姚鼐进一步将八股文与四六文、寿序作对比,认为从文体体性来说,八股文尊于四六、寿序。骈文在八家之后名声已坏,寿序晚起且属应酬文,八股文与之相较尚不足说明体尊,姚鼐又引词、赋、笺、疏作比,断言道:“苟有聪明才杰者守宋儒之学,以上达圣人之精,即今之文体而通乎古作者文章极盛之境,经义之体其高出词赋笺疏之上倍十百,岂待言哉!”*姚鼐:《停云堂遗文序》,《惜抱轩文集》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453册,第27,27页。在其观念中,八股文尊于别的文体缘于与圣贤相联系。推崇程朱理学是姚鼐的学术旨趣,以阐圣贤之道为宗旨的八股文为其所重也就理在必然。程朱理学为清代推行的意识形态,即便在乾嘉汉学兴盛的时代,孔孟之道仍是此时政治伦理思想的圭臬。在古代人文价值体系下,胆敢非圣弃古的人并不多见,理学地位遭遇挑战,八股文精神基座受到根本性动摇,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因此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就学理而言,姚鼐以阐明圣贤之道为由推尊八股文是完全成立的。但是,姚鼐在文体无尊卑的大命题下给八股文定位,在实际阐述上为了推尊八股文,又将四六、寿文、词、赋、笺、疏与八股文相比,扬此抑彼,明显背离文体无尊卑这一理论基点,这是其理论的重大破绽。
同时姚鼐对八股文的创作现状予以猛烈抨击:“美才藻者,求工于词章声病之学;强闻识者,博稽于名物制度之事。厌义理之庸言,以宋贤为疏阔,鄙经义为俗体,若是者大抵世聪明才杰之士也。国家以经义率天下士,固将率其聪明才杰者为之,而乃遭其厌弃!惟庸钝寡闻不足与学古者乃促促志于科举,取近人所以得举者而相效为之,夫如是则经义安得而不日陋?”③姚鼐:《停云堂遗文序》,《惜抱轩文集》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453册,第27,27页。推尊经艺却又批判经艺创作,看似矛盾实是姚鼐推尊文体的一种策略。时文遭人诟病很大程度是受现实末流的拖累,在八股文殆成绝学的处境下,姚鼐理想中的“守宋儒之学,以上达圣人之精”而“通乎古作者文章极盛之境”的八股文已属凤毛麟角,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对理念八股文与现世之八股文末流切割划界,从而达到正本清源、以正视听的目的。
综上而言之,姚鼐认为:制艺以阐明孔孟之道为旨归,故其体尊;制艺之弊乃操术者之误,而非文体本身不佳。他的这种观点与策略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如朱珔《制艺丛话序》云:“天下必能自竖立卓尔不磨者,乃不受转移于风气,否则骛乎此,复艳乎彼,驰逐东西,迄无一效……甚且模仿旧调,填砌字数,肤饰庸滥,徒具形而无君形者存,致议者以制义为诟病,不知特末流之过,岂制义之本如是哉。”*梁章钜:《制艺丛话》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718册,第526页。
姚鼐在理论上端正了对八股文价值的认知后,又进一步为操作者指引为文之术,其云:“使为经义者能如唐应德、归熙甫之才,则其文即古文,足以必传于后世也,而何卑之有?”⑤姚鼐:《陶山四书义序》,《惜抱轩文集·后集》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453册,第138,138页。他希望人们能像唐、归二人那样以古文为时文,其门人鲁九皋作科举之文以古文法推而用之,故得到了他的揄扬。“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起于明正嘉年间,唐顺之、归有光等人曾积极倡导并努力实践。明末艾南英以诸生操选政,亦公然以“以古文为时文”相号召,将“以古文为时文”推广到一般士子的写作中。在清代,倡导这一口号的人更多,甚至获得官方的推崇,乾隆二十四年(1759)奉上谕:“有明决科之文流派不皆纯正,但如归有光、黄淳耀数人皆能以古文为时文,至今具可师法。”*梁章钜:《制艺丛话》卷9,《续修四库全书》第1718册,第603页。八股文取法于古文,在有些人眼里正是它可尊的理由之一,如王汝驤云:“(时文)若得左马之笔发孔孟之理,岂不所託尤尊而其传当更远乎?愚故谓有明制义,实直接《史》、《汉》以来文章之正统也。”*梁章钜:《制艺丛话》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718册,第537页。姚鼐主张以古文为时文,但又能清醒认识二者间的界限与先后之顺序。他在《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序目》中指出:“读四书文者,欲知行文体格及因题立义、因义遣辞之法,故无取乎多。若夫行气说理造句设色一皆求之于古人,徒读四书文则终身不能过人也。”*郑福照:《姚惜抱轩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600页。倘若本解古文,“直取以为经艺之体则为功甚易,不过数月内可成”*姚鼐:《与管异之》,《惜抱先生尺牍》卷4,陆国强等编:《丛书集成续编》第130册,第927,927页。。方苞恰恰未能明白这个道理,姚鼐委婉地批评他:“于古文时文界限犹有未清处,大抵从时文家逆追经艺。”④姚鼐:《与管异之》,《惜抱先生尺牍》卷4,陆国强等编:《丛书集成续编》第130册,第927,927页。“以古文为时文”而非“以时文为古文”,如此严格区分彰显着姚鼐的古文本位主义。
三、焦循与阮元的文艺定位
姚鼐强调时文与古文的相通性,焦循与阮元则有意区分时文与古文的差别;姚鼐突出八股文阐释圣贤之意的功能,焦、阮则始终将八股文放入文艺范畴中审视。尽管焦、阮二人在具体阐述上存在差异,但他们目注唯八股文之形式,致力于从“文艺”范畴上对其加以赞誉则是一致的。
(一)楚骚、汉赋、魏晋六朝五言、唐律、宋词、元曲、明人八股,都是一代之所胜*焦循:《易余籥录》,陆国强等编:《丛书集成续编》第91册,第463,479页。。
焦循是对八股文形式美研究最着力、体悟最深的清代学者。他对八股文的评判是建立在对八股文艺术特征理解上的,并将它放在文体史上予以价值定位。
焦循对八股文形体美有浓厚兴趣,将它与弈、词曲并称为造微之学。他对八股文形体之美有如下描述:“其法全视乎题,题有虚实两端,实则以理为法,必能达不易达之理;虚则以神为法,必能著不易传之神。极题之枯寂险阻虚歉不完,而穷思渺虑,如飞车于蚕丛鸟道中,鬼手脱命,争于纤毫,左右驰骋而无有失。至于御宽平而有奥思,处恒庸而生危论,聚之则名理集于腕下,警语出于行间,别置一处不可为典要者。”*焦循:《里堂家训》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第532,532,532页。焦循一反常论,指出时文与古文二者不可以相通,因为“古文以意,时文以形。舍意而论形,则无古文;舍形而讲意,则无时文”*焦循:《时文说二》,《时文说一》,《雕菰集》卷10,《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册,第208,208页。。“时文以形”这一特性是由诠题决定的,“古文不必如题,时文必如题也”。时文之诠题虽源出于唐人之应试诗赋,但二者诠题之法相差甚远,“应试诗赋虽必如题,不过实赋其事而止,无所为虚实偏全之辨也,即无所为连上犯下之病也,亦即无所谓钩勒纵送之法也”⑧焦循:《里堂家训》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第532,532,532页。。焦循认为八股文的这种造微之技非寻常者可为,时文之题出于四书,其分合裁割千变万化,工于此技者亦必千变万化以应之而不失铢寸,倘若不是自幼训练,不可能精通此道。“题有截上截下,以数百字而适完此一二句之神理,古文无是也。题有截,因而有牵连钩贯者,其即离变化,尤未可以苟作。”⑨焦循:《时文说二》,《时文说一》,《雕菰集》卷10,《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册,第208,208页。
在焦循看来,按照文体递变原则,八股文处于文体演变序列底端,它融合了以前文体的各种因素。“是故其考核典礼似于说经,拘于诗说经者不知也;议论得失似于谈史,侈于谈史者不知也;骈俪摭拾似于六朝,专学六朝者不知也;关键起伏似于欧苏古文,橅于欧苏古文者不知也;探赜索隐似于九流诸子,严气正论似于宋元人语录,而矢心庄老役志程朱又复不知也。”⑩焦循:《里堂家训》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第532,532,532页。他认为复合因素的形成是文体发展的必然结果:“诗既变为词曲,遂以传奇小说谱而演之,是为乐府。杂剧又一变而为八股,舍小说而用经书,屏幽怪而谈理道,变曲牌而为排比,此文亦可备众体:史才、诗笔、议论。”焦循:《易余籥录》,陆国强等编:《丛书集成续编》第91册,第463,479页。焦循又以黄淳耀“人而无信”一章题与曹勋“敬鬼神而远之”题等具体作品为例,认为此八股文不逊汉赋唐诗、唐宋古文。焦氏从文体形式褒扬八股文的视角较合理,周作人附议云:“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奥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价。”*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2页。今人著《说八股》亦应和云:“由技巧的讲究方面看,至少我认为,在我们国产的诸文体中,高踞第一位的应该是八股文,其次才是诗的七律之类。”*启功、张中行等:《说八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6页。
焦循受《周易》辩证思想浸染甚深,通变思想贯穿着他的文学史观,他认为,楚骚、汉赋、魏晋六朝五言、唐律、宋词、元曲、明人八股,都是一代之所胜,并心生“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的编纂计划*焦循:《易余籥录》卷15,陆国强等编:《丛书集成续编》第91册,第463页。。在焦循之前,王思任《唐诗纪事序》、李贽《童心说》、尤侗《艮斋杂说》等人都持八股文为有明一代之文学的观点。对于明代而言,八股文是一种新兴的事物,明代尊体者当然可从此着眼。但是八股文沿用至清代已是明日黄花,清人的辩护已失去这种优势,焦循的八股文一代文学之说仅沦为一种学术探讨。
(二)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也*阮元:《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揅经室集·三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479册,第198页。。
阮元从推尊骈文立场出发推崇八股文,是清代骈散意气之争的产物。他将八股文纳入骈文,此番苦心孤诣实是借此扩大骈文阵营,壮大声势以抨击古文。如果说焦循推尊八股文的视角尚有一定的社会共性,阮元的推崇理由则可谓别出心裁。
阮元云:“且时文以八比为式,比者偶也,甚至一比多至一二百字,对比偶之,一字不敢多少,虚实皆须巧对,是时文为偶之最。”又云:“时文曰八股者,宋元经义,四次骈偶而毕,故八也。今股甚长,对股仿比偶之格矣。震川辈矜以古文为时文,耻为骈偶,孰知日坐长骈大偶之中而不悟也。出股数十字或百字,对股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起承转合,不差一毫,试问古人文中有此体否?”*王章涛《阮元评传》,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378—379页。就句式而言,八股文不拘四六,对仗随意,让人很难将它与骈文联系起来。阮元跳出局限于字句的狭隘视角,放眼于段与段之间的形式关系,八股文对偶特征之秘便轩露而出,确为不刊之论。吴承学先生亦云:“从语体来看,八股文综合了中国古代骈散两种语体:八比是骈体,而其他则是散体,由于八股是八股文的主体,所以八股语言的主体是骈体。”*吴承学:《明代八股文》,《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6页。
在古人的文章观念里,一般不会将八股文归入骈文范畴,彭元瑞《宋四六话》、孙梅《四六丛话》、李兆洛《骈体文钞》等都未列入八股文。赵翼、钱大昕、袁枚等人的考证之作也是将八股文放入典章制度里考察。这种观念至今仍有存在,如邓云乡云:“八股文在历史上是一种教育和考试的专用文体,它不是阐述各种学术观点的论文,也不是什么文学艺术作品,不能用班马史汉、古人著述、以及诗、词歌赋、小说戏曲和它相提并论。”*邓云乡:《清代八股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而阮元却独标新义,从语体的形式上着手,倡言“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也”。不仅如此,在广东创办学海堂后,他又组织人员编纂四书文话史料。阮元将习焉不察的问题提出来,对民国期间的骈文观念影响甚大,如刘麟生《中国骈文史》、瞿兑之《骈文概论》都将八股文纳入骈文研究范围,时至今日,这种观点已基本得到学界的认可。
究其实,阮元本人并不喜欢八股文,他曾谕阮福云:“我幼时,即不喜作时文。塾师曰:‘此功令也,欲求科第不得不尔。’俗喻谓之敲门砖,门开则弃之,自获解后即不恒作。”*王章涛《阮元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3年,第767,974页。又据梁章钜《师友集》卷1记载,阮元修书给梁章钜云:“弟生平最怕八股,闻人苦读声谓之为唱文,心甚薄之。”⑨王章涛《阮元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3年,第767,974页。阮元创办诂经精舍、学海堂均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不预举业。阮元不喜八股文,由这一办学宗旨亦可略窥端倪。那么阮元何以言八股文为“文之正统”,并编纂四书文话为之张帜呢?要解决此疑问,当置诸于清代骈散之争的大背景下考察。当时古文家呼号叫嚣,提倡以古文为时文,阮元意在通过此种方式剥离八股文与古文的关系,扩大骈文的涵盖范围。同时,这也宣告那些自诩以古文为时文的古文家终难脱为骈文的命运,这不正是对他们忤视骈文的一种辛辣讽刺吗?八股文身上关涉到骈散两派的文学诉求,姚鼐与阮元虽都推尊八股文,但意图与方法却相差甚远。
焦循与阮元将八股文定位为“文艺”,从文章学角度褒扬八股文,属形式主义论者。八股取士就本意而言,是选拔合乎统治思想并有治国之才者,并借此将德才理念推向整个社会,形成一种社会价值风尚。相对应的是,正统文人若肯定八股文,强调的是它所阐释的道理与士人德、才的同构关系,“文”仅是呈现“道”的工具而已,“道”才是他们津津乐道的首位。八股文作为“艺”之美多数人并无异议,但是很少人因之而高评时文品位,尊八股者一般也不会以此作为主要理据。至于有人将时文高超技法贬为雕虫小技,这与焦、阮的文学观更是霄壤之别。当然,焦、阮所言的八股文是抽象的,即他们所言的制艺在内涵上只可能指向那些理想的、理念上的八股文。
焦循钟爱八股文情溢于表,但存在一个价值定位前提。焦循曾将文章划分为科举应试之文(用之一身)、应酬交际之文(用之当时)、军国之重与民物之生之文(用之天下)、布衣之士独得之文(用之百世)四种,在他的这种划分体系中,八股文作为“用之一身”之文无疑位于末流地位。同理,阮元张扬骈文时顺带推尊八股文,但他对八股文的定位也是以“卑”为前提的:“(四六)文体不得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阮元:《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揅经室集·三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479册,第198页。焦、阮均将八股作为“文艺”来看待,代表着为八股文辩护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致命的缺陷在于在文化品位定性上已暗自降格。
四、尊经守注下的代圣立言与自我情感抒发
代圣立言的属性以及苛刻的清规戒律限制了个体情感的表达,是八股文遭人诟病的主要口实之一。但代圣立言的文体机制有可能在圣人之言与自我之间形成一定的张力,朱注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有识者的精心研理,在学理上与实践上都留有辩护空间。而王芑孙主张八股文“至性至情腾踔而出”的观点则完全突破圣人与自我间的张力,但就当时特定政治环境而言,充其量算是对明末八股文借题发挥盛况的一种憧憬。
“代圣立言”是八股文区别其他文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刘大櫆认为八股文创作“立乎千百载之下,追古圣之心,愉戚同乎圣人,如闻其声,如见其形,是八股文美妙之关键所在”*刘大櫆:《徐笠山时文序》,《海峰文集》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427册,第404页。。也有人从阐道效果褒扬八股文,认为“前人以传注解经,终是离而二之。惟制义代言真与圣贤为一,不得不逼入深细”*管世铭言,引自梁章钜:《制义丛话》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718册,第535页。。但“诗以言志”的诗学本体论表明,文学是个体生命的律动,代言而非自言不可避免是八股文的软肋。如袁枚就曾以“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为优孟衣冠代人作语者”为由,批驳时文与戏曲皆以描摹口吻为工,从而鄙视八股文*袁枚:《答戴敬咸进士论时文》,《小仓山房尺牍》卷3,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5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0页。。
八股文代圣立言机制以尊经守注为建立前提,清政府扶植朱学,规定八股文以朱注为准,违者率不得入彀。那么尊经守注是否真的限制个人思想的表达?“《朱子集注》的体例,原本多样,或详略互见,或兼收异解,或可否并存,或不加断案。读者据题写作,并不见得会受到标准答案的拘限,甚至尚能各自于朱注内外临机决断。”*郑邦镇:《八股文“守经遵注”的考察——举〈钦业四书文〉四题八篇为例》,收入(台湾)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印:《第一届清代学术研讨会—思想与学术—论文集》,1989年,第220—221页。朱注实并未完全限制个人思想的表达,更何况清代八股文并未严格遵守朱注。焦循曾指出五经之义千变万化,阐之不尽,寻之不竭。二千余年来说经之人各竭一人之精力以为得定解,久之又竭一人之精力而前之定解复不定,如此循环无端而神妙不测。破陈说而立己见的情况在“抵掌攘袂,明目张胆,惟以诋宋儒、攻朱子为急务”*方东树:《重序》,《汉学商兑》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第536页。的乾嘉汉学时代尤显突出。清儒以为经典真意被前人解读遮蔽,试图重新寻觅儒学真谛,这种时代学术风气必然会波及时文写作与取士。确然,清人八股文写作并非简单沿用朱注,而是积极咀嚼义理。考官科考录取亦不完全以旧注为准,据陆继辂《合肥学舍札记》载:“嘉庆五年,江南乡试题‘述而不作’一节,予初以老为老聃、彭为彭祖,文成而悔之,遂改从商贤大夫。是科用旧说者皆未中式。又一科‘放勋曰劳之来之’题,亡友臧在东独依赵注,作‘放勋曰劳之来之’,亦被落。”*陆继辂:《合肥学舍札记》卷3“试文不必宗旧说”条,《续修四库全书》第1157册,第314—315页。因此陆氏告诫子弟试文不必宗旧说。梁章钜《制艺丛话》卷11亦载:阮元乾隆丙午年(1786)科乡试于试题“过位”二节用江慎修新解,中式第八。因此《制义丛话·例言》总结道:制科举文以朱子《章句集注》为宗,相沿至今,遂以背朱者为不合式,“其有与《章句集注》两歧,而转与古注相符、与古书有证者,亦未尝不可相辅而行”*梁章钜:《制艺丛话》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718册,第529页。。卢前《八股文小史》与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都指出清代八股文不同于明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义理之求胜”,“识力透到之处,往往足补专注之不及”*卢前:《八股文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2页。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55页。。不同个体对经传理解的精深程度不同,其儒学修养差异自然可反映出来,这就是取士之法通常所言的“窥人心术”。但我们必须明白,精心研理体道而为时文者毕竟不占主流,芸芸众生中更多的是为举业而举业者。在揣摩求合、剽窃蔚然成风的境况下,“窥人心术”恐怕只能在学理上成立,或仅适应个别现象。
八股文“体有式、语有禁、字句有限”,又加上风会所趋与试官好尚各殊,时文与性情脱节是常有的事。但其中确有性情心术之流露有深焉者,如唐仲冕指出:“自前明来,钜人长德多以时文名世,而功名节义卒如其文,迄今读之犹令人沉潜而感发,几忘为制举之业。”*唐仲冕:《屠韫斋时文序》,《陶山文录》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478册,第394页。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规定,本意欲将读书人置于古圣贤生活的时代,引导他们想圣贤之所想,潜移默化达到束修身心的目的。同时,在古代儒学逻辑里,“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沿着这一理路,尊奉程朱理学者认为:八股文品位档次取决于性情体道深浅与养就圣人之志的高低。但是,八股文阐“道”毕竟处于“圣贤之思”的观念场中,施展空间尚狭,要求时人之志与圣人之志合而为一,也只能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追求,均不能真正解决对八股文无性情的责难。王芑孙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八股文应表达个人思想,进而反映时代精神:“制艺,注疏之一体。上者为圣贤立言,下者能自立其言以附儒先之后,抒其所独得,发其所不能已。至性至情腾踔而出,其文传,而其人之是非好恶见其中,其一时之悲愉欣戚见其中,即其世之盛衰升降亦见其中,所谓接统于班马韩欧,而所讬尤尊者此也。”*王芑孙:《书时文读本后》,《渊雅堂全集·惕甫未定稿》卷23,《续修四库全书》第1481册,第244,244页。王氏认为制艺有“上者”与“下者”之别,实际上他更重视“至性至情腾踔而出”、“其一时之悲愉欣戚见其中,即其世之盛衰升降亦见其中”的“下者”。他认为八股文“接统于班马韩欧,而所讬尤尊者”正是缘于这一点。王芑孙认为:“为之者本其孤孑之诚、精刚之气以浩然行乎天壤之间,而声音笑貌寄焉,而不废其为今文也,非其所以为古文也,而犹之其所为古文也。不然,四书之为书也,汉宋诸儒说之详矣,何烦此千万人者执笔复为衍说一通耶?”⑧王芑孙:《书时文读本后》,《渊雅堂全集·惕甫未定稿》卷23,《续修四库全书》第1481册,第244,244页。倘若八股文真能如王氏所言“至性至情腾踔而出”,则八股文代圣立言机制下的圣人之言与自我间的张力完全断裂。
王芑孙的骇俗观点很大程度上缘于他的个性。王氏性素简傲,为文亦不依人篱下。他在给翁方纲信中曾阐明独创精神云:“二十年不惟于并世人中无所依傍,即古人亦不肯专专奉一先生之言以自域其神明,而拘挛其体势。”*王芑孙:《答翁覃溪先生书》,《渊雅堂全集·惕甫未定稿》卷8,《续修四库全书》第1481册,第62页。但王氏此种观点亦并非空穴来风,有其一定的历史依据。明中后期阳明心学盛行,文人写作追求个体意识,八股文也不例外。如山阴狂士徐渭制义自肖其人,他的“今之矜也愤戾”八股文被清人《四勿斋随笔》评价为“直是文长自作小传”。在理论方面,袁中道曾主张“时义虽云小技,要亦有抒自性灵,不由闻见者”*袁中道:《成元岳文序》,《珂雪斋集》卷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82页。。“新学横行”引发明代八股文出现深刻变化,方苞总结此变化云:“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方苞编,王同舟、李澜校注:《钦定四书文校注·原本凡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近人钱基博指出:“明贤借题发挥,往往独抒伟抱,无依阿淟涊之态。”*钱基博:《明代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12页。今人金克木亦认为八股文“不论怎样僵死,还是扼制不住有突出才、学、情性的人。人格仍旧和风格联系。文体还掩不尽文心”*启功、张中行等:《说八股》,第125页。。这些评价主要适应于明代新学横行后的八股文。
晚明清初之际,王学分化,流弊丛生,有识之士倡导程朱理学予以纠偏补正,同时新朝扶植程朱理学,王学因此歇息不张。明代八股文张扬个性的趋势以王学盛行、相对宽松的会讲风气为前提,而在清代高压的政治学术环境下,士人那种嚣张、洒脱之气已不复存。就体制本身而言,八股文大结部分是出口气,不会因入口气的限制而在圣贤之思上腾挪,士子可获得一个自由表达情感的机会。但大结部分因明末人多爱借此藏关节,满清入主中原后,为钳制言论于康熙六十年悬之禁令。虽乾隆期编修杨述曾有复用大结之请,却未被采纳。大结的废弃,使八股文与性情之间的建构成为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如果说袁中道所言“时义虽云小技,要亦有抒自性灵不由闻见者”以现实为基础尚可成立的话,王芑孙的这种主张则没有现实政治环境依托,不可能在实践上广而为之,仅能作为一种历史的回顾。
五、余 论
八股文何以引起褒贬截分两橛的复杂感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清代这一褒贬对立态度产生的原因作一检讨,并对褒扬方的辩护方式、效能作一评估。
王廷佐《莘民遗稿》云:“今日科场,君子小人所同应。君子应之,谓是事君行道之始;小人应之,谓是受爵得禄之始。心术不同,故一则诱以揣摩之术而不得,一则禁其为揣摩之术而亦不得。”*柯愈春:《清人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00页。诚哉斯言!君子与小人以不同心态参与科考、从事八股写作,加上个体资质的不同,必然造就才能高低不一的士子,产生不同品位的八股文,这种结果是造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争论纷纭的潜在基础。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政治功能层还是文体层上,褒贬双方都有意或无意分离理念层与实践层。反对者多着眼于现实流弊,褒扬者则多有意识从理念层面言说。辩护与批判双方不在同一个平台对话,自然难以评判,不可通约。杨文荪揭示争论双方这种“盲人摸象,诸人只言,各照一隅,罕观通衢”的缺点,其云:“重之者曰制义代圣贤立言,因文见道,非诗赋浮华可比,故胜国忠义之士轶乎前代,即其明效大验。轻之者曰时文全属空言,毫无实用,甚至揣摩坊刻,束书不观,竟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者,故列史《艺文志》制义从未著录。是二说也皆未尽然。夫制义之重也,有重之者;其轻也,有轻之者,非制义之有可轻、有可重也。自有制义以来,固未有不根抵经史、通达古今而能卓然成家者。若他书一切不观,惟以研求制义为专务,无惑乎亭林顾氏谓八股盛而六经微也。”*杨文荪:《制艺丛话序》,见梁章钜:《制艺丛话》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718册,第527页。盖万事万物可分二层,不得以流弊否定前者,亦不可执理念而无视现实,以此立论方可破方隅之见。就此,阮元与钱谦益两人必须引起注意:他们分别为八股文的政治取士功能及其文章学评判提供了良好平台,双方只有在这一平台上才能理性探讨问题,规避拘墟短视的意气之争。
阮元云:“唐以诗赋取士,何尝少正人?明以四书文取士,何尝无邪党?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皆归于正;下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亦归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书文囿之,则其聪明不暇旁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诵习惟程朱之说,少壮所揣摩皆道理之文,所以笃谨自守,潜移默化,有补于世道人心者甚多,胜于诗赋远矣。”*阮元:《四书文话序》,《揅经室集·续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479册,第497—498页。阮元将应举对象划分为三等,强调科举教育是一种大众教育,判断八股取士制度是否合理自然要以它在多大程度上网罗、培育了“中等之人”。从这个角度说,八股取士制度有一定合理性,何怀宏云:“八股(文)虽然并不具有总能把最好的人推到最高位置的确定性,但它还是把大量的庸才挡在了门外。”*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12页。阮元提供的评估视角、方法无疑是正确的,对于今天的教育评估也有借鉴意义。钱谦益云:“杜工部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余谓时文亦然,有举子之时文,有才子之时文,有理学之时文。是三者皆有真伪,能于此知别裁者,是亦佛家所谓正法眼藏也。”*钱谦益:《家塾论举业杂说》,《牧斋有学集》卷4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08页。钱氏将八股文分为举子之时文、才子之时文、理学之时文三种类型,并进而细分为真伪二体。清代有关时文雅俗尊卑的风云争论,倘若在钱氏时文划分建构中言说,方能一见分晓。钱氏少事科举之业,聊以掉鞅驰骋,心颇薄之,通籍以还,都不省视。尽管如此,因其有一套合乎逻辑的划分,故能持平对待,兼容并包,采录对立双方的观点。
总的说来,评判八股文可以分政治功能与文体两个维度。清代批判风气兴起主要纠结于作为一种取士工具的八股文,这是对八股文附加功能价值的讨论,而非关涉文体本身。八股取士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确功不可没,但就整个实施时期而言(尤其是后期),其弊端是主要的。八股文作为取士工具立法之始诚然意美法良,只不过作为科举工具先天所带的功利性缺陷以及后来条条框框的束缚,使它在后来的发展中与当初的设想背道而驰。八股文于清末强势声讨中黯然谢幕,是历史给该制度成功与否的盖棺定论。无论最初的动机如何、实施过程如何,功能价值的衡量标准只有一个——实际效果。因此,尽管维护者所言不乏合理成分,但此种制度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状况使得维护方有强辩之嫌,所以在功能之争上,以路德为代表的辩护方处于下风。但对一种文体雅俗尊卑的评判是不能简单以现实创作为依据的,主要当依文体本身性质判定。基于这一认识,剥离八股文与取士制度间的政治功能关系,着眼文体体性肯定八股文是较有效的途径。姚鼐、焦循、阮元、王芑孙等人在文体层面论述时又普遍采取与“末流”划开界限,其褒扬以八股优秀之作为基础,甚至完全是在学理上展开,在辩护方式、理路的选择上是成功的。